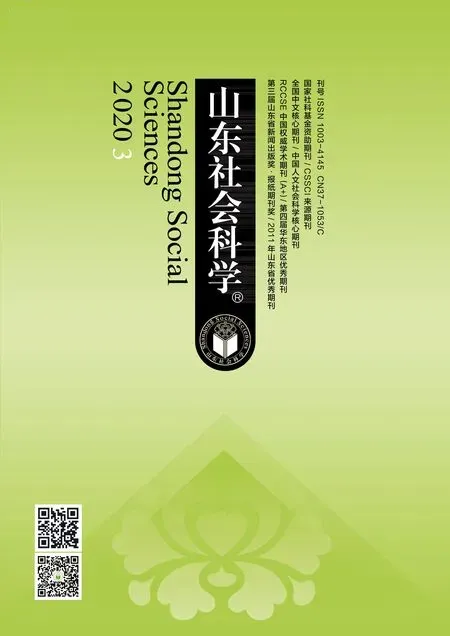论个人破产建构的中国逻辑
——以破产与免债的界分为起点
欧元捷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888)
自201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着力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以“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不仅如此,学界对建立个人破产也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个人破产能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促使债务人重新振奋,有益于社会的安定和谐。(1)汤维建:《关于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想(上)》,《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许德风:《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或许是为了给新设制度的合理性背书,现有研究倾向于为个人破产树立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将其美化成债务人、债权人与社会多方共赢的机制。然而,这种纸面形象无论如何都与社会的一般认知相矛盾——欠债还钱的公理即便存在例外,但为何破坏规则能成为一件好事,破坏规则者反而受到更多关照?实际上,美国破产法价值观的强势输出,才带来了债务人重生、破产免债、破产免责等观念的传播流行,但盲目追逐重生主义的光环,既忽视了个人破产的剥夺、惩戒和消极的本性,也带偏了个人破产的研究重心。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明确破产与免债的本体差异,继而考察重生政策如何影响破产与免债的现实架构,最后回到我国,指出目前不宜热切投入重生主义的怀抱,破产与免债理当区分开、分步来。
一、缘何不同:破产与免债的本体论
从广义上讲,个人破产的整体框架内可容纳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和解、重整等预防破产的机制,旨在拯救濒临破产的债务人,使其不至于沦为破产人;其次是破产本身,旨在宣告债务人破产,从法律上确定其破产人的地位;最后是债务免除(2)债务免除一词,有时也用来表示和解、重整计划之中提供的减免部分债务的优惠,不过本文所论的债务免除,仅指破产框架下使破产人“复活”的剩余债务免除。,旨在给予特定破产人以重生的机会。这其中,预防破产与破产有实质上的排他关系,破产与免债则有逻辑上的先后之分,若是不加区别地在“个人破产”之名义下讨论,则容易引起思路上的矛盾混乱。鉴于我国尚无明确的语义划分,所以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的个人破产是最狭义的,单指清算分配并宣告破产的制度本身,由此才产生比较个人破产与债务免除的论题。
(一)以人格减等为本旨的人格破产
破产古已有之,债务人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等事由,就可能自愿或非自愿地走向破产。破产的基本工作在于将债务人的现有财产分配给全体债权人,但个人破产不同于企业破产的一点,是企业实体在破产后便不复存在,而个人破产后却始终面临着如何对待破产人的问题。就此,个人破产的历史发展中大体有三种处理模式:(1)人身剥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债务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其生命、身体便交由债权人处置。公元前5世纪的《十二铜表法》规定,债权人有权将债务人卖到国外为奴,甚至杀死,而多个债权人可共享出卖的价金,或者分割债务人的尸体。(3)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69页。(2)自由剥夺模式。历史上对债务人自由的剥夺是非常普遍的,债权人可以借助公力救济或直接通过私力救济,将不能偿债的债务人监禁,以此来进行逼债或者处罚。在法国,1538年最早的一部破产法就确定了破产有罪主义,破产者常被处以极高的监禁刑。(4)文秀峰:《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在英国,直至1926年,破产法才基本上取消了债务监禁制度。(5)陈根发:《债务人处罚的历史性考察》,《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3)人格减等模式。扣押、拘禁的流行给债务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逐渐为主流价值观所不容。正是在保障生命权、身体完整权不受侵害的理念下,个人破产抛弃了经济责任引起身体责任的老路,转而从身份地位等人格层面对破产人进行限制。也正是在保障此类基本生存权利的意义上,可以说个人破产开始包含了对债务人利益的考虑。
现代社会,人身剥夺、自由剥夺型的破产已经落幕,个人破产转向了人格减等模式,这具体包括了经济人格、政治人格和伦理人格的减等。详言之,人格减等首先指经济人格不再完整,破产人不仅在清算程序中丧失对现有财产的控制权,之后的财产管理权以及商业行为资格也受到限制。在遵循市场机制,让不具有经济交往能力者退出市场这一方面,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意思相近。制度上虽然允许破产人保留生活必需的财产,但也只为维持一种最低标准的生活,其日常收入、储蓄和消费均受到监管,更不可再进行投资、经营、借贷、担保等商业活动。此外,人格减等通常还包括政治人格、伦理人格的减等。破产人身份的羞辱意味即便不再浓厚,但破产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社会信用评价必然遭到降级,继而对其职业资格、身份权利等诸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如在日本,公法上,破产人不能担任律师、注册会计师、专利代理人等;私法上,破产人不能成为监护人、遗嘱执行人、法人理事等。(6)[日]山本和彦:《日本倒产处理法入门》,金春、史明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二)作为一种调整工具的债务免除
众所周知,债务免除不是个人破产的固有内容,个人在破产后原则上还对未清偿债务负有偿还责任。直到1705年,为了鼓励债务人配合收债,英国才率先规定,待破产人履行了法定义务,便解除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时所欠的债务责任。(7)沈达明、郑淑君:《比较破产法初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现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为破产人获得债务免除开放了制度上的通道,打破“一朝破产、终身破产”的旧律,给予特定破产人以重生的可能。其背后的共识已经不是起初的鼓励债务人配合,而是破产制裁性后果的终身持续性显得过于严苛。
不过,破产是破产,免债是免债,两种机制在对象、效果和基本理念方面都有实质差异。其一,从起点上看,免债通常针对的是“诚实且不幸的人”,其目标群体较破产要小。破产人“诚实且不幸”的预设,实际构成免债正当性的来源,因为这种人设支持了破产人可归责程度小、应享有第二次机会等一系列主张,继而挑战和打破终身偿债。相比之下,债务人的无辜不会被作为申请破产的一般化前提,针对不诚实的债务人,债权人亦有权提出破产,要求即刻清理分配其现有财产,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债权。其二,从落点上看,破产宣告的是失权,而免债是以复活告终。破产带来的是从债务人到破产人的身份转换,但免债机制恰恰是在一定条件或期限满足之后,将破产人这一身份解除,结束破产失权状态。其三,从基本理念上看,破产只管“触底”,不管“反弹”,免债却承载着债务人重生主义的精神。通常而言,在不突破债务人生存底线的前提下,破产对债务人进行了全面的剥夺。债务人在破产前可能得到财务咨询等帮助,破产后也可能从国家社会保障体制中获得救助,但这均不属于破产本体的考虑范围。与之不同,免债既然以“诚实且不幸的人”为目标对象,以复活为目标效果,便要考虑债务人的救济帮扶,理论架构上也着重强调这部分债务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积极意义。
由此可见,免债之于破产,属于一种具有调整意义的次生工具。一方面,破产并不与免债相绑定,现今依然有未设立免债机制的国家,而即便立法上允许,破产也不是必然通向免债。如在美国,法院可能因为债务人不配合、不诚信等事由而否定免债;在日本,免债裁定作出后,也可能由于债务人的诈欺行为而被撤销。另一方面,免债所发挥的调整力,有反向消解破产效果的作用。破产与免债之间显然存在一种张力,免债越快越宽松,债务人则越早脱离破产地位越容易获得重生。
二、如何利用:破产与免债的程序观
个人破产与债务免除虽然是原理完全不同的两套机制,但其程序处理总相伴相随,制度设计者需要站在此岸望彼岸,协调两者的运行关系。现实中,怎样建构破产与免债的程序,如何发挥免债机制的调整力,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欢迎债务人的重生。而这一问题属立法政策范畴,其答案极大程度地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影响,并且也会随着外部需求的变化而调整。破产与免债的程序样态在各国分化明显:以德国为代表的严格派,采用独立的免债程序,克制谨慎地缓和破产的消极效果,立法政策上只能说是允许重生罢了。可供对照的是美国破产法第七章,却有积极促进重生的意图,从程序上把破产和免债两步并作一步走,使破产程序结束时即获免债效果,而不再保留程序外的失权期间。这样,免债的效果被推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它与其说是在缓解破产对债务人的严苛,不如说直接提升了债务人福利,而此种效果恰也契合美国社会的情况。
(一)允许重生:以德国破产法第九章为例
德国破产法上允许债务人重生的时间相对较晚,直到1999年才新增了独立的免债程序,它以破产程序为必要的前置条件,其自身由审查阶段和托管阶段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审查阶段主要是法院审查债务人的申请是否合法,审查是否存在《破产法》第290条允许的债权人异议,继而作出准许或不准许债务人申请的裁定。当然,许可申请只是进入托管阶段的“门票”,不表示债务人立即获得免债。在通常为期6年的托管阶段,债务人对自己的收入和财产依然不具有管理支配权,必须向托管人报告,接受托管人的监督。托管期届满后,法院认为债务人遵守各项法定义务,并且没有出现隐匿转移财产等不当行为,才作出免除剩余债务的裁定。(8)Stephan, in: Munchener Kommentar zur Insolvenzordnung, 3.Auflage 2014, Vor §§ 286 bis 303 Rn.31.
免债程序虽然被规定在《破产法》文本中,却已然是个需额外申请的、有专门目标的独立程序,与破产程序保持着一定的界限与距离。首先,破产与免债的程序目标是分离开的,虽说法条上规定“诚实债务人有机会从剩余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但学理上认为,应当避免将免债理解成破产法的程序终点或程序目的,债务人拥有免债机会不妨碍破产程序的目的仍放在实现债权上。(9)Henckel, in: Jaeger, Insolvenzordnung, § 1 Rn.20.或者,也可以说免债只是独立的免债程序的目标。(10)Henning, in: Karsten Schmidt, Insolvenzordnung, 19.Auflage 2016, § 286 Rn.1.其次,免债程序的审查阶段与破产程序通常并行存在,但交叠只是时空上、技术上的,不妨碍免债与破产在内容上的界限清晰。(11)Ahrens, Entschuldungsverfahren und Restschuldbefreiung, NZI 2007, 194.破产也不必然与免债相捆绑,存在只处理破产、不处理免债的情况,如在免债程序不被许可、因债权人异议而被否决时,又或者债务人没有提出免债申请时,破产程序将径自进行。(12)Stephan, in: Mu?偨nchener Kommentar zur Insolvenzordnung, 3.Auflage 2014, Vor §§ 286 bis 303 Rn.28ff.
整体观之,德国破产法内允许重生,还是立足于人道主义这类基础的价值观,免债也停留在缓和终身破产之严苛的本意上。第一,免债程序可被视为附期限的偿债计划或附条件的复权计划,它要求债务人通过未来的劳动,继续对破产后未偿清的债务履行义务,只不过法律为这一义务的履行划定了期限。6年的托管期间并不算短,但毕竟已经突破了德国《破产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的、破产本意下的无限期清偿责任,也就达到了使债务人“有机会从剩余的义务中解脱出来”的立法目的。第二,免债程序的终点是复活,过程中却保留了破产意义上的惩戒。通常认为,托管阶段体现了破产法的实体精神,它既要求选派托管人、按份额分配财产、债权人平等受偿,还对债务人提出了种种行为活动的限制。(13)Ahrens, in: Gottwald, Insolvenzrechts-Handbuch, 5.Auflage 2015, § 76 Rn.15.所以破产程序虽然随着法院许可免债申请而停下脚步,但在托管阶段债务人还是处在一种“类破产”的地位上。假若债务人违反托管阶段的限制,或是被发现在之前的破产程序中有欺诈、隐匿等行为,那么其在托管期届满后也不能获得免债裁决。第三,免债程序虽然独立,但又有附随从属的地位,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要求破产在先。免债程序不仅将债务人的未来收入在债权人间分配,而且要求在先进行了对既有财产的清算分配。即便是无财产可供分配的场合,破产程序也需要启动,这被认为有助于清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了解债务人整体的义务。(14)Braun, Insolvenzordnung, 7.Auflage 2017, § 289 Rn.2.
(二)促进重生:以美国破产法第七章为例
美国破产法中并没有独立的免债程序,《破产法》第七章程序(也称“清算型破产程序”)将破产与免债同时处理,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清算分配之后若没有债权人异议,债务人将即刻、自动获得债务免除。自动的债务免除,是指免债不需要像德国破产那般专门审查和作出裁定,只要债权人未提出异议,免债是自动实现的。至于即刻的债务免除,则指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结束的同时获得免债,这又不同于英国等国家设置免债等待期的做法。
因为这种即刻、自动的债务免除,美国《破产法》第七章的程序外形已经极大偏离了破产程序的原貌:第一,债务人经过清算分配就获得免债,程序客观上以债务人的复活告终。因此,第七章程序更像是一种免责程序,债务人在程序结束时不仅实现了免债,而且不再承担人格减等的破产责任。很大程度上,这种效果缘于破产与免债在终点上重叠,通常紧接在破产程序之后的失权期间便不复存在了。第二,惩罚债务人的因素被极大弱化,第七章程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给债务人带来的是福利增加。在此,破产的消极后果仅限于剥夺现有财产,再考虑到债务人享有的财产豁免,清算分配的惩罚意味也变得很淡。所以相比于《破产法》第十一章的债务调整,债务人自然更偏好直接破产,在允许债务人自由选择第七章程序和第十一章程序时,多数债务人会选择直接破产。“没有人想落得一个破产的下场,但美国的债务人只是把破产视为通向欣欣向荣彼岸的一个途径,而非‘剧终’。”(15)[美]小戴维·A·斯基尔:《债务的世界:美国破产法史》,赵炳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第三,由于显而易见的利益倾斜,第七章程序长期处于被过度利用的状态,为此,2005年美国《破产法》的改革引入了收入测试,评估表明债务人未来月收入结余低于一定数额的,才准使用第七章程序。如此,改革收紧了申请破产的条件,不过美国国内对此有激烈争议,某种程度上,这一限制性的措施违背了第七章的原意。
不难发现,美国《破产法》第七章的程序设计,已经不限于允许债务人重生这种门槛意义,而是积极地促进债务人重生。这种强化重生主义的政策考量,是长久以来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经济环境变化的产物,建立在复杂又多变的对债权人、债务人、信贷市场及破产法功能的假定预设上。首先,美国破产法的废立、修改大多与经济调节密切相关,甚至在1898年《破产法》之前,破产制度一直作为应对危机、调节经济的临时措施而存在。(16)陈云良、梁杰:《2005年美国破产法修改与世界金融危机:兼论破产法的经济调节功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现今被作为美国破产法价值目标之一的债务人重生,其概念的最初提出可追溯至1934年的判例,彼时的美国社会仍处在经济大萧条的余波中,重生概念的确迎合了稳定经济、救济不幸、重振市场信心的社会需求。(17)Local Loan Co.v.Hunt, 292 U.S.234, 244(1934).Se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Bankruptcy BASICS, November 2011, Revised Third Edition, p.6.其次,强化的重生主义、宽松的债务免除有加强人们商业风险偏好的事前效应,这也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所欢迎的。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快速扩张的家庭债务与强劲增长的消费支出,这成为美国债务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18)宋玉华、叶绮娜:《美国家庭债务与消费同步运动的周期性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5期。“债务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特征在于依靠借债实现先投资后积累、先消费后收入。”(19)陈英:《从“过剩经济”到“债务经济”——当今发达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于是在刺激负债、借贷、投资等商业冒险的考虑下,立法者也有意鼓励破产,利用破产来“逃债”在一定程度上被正当化了,成为国家福利的一部分。反面的例证是纯粹的侵权之债与家庭义务中的债务,因其不大可能源于商业,故立法上不允许免除。(20)Charles G.Hallinan, The “Fresh Start" Policy in Consumer Bankruptcy: A Historical Inventory an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Volume 21, 1986, pp.63-64.
强化的重生主义既来源于外部需求,也要融入外部环境,其存立还须考虑社会整体的接受程度。在美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塑造和巩固了破产法的社会保障角色,债务经济模式固有的高风险也为所谓的“风险分担说”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正因为美国社会见证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普遍经营失败,一种接纳破产免责的社会意识得到强化,即商业社会中的经济风险不一定源于行为人的不诚信或不负责,经济风险并不比自然灾害更可控或更可预测。也因为长久以来所浸润的经济环境,美国社会对于借贷行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导致对于财务失败和破产的态度转变。负债曾经被视为不自律以及财务管理不善,现今则被当作成功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1)Charles G.Hallinan, The “Fresh Start" Policy in Consumer Bankruptcy: A Historical Inventory an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Volume 21, 1986, p.56.
综合比较德国与美国的立法,可看到二者不仅仅有许可免债或当然免责的表面差异,其背后迥异的价值取向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一系列历史选择的叠加。美国破产法的世界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但它恰恰又是实用主义导向下极具美国个性的制度。在其视野内,债务人群体不再是贫弱者,而是能对经济做出可观贡献的人,只是财务上的无望阻碍了他们参与经济活动,故而有必要促使其快速摆脱困境、重新投入生产消费。(22)Joseph Spooner, Seeking Shelter in Personal Insolvency Law: Recession, Eviction, and Bankruptcy's Social Safety Net,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44, No.3, September 2017, pp.382-386; Charles G.Hallinan, The “Fresh Start" Policy in Consumer Bankruptcy: A Historical Inventory an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Volume 21, 1986, p.57.而德国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才接受了重生主义的影响,但现实中缺乏促进债务人重生的外部需要。促进重生虽能给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但于德国的效果却不明显,经济学实验将原因归于两国在经济不确定性、收支模型等方面的差异。(23)Livshits/ MacGee/ Tertilt, Consumer Bankruptcy: A Fresh Star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Working Paper 617, Revised January 2003, pp.3-24.所以归纳起来,破产与免债的具体建构很难说有一个范本或者标杆,债务免除的难易、对待重生的态度可谓是应需而定、应需而变,破产与免债的程序观应当是一种本土观。
三、我国立场:破产和免债的主次说
我国对个人破产的研讨和立法起步较晚,现今不可避免地要同时考虑破产和免债两个议题。这一点不像德国那般,在破产相当完备之后才面对免债的建设。因此,系统化的布局规划尤为关键,可是现有文献中的思路却显得杂糅不清——主流观点极为推崇债务人重生主义,在抽象的价值层面追随了美国破产法的精神;可到程序具体建构时,却否定美式的债务免除,转而倾向于设置像德国那样严格的复权条件。沿着当下的思路,我们无疑会先建构出一个“免责法”(或者说“逃债法”),再来为之制定防止滥用的“补丁”。然而,不管是基于破产与免债的法理,还是考虑我国的社会现实,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关注破产本体的“惩戒法”,在此基础上再为免债的设计。
(一)慎待重生价值
在我国个人破产的讨论中,对债务人重生价值的大力褒扬是有目共睹的。不少研究也将重生价值作为我国应当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的理由,认为个人破产本质上是一种宽容失败的制度,因能够解除债务人的财务危机、帮助个人对抗社会风险而有存在之必要。(24)《中国需要个人破产制度宽容创业失败》,《法制日报》2017年9月18日第6版;刘静:《试论当代个人破产程序的结构性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这些明显带有美国破产法烙印的观念,在我国有无扎根生长的土壤还是值得怀疑的,而破产研究从一开始就直奔债务人重生而去,反倒给破产的自身建设制造了困难。
1.外部环境不兼容
如前所述,促进债务人重生的立场,因特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也依赖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存续。美国《破产法》第七章程序让免债“反客为主”,与其说是因为越来越偏重债务人的利益,不如说是在债权保护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权衡的结果。我国的情况与美国存在很大的不同:首先,不同于美式债务经济的逻辑,强化风险偏好、刺激投资负债对我国经济不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性的意义。长久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未将债务作为驱动力,并且在家庭债务结构上,不同于消费占比高的美国家庭负债结构,中国家庭负债中的房地产方面占比很高,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相对要弱。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决定了重生主义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价值有限。最基本的是,我国个人所面对的经济风险和收支不稳定性,以及我国社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都与美国社会的情形不同。
从我国当下的经济调控来看,顶层设计开始强调结构性去杠杆,政策上要降低而不是鼓励自然人负债。在此必须指出一种观点的片面性,即认为免债机制有助于我国应对过度负债问题,故而为我国所需。实际上,免债机制固然能在危机爆发后应对大批出现的破产者,但其自身对负债也存在事前的激励效应,从而诱发过度负债的问题。而个人盲目追逐负债将与企业融资、银行系统发生连锁反应,于是不单单关涉到借贷的道德风险,还触及到金融风险。所以现阶段宣扬重生价值既无必要,还可能有危险。
2.内部建设受干扰
以促进重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还给理解和建构破产制造了干扰,如“破产无责”“破产不惩戒”“破产积极”等极具误导性的理念流行,对破产自身的目标、内容、门槛及效果的把握就容易出现偏差。
第一,破产目标被遮蔽。现有文献中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个人破产最重要的内容在于免债,或者直接将债务免除作为个人破产的程序目标。(25)解玉娟:《试论我国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在其字里行间,破产好像都不能够自立,还需借助与免债机制的牵连性,使自己也披上重生主义的外衣,方能在现代社会立足。可正如前文所论,破产本不包含免债的含义,破产连带着如何复活的论题,不代表破产本身追求债务人重生。只有站在债务人的视角,才有可能把免债当作破产的目标来看待,而当债务人期待以破产为跳板获得免债,就已经是为破产以外的目的来利用破产了。实际上,个人破产的人格减等本旨原是容易理解的,其与债务免除的区别也十分显著,但直接投入重生主义的怀抱,破产自身的目标就模糊了。
第二,破产内容被错置。与破产目标认识上的误区一脉相承,不少研究者主张现代破产已经从惩戒主义转向了不惩戒主义,立法的指导思想已经从保护债权人转向了保护债务人。(26)汤维建:《关于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想(上)》,《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杨显滨、陈风润:《个人破产制度的中国式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可是刻意不讨论破产的惩罚性内容,将人格减等的内涵边缘化,破产自身便空心了,而目前处于研究视野中心的,却是如何防止破产的滥用。这种局面首先就是反逻辑的,相当于在从无到有的建构中,就有一股解构的力量在。如果我们规划出的破产,预期会使多数人将滥用作为优先选项,那么此一制度规划无论如何也不算成功。
第三,破产门槛被抬高。破产的目标不清与内容错置,也给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带来了混乱,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破产原因的从严把握。这缘于将破产等同于免债,淡化破产的惩罚性之后,人们对债务人明显受益这一必然后果又存有担心。也是从防止滥用的角度出发,有学者建议只在个人因失业、重大疾病等导致经济状况出现重大变故时,才能申请破产(27)孙颖:《论我国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还有学者主张通过规定较窄的债务类型、较高的负债数额、较低的债务人收入,来限制破产的适用(28)赵万一、高达:《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法商研究》2014年第3期。。然而,从破产的原意以及多数国家的立法来看,破产的原因就只是支付不能而已。我国研究者的初衷应当是防止免债的滥用,而不是防止破产的滥用,因此要限制的其实是免债的条件,而非破产的原因。
第四,破产效果被美化。目前的讨论中,个人破产的形象趋于正面,被认为有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促进债务人重生和维护社会利益的积极效果。(29)程春华:《破产救济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许德风:《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这种多方共赢的假想,也造成了政策制定者鼓励适用破产的假象。可相反,破产给社会和债权人都带来伤害:对社会而言,破产不制造或增加财富,反而打破了正常市场规则,为债务人开启例外的同时,社会也要分担破产的司法成本、行政成本、经济成本。对于债权人来说,所谓的破产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保障的只是债权人的全体受偿,这种不充分的清偿最多实现了债权人群体内的公平,远非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公平。假如能够承认和正视破产的消极本色,就知道破产的产生或许不可避免,但本身不值得鼓励,更不应当诱导。
(二)回归人格减等
我国现阶段迫切需要就破产言破产,破产与免债不仅需要区分开,而且必须明确破产的基础性、根本性地位。就此,可从法理逻辑和现实需要两个层面上展开。
1.破产在先的法理逻辑
基于破产与免债的本体论,可知免债处在破产的逻辑延长线上,两种机制本就有先后之分,即先存在破产,才能够谈免债。毕竟,免债是对破产无限清偿责任的矫正,假若债务人不承担破产的消极后果,免债的这种调整属性就无从谈起。若是颠倒破产在先的逻辑,先强调保护债务人,却不论破产责任承担,破产与免债整体给人的印象就是单纯增加债务人的利益,而不是预想中的施以援手。目前正是因为免债喧宾夺主、破产遭受冷落,才加强了“假破产、真逃债”的预期,激发起各界对制度滥用的担忧。
免债以破产为逻辑起点,破产则以人格减等为立足点。缘起于债务人的支付不能,破产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利益失衡:一方面,债务人破产时通常已经山穷水尽,再考虑到必要生存财产的保留,债权人借助清算得到的分配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与企业破产导致企业解散的严厉后果相比,单纯的财产清算对债务人的惩戒意义微弱。(30)龚保华:《浅议权益破产法律责任》,《齐鲁学刊》2008年第3期。鉴于此,现代破产摆脱了身体责任的思路后,也只担保债务人的基本生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用人格减等的方式取代人身剥夺和自由剥夺,已经是破产给予债务人的保护,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体现在承担责任的方式方法上,而非直接否定责任。说到底,法律的建构只能基于理性,却难以要求人们高尚。并且法律包含的理性不该是单向度的要求,即便是风险和损失的分担,也不能单方面地在债权人群体中进行。原则上,债权人的损失需要对价,债务人给他人造成损失则需要担责。所以,破产建构须得以人格减等为基,研究的重点首先是破产人地位究竟如何设置,要从哪些方面限制破产人的经济、政治、伦理人格。此外,考虑到我国民商事法律没有针对自然人破产人的资格限制,故有必要在个人破产的立法中统一规定。
2.强化责任的现实需要
破产回归人格减等的本旨,突出其惩戒的底色,也属于我国的现实需要。我国传统上着重储蓄,现今也很难说借贷及超前消费是普遍的生活方式,民间社会更没有经历过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社会意识里,通常的投资经营失败不会被理解为不可归咎于行为人自身的意外,欠债不还者的社会形象比较负面,债务人更不因为处在经济的洼地而被当然地抬上法律保护的高地。在我国,要认可破产作为按期足额清偿债务的例外,更要着力论证其成为例外的正当性,将例外限定为归因于社会性外部因素(31)如因政策有效性区域差异导致的个人偿债能力降低,参见朱庄瑞、吕萍:《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有效性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105个城市地价监测点调查问卷的分析和建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2期。或者债务人责任较低的情形。在宽容债务人的心理基础本就薄弱的环境下,单纯谈对债务人的人文关怀,于债权人、社会公众也缺乏说服力。从社会接受度的角度考虑,更要旗帜鲜明地强调破产责任的承担,以增加立法的筹码。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国现实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为欠债不还,而不是遭受不幸的债务人深受追债困扰,迫切地需要法律提供免债等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推动个人破产制度建构,有发挥其分流作用的考虑,也即让“执行不能”案件退出执行、转入破产。不过,能分流不代表要鼓励破产,单纯从数据上减少执行程序中的案件只是一种表面工作。在比破产分流更高的位阶上,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政策部署,其本质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债权,而执行难就难在逃债问题在现实中非常突出。故就此意义而言,明确个人破产的惩戒基调更具积极性,让“个人破产的后果很严重,使得一般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敢轻言破产”(32)倪寿明:《积极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29日第2版。,让破产先成为债权人手中的武器,债务人才可心中有戒、行之有界。
总之,在我国的语境下,提出“个人破产不等于恶意逃债”尚嫌不够。破产不仅不等于恶意逃债,也不应该等于逃债,虽说破产后有免债的希望,但是破产并不免责。在考虑债务人如何重生之前,首先应解决好破产人人格减等的内容建构,合乎法理也契合现实的个人破产法才能照应“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法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