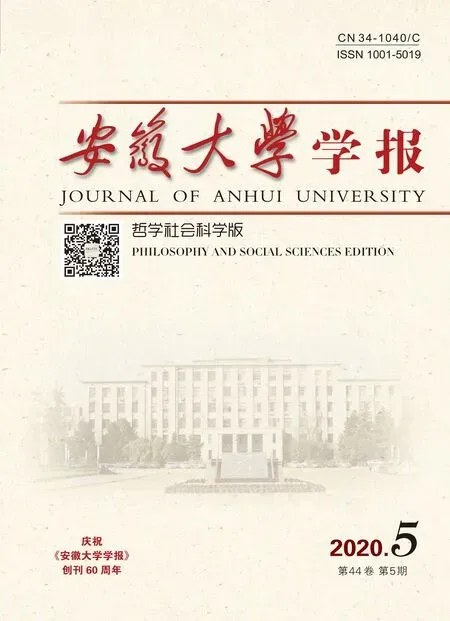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诗性隐喻谱系
李瑞瑞,孙迎光
马克思首次运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将《资本论》视为艺术的整体,其资本批判的辩证叙事方法既有概念性的理性思维,表现为经济学范畴的理论形式;又有隐喻性的诗性思维,表现为诗性隐喻的形式。理性批判与诗性批判不可分割地统一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之中,其中,理性思维是主线,诗性隐喻是辅线,理性思维内含诗性隐喻(如上层建筑概念内含隐喻),诗性隐喻的出场必然伴随有理性批判。虽然如此,隐喻性的诗性思维也仍铺展出相对独立的叙述线索和体系,形成一个对资本批判的诗性隐喻谱系。
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马克思思想中的隐喻维度,但马克思资本批判中诗性隐喻的谱系性问题尚没有得到挖掘。德里达指出:“马克思就一直想在一种本体论中建立他的对幽灵的幻影的批判或驱魔术。”(1)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而这种批判或驱魔术正是在诗性隐喻谱系中获得形象化的呈现的。并且,任何一个资本批判的隐喻都不可能在孤立地考察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把握,它们是在整个《资本论》的诗性隐喻谱系中获得界定和赋义的。忽略了诗性隐喻谱系,就无法对《资本论》的艺术性获得整全的观照。此外,金永兵教授指出:“在整个 20世纪,‘马克思的幽灵’始终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逐渐脱离政治性束缚而趋向于‘回到马克思’。”(2)金永兵、朱兆斌:《“回到马克思”与当代性建设——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对马克思的幽灵隐喻及其谱系的审视,正是“回到马克思”的一个有机节点。
保罗·利科指出:“隐喻就是一种形象化表达。”“用一种观念的符号来表示另一种观念。”隐喻是在感性的东西中指引需要被理解的东西,而后者本身不是感性的。隐喻处于像与不是之间,A(可见的外观)暗示着B(不可见的意义),借助A得以领会B。隐喻实现了感性现象与超感性意义的统一,它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发现相似性。“隐喻可以被视为‘微缩的诗歌’”(3)保罗·利科:《活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1页、109页、127页。,隐喻性思维是诗性思维。
马克思是一个隐喻天才,他对资本批判的叙事充满了想象力。通过创造性的想象,马克思以感性的事物描述抽象的事物,将不可见的事物“置于眼前”,以此产生惊异的理论效果,给资本批判注入感性的力量和活力。马克思称莎士比亚为最伟大的戏剧天才,后者激发前者诗性写作的灵感。《资本论》的核心是资本,《哈姆雷特》中的“幽灵”被马克思转接到资本之中,世界历史成为资本这一幽灵展演的舞台。围绕着“幽灵”,马克思建构了他的诗性隐喻谱系。这个谱系呈现为三个方面或阶段:幽灵出场、幽灵显形、驱逐幽灵。幽灵出场涉及的是资本的现象呈现。《资本论》开篇第一句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下引该书仅随文夹注页码。“表现”(erscheint)涉及外与内、显与隐。上述两个“表现”预示了一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马克思是从特定时代社会财富的“显相”——商品出发,展示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当马克思说“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第75页),显然,这是要从“表现”去探求“本质”。由此,幽灵显形涉及的就是资本的本质呈现。马克思由外到内、由显到隐,借助辩证思维方法让“显相”掩盖下的资本本质得以呈现。进而,驱逐幽灵指的就是消灭资本的统治。从现象到本质的揭示服务于驱逐幽灵这一目的。这三个方面内在地关联,构成总体性的诗性叙事。
马克思的诗性隐喻谱系不是理性批判的简单修饰,不是美学的附加物,其指向的是《资本论》的核心问题,即资本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灭亡趋势。这个谱系有着光彩夺目的神韵和独特的哲学内涵,彰显了马克思诗性思维的智慧。
一、幽灵出场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马克思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第88页)他指认在简单而平凡的商品之中,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这一指认给资本主义社会盖上了幽灵印章,幽灵隐喻带给世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一种全新的感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辩证理性分析与诗性隐喻叙事,将看似平常的商品神秘化,将寻常的货币魔法化,将普通的资本幽灵化,使人们对熟悉的东西产生陌生感、惊异感。由此,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秘与怪诞。
1.幽灵般的对象性——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
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王子复仇的一切活动都从幽灵出场开始。《资本论》的叙事方式与此一样,帷幕拉开,幽灵出现,资本主义“神学的怪诞”景象徐徐展开,并越来越鲜明,最后呈现出触目惊心的场景——《资本论》展示的“机器大工业”和“工作日”地狱般的场景。《资本论》开篇提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给人造成沉重感、压抑感。这句话暗示着人受到抽象的统治,现代世界已经进入幽灵与幻影时代。随着马克思理论分析的不断深入,由商品到货币,由货币到资本,由资本周转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由生息资本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等等,这一世界的魔幻色彩愈显浓厚。
在《哈姆雷特》中,由于甲胄的遮蔽,老哈姆雷特亡灵的出场变成不可见的。这一不可见的东西引发王子的焦虑,他急切地试图辨认出这一亡灵。《资本论》中的幽灵也是不可见的。在“庞大的商品堆积”中隐藏着巨大的谜。马克思指出:“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第51页)“幽灵般的对象性”隐喻着处于隐藏状态的商品价值,所有商品犹如被甲胄遮蔽,使人们无法直观其价值真面目。马克思借助想象将价值幽灵化,使其具有异灵般的生动形象。“如果没有上述隐喻,与‘抽象人类劳动’相应的劳动时间之成为商品价值难以言表,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5)马天俊:《论〈资本论〉商品观的空间时间逻辑》,《现代哲学》2014年第4期。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受资本逻辑支配,“幽灵般的对象性”不是这一社会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生俱来的、隐性的、本质性的社会现实。这一社会现实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关注到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商品构成的社会,“庞大的商品堆积”与“幽灵般的对象性”形成辩证隐喻:在这个感性的世界——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世界,隐含着价值这一超感性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展示了商品的感性与超感性的辩证统一。隐喻引发人们辨认幽灵真面目的欲望,这是《资本论》引人入胜的地方。
幽灵般的对象性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抽象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物化。何以马克思要赋予它幽灵的形象呢?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物质之“物”,它是活劳动变成的死劳动。“幽灵般的对象性”与“死劳动”同样形成辩证意蕴的隐喻:这一“死”者仿佛具有“活”的灵魂,它不可见,在这个社会成为一种邪恶的力量,以隐身的形式控制人、压迫人。
随后,马克思进一步展示了商品的神秘性,将桌子的“舞蹈”搬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舞台:“……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第88页)商品这一对象化劳动,作为一种与工人相异的力量从活劳动中获得自己的灵魂,它的戏剧性的幽灵舞蹈在资本主义的舞台上疯狂展演。只有在《资本论》的透视镜中世人才看到这种魔幻展演。
2.机械怪物——机器大工业制造着人间地狱
幽灵有自己的母体,认识幽灵需要找到其老巢——机器大工业。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商品的机器称为“机械怪物”。这一隐喻与幽灵隐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机械怪物是死劳动,它也是一个控制人、压迫人的“活物”。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大工业,它对资本家是有益的,但对工人却是有害的。机器具有令人惊讶的魔力,“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第438页)。庞大的机械怪物产生庞大的商品堆积。前者的庞大是形体的描述,后者的庞大是数量的描述。这里再一次浮现出幽灵舞蹈——“机械怪物”的庞大肢体运动与器官的疯狂旋转。“机械怪物”是商品“幽灵舞蹈”的诞生地。“机械怪物”的疯狂旋转使大量商品涌入市场,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幽灵的狂欢场。“机械怪物”的疯狂旋转伴随着商品的幽灵狂舞,形成资本主义的魔幻世界。
资本的狂欢制造着人间地狱。马克思不仅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也经常阅读但丁的作品,《资本论》同样受到但丁《神曲》的启发。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第13页)这句话内涵极为丰富,它改编自但丁《神曲·炼狱篇》的第五章。维吉尔带着但丁到了炼狱,维吉尔对但丁说:“人家的窃窃私语与你何干?跟随我,让人家去说长说短!”(6)但丁:《神曲》,王维克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47页。马克思修改了这句话。修改后的话语包含三层意思:第一,维吉尔即“理性”,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马克思在揭示具有正负效应的魔法师的功过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弊端。由而《资本论》不再跟随维吉尔。第二,《资本论》不对舆论的偏见让步。第三,通过《资本论》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引导世人巡览资本主义的地狱空间,让世人感受到《炼狱篇》中的描述并不遥远与陌生,它就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之中。
《资本论》在“机器大工业”和“工作日”中描述的种种剥削和虐待形式,展示了 “机械怪物”的狂舞和商品的幽灵舞蹈制造出类似但丁笔下的人间地狱的场景。马克思指出:“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如果但丁还在,他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第286页)马克思在此处对人间地狱的描述与在序言中改编的格言前后呼应。庞大的机械怪物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运作,压榨工人制造出庞大的商品堆积,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资本积累,制造出地狱一般的场景。
3.拜物教批判
拜物教产生的条件在于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在于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建构起了“魔幻世界”,物与物的关系主宰着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如虚幻的宗教。马克思用原始宗教的信仰形式——拜物教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展开一种拜物教批判。幽灵、机械怪物使工人的生产活动仿佛是某种异己的神灵或魔鬼的活动,而不再是自己的自主活动。在这个异灵空间中,盛行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马克思指出:“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第90页)在拜物教的幻境中,人制造了商品,但作为商品生产主体的人却被作为客体的商品所支配。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获得的就越少;商品的价值越高,他的价值就越低;人越是对商品崇拜,就越是丧失自我。人与商品、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就像在宗教世界中人与神的关系一样,商品、货币与资本成为“物神”。拜物教隐喻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普遍异化状态。
4.具有拜物教性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颠倒的世界”
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产生了拜物教,拜物教产生了颠倒的世界。在《哈姆雷特》中,王子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7)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6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它意指王子赋有扭转乾坤的责任。《资本论》中同样有这样一种视角,它展示了资本主义世界颠倒混乱这一主题,让人看到具有拜物教性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颠倒的世界”(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资本是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它像魔法师一样具有颠倒一切的力量,它使个体受抽象统治,使人屈从于物的力量,造成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颠倒,活劳动(人)和死劳动(物)的颠倒,以及产品和生产者的颠倒。这种颠倒恰恰是资本存在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这一世界“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0页。。这一隐喻为无产阶级扭转乾坤埋下伏笔。
在资本的“兴妖作怪”(马克思语)下,颠倒的世界是由魔法控制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5页。。马克思通过货币的神力描绘了这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展示了“幽灵般的对象性”的代表——货币的神力,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5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炼金术隐喻进一步展示了在颠倒的金本位社会中货币的神力:“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第155页)炼金术具有“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的效力,这一隐喻充分展示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魔法控制的世界。
5.日常生活披着神秘的纱幕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道:“这是一个寒冷的黑夜的乌云,是《哈姆雷特》中为亡魂的显形设置的背景或布景。”(12)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63页。与《哈姆雷特》一样,《资本论》也有一个神秘的纱幕作为布景,只有在这一背景中才有机械怪物的狂舞和商品的幽灵舞蹈。
在思想史上,马克思最早提出“日常生活”概念,并通过隐喻,对其进行了有历史深度的解读。他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第97页)这一日常生活的概念早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神秘的纱幕隐喻向人们表明,日常生活世界并非如胡塞尔所说是清楚明白的世界,而是披着神秘纱幕的、捉摸不透的世界;其也并非如胡塞尔所说是可以直观的世界,而是必须进行抽象的辩证理论分析的世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就有“神秘的纱幕”,就有幽灵舞蹈。人们不能回归这样的日常生活世界,而应该通过革命实践超越这一世界。《资本论》就是以批判和超越日常生活世界为目标。认同甚至理想化日常生活世界就丧失了超越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胡塞尔回归生活世界的思想就是一种物化意识。当前,对学界“回归生活世界热”的理论反思可以借助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元素的“神秘的纱幕”隐喻来进行。
隐喻使文学的意义领域(幽灵传说)走向经济学的意义领域(商品世界),使商品世界中抽象的东西变成具体的东西,无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的东西,非感觉的东西变成可感觉的东西。在幽灵出场中,马克思展示了蕴含着幽灵般的对象性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并披着神秘的纱幕。这种隐喻性叙事由小到大:商品—机械化大生产—拜物教—颠倒的世界—神秘的纱幕,它们形成了一条隐喻链。这条隐喻链一方面不断强化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秘色彩,使资本主义世界变得越来越怪诞;另一方面,它使人的视野越来越开阔,最终进入人类社会的宏大历史背景中——从披着“神秘的纱幕”(资本主义社会)到揭掉“神秘的纱幕”(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隐喻链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神秘与怪诞图景激发读者探明资本主义秘密的欲望,犹如哈姆雷特急切地想探明父亲亡灵的秘密。幽灵出场是资本的现象展示,幽灵显形则是资本的本质展示,从前者到后者构成了由现象描述到本质刻画的辩证隐喻发展过程。
二、幽灵显形
幽灵舞蹈—机械怪物—拜物教—颠倒的世界—神秘的纱幕使资本主义世界变得高深莫测,奇幻迭出。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理性与诗性的层层解析,以辩证智慧的光芒使这一神秘世界彰显于人前。马克思的诗性隐喻使隐藏着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显明可见和可抨击的。马克思通过“显微镜下的解剖”(辩证思维),揭露了吸血鬼——资本的人格化的本质,阐述了G—W—G′资本增殖逻辑的秘密,破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物化理解,说明了资本像“特殊的以太”一般的统治力量。进而,马克思揭开拜物教的面具,洞察到隐藏于商品物与物的形态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与压榨关系,如此便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幽灵、怪物统统显现出原形——幽灵显形。
1.显微镜下的解剖——辩证思维方法
在《资本论》中有一把打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钥匙,这把特殊的钥匙就是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第22页)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第8页)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抽象力——辩证思维方法,并且解析要从“具体而微”的商品探究开始。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商品视为琐事,便与幽灵现象失之交臂。马克思打破传统偏见,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一些琐事的地方,确立《资本论》的研究起点。商品成为所有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胚胎,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一步步抽象出(蕴含着价值的)商品、(代表商品价值的)货币、(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中的具有幽灵特性的社会关系,把握到幽灵的命脉。
“显微镜下的解剖”隐喻与《资本论》观察的起点“商品”相联系。此外,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隐喻为一个“有机体”。他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第10~11页)而 “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解剖学”。于是,在《资本论》中产生了一个隐喻群:“显微镜下的解剖”—“细胞”—“机体”—“解剖学”,通过诗性隐喻和对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有机体结构与发展过程的辩证理性分析,马克思形成了著名的分析历史的“人体解剖法”和“社会有机体”思想。隐喻群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解剖学的病体解剖对象,其从总体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复杂联系。
马克思通过“显微镜下的解剖”,问诊这一畸形的有机体,了解其征象与病史,揭露隐藏的病症,研究这一有机体的发展规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马克思找到了病症,阐明资本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从而呈现“自动的物神”即资本增殖的秘密,并最终预见到,随着资本增殖,这一机体的病毒细胞剧增,最终资本主义将病死于这种增殖。“人体解剖法”为揭开资本的秘密投射了全新的光亮。
2.由蛹成蝶与吸血鬼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有机体,向世人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榨取。为了揭示这种榨取,《资本论》提供了两个具有反差的辩证隐喻。一个是由蛹成蝶的隐喻,这个过程的外在形式是美的;另一个是吸血鬼的隐喻,这个剥削的内隐的过程是丑陋的。马克思表明由蛹成蝶的过程就是吸血鬼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过程。
马克思说:“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第193~194页)资本家幼虫是个病态的有机体,其由蛹成蝶的过程在于:资本家要使货币变为资本,就要到市场上找到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增殖的秘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货币的占有者,即资本家,这在流通领域中。货币转化为资本,还需要通过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工人剩余劳动,这不在流通领域中。由幼虫到蝴蝶隐喻这一资本增殖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称资本是“有灵性的怪物” 或“有形的神明”,并指出它具有“幽灵般的现实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雇佣劳动使死劳动支配活劳动,资本支配工人。这里,死劳动与活劳动形成一对辩证隐喻。马克思指出,“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第227页)。然而,资本主义却将剥削隐藏起来,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是隐而不显的。从表面上看,资本家与工人进行公平交易,由蛹成蝶的华丽变身让人们意识不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然而,资本的嗜血本性却在《资本论》中“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章显现出来,它表现为一幕戏剧:“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第205页)这一幕戏剧就是吸血鬼吮吸工人活劳动的戏剧,其揭示出“从事劳动的工人被自己的产品奴役,掩藏在这种劳动背后的是资本主义非人化的经济制度下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13)罗克全、王洋洋:《共享发展对劳动异化的现实超越》,《江淮论坛》2019年第2期。。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第269页)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第349页)。马克思将资本人格化为吸血鬼,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来塑造它的形象。吸血鬼是夜幕下活动的幽灵,它用锋利的尖牙寻找工人的血液,但它不是公开地杀戮而是隐秘地榨取。马克思通过虚拟的恐怖的隐喻,使隐蔽的剥削事实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资本像吸血鬼一样,贪得无厌,无限增殖是它的生命动力。借此,马克思破解了资本的秘密,他揭示的资本增殖逻辑成为今天人们剖析现代社会的钥匙。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死劳动对活劳动中剩余劳动的吮吸,这是G—W—G′的资本运动的实质。
在《资本论》中,吸血鬼隐喻将抽象的资本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情景,在感性形象(吸血鬼)与思想内涵(资本的本质)之间创造出神奇的关联效应,将资本的贪婪本性淋漓尽致地展露出来。马克思揭开了资本的面纱,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面目,揭示了人间地狱的苦难根源,激发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情感。
3.破除物化——消除魔法妖术
由蛹成蝶与吸血鬼都属于幽灵的魔法妖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了日常生活的“神秘的纱幕”,这一纱幕越是神秘,越是使日常生活变得模糊不清,就越是需要对其进行揭蔽,进而消除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而揭蔽的前提条件就是破除物化理解。
“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物的关系遮蔽人的关系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永恒性的承诺这样的逻辑前提基础上的。”(14)高云涌、王林平:《作为认识论的“〈资本论〉的逻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叶障目,将资本混同为生产资料,看不透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将资本视为自我增殖之物,不承认两大阶级的对立,无法辨识“魔法妖术”。马克思破除了这种神秘,他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第89页)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学家们”所不知道的秘密,指出拜物教产生的真正原因,洞察到商品、货币和资本背后的社会关系。资本表面上看是物,在实质上,它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关系,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一种剥削关系。物化是一层大幕,只有拉开大幕,洞察到社会关系,才能见到幽灵舞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第10页),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阶段,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视为永恒范畴。这种经济学永远看不到神秘的纱幕,也就更不会去揭开纱幕。
马克思不把商品、货币、资本视为不受时间限制的普遍有效范畴,他指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第93页)这里的“其他的生产形式”是指资本主义前后的生产形式,马克思不是要回到“前”,而是要前进到“后”。前进到“后”才会有“驱魔”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资本论》就像德里达所说是一种驱魔术。“后”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与物的颠倒关系。《资本论》既揭示了物化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又揭示了资产阶级物化的社会意识的本质, 如此“‘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从而揭开了笼罩着商品世界的一切 ‘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15)白刚:《“抽象力”:〈资本论〉的“认识论”》,《哲学研究》2020年第3期。。
4.资本作为“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
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它具有控制一切的“法力”。“普照的光” “特殊的以太”作为隐喻,传达出对资本权力的深刻洞察。资本是“普照的光”,它的奇幻的魔法不是照亮了一切事物,使它们清晰可见,而是掩盖了一切事物,使它们改变了色彩。 “特殊的以太”隐喻资本决定并改变着一切存在的性质。这两个隐喻告诉世人资本具有作为“炼金术”的货币“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的神奇效应。“普照的光” 与“特殊的以太”是炼金术隐喻的“升级版”,意指由货币羽化为资本的辩证转化过程。炼金术不过“流通于一炉”, “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却“流通于天下”。“炼金术”与“普照的光” “特殊的以太”在魔法上同根同源,从前者进展到后者,这一魔法已经变得至大无外。
幽灵显形的隐喻性叙事也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辩证分析方法(“显微镜下的解剖”)—揭示剩余劳动的榨取(由蛹成蝶与吸血鬼)—破除物化(消除魔法妖术)—展示资本的统治力量(“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这条隐喻链,一方面不断消除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秘色彩,另一方面使人看清了资本贪得无厌的本性。
三、驱逐幽灵
马克思关于幽灵出场与幽灵显形的所有隐喻性叙述都是为驱逐幽灵、改变世界服务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视为超历史之物,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视为永恒的存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阐述了资本瓦解的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17)《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9页、189页。。它是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助产婆”。“炮弹”“翻不了身的打击”“助产婆”隐喻了《资本论》所要揭示的驱魔力量。
在驱逐幽灵的隐喻中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趋势的展示,“魔法师”“丧钟就要响了”隐喻资本主义社会趋向灭亡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是驱逐幽灵的革命主体的出现,“执刑者”“掘墓人”预示着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的力量。两方面的隐喻表明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从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1.具有正负效应的魔法师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406页。这是主体召唤客体、客体支配主体的辩证隐喻,魔法师用法术召唤出了魔鬼——资本,然而事与愿违,与魔鬼进行“交易”的魔法师却不能控制魔鬼。这一隐喻展示的怪诞图景预示着资本终将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的历史规律。
魔法师的法术暗指资本具有辩证的正负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另一方面,它在创造经济辉煌的同时制造了人间灾难。马克思指出资本造成主要生产力即人的片面化,魔法师的法术将人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它解放了生产力却禁锢了生产者。魔法师闯下大祸,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后果,终将葬身于自己的法术之中。
2.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马克思的诗性隐喻揭示了魔法师的法术具有自噬性,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我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在“死”(劳动)控制“活”(劳动)的怪异的法术中,资本的灵魂显灵,在这一幽灵的无穷无尽的自身增殖中蕴含自身毁灭的辩证发展趋势,法术最终将成为钉在魔法师棺木上的钉子。马克思指出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第874页)。《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的自我增殖、自我否定的揭示上,这一辩证思想的主题在这里通过诗性隐喻形象地表达出来:桎梏、外壳、炸毁、丧钟,它们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其中,“丧钟就要响了”成为马克思的著名预言,这一隐喻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它昭告世人资本主义物化的社会关系必将崩溃,拜物教将终结于生产力的发展,终结于无产阶级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改造。这一振聋发聩的昭告从此以后始终回荡于资本主义社会上空。
3.无产阶级成为执刑者与掘墓人
在《哈姆雷特》中,幽灵引导王子复仇,而资本主义的幽灵将引发无产阶级的复仇活动。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蕴含着抽象劳动和剩余价值,在商品中就包含吸血鬼对剩余劳动的吮吸。因此,商品蕴含着两个阶级矛盾与斗争的因素。“机械怪物”制造出让贫困者更加贫困、富裕者更加富裕的噪声。它唤起了马克思强烈的批判意识,指认吸血鬼化身的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指认将吸血鬼的贪婪丑陋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商品最终引出了类似莎士比亚戏剧中复仇者的形象——执刑者与掘墓人。复仇者的形象是无产阶级能动性的展示,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
《资本论》围绕着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展开,它揭示了资本历史辩证法在于“死劳动”控制“活劳动”,“活劳动”又是消灭“死劳动”的力量。“活劳动”与“死劳动”外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执刑者与掘墓人的隐喻出自这种历史辩证法:资本主义既生产资本又生产无产阶级,而作为“活劳动”的无产阶级是一种否定的力量。无产阶级是资本逻辑自我运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毁灭和向更加高级社会转化的力量。马克思还将无产阶级隐喻为被锁缚的普罗米修斯,无产阶级要砸碎身上的锁链,“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由于无产阶级处于超出但丁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之中,解放的需要和能力使其成为资本批判的“物质武器”。
马克思指认无产阶级是判处资产阶级死刑的执刑者,“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581页。。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3页。商品这一幽灵使商品的生产者变成执刑者与掘墓人,无产阶级就是驱魔者。执刑者与掘墓人隐喻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必然朝向更高的形态迈进。马克思哲学要求实现人民的幸福,“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实现人民的幸福就需要变革由魔法妖术笼罩着的生活世界,人民群众需要用“物质力量”去砸碎锁链。马克思将自己创立的人类解放的理论称为“高卢雄鸡的高鸣”,它引导无产阶级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资本批判的革命意义与隐喻紧密相连,魔法师、丧钟就要响了、执刑者与掘墓人构成了以隐喻开辟的广阔的驱逐幽灵的语义场,这个语义场犹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葬礼上的祭文,它让一幕幕戏剧浮现,使外在显现的东西(形象化比喻)与对未来社会的期望内在统一起来,展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劳动逻辑一定会扬弃资本逻辑,劳动者的主体性一定会取代人格化资本的主体性。
四、结 语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诗性隐喻将内在的意义与外在的形象融为一体,上文分析的幽灵出场、幽灵显形、驱逐幽灵中的隐喻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特点,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形象化的、魔幻的世界。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诗性隐喻形象地揭示了资本或隐或显的面貌。
《资本论》从“庞大的商品堆积”到“阶级”有两条叙事脉络:一条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理性思维叙事,另一条是隐喻性的辩证思维叙事。商品、货币、资本是辩证理性批判的核心概念,对商品、货币、资本中劳动价值的幽灵隐喻成为诗性隐喻谱系的核心范畴。理性的逻辑环节与诗性的隐喻谱系相互渗透,使两条叙事脉络产生互文性。理性思维在揭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复杂性方面可能不免力有不逮,而在理性思维难以企及的地方,诗性隐喻便可予以建构性的“补足”。诗性隐喻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中成为内在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它具有明晰的结构,它将幽灵与众多隐喻内在地联系起来,通过幽灵出场、幽灵显形和驱逐幽灵三个阶段,以隐喻的形式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辩证道理,揭示资本自身运动的展开方式。其中“庞大的商品堆积”与“幽灵般的对象性”、“幽灵般的对象性”与“死劳动”、“死劳动”与“活劳动”、“丧钟就要响了”与“执刑者”“掘墓人”等构成了辩证隐喻的对子,形象展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揭掉神秘的纱幕” “消除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等形成隐喻的纵向历史分析的维度,“人体解剖法”和“社会有机体”等等形成隐喻的横向社会分析的维度,这些展示出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辩证思维。从幽灵出场到幽灵显形体现了对资本由现象到本质的辩证叙事方法,驱逐幽灵揭示的是资本的历史辩证法,它们形成了对资本辩证运动的诗性的总体把握。观念性的诗性隐喻谱系的辩证叙事体现了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它是用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