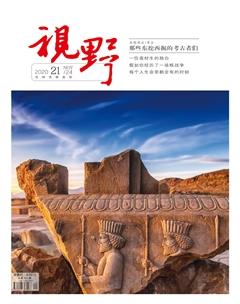学考古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王笑寒

神秘的考古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学科?学习考古又是一种什么体验呢?今天,让一位考古学专业的朋友為大家讲一讲自己的亲身体验。
2013年7月起至今,学习考古学已有整整7年时间。在我的印象里,这7年内的时光中,除了去年浙江杭州良渚古城成功“申遗”引发了关注之外,考古学能“出圈”的事情并不多:这浑身泥土的学问,大多数时候只在图书馆和大学的角落里安闲自得。
既然有人对考古学这个谜一样的专业充满好奇,我就不妨来谈谈自己学习考古学的经历。
人们对考古学的印象往往两极分化:要么认为考古学是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的冷门专业,早晚得“饿死”;要么觉得学考古学的可以帮人鉴宝,早日实现“财务自由”。在网络上的这类噪音中,考古学俨然成了“薛定谔的考古”——测不准。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老百姓,外国人对考古学也同样有“测不准”的疑惑。
在学习了一些考古学知识后,我的看法可能要保守一些:任何对考古学的直接判断,都是相当值得警惕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故弄玄虚——我相信大多数对考古学了解较多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觉——考古学的内容实在太过庞杂,任何一个人企图回答“考古学是什么”的问题时,都会发现自己是盲人摸象。实际上,就连读到博士、走入高校的职业考古研究者,也未必能把这头大象摸全乎了。
虽然考古学包罗万象,但总体来说,学习考古学,主要包括“体”和“脑”两方面:“体”是指田野考古,业内人称“下工地”,也就是进行室外发掘;“脑”则指日常学习,主要是上课(接收信息)和读书(获取知识)。背景介绍大致如此,接下来我就分别从“体”“脑”两方面来说说,学习考古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
劳其筋骨,乐其心志:考古发掘体验
每个考古学生都会在大三或大四经历田野发掘实习,然而,与《盗墓笔记》《鬼吹灯》不同,真正的田野发掘地点大多不是充满金银财宝的墓葬或遗址。当然,随着城市建设的增加,在城市里进行的考古发掘也很多,但在城市发掘,远没有去乡下发掘来得浪漫:这大概是因为,乡下虽然缺少城市便利的生活设施,但往往能给城市中长大的学生以惊喜。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星光闪闪的银河、一望无际的原野……凡此种种,使得每个考古学生的田野发掘的“第一次”,很有可能以一声睁大双眼的“哇”来开头。
在发现田野的浪漫之后,接踵而来的却并非诗与远方,而是“劳其筋骨”的体力活儿,这让很多人都吃不太消。这种诗与远方的退却和劳其筋骨的进击,从考古学生的“田野标配装”便能看出: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靴、遮阳帽,外加一把铁锹……
说起考古从业者的“破烂行头”,圈内很多人都自嘲是“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一问才知道是考古队的”。虽然装备本身不太好看,但在荆棘遍布的野外干起体力活来,却相当好使。在发掘现场,考古学生干得最多的就是用铁锹出土和用推车运土,这也难怪著名作家张承志(他本科也是考古专业)要将考古学说成是“浑身泥土”的学问了。
与用推车运土相比,把铁锹插在干涸的泥土里出土非常不轻松,好在国内的考古单位大多会请当地的农民来当临时工,帮学生干出土的活儿:不过,国外的考古学生就没这么幸运了——国外高人力成本与窘迫的考古预算使得“外国民工”成了地地道道的奢侈品,考古学生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笔者有幸在若干年前参与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次考古发掘,没想到罗马人喜欢用陶片混合泥土来建造地板,为了进一步发掘,我不得不自己手持手镐,一点一点地把那些坚硬如水泥的“马赛克地板”敲掉,第二天虎口肿了一圈,也算是“此手无憾”了。
除了用铁锹粗线条地挖出不重要的土层之外,精细的体力活儿当然也要做。实际上,拿着毛笔一般的细刷刷去文物上的泥土是考古从业者真会做的事,这是少数电视剧和纪录片正确呈现考古发掘的地方,虽然这些镜头几乎全部都是发掘完后,考古人员和拍摄人员“装模作样”地补拍的。
不过,最令考古学生崩溃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拿着毛刷刷出土文物,而是被业内称为“刮面”的活动:其操作方式一般是学生半跪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手持手铲或鹤嘴锄,慢慢地清理地面上的浮土,直到刚挖开的地面上光洁如新,能够看出地面上呈现出不同颜色的地块为止。
与电视剧中使用探测器不同,从考古学上说,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刮面活动才是能否真正确定地下埋有遗迹的关键,这是因为,古代人类活动都依托于地面,不同性质的活动会导致地面被不同程度地使用,最终反映到土地上就是土质、土色的细微差别。正因对土质、土色的细微判断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通过刮面来判断遗迹现象是考古学家一生都不断修习的课程,也是每一个中国考古学生必须得到足够训练、衡量菜鸟考古学生田野考古水平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上述体力活动都属于“劳其筋骨”的话,那么田野考古发现则是彻彻底底的“乐其心志”:在考古发现之前,有经验的发掘者实际上都大有可能想到了“会挖到什么”(所谓“想得到才挖得到”),但却总是心怀忐忑。然而,当自己的理论预设得到了真实考古发现的验证以后,那种一半从未知中发现新知,一半从已知中得到验证的喜悦,就仿佛是心情阴郁的人突然遇上了好天气,使得任何语言描述都相形见绌。
不过,对考古学生而言,考古发现却并不只是喜悦,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是考古与盗墓最大的不同之处。对考古从业者来说,在考古发现过后,不仅要详细地记录、准确地绘图,还要评估它在整个发掘空间中的位置,和其他考古发现的关系——对这些细微问题的“要素察觉”,小到会影响研究者对遗址或遗物功能的判断,大到会成为衡量不同考古学家水平高下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真正的考古学中,考古发现远不是考古工作的结束,反而是考古工作的开始:在把考古发现记录、绘图完毕后,还要在实验室对其进行大量科技分析研究,以最大程度地挖掘考古发现的信息——哪怕它只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器,也值得研究者花费上百、上千个小时去仔细分析。
用一句话来总结考古学生的发掘体验的话,我愿说是“劳其筋骨,乐其心志”:的确,田野发掘中有不少体力活,经常让人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每当考古发掘结束时,大家都会对考古工地依依不舍。热情淳朴的本地人、朝夕相处的同学、激动人心的发现、群星璀璨的夜晚、油菜花开的盛夏,无一不讓人深深留恋。
在猜测与想象之间摇摆,在理论与未知面前探索,田野考古就是这样的九曲八折,也是如此的充满魅力。
误解无碍,理解万岁:考古印象漫谈
关于对考古的想象,更多来自《鬼吹灯》和《盗墓笔记》。在这两部小说中,考古学家往往被刻画成是“工作洛阳铲,上班黑驴蹄,下班古玩城”的群体。这些似是而非的描述真的准确吗?
这些描述中,“工作洛阳铲”可能是最贴近现实的:考古学家的确会非常频繁地使用洛阳铲,但洛阳铲是拿来勘探的(找到什么地方有遗址),而不是用来发掘的(揭露已经知道了的遗址)。实际上,考古学家最常用的工具是手铲,前面提到的刮面就要用到它。
在考古学界,手铲也有象征意义:昔日美国考古学界百家争鸣的时候,有位著名考古学家写了篇讽刺文章,里面的几代考古学家为了所谓的“金手铲”(Golden Marshalltown)而争得不可开交。不仅如此,手铲的抓握方式也大有讲究,受过训练的人能够通过别人抓握手铲的方式,一眼识别出来此君有没有受过田野考古的洗礼。
与“工作洛阳铲”相比,人们对考古“上班黑驴蹄”的印象,就有些离谱了。不过,由于这个印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某考古界才子也要自嘲“上班如上坟”。实际上,考古学家要处理的遗迹远不止墓葬,城市、道路、房子、水井、垃圾坑(考古学家处理最多的遗迹)乃至茅厕,都是考古学家关心的东西。
古代茅厕里可能残留人的粪便,粪便中会留存有一些寄生虫卵,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寄生虫卵找到灌溉的证据(血吸虫)、了解古代人的食谱(不同食物上所带的寄生虫不同)、重建古代的卫生环境(蛔虫和鞭虫),乃至分析古代人群的迁徙路线(寄生虫传播)。当然,就算真的挖到了墓葬,考古人员也绝不会拿着“黑驴蹄子”下去,因为墓葬里的尸骸也不会变成“粽子”。
其实,在“工作洛阳铲,上班黑驴蹄,下班古玩城”中,最离谱的并不是“上班黑驴蹄”,而是“下班古玩城”。这简直是荒谬极了。这是因为,中国考古学在创立的时候就立下了不搞收藏的行规,所以,真实的情况是“搞收藏的不懂考古,懂考古的不搞收藏”。当然,考古的行规也好理解: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作为文物的第一经手人,考古学家当然要严格遵守行规,否则怎么能保证“把文物上交给国家”呢?夏鼐,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搞考古不搞收藏”的行规就是他立下的。
其实,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考古发掘的规矩一般是逢下雨会休息。在连逢阴雨或晚上休息时,新生代的考古学生往往是玩会智能手机,年龄长一点的考古人则是喝酒。喝了酒的考古人格外可爱,喜欢拿圈内趣事开玩笑,甚至有大侠编了一本《考古武林谱》,把各大高校的考古系都归了门派,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是“六扇门”,北京大学是“少林派”,西北大学是“华山派”,吉林大学是“长白山派”。笔者曾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被此君调侃为“从长白山派岭南分舵跑去了长白山派燕山分舵”(中山大学和吉林大学里任教的老师有许多吉林大学培养的博士),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当然,考古不仅实在有趣,对社会的贡献也十分巨大。它甚至可以解决“我们是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谁”,不仅取决于我们“现在是谁”或“未来是谁”,更取决于我们“曾经是谁”。实际上,我们的“中国”这个名字也来源于一件名叫“何尊”的西周青铜器,因为这件青铜器上刻有“宅兹中国”的铭文——这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
正是因为考古如此重要,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考古、体验考古、思考考古。对于喜欢考古的人来说,考古就像侦探,需要从历史的迷雾中拨云见日。举例来说,有很多学者质疑夏朝的存在,因为他们发现春秋的人只知道大禹,战国人却知道五帝,汉代人则知道了伏羲、神农,魏晋的人干脆知道了盘古开天辟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时间越往后,距离历史越远的后人反而了解的历史更靠前,这是很不合逻辑的。于是,便有了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古史辨学派的人怀疑夏朝是后世杜撰出来的内容。当时也有人认为,古史辨派的说法只是理论假说,应该从实际出发,寻找夏朝的遗址。这些人中有位叫徐旭生的老先生,他遍查古籍,根据“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认为夏人的活动范围大体在豫西一带,便亲自去河南郑州、洛阳等地调查,最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个遗址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普遍被考古学家认为最有可能是夏朝的都城。
这一出“寻夏记”的侦探故事,自古史辨派以来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日后也还将继续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