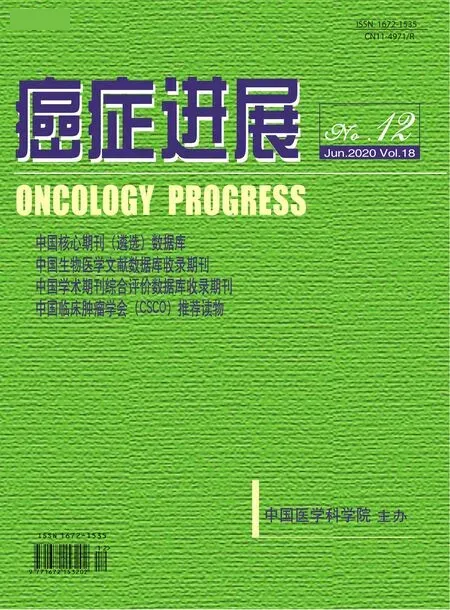全肺切除手术治疗局部晚期肺癌的研究进展△
余向洋,牟巨伟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北京 100021
1933年4月5日,美国华盛顿大学附属巴恩斯医院外科学主任Graham教授,借助当时临床广泛采用的肺门止血带阻断法,成功为48岁的妇科医生Gilmore进行了世界首例左侧全肺切除手术,揭开了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的历史序幕[1]。但随着肺叶切除手术(1949年)和袖状肺叶切除手术(1952年)的开展,以及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CT)肺癌筛查的推广,全肺切除手术在临床中的应用比例日趋减少[2-5]。同时,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均较高,也是限制其临床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2,5-6]。此外,研究显示,全肺切除手术并不能够改善早期(Ⅰ~Ⅱ期)肺癌患者的远期生存[6-8],因此,该术式目前主要运用于部分局部晚期(Ⅲ期)肺癌患者的多学科综合治疗,以期能够实现长期生存甚至临床治愈。2020年,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最新发布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诊疗指南以2A类证据推荐:在保证切缘阴性的情况下,可选择为局部晚期NSCLC患者实施全肺切除手术;同样,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发布的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2018版)中,也以2A类证据推荐:可选择全肺切除手术治疗Ⅱ~ⅢA期NSCLC。
由此可见,全肺切除手术能为局部晚期肺癌患者带来可观的长期生存,但较高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又令很多外科医师难以抉择。本文将对可耐受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选择、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死亡预防、综合治疗策略制订和胸腔镜下全肺切除手术实践现状进行综述,旨在帮助外科医师在为肺癌患者制订全肺切除手术方案时,已胸有成竹。
1 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选择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近2/3的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超过65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的年龄分段标准,该类患者属于老年患者[9]。日常的临床诊治中,部分老年患者会因为局部晚期肺癌需要接受含全肺切除术在内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因此,年龄亦首当其冲地成为手术患者选择和手术预期的重要参考因素。1997年,日本学者Mizushima等[10]对单中心全肺切除病例进行汇总分析,发现年龄≥70岁患者的围手术期病死率高于对照组(<70岁)近8倍;2002年,van Meerbeeck等[11]对比利时癌症注册数据库中的657例接受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进行系统性评估,结果显示,总体的围手术期病死率为6.8%,但年龄≥70岁患者的围手术期病死率却高达17.8%。2010年以来的相关研究结果却显示:随着加速康复外科和多学科综合管理的广泛开展,高龄并未增加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风险。法国Blanc等[5]对既往10年单中心的全肺切除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高龄没有增加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但在发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患者中,高龄是其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Weder等[12]对33~74岁的欧洲多中心的全肺切除病例进行的回顾性分析,亦未发现年龄对围手术期并发生症和死亡产生影响。
此外,约50%的年龄≥60岁的肺癌患者可能合并基础疾病,而合并基础疾病已被证实对肺癌患者的生存有不利影响[13]。Blanc等[5]对单中心543例全肺切除患者的围手术期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合并基础疾病是术后发生呼吸系统并发症(主要为肺部感染)、出血和失血性休克的高危因素,而上述并发症又是导致ARDS的主要诱因。Charlson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于1987年由Charlson等学者提出,是目前临床上较为常用的对全身多脏器合并症进行积分评价的量化系统[13-14]。Blanc等[5]的研究中亦纳入了该指数,结果显示,全肺切除手术后发生ARDS患者的CCI为6分(范围5~7分),高于未发生ARDS患者的5分(范围4~6分)。因此,术前进行CCI评估是必要的,能够有效筛选可耐受手术的患者(CCI≤5分)。此外,临床上现行的合并症评估量表还包括简化合并症评分系统(simplified comorbidity score system,SCSS)和改良的Glasgow预后评分。由此可见,在充分评估心肺功能的基础上,基础疾病控制良好、术中妥善处理残端和创面的老年患者,全肺切除手术并非绝对临床禁忌。
全肺切除手术后,因一侧肺动脉主干缝闭,所有经体循环回流的血液需由健侧肺动脉主干流出,导致流出道相对狭窄,肺动脉压、右心内压均随之升高,心肌收缩力亦相应增强,患者术后可因肺动脉血流瘀滞,心肌供氧不足和电生理受干扰等诱因发生心血管并发症。此外,随着健侧肺动脉血液流量增多、流速增快,短时间内健侧肺毛细血管渗出增加、通气/血流减低,导致机体缺氧而发生肺部并发症。无论心血管并发症还是肺部并发症,均对全肺切除手术后患者的短期和长期生存结果产生不利影响[6,15-16]。因此,基于术前充分地心肺功能评估,选择可耐受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最终达到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目的,是合理开展该术式的必要前提。根据欧洲肿瘤内科学会NSCLC诊疗指南推荐,对于拟行肺切除手术的患者,除常规采集心血管病史、体格检查、基线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外,还需要借助改良的心脏风险指数(revised cardiac risk index,RCRI)量表进行术后心脏风险评估,如评分超过2分(即风险等级C级),其主要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率高达10%[17],需要至心血管内科进行进一步检查或治疗[18]。初诊或经心血管内科治疗后RCRI评估为低分险(即风险等级A或B级)的患者,还需接受常规的肺功能评估[18]:对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和一氧化碳弥散量(carbon monoxide diffusing capacity,DLCO)均超过预计值80%的患者,可接受任何肺叶(包括全肺)切除手术;若其中任何一个指标低于预计值的80%,则需进一步评估运动肺功能,对于运动肺功能中最大耗氧量超过预计值75%,或超过20 ml/(kg·min)的患者,亦可耐受任何肺叶(包括全肺)切除手术;如患者均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推荐进行肺灌注显像扫描,以预测全肺切除手术后患者的肺功能(可耐受全肺切除患者需预计术后FEV1和DLCO均超过50%),且肺灌注显像预测的术后肺功能(FEV1%<55%)能够有效判断术后严重肺部并发症ARDS的发生,术前的FEV1%却不具有这样的作用[5,19]。此外,临床实践中,绝大多数拟行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多合并肿物阻塞气道或存在患侧肺气肿、肺大疱等,可导致FEV1或DLCO不能满足上述条件,但切除肺功能不佳的肺组织,可改善患者的术后肺功能,因此,该类患者并非手术绝对禁忌[18]。推荐对于所有可能行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术前完善肺灌注显像联合肺功能测定以预测全肺切除术后的肺功能,从而使更多的局部晚期肺癌患者获得临床治愈[5,12,18,20-22]。
2 围手术期并发症
全肺切除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较为常见,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其发生率高达3.4%~54.0%,主要为心血管并发症和肺部并发症[6];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又是导致围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15,20]。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和治疗并发症,是降低全肺切除手术患者术后病死率,实现长期生存的关键[2]。
Thomas等[16]对法国国家普胸外科数据库中4498例接受全肺切除患者的围手术期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全肺切除术后患者的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率高达14.1%(634/4498),其中心律失常是最常见的心血管并发症,约占75.2%(477/634);倾向性匹配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男性、体力状况评分≥2分、主动戒烟史、扩大切除、不完全切除等与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明显相关。此外,另一项法国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更晚的pTNM分期(ⅢA~Ⅳ期)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明显相关[6];因此,对于术前评估拟行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应该采用经超声支气管、超声食管镜或经颈纵隔镜的纵隔淋巴结活检、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等检查,以更加准确的判断分期,不仅能够预测患者的术后生存情况,还能够提示围手术期风险[6]。d'Amato等[23]的研究结果还发现,左侧全肺切除手术患者术后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右侧。针对肺切除术后循环系统变化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显示,与诱导麻醉开始时相比,全肺切除手术24 h后,患者的中心静脉压、肺动脉压楔压、肺动脉压和外周血管阻力指数均保持增高趋势,但右心室射血分数却呈相反的减低趋势;此外还发现,与基线水平相比,手术结束时、术后2 h和24 h,患者外周循环血中的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血管内皮素、血管加压素、前列腺素和心房钠尿肽均有明显的增高现象[24]。Reed等[25]针对肺叶切除手术患者的右心室收缩功能改变展开研究,结果发现,肺叶(包括全肺)切除术后早期(1~24 h)右心室射血分数没有明显下降,但术后48 h起明显下降,可引起肺切除术后患者的循环障碍。由此可见,全肺切除手术因创伤过大、胸腔渗出液体量过多、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大、左心室射血分数减低和血管活性物质增加等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导致心肌供氧不足、心脏电生理干扰和血液循环障碍,最终导致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24-25]。因此,对于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术后(尤其0~48 h)应加强外周循环血压、中心静脉压和心电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制订或调整液体输入和食入量,必要时,在保证循环稳定的前提下,积极应用药物治疗心律失常。
支气管胸膜瘘(bronchopleural fistula,BPF)和ARDS是全肺切除手术后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也是造成围手术期死亡的最主要原因。BPF多发生于全肺切除术后7~14天,发生率约为1.7%~13.0%,其引起的围手术期死亡率却高达20.0%~100%[6,16,21,23,26-27]。d'Amato等[23]对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过去15年收治的330例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发现,BPF却是围手术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术前新辅助化疗并不会增加BPF的发生率[23]。据Thomas等[16]对法国国家普胸外科数据库中4498例接受全肺切除病例的围手术期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不会增加BPF的发生率,但存在主动吸烟史、饮酒史,右侧全肺切除,以及过长的手术时间是BPF发生的危险因素。此外,美国布朗大学Daly等[21]对30例接受高剂量新辅助放疗(59.4 Gy)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同样发现,高剂量新辅助放化疗未增加BPF的发生率,且该综合治疗策略能够为局部晚期肺癌患者带来可观的长期生存(5年生存率为38%)。既往的研究已证实,可采用不可吸收丝线连续缝合或患者自身组织(如肋间肌、前锯肌和膈肌瓣,胸腺,心包和纵隔脂肪等)加固残端的方法,有效降低BPF的发生率[6,20-21,23,28]。
既往的回顾性研究认为,ARDS的发生主要与一侧全肺切除后健侧肺循环血量增多导致的肺水肿密切相关;其在全肺切除手术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0.9%~46.0%,但引起的围手术期病死率却高达 33.3%~59.8%[5,12,16]。Blanc等[5]对 543 例全肺切除后围手术期ARDS的发生、管理和预后进行了系统陈述:首先,多因素分析仅发现右侧全肺切除和高CCI是ARD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可能归因于右肺在灌注和通气方面通常占优势,在右侧全肺切除术后,肺动脉压的升高梯度大于左侧全肺切除术后[5]。部分早期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与常规肺功能检查结果(FEV1和DLCO)相比,术前、术中和术后借助经胸超声对肺动脉压力进行测量[较基线水平升高4 mmHg(1 mmHg=0.133 kPa)以上]能较更好的预测全肺切除术后ARDS的发生情况[29-30]。其次,重度ARDS、高龄(中位67.5岁)、右侧全肺切除是围手术期发生ARDS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5]。但上述研究显示,新辅助放化疗并未增加围手术期ARDS的发生率,也未增加ARDS患者的死亡率,这与法国基于单中心298例全肺切除病例的回顾性研究结果一致[5,27]。但对已经发表文章进行横向比较发现,新辅助治疗后行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的ARDS发生率较高(3.4%~46.0%vs1.8%~21.6%)[5-6,8,12,16,21-22,31-37]。
由此可见,术前的充分评估和健康宣讲、术中创面和残端的妥善处理、术后严密的循环监护,可有效降低全肺切除术后致死性并发症(BPF和ARDS)的发生,最终实现局部晚期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
3 围手术期死亡
美国外科学院国家外科质量改进计划数据库的分析结果,定义手术后30天内发生的任何原因死亡为围手术期死亡[38];但部分研究者认为,胸部肿瘤手术(尤其是食管癌手术和全肺切除手术)相关的致死性风险并未在术后30天结束,建议将这一观察期延长至胸部肿瘤手术后90天较为合适[20,27,39]。多项研究显示,全肺切除手术后30天患者的病死率约为0~26.0%,而31~90天病死率约为3.0%~21.0%[5-6,8,12,16,21-22,31-37],因此,推荐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死亡统计应该以手术后90天为时间节点。
基于法国多中心全肺切除患者的多因素分析发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手工残端缝合和较晚分期(>ⅢA期)是术后90天死亡的危险因素[6]。此外,Doddoli等[15]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龄(≥60岁)、男性、右侧全肺切除、发生术后心血管和肺部并发症与较高的90天死亡率有关。同样,法国学者研究也显示,右侧全肺切除与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死亡的发生密切相关[5]。基于文献证据推测,右侧全肺切除后较高的围手术期病死率可能出于以下原因:右肺在通气和灌注方面通常占优势,可能导致右侧全肺切除术后的肺动脉压升高梯度高于左侧全肺切除术后[5,40];右侧全肺切除术后,肺组织对腔静脉的压迫解除,回心血量增加,引起右心容量和压力负荷均过重[25];上述现象均加重了心肌收缩、缺血和损伤,以及肺毛细血管的渗出,诱发心血管和肺部并发症的发生[5,25,40];此外,窦房结位于右心房与上腔静脉交界处终沟的心外膜下,易受右侧胸腔内压力和上腔静脉扩张的影响,从而诱发心律失常等相关并发症[29]。
Swartz等[33]研究显示,全肺切除手术后12 h内的液体输入量<1000 ml组患者的30天病死率仅为2.6%;而当输入量>1000 ml时,30天病死率增加了近7倍(17.3%)。美国国家住院患者数据库的分析首次证实,与在低体量胸外科中心接受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相比,在超高体量胸外科中心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的30天病死率减低了约5.0%[41]。但目前,临床对新辅助治疗是否增加了围手术期死亡尚存在争议。d'Amato等[23]对单中心315例全肺切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增加了90天病死率;但Weder等[12]基于两家胸外科中心的176例全肺切除患者的病历资料,结果却显示,新辅助治疗并未增加90天病死率,且新辅助放化疗组患者的90天病死率低于新辅助化疗组患者。此外,基于法国国家普胸外科数据库的分析也呈现出令人意外的结果:新辅助治疗是全肺切除术后90天死亡的保护因素[16]。在讨论中,上述研究者们认为,对接受新辅助治疗后行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的术前评估更加充分、病例筛选更加严格、术中创面和残端处理更加仔细、术后监护更加密切,是实现新辅助治疗后患者短期结果更好的原因。由此也恰恰说明基于上述的全程周到管理,全肺切除是可以安全开展的,并为局部晚期肺癌患者带来长期生存。
4 胸腔镜下全肺切除手术
早在1993年,英国胸外科Walker教授就报道,其团队运用胸腔镜成功开展了左侧全肺切除手术[42];但在这之后,所有关于胸腔镜下全肺切除手术的文献报道也仅局限于个案,缺乏大宗的病例报道。直到2019年,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Yang教授首次报道了多中心胸腔镜下全肺切除手术的回顾性研究结果:与开胸下全肺切除手术患者相比,胸腔镜下全肺切除手术的患者需要更长的手术时间,但可清扫更多数目的淋巴结和更多的纵隔淋巴结;共23例(19.0%)需要中转开胸,但基于临床特征、术前心肺功能检查结果和手术年限的相关性分析,并未发现与中转开胸有关的危险因素;最后,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后证实,两种手术方式间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总生存和无复发生存率均无明显差别[37]。此外,随着单孔胸腔镜下手术操作和切割缝合器械的发展,西班牙胸外科Gonzalez-Rivas教授团队还于2013年报道了世界首例单孔胸腔镜下全肺切除手术病例[43]。因此,对于常规胸腔镜技术开展成熟的高体量胸外科中心,可为部分局部晚期肺癌患者制订微创化的全肺切除手术方式,从而改善患者的近远期结果。
5 小结
虽然全肺切除手术伴随着较高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但基于术前心肺功能和全身状况的充分评估、基础疾病的良好控制、术中妥善处理残端和创面、术后密切的循环和心电监护、多学科医生和护理团队全程参与的情况下,全肺切除手术是可以作为局部晚期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策略选择,为该类患者带来可观的长期生存(文献报道5年生存率约为10.8%~66.0%)或临床治愈机会[6,10-12,15-16,20-23,27,29-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