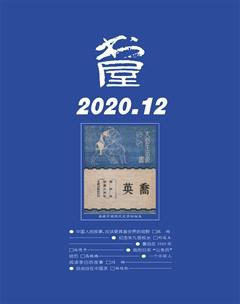试玉辨才活水来
叶隽
张贵永(1908—1965),字致远,浙江宁波鄞县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0年留德,1933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留英研究西洋史。1934年归国,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西洋史、西洋史学史、西洋外交史等课程。他作为历史学界较少的留德学人,其对德国史学的引介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可能因为他日后去了台湾,所以大陆对他较少提及。
张其昀称:“致远兄盛年凋落……学术界都深表哀悼,因为他是造诣高深,人格完美,有国际声望的史学家。”接着说:“学者的生命虽有限,但精神则不朽。一位伟大学者的逝世,譬如一颗种子,在地下生了根,其将开花结果,发荣滋长,是可深信不疑的。致远兄生平中、外文字著述不胜枚举,最近一篇论文综述他的老师柏林大学教授曼纳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史学,体大思精,光焰逼人(原文题为《曼纳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载在《华冈学报》第二期,1965年12月)。他是曼纳克的嫡传,这次赴德讲学,便是应曼纳克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邀请。此文盛赞他老师的德业,何尝不是他一生心血的写照,他的志愿要把中、西学术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开创新运,他不愧为当今文艺复兴的一位持炬者。”这段评价可谓甚高,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张贵永的师承渊源,即其导师为德国史学家梅内克(Friedrich,Meinecke,1863—1954),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大学者。二战之后,西方思想界普遍认为希特勒的国社党及其德国浩劫乃是德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如卢卡奇即称之为“理性的毁灭”,而梅内克则认为是“德国的浩劫”,强调其偶然性;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德国精神自启蒙运动以来所走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德意志道路”从根本而言大有裨益。此处不赘。但張贵永的师承来历,对其整体的学养形成无疑是重要的背景。
作为及门弟子,张贵永曾专门撰文《曼纳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介绍梅内克的史学思想,开篇即指出其在学术史框架中的定位:“精神史或思想史的研究在近代德国的史学发展上可以说具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中尤以狄尔泰、屈络铨与曼纳克的贡献最为显著,他们的影响亦最深远。”一方面凸显梅内克在德国理想主义思脉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揭示其不得不面对的困局。譬如他就认为:“曼纳克的精神理想与屈勒次克所提出的实力政治的文化目的均不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二十年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三大势力成为大国的强权政策,国家利益的破坏力量也就无法限制。因此,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想家像曼纳克那样只得被迫承认权力政治与国家利益的根本矛盾,认识自己国家民族和国际集团的共同关系,指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另一方面却又尽可能地使它们接近。在国家利益里‘神与魔鬼一起存在……永远不能脱离狮身人面的怪相,而又无法清除它。实际政治家应以神与国家为内心凭借,使正常存在的魔鬼不至于过分伸张它的势力。史家不仅应该认识因果演变,并须拥有兰克‘与神相契(Unmittelbar zu Gott)的精神。”这段话真可谓是梅内克的知己之言,常人难以体会。作为一个大学者,梅内克其实是有自己的理念和抱负的,但他却不能不和光同尘,即不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切割而进入到纯粹的学术世界中去,而是必须将其研究与现实适当挂钩,甚至有时难免屈己从人。尽管如此,梅内克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史学面相仍是值得关注的。张其昀引述张贵永论及梅内克的话尤其发人深省:“历史的理则,一言以蔽之曰:‘思想创造时代。他说道:精神史或思想史的研究,在近代德国史学发展上可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中以曼纳克的贡献最为显著,影响亦最为深远。他的著作代表着哲学与史学的综合研究,他是一位兼具有严格训练的治学方法,与深湛淹博的思想通识,与擅长写作的艺术手腕。他能以最精细的分析,发挥一切生命合一的观念,个人与全体合而为一。他能透过时代潮流揭发历史真相。他一贯主张法治,以及信仰与思想自由。他的巨著《精神史》,最能表明他的崇高人格。这一位史学大师,在现代德国人民心目中,真是罕见的崇宏与独特,其心灵的纯洁无疵,尤为举世学人所钦敬。”
张其昀的见地很好,也善于推理,他说:“宇宙本是整个的,学术也是整个的。分工只是方法,合作才是目的。一位伟大的史学家,除了本身所应具的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而外,又应具有哲学的达观,文学的修养,政治的热诚,和宗教的信仰。开胸襟,集众长,以期‘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致远兄所以能成为青年学子向慕效法的模范者在此。”这话确实捕捉到要害所在,治学必求问道,否则格局不大,境界也未臻高妙;如此则分工仅属必要,求全才是目标。作为大学者更是应当胸中有大气象,不仅要文史哲兼通,兼及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等,甚至对自然科学也宜有所涉猎,庶几可以逐渐近道。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在实践中,一个学者能努力借助若干自己有兴趣的命题进入多个不同领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张贵永正是属于此类史家。张贵永的著述并不算多,但在各个领域都颇有贡献,张其昀推崇他说:“致远治学,深受十九世纪以来德国史学的影响,博而能精,其在学术上重要贡献,则是关于中美、中英、中俄外交史的研究。”在论文集之外,张贵永曾根据英国史学家斐雪(Fisher,Herbert A.L.,1865—1940)的《欧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改编成《西洋通史》二卷,虽然他谦称:“我等于把原著译成中文,自己毫无贡献可言,只是改正了好些错误和不合时宜的见解而已。”但事实上他颇是下了功夫,仅就翻译而言,如此皇皇大作,就相当费力;至于纠正史实错误、更改观点,更是非常人所可为。这也可见出那代学人的学术态度,是很端正和从容的,对于这类自己难以进行原始研究的通史著作,就是直接翻译西方名家的著作。
张贵永还曾担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并深受好评。“现在的系主任是张贵永先生。张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史学,在系内主讲西洋近世史及西洋史学史等,和蔼可亲,深为同学所敬爱,讲起书来,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娓娓动听,对于西洋史学史及西洋史学方法,更多精辟的见解。”当然,其后移居台湾,长期在台湾大学等任职,无论是在具体历史研究还是在史观方面都有所成就,此处不赘。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那代留德学人的旁骛和通识,譬如朱偰对德语文学的兴趣和翻译、欧阳翥的中国古典学养和旧体诗写作、徐梵澄的德文与梵学知识等;张贵永也是如此,他的眼光非常宽阔,譬如他就有一篇文章《歌德与近代历史思想的起源》,开篇就说:“德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果没有歌德,怕不是现在这样。”他当然不是空洞地下这个结论,而是能将其放置到具体的思想史语境中去讨论:“像歌德那样的影响,真能改变精神趋势,只好从直觉的综合研究与个人的内心体验中获得。康德与黑格尔固能领导世人进入新的思想途径,这也许要比歌德所指示的更加明显。席勒的诗,虽然终是思想充实的内容居先,但对于德国人的心起了感应,至少在十九世纪有他的成功,这也许要比歌德所能赐予的更显得直接与简爽。可是思想与情感联合一起,就是内心生活的总和,从来没有像歌德那样深刻把握着。连浪漫主义和在他们之前的赫尔德(Herder)都不能如此,虽然他们全部过程中有其不能忽视的伟大影响。历史意象原是基于思想与情感的交互影响;要阐明历史观的起源与演进,就只能从人类内心生活追寻其发祥之地。如果有人相信,歌德的情感与思想对于德国人和甚至非德国人的心灵有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否有裨于新历史观念的起源?这里固然容易起种种疑难。当作一个历史思想家,这自然不是歌德的本身事业;历史世界只是他创造范围的一个方面。他自己并且在他的一生中一再对于世界历史的价值以及我们对它的知识有不乐意的表示。他是诗人艺术家与研究自然的人。自然、艺术、人生系他所标揭的三大对象,历史他似乎未曾说起。可是这些对象的互相平衡,就会引导到历史。因为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终是把人生放在艺术之上。人生与自然最后是合一,形成活泼自然(lebendig-natürliche)的世界,这里面就包括历史世界。”应该承认,不愧是留德学人,张贵永的学养很好,不但精通史学,而且对文学、哲学都相当熟悉。而这段论述歌德思想、情感和精神的文字,见地极为高明,绝不输于任何专业的德语文学研究者,这种通识能力的达致绝非一蹴而就,乃是积年之功。所以,要理解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德国学”流脉,必须将海外学者的贡献纳入考察范畴。他还写过较为通俗的文章《歌德与历史》,可见他对歌德与历史的关系是深有兴味的。张贵永与冯至交好,不知当年谈兴飞逸中,歌德是否也是一个重要话题?1935年,冯至夫妇归国,姚可崑回忆说:“我们的船在9月上旬的一天到达上海,冯至在柏林时认识的一位学历史的同学张贵永在码头上迎接我们。他陪同我们到旅馆里略作安排后,便和他的夫人邀请我们到一家饭馆里晚餐。他说,他和他的夫人因事来上海,只住几天,正巧我们这时回国,蒋复璁拜托他来照顾我们,并请他转告冯至,务必到南京去看一看,那里有不少留德的同学。蒋复璁于1932年回国后,就筹备成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朱偰、滕固都在那里。张贵永是中央大学历史教授。”在我看来,烙有德国印迹的历史学家张贵永固然重要,他作为留德学人的生命史也同样有意义,譬如这里由当事人回忆提及的留德生活史就同样值得钩沉,甚至还包括他们归国以后的学术轨迹和场域互动,按照徐梵澄的说法:“确有一班曾往德国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深造的人散在各界。没有成派,但总有些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或正或反,有形或无形,是受了德国文教之熏陶,亦原本于我国固有的教育,彼此同似,隐约成了一流。”而值得另书一笔的,是另一位学人留下的他们留德时代的生命史记忆。浦薛凤(1900—1997)是政治学者,曾先后留学美、德,1933年赴柏林大学进修,与张贵永交好。他在清华任教,可以按规定获得出国研究一年的机会,“予之核定计划系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康德、黑格尔与菲希特三位之政治哲学,以及搜购三位之著作德文全集”。到德国之后,即见到张贵永:
初抵德国首都,暂住闹市中心旅馆,午饭后偶在附近散步,巧遇清华学生张贵永(致远),时在柏林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经伊陪同寻觅与选择之下,向某一住户租得宽大之楼房一间;嗣又经伊介绍,认识姚从吾(士鳌)兄。此后,吾三人时常会晤聚餐。双十节国庆,留德中国学生开会庆祝,举行午宴;予经致远接洽,邀请在此专修音乐之清华女生姚锦新小姐参加。当场并认识几位留德男、女学生;其中有陈士华一对与郭君,相互来往,或偕同出游,或到士华寓所盘桓。两月后,予曾自己在康德大街觅得更合式之住房一间,定期迁移。关于每日三餐,无法向房东包办伙食,只有自行解决。等于天天往小餐馆。好在市区颇多出售“冷碟”肉食与切好面包,可以带回寓所,做成各色三明治,味道可口,方便价廉。有两三处中国饭店,周末辄约致远、从吾等前往“牙祭”,饱尝一顿,其中最好一道,乃是螃蟹,而且是道地河蟹,团脐尖脐,脑肥肠满,不亚于北京正阳楼蟹味。据云,此类蟹种乃来自上海。盖停泊黄浦江内之德国轮船船底,有螃蟹爬进臥藏,竟能远涉重洋,回抵德港,由此生存繁殖。至于在柏林之来往行动,一周之内即已学得购买长期月票(贴有照相),携带乘坐极属方便。衣、食、住、行,件件解决,始能谈到读书研究。
这段回忆很重要,因为给我们提供了留德时代的具体交谊情景,以张贵永、姚从吾的好学勤奋,居然也有这样的雅兴,不但热心帮忙,而且也乐于聚餐,善于大快朵颐,如“吃螃蟹”;至于聚会、出游、迁居、餐叙等,更是留学生的常态,这些都为我们理解那代留德学人提供了很好的一手材料。浦薛凤与张贵永并非仅是留德时期的遭逢,而是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予每晤致远辄喜与谈学问论世事,总觉其渊博而中庸,不偏激,不武断。致远不喜月旦人物,此殆生性使然,与予相似,而其为人真是‘谦谦君子。在予固自始引为忘年交,在致远则一向执弟子礼,此种古人风度在今日实不可多得。”如此可见张贵永之人品、性格于一斑。可惜的是,天不假年,相比同代人,张贵永辞世颇早,在1965年,即未及花甲之际,就因病辞世。柏林自由大学文学院院长何尔宓教授(Dr.H.Helbing)致悼词说:“张博士具有谦虚和仁慈的人格。这位极孚众望的学人在他的祖国和外国都拥有很多朋友,并且也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偶像。柏林自由大学与文学院很感激这位学人,因为他在百忙中应邀在多年别离之后再度来到柏林,然而他的寿命却在这里终止了,我们很惋惜他的早逝。”他继续说:“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位故人将永远是一个君子,一个正直的同僚,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和一位伟大的学者。”悼念之词难免要尽夸赞之能,且是外人之语,但我们可以看出张贵永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显然是积极的,不过“伟大的学者”之誉显然不符实际。总体来说,张贵永作为史学家,在输入德国史学和史学研究方面是有贡献的,但著述数量有限,也缺乏分量足够重的大作品,其意义或更在于体现出那代知识精英和学人的通识风采,是留德学人群体中为数不多但却自有特点的史学家,能以通史通识激活所面对的一团乱麻似的纷繁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