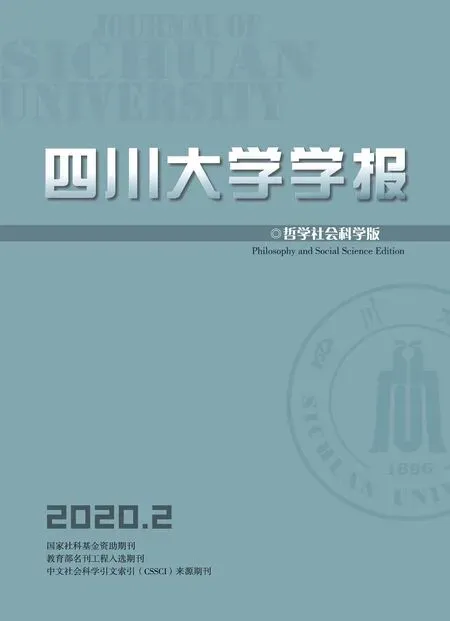“知识求人”的时代:网络语境下的知识变革及新知识素养构建
一般而言,社会文化的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基于一系列影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的动态历史过程。在这众多的影响因素中,人类意识世界里的核心载体——知识所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再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人类文明史的每一次迭代转型,都离不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从本质上讲,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知识的追寻史。
在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中,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这一生态链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和知识精英手中,知识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而今,在媒介技术不断演进与变革,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赋权之下,知识具备了流动性、开放性、联结性和交互性等特征,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也呈现出过去时代未曾有过的全新图景。“知识就是力量”在人类文明迈入网络时代后愈发凸显,正如有学者所说:“知识,尤其是数字化的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运用的知识,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1)夏德元:《知识的数字化传播与知识分子的角色重构》,《南国学术》2018年第1期,第25页。在此情形下,如何更为深入地揭示当前网络语境下知识变革的现实图景,尤其是对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对于知识的性质、结构与形态带来何种影响、给知识生态带来哪些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分析,已然成为当下网络传播研究中最具时代特色,也是最值得关注的话题之一。鉴此,本文所关注并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的问题是:受到媒介技术演进与变革的影响,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知识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嬗变,以及在网络语境下的知识存在与知识生态面临着哪些特殊挑战,而社会个体又当构建起怎样的知识素养,以应对当下知识网络化所带来的冲击?
一、从“人求知识”到“知识求人”:媒介技术变迁下人与知识关系的嬗变
孙中山曾对知识做过如此表述:“有知识,故能趋利而避害也。”(2)孙中山:《为〈大光报〉年刊题词》(1920年1月),《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3页。按照这一理解,知识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人类为求生存而适应环境的产物。该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比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正是因为人类缺少了像其他动物一样的本能,因此必须去寻求自身行为的指标,去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从中获取为求生存所需的知识。(3)John Dewey,The Quest for Certaint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New York:Minton,Balch & Company, 1929, p.38.长期以来,一方面人类需要通过创造、生产和加工知识寻求社会以及自我的良性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知识也借助人类的力量,通过特殊的手段进行保存和传播。如此一来,人类与知识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经历着嬗变过程。对此,我们有必要略做回顾。
从早期的人类社会开始以至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知识作为一种重要资源,总量极其有限,呈现出鲜明的“中心化”特征,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控制权被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和知识精英掌握,致使知识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此时的人们即便表现出对于知识的强烈渴求和需要,也会受到社会分工以及社会阶层分化等因素的影响,在知识生产、传播格局中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并由此带来人类不断扩大的知识需求与极其有限的知识供给之间尖锐的供求矛盾。
在人类社会最早阶段,巫术作为一种应付自然、适应环境的知识,“不仅渗透在上古生活和人们信仰心理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深深地杂存在当时人们的原始知识和实用技艺当中”。(4)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1页。作为巫术的执行者,巫师一般被视作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知识精英,正是基于他们“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疑难的解答者,很多后世分化出来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医学、农技以及文学艺术等各种形式,当时都是由其所掌握和垄断”。(5)童正恩:《中国古代的巫》, 《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196-197页。巫师通过占卜吉凶、祭祀驱鬼、祈雨求福等方式,生产着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早期人类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播给普罗大众,以教化民众、巩固统治。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宗教逐渐取代了巫术的地位,宗教神职人员成为知识的主要生产和传播者,他们不仅继续充当着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负责解释各种超自然神迹和异常自然现象,而且也通过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仪式活动,传播天文、气象、医药等知识,普通民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们的教化。在传统中国的“四民社会”中,“士”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亦发挥着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功能,士大夫被儒家文化传统赋予和规定了超乎常人的各种特权和威望,成为“礼治社会”中名副其实的知识精英和文化领袖,他们不仅掌握了礼治背后的道德价值和知识文化的解释权,同时创造着宗法家族、社会共同文化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知识,并成为这部分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播者。可以说,在整个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士大夫正是通过积极参与对民众的教化、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而在西方社会中,进入中世纪最初的几百年间,教会一直拥有着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垄断权力。作为精英阶层的教士和僧侣们不仅每天从事传教布道的工作,而且利用闲暇时间研读欧洲古典文化,学习几何学、物理学、法律等科学文化知识,而普通民众甚至贵族除了接受宗教知识外,很难接触到其他知识,更谈不上接受更高层次的文化教育。
知识真正实现去“中心化”,开始从高高在上的位置“飞入寻常百姓家”,媒介技术作为改造与形塑知识活动的内生性变量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介技术的变革一方面从根本上优化了传播环境,同时又通过塑造主体的观察方式、感知方式、思维方式来现实地推动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6)赵涛:《电子网络时代的知识生产问题析论》,《哲学动态》2015年第11期,第25页。观照人类社会传播媒介演进与发展的历史即可发现,以造纸术和印刷术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是知识的社会化传播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知识共享水平获得显著提升的开始,从此知识开始朝着“平民化”方向移位和流动。
以印刷术为例,这项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明大大提升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正是印刷术的发明让人类摆脱了手工复制知识的束缚,使得文字信息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进而带来知识的大众化传播。譬如,当印刷术传入欧洲,即对当时的欧洲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印刷术的出现冲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在中世纪的欧洲,《圣经》一般是手抄在羊皮纸上进行阅读,由于羊皮纸成本极其昂贵,加之教会才拥有对《圣经》教义的解释权,因此阅读《圣经》只是少数教会人士的特权。当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用他发明的印刷机第一次印制出200册的拉丁文《圣经》时,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只能在教堂中接受基督教义的传统随之改变。正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言:“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厨房桌上,而且用的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上帝的信息既然如此唾手可得,基督教徒就不再需要各界神职人员为他们诠释教义了。”(7)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 吴燕莛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年,第49页。其次,印刷术的使用带动和引发了欧洲的社会革命。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广泛普及,欧洲在17世纪前后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不仅为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等领域带来了新的转变,也将科学从中世纪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知识启蒙。
20世纪初,随着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崛起,人类社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再次得到加速,又一次从根本上刷新了人与知识的关系。具体来说,电子传播媒介的普及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带来新的时空效应,使知识传播无远弗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对知识的感受从文字印刷的抽象和线性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学习者可以获取更加身临其境、形象生动的体验和感受。当电子媒介的数量不断增加且流通广远之后,它们同印刷媒介一道成为推广知识、普及教育的重要工具,对突破知识精英的垄断,促进知识的大众化、平民化以及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如今,互联网技术所构筑的新的技术条件和活动空间,为身处知识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全新的知识创造、获取和传播通道,催生出新的“用户创造和生产知识”这一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的新范式,再一次重塑着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具体来看,互联网“为当代知识生产活动开辟了一个以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并存的多元的全新场域”,(8)赵涛:《电子网络时代的知识生产问题析论》,《哲学动态》2015年第11期,第22页。其所具备的便捷性、互动性和低门槛性等特征,不仅“复活了知识自由,打破了知识垄断,使大众都参与到知识的生产之中”,(9)史春晖:《网络逻辑与知识共享: 技术重构人与知识的关系》,《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5期,第27页。而且进一步“摧毁了金字塔组织模式,碾平了生产的边际成本,极大地释放了知识分享的能力”。(10)段永朝:《互联网思想十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年,第20页。有学者指出,网络语境下的“知识存在于连接中,是一种联通化知识(connected knowledge),……联通主义学习的学习观不仅强调建立与已有节点之间的连接,还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创造新的节点,并与之建立连接,促进知识的生产”。(11)王志军、陈丽:《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及其最新进展》,《开放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6页。在此情形下,人们的头脑开始互联互通,一些热情而富有创造力、具备丰富知识背景的网民积极地利用互联网平台,在其所构筑的虚拟空间中不计酬劳地生产、传播和消费知识;而其他网民只需轻轻点击鼠标,就能高效实时地获取到自己想要的知识,网络空间由此演变成为一个巨型“图书馆”。
由于“信息、知识和文化是人类获得自由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们的社会中,如何生产和传播知识深刻影响到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以及可能是怎样的”。(12)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早期人类社会受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少数精英人士所掌握,知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那个知识匮乏且获取门槛极高的年代,“人求知识”形象地概括和揭示出了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样态。而随着媒介技术的深刻变革,媒介作为一种传播文化知识和沟通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不断重塑和刷新着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传统生产、获取和传播知识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的今天,知识的急剧扩增甚至是过剩进一步凸显出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注意力开始取代知识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人类与知识的关系也从过去的“人求知识”走向“知识求人”。“知识求人”是在人类社会知识资源的无限性与人类注意力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作用下,产生的一种人与知识之间的新关系,其实质是当人类社会知识总量严重过剩时,注意力作为人的一种选择能力就会相应地变得稀缺,知识的获取和吸收也相应地变得愈加困难。换言之,当人们面临一边是蜂拥而来的呈指数级增长的知识总量,一边是人们的时间及注意力资源不断碎片化和稀缺化的局面时,浅层吸收知识或者说是难以真正地理解和学习知识就成为一种常态。
总之,从“人求知识”到“知识求人”,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嬗变过程,形象地勾勒和描绘出媒介技术变迁视野下人类社会中人与知识关系的演变轨迹。
二、网络语境下知识存在的重构及其新挑战
一般来说,任何知识存在都有其适合的知识情境,相反,知识情境的变革反过来也会直接影响到知识存在。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知识的“容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人类知识的结构、性质与形态正在经历一次进化意义上的重构与转型。
从知识的结构来看,传统时代知识的结构是一种“层级流动”的序列结构,这意味着知识从生产者传递至学习者手中,必须经过一个预设的、结构化的“知识过滤器”。如今,“扁平化、分散化与互联化的网络形构交织出了一套协同、交叉与共融的知识性网络”。(13)蒋晓丽、朱亚希:《超越与联盟:传播符号学的生成发展和应然指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8期,第7页。在不断生成的、松散联通的、去中心化的网络形构中,知识的结构不再是以“点状”或“树状”结构呈现,而是体现出“链态”分布的全新态势。在无定形的、相互交织的、不可掌控的网络中,知识之间可以通过新的链接和连通,实现对话、争辩、碰撞甚至是冲突,从而不断地产生新的知识。
从知识的性质来看,传统时代的知识是一种静态的、有组织的并由专家定义的综合体,其最大的价值在于结论的确定性和权威性。然而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下,知识已经“摆脱了旧媒介的属性,而拥有了新媒介的属性”,(14)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 胡泳等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105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网络化知识数量极其丰富,并处在时刻变化和存在于特定场景之中,因而具有丰富性、流动性和情境性的特征。其次,由于网络平台允许和接受“永久性分歧”,知识不再要求定论性的东西,故网络化知识具备未决性的特点。再次,当缺乏适当引导时,网络环境下的知识讨论会变得漫无边际,甚至让谬误成为事实,导致大量伪知识泛滥,这使得网络化知识拥有复杂性的特征。
从知识的形态来看,传统时代的知识形态多以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为表征,单向度和线性化传播的路径依赖表现明显。而今,网络语境下的知识拥有了超越这些局限的全新特征,栖身在网络化的时空,知识处在更加动态的、多元化观点并存的状态之中,无论在其形成过程,还是在传播与应用过程中,都是以多媒体、非线性、交互性等形态呈现。正如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所言,“在网络世界中,知识不存在于书籍之中,也不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15)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 第72页。
互联网技术除了直接对人类知识结构、性质以及形态产生巨大影响以外,还给当下的知识生态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结合当下知识生态所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笔者认为,这种冲击与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知识表征碎片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碎片化(fragmentation)已然成为当代社会的显性发展趋势之一,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知识领域,碎片化主要表现为知识呈现碎片化和知识习得碎片化两个方面。首先,网络时代的知识多以碎片化的样貌呈现,这种碎片化的知识通常来源广泛且分布零散,多隐藏于零碎的信息之中。相较于整体性知识而言,碎片化知识一方面具有成本低、易于使用和组合、便于理解等优势;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低认知成本、重视事实的简单组合而非以逻辑的推演使复杂事物简单化等方面的特征,碎片化知识往往与非逻辑性、单一性、无序性以及冗余性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其次,传统时代个体对于知识的获取和学习通常是以整体性、系统性的方式进行,知识学习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社会个体在知识习得过程中需要学会不断地与其他相关知识建立起联系,并将其有机地整合到现有的知识框架和体系之中,完成知识从“量”到“质”的转变。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知识获取渠道的便捷化、知识数量的海量化以及休闲时间的碎片化使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获取和学习方式,被分散化、碎片化的知识获取和学习方式所取代。以碎片化方式习得知识的社会个体,在知识体系和思考能力上不仅不会得到显著提升,长此以往,也许还会导致其思维变得简单、浅显,甚至丧失独立、全面的思考能力。
其二是知识体系膨胀化。知识是人类用以表现对世界包括自身在内的认知的结果,零碎的、分散的知识经过结构化加工与整理,便会形成一种知识体系,亦即一种高度有序的知识集合。传统时代人类为维持知识体系有效运转和有序累积,一直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在知识权威和专家的精心组织下,知识体系一直是以一种有序、动态的方式不断发生着自在的跃迁,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零散到系统。然而,随着知识网络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人类的知识体系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知识体系膨胀化,在网络时代知识表征碎片化的背景之下,人类过去系统化、结构化和有序化的知识体系被不断打破和切割,呈现出日渐膨胀的、无法全知(too big to know)的甚至是无边界化的特征。知识体系的膨胀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直接后果,比如互联网时代下的人们很难将日常生活中大量充斥着的碎片化的、零散的、孤立的知识通过某种逻辑链条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体系化、有序化的知识结构。正因如此,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含金量并没有因为知识体系的无限膨胀而越来越大,相反,知识正在朝着迅速贬值的方向发展。
其三是知识秩序无序化。需说明的是,这里的知识秩序侧重于知识的组织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先哲们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清晰而完整的知识分类方式,构建起了多种具有可控性的、有序化的知识组织秩序,比如狄德罗提出的按字母排序的线性秩序,林奈提出的以“纲—目—属—种”为分类形式的树形秩序,以及阮冈纳赞提出的“冒号分类法”这种链式秩序,等等。而今互联网革命的进程不断解构着由知识权威和专家所组织的传统秩序,同时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数字秩序”。在这一新秩序中,作为组织对象的知识以虚拟的“比特”形式存在,不再受到组织者的控制以及物理空间的限制,用户可以自由地进行统合和分割。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数字时代,由于知识的组织不再受其载体物理特性的制约,因此,可以摆脱必须编排页码的纸质图书限制,不必被刻板地排序,……也不必被非此即彼地分类。知识排序与知识归属的特征逐渐模糊,知识关联与知识链接的特性日趋鲜明。”(16)藤广青、毕强:《知识组织体系的演进路径及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探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9期,第51页。然而,这种不加任何指导和控制的知识组织秩序在带来知识丰富性提升的同时,也使得当下知识秩序因互联网超文本、多样性、关联性、链接性等特性变得更加无序化,(17)藤广青、田依林、董立丽、张凡:《知识组织体系的解构与重构》,《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9期,第17页。并且“知识的‘无序化’促使人们创造出一种比以往任何一种知识组织秩序结构都要庞大的混乱”,如当下热门的维基百科、Flickr就是知识秩序杂乱无序的典型代表,因为传统的、有序化的、层级森严的知识组织秩序在其中早已无从体现,取而代之的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无序化的知识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用户不需要知道内部知识组织秩序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每一位用户都可以将其割裂,并且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为这些碎片化的、网络化的知识排序,重新将其整理。(18)参见戴维·温伯格:《万物皆无序: 新数字秩序的革命》, 李燕鸣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137-138、273页。
其四是知识消费娱乐化。早在电子媒介兴盛的时代,尼尔·波兹曼就曾对电子媒介文化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电子媒介的出现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娱乐化。(19)参见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如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娱乐化生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娱乐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导逻辑,人们心甘情愿参与到由互联网技术所建构的“游戏化”情境中,在现实与虚拟的连结状态中自由切换以寻求及时的享乐和快感。而在知识消费领域,网络技术的发展撬动了传统时代知识精英对于知识的诠释权利,从众人协力创造的维基百科时代,到任何人都能发表即时化观点的博客时代,再到以互动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生产被裹入娱乐元素。不管是知识付费平台上“知识网红”的直播,还是层出不穷的表情包、漫画、段子、短视频,大量专业化、枯燥化的知识都在以娱乐化的方式传播和普及。可以说,网络时代下的知识消费正在从过去的工具化、实用化向娱乐化转变。相比于传统时代的系统知识,娱乐化知识有助于用户获得放松和愉悦,因而更能吸引用户利用碎片化时间,这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时代,无疑具有相当的优势。然而,当娱乐化超过一定的限度之时,不仅知识的严肃性会遭到消解,知识的品格随之削弱,而且社会个体由于长期沉溺于娱乐化知识所塑造的伪语境中,很难保持清醒的认知,从而迷失在潮涌而来的娱乐化知识洪流中。
其五是知识焦虑放大化。对知识的渴求让人类摆脱了愚昧和无知的状态,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文明。如今的互联网为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渠道,然而,知识的丰富程度和新知识的层出不穷,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因担心自己知识匮乏而落后于他人的焦虑感和恐慌感。于是,整个社会的“知识焦虑”在这样的氛围下被不断凸显和放大。究其实质,知识焦虑是一种信息焦虑,主要缘于两个层面:其一,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面对信息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因知识匮乏而内心恐惧的焦虑情绪;其二,当人脑接收到的知识数量远远超过人脑可承载的容量之时,也容易造成紧张、焦虑和不安的情绪。此外,近年来以知乎、分答、得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付费平台及知识付费产品的兴起和走红,在为用户节省知识筛选时间、提高知识获取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用户的焦虑感和紧张感。笔者认为,当下知识付费领域的不断成熟与用户知识焦虑的不断放大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知识付费服务的出现,满足了消费者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信息、新知识以及新的认知迭代而渴望快速接触和获取知识的需求,但作为短暂性“麻醉剂”的知识付费服务并不能彻底缓解知识焦虑,反而还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们在庞杂的知识面前更加“饥不择食”,知识焦虑不减反增。而当人们在庞大知识体系面前感觉到无助之时,便会一次次伸手去抓知识付费服务这根“救命稻草”,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三、基于知识网络化变革的个体新知识素养构建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就被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用来描绘知识产业占据重要地位的新知识时代。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社会变革,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20)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高恬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21页。到了80年代,“知识社会”开始取代“后工业社会”的说法,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知识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用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话来描述,那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它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知识”。(21)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8页。至此,知识最终成为人类社会中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知识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以及知识网络化变革趋势的加深,知识存在不仅呈现出了新的特征,而且也对社会个体的知识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素养”概念“源于对知识、能力及资源在动态竞争环境中的作用的充分理解”,(22)宁烨、樊治平:《知识能力的构成要素:一个实证研究》,《管理评论》2010年第12期,第96页。一般是指社会个体通过整合并运用知识,形成的能够适应、协调外界环境的一种综合能力。因此,动态适应性是知识素养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当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时,知识素养的内部能力结构就会相应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以前,个体知识素养更多体现在发现、获取与应用知识的能力。随着知识网络化现实的不断加深,人类的知识存在和知识生态链的运作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知识从一种个人利益走向公共资源已经变得不再稀缺,而真正缺乏的却是有效地将知识转换为价值的知识素养。在此背景下,新知识素养的构建就成为社会个体应对知识网络化冲击的当务之急,而如何构建知识素养,首先需要做的是明确新知识素养的内部能力结构主要涵括哪些方面。
在讨论新知识素养的内部能力结构之前,我们有必要借鉴网络语境下其他素养概念,诸如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等的内部能力结构的相关讨论成果。截至目前,学界围绕以上概念内部能力结构构成的讨论相当多元。比如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和谢莉·休斯(Shelley Hughes)提出,信息素养主要包含三个维度:工具素养(tool literacy)、批判素养(critical literacy)和社会结构素养(social structural literacy)。(23)Jeremy J. Shapiro and Shelley K. Hughes,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a Liberal Art: Enlightenment Proposals for a New Curriculum,” Educom Review, Vol.31, No.2, 1996, http:∥net.educause.edu/apps/er/review/reviewArticles/31231.html.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艾伦·海斯珀(Ellen Helsper)认为,网络素养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括使用、分析、评论和创造网络内容的能力。(24)Sonia Livingstone and Ellen Helsper, “Balanc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in Teenagers' Use of the Internet: The Role of Online Skills and Internet Self-efficacy,” New Media & Society, Vol.12, No.2, 2010, pp.309-329.在路易斯·梁(Louis Leung)和保罗·李(Paul Lee)看来,网络素养应包含理解、批判、应用以及管理内容意义的能力。(25)Louis Leung and Paul Lee, “The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arenting Styles on Internet Risks,” New Media & Society, Vol.14, No.1, 2012, pp.117-136.在借鉴上述国外学者对于媒介素养等概念的讨论并结合网络时代知识变革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新知识素养的内部能力结构主要涵括认知、分析和协调这三个重要能力维度,由此出发,以下尝试从甄别与筛选知识、理解与批判知识、定制与管理知识三个方面,为社会个体如何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知识素养提出可供借鉴的建议。
(一)甄别与筛选知识的素养
网络时代甄别知识的素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个体需厘清数据、信息和知识三者之间的区别。通常来讲,数据、信息和知识被看做是对客观事物感知的三个不同阶段,然而在网络时代三者经常被混淆,甚至出现混用的情况。实际上,数据是指用来表示某些事物的文字、图像等符号记录,它是构成信息和知识的一种原始材料;通过一定手段在数据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后,数据就演变成为信息,因此信息是加工处理之后的有逻辑的数据组合;而知识是在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专业化的认知,具备可以指导“如何”行动的巨大价值。二是社会个体需学会辨别“真知识”和“伪知识”。陶行知曾指出,“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就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就是真知灼见”;(2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教育文选》,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第64页。相反,如果没有能够与个体的生命体验、人生经验产生联系则应是伪知识。真知识除了教会人们适应自然、维持生存,帮助人们从愚昧无知走向文明开化以外,还能让人们学会从生活经验中积累知识,从抽象思维中构建起知识体系,获得人类文明不断进化的最强劲动力;反之则是伪知识。
除了具备甄别知识的素养以外,互联网时代社会个体还需具备快速筛选知识的素养。当下,人们可以借助“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等新兴技术手段,发挥其“筛选器”的作用,实现知识的快速筛选。 “算法”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能够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能力和处理能力,从浩如烟尘的知识中快速高效地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此外,Web2.0时代下“社会化信息获取”(social information adoption)也可以成为人们筛选有价值知识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正如戴维·温伯格所说:“社交工具则将我们朋友们的选择作为指南,帮助我们寻找到感兴趣的东西。”(27)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第16页。
(二)理解与批判知识的素养
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指出,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制造出一种特殊的“谷歌认知”方式,这种快捷、简单的认知方式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搜索引擎获得知识,继而成为“接受型的认知者”。(28)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的很多,智慧却很少》, 赵亚男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 “前言”,第XXI页。诚如林奇所言,互联网技术虽然提升了人们在各种信息之间建立连接的能力,却使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推理和解释能力不断下降。同时,网络技术的便捷性容易让人们沉迷于以“游击”的方式到处采集碎片化的知识,知识获取速度与效率虽有所提高,却也造成人们注意力的分散,使得思考和批判知识的能力大不如前。为此,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互联网时代“许多人都太容易被近在指尖下的信息所诱惑或迷惑,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才是可靠的知识和如何寻找真相”。(29)徐贲:《互联网时代的真实与自由》,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的很多,智慧却很少》, “序言”,第V-VI页。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激发一切创新的根基。在知识经济的架构下,知识不能仅停留在对事物的认知层面,更需予以有效应用,这就要求我们对知识予以推理解读,整理出某些可以决定行动的结论,再经由批判的过程,真正掌握知识的本质及含义,并将其作为行动的依据。简言之,要想将知识更好地转换为价值,我们必须具备理解性认知和批判性认知这两种基本素养。所谓“理解性认知”,是指能“找到证明依据,并针对证据的关联性拥有创造性的见解,能够对事实进行解读,而不是单纯依赖于表象”。(30)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的很多,智慧却很少》,第17页。而所谓“批判性认知”,是指社会个体必须超越知识的“真理观”,在知识面前树立一种质疑、反省、解放与重建的批判态度。正是基于“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31)艾彦:《强纲领,相对主义与知识成因的社会定位——简评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1年,“译者前言”,第6页。因此,在面对海量知识时,我们应当具备批判与质疑的能力,即“通过批判考察所断定的东西也即被断定的事实本身直接地检验它的正确性”。(3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傅季重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 第35页。
(三)定制与管理知识的素养
在知识网络化语境下,由于知识体系的不断膨胀和无序化,社会个体需要实现知识体系的私人化定制,并借助知识管理实现知识效益最大化,即具备所谓定制与管理知识的素养。网络时代的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以个体用户代替规模用户、个性需求代替共性需求的私人定制化时代,这就意味着生产者需要针对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进行更加精准的生产、销售与推广,以增加产品的适用程度,提升用户的获得感与满足感。聚焦到知识领域,所谓“知识定制化”,是指社会个体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兴趣,为自己量体裁衣,定制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知识体系。这种私人化知识体系的定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社会个体需根据不同应用场景的特点,定制出适合自身日常经验的“场景化”知识体系,也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口中所谓“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哈耶克认为,“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对于每个人来说更有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33)Friedrich August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35, No.4, 1945, pp.521-522.其二,社会个体需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完成更加另类的、独特的、适合自身特质的“个性化”知识体系定制。这种个性化的知识体系不仅能够满足当下社会个体追求个性、崇尚独特的内在心理需求,而且还能提高整个知识体系运转的质量和效率。
除实现知识体系的个人化定制以外,社会个体还需保持知识体系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适时、适度、有序更新。当知识体系初步构建起来之后,社会个体需要学会利用“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方式将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归纳、消化直到内化。同时,在适当的时候社会个体也要通过“复盘”的方式,对掌握的知识进行回顾和总结。此外,由于知识始终处于不断的动态的更新之中,社会个体应及时摒除墨守成规的思维,不断地对新的事物进行接收。也就是说,只有及时把握最新、最前沿的知识动态,不断打破原有的不合时宜的知识体系,社会个体才能最终实现知识体系的有序更新。
总而言之,当下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革命”是继信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又一“冲击波”。在网络社会中,知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创造活动的产物和再生物,不仅是人类社会认识世界的结果,更是决定人类社会进步、创造世界未来的强大工具。未来,我们除了对知识的新形态、新定位及新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持续关注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随时保持一个理性和清醒的认知,防止知识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异化”成为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另类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