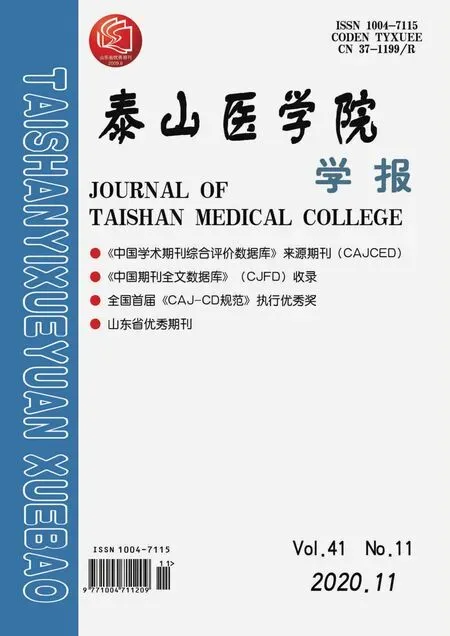血栓烷A2与脑血栓相关性研究*
康 慧 张敬军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6
脑卒中是常见病、多发病,发病机制复杂,受遗传及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脑卒中每年死亡人数约为620万人,约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1%。中国脑卒中死亡率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最常见的脑卒中类型是脑血栓,主要特征是脑组织缺血缺氧,约占脑卒中的69.6%[1-2]。脑血栓形成与血栓烷A2(thromboxane A2,TXA2)密切相关,是国内外研究重点之一,本文探讨TXA2与脑血栓的形成及治疗的关系。
1 TXA2的生物合成及功能
1.1 TXA2的生物合成
TXA2是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PG)中活性较强的一类,前列腺素由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在各种酶的催化下合成,AA是一种高级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的必须脂肪酸之一, AA在人体内广泛分布,在血液及肝脏等器官都能检测到AA生成,膜磷脂在磷脂酶A2(phospholipase A2,PLA2)催化下生成AA,继而AA在环氧合酶(cyclooxygenase,COX)催化下生成前列腺素H2(prostaglandin H2,PGH2)、前列腺素G2(prostaglandin G2,PGG2)。在血小板与巨噬细胞内有血栓烷合成酶,血栓烷合成酶催化PGH2生成TXA2,TXA2半衰期约30 s,迅速水解为血栓烷B2(thromboxane B2,TXB2)。在血管内皮与平滑肌细胞上PGH2在前列环素合成酶(prostacyclin synthase,PGIS)作用下则生成前列环素(prostaglandin,PGI2),PGI2半衰期约3 min,快速水解为6-keto-PGF1ɑ。因此,在各项实验研究中通常采用采用TXB2代表TXA2的含量及分布,6-keto-PGF1ɑ代表PGI2的含量及分布。
TXA2在COX和血栓烷合成酶催化作用下合成。COX是花生四烯酸合成的限速酶,COX广泛分布于细胞膜上,COX有3种亚型:COX-1、COX-2和COX-3。COX-1属于固有酶,在人体内各部位组成性表达,特别是在血小板、粘膜上皮、内皮细胞及胃肠道细胞中表达较多,主要发挥调节血管张力、参与血小板生成和聚集、保护胃肠道黏膜、维持稳定的肾脏灌流等作用,使人体组织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在中枢神经系统,COX-1组成性表达于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3]。COX-2属于诱导酶,通常被看作是病理性酶,机体组织在正常生理情况下表达很少,在病理状态下细胞经诱导可产生大量的COX-2,参与氧化应激、炎症反应、诱导神经元损伤等过程,在中枢神经系统,COX-2广泛表达于大脑皮层和海马[3]。COX-1具有较窄的底物特异性,主要氧化花生四烯酸,COX-2具有更广泛的底物特异性,与COX-1相比能更有效地氧化多种脂肪酸。COX-1和COX-2的一个功能差异是COX-2能够有效地氧化花生四烯酸的中间衍生物,如2-花生酰甘油三酯(2-Ag)和阿南达胺(AEA)[4]。在人类体内分离出COX-3,COX-3是COX-1的变异型[5],COX-3主要分布于大脑和心脏,与人类多种疾病相关,比如肿瘤、阿尔茨海默病等,研究发现在脑肿瘤组织中COX-3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脑组织,而COX-1和COX-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在TXA2形成过程中,COX-1起主要作用,COX-2主要在前列环素的生成中起作用。血栓烷合成酶属于细胞色素P450超家族,是一种内质网膜蛋白,最初在血小板中被分离出来,主要在凝血酶原细胞和单核细胞前体造血干细胞、白细胞和巨噬细胞中合成,后来在肺、肾、胃、肠、肝脏等器官也检测到血栓烷合成酶[7]。
1.2 TXA2生物功能
TXA2与受体特异性结合后发挥生物学作用,血栓烷受体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CR)超家族,可与G11、G12、G13、Gq及Gi等多种G蛋白偶联。在血小板、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等细胞膜上都能检测到血栓烷受体表达,广泛分布于人体各组织器官中。血栓烷受体是一个进行选择性剪接的基因编码,产生两种表型:ɑ型血栓烷受体(TPɑ)与β型血栓烷受体(TPβ),两者N-端328个残基具有相同序列,但在C端尾部序列不同,TPɑ在人胎盘中被分离出来,TPβ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被分离出来,两者发挥不同作用[8]。TPɑ和TPβ与不同类别G蛋白偶联,TPɑ主要与Gs蛋白家族偶联,而TPβ则主要是Gi蛋白家族偶联[9]。TPɑ在人体内分布广泛,TPβ仅在体内特定组织分布,血小板中两种亚型的血栓烷受体均有分布,以TPɑ分布为主[10]。
G蛋白偶联受体与异源三聚体G蛋白相互作用并启动多种信号通路,血栓烷受体主要与四种不同的G蛋白偶联,其激活后的信号传导可引发细胞和分子水平反应,例如细胞内钙离子测定、细胞骨架重置、磷酸肌醇代谢、激酶活化、整合素激活和DNA的合成、细胞的增殖凋亡等[11]。
2 TXA2与脑血栓的发病机制
动脉粥样硬化是脑血栓的重要病因,多种脑血栓危险因素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内皮损伤,在受损的内皮上血小板被激活并黏附和聚集导致血栓形成。在生理情况下TXA2与PGI2维持动态平衡,二者共同维持血小板内环境的稳定[12]。TXA2在血小板生成,发挥收缩血管和促进血小板聚集的作用,TXA2与其受体的结合促进脑血栓形成,PGI2在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产生,具有舒张血管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TXA2与PGI2失衡在脑血栓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动脉硬化斑块破裂导致血管胶原暴露,血小板黏附于胶原表面,被胶原激活后发生肿胀和变形,随后释放血小板ɑ颗粒、致密颗粒,再从颗粒中释放出TXA2,TXA2与血栓烷受体特异性结合。研究证实血小板上主要有Gq、G12和Gi三种G蛋白参与信号转导,其中Gq是第一个被发现与血栓烷受体进行功能性和生理性偶联的G蛋白,在信号转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血栓烷受体激活使偶联的Gq蛋白分离为ɑ、β、γ三个亚基。Gɑq激活磷脂酶C-β(phospholipase C-β,PLC-β),磷酯酰肌醇二磷酸(phosphatidylinositol bisphosphate,PIP2)在PLC-β作用下生成两个第二信使,分别是三磷酸肌醇(inositol triphosphate,IP3)和二酰甘油酯(diacylglycerol,DAG),在第二信使作用下胞外信号转变为胞内信号,其中IP3动员细胞内源钙流入细胞质,使细胞内Ca2+浓度升高,促进血小板聚集反应; DAG增强蛋白激酶C (protein kinase C/calcium dependent protein kinase,PKC)活性,促进血小板致密颗粒释放第二信使类物质,如TXA2、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diphosphate,ADP)等进一步加强血小板的聚集促进血栓形成[13]。
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过程中,TXA2与受体结合刺激内皮细胞黏附分子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在内皮细胞中表达,诱导内皮细胞活化使内皮细胞通透性增高,血脑屏障破坏,大脑内环境失去稳定性从而加剧脑血栓形成[14]。TXA2与受体结合介导的信号转导也与氧化应激和微血管痉挛有关,可能促进脑组织缺血的发生及发展[15]。
在一项研究中在招募了230名脑血栓患者和143名健康对照者的观察性研究中,提取外周血DNA进行基因分型,结果显示血栓烷受体 rs768963的C等位基因与脑血栓有关,血栓烷受体 C795T、T924C和G1686A的基因型与脑血栓无关[16]。
3 TXA2与脑血栓的治疗
3.1 环氧合酶抑制剂
TXA2主要在血小板经环氧合酶和血栓烷合成酶催化生成,其中COX-1在TXA2生成中起主要作用,COX-2在PGI2生成中起主要作用。
阿司匹林是临床上经典的非选择性环氧合酶抑制剂,也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通过乙酰化COX第529位活性位点上的丝氨酸残基,使COX-1失去生物活性,TXA2生成量减少,从而阻断COX-1途径的血栓形成,并且这一抑制作用是不可逆的[17]。临床上,阿司匹林广泛用于脑血栓等疾病二级预防。研究报道,使用阿司匹林治疗后,非致死性脑血栓降低25%,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死亡率降低34%[18]。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并非所有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后都能收获良好治疗效果,仍有部分患者规律服用阿司匹林未能起到预防血栓形成作用或再次发生脑血管事件,这种现象称为“阿司匹林抵抗(aspirin resistance, AR)”,目前AR的原因和机制尚未阐明,相关研究推测AR可能与遗传、环境、药物剂量等多因素有关。研究发现AR患者有更高的脑血栓事件复发率[19]。同时另一项研究表明,AR是中国脑血栓患者死亡率一个有效的预后指标[20]。
新的选择性环氧合酶抑制剂,如选择性COX-1抑制剂吲哚布芬、高选择性COX-1抑制剂P6和Mofezolac等。吲哚布芬可逆性抑制环氧合酶,从而减少TXA2生成,大量临床研究证明,吲哚布芬疗效确切,可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尚需要进一步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证实。Calvello等[21]研究证实,高选择性COX-1抑制剂P6和Mofezolac具有控制神经炎症和神经保护作用。
3.2 血栓烷合成酶抑制剂
在TXA2合成过程中,血栓烷合成酶是另一关键酶,催化PGH2生成TXA2,血栓烷合成酶抑制剂特异性抑制血栓烷合成酶从而减少TXA2的生成,从而抑制血小板聚集,同时血栓烷合成酶抑制剂还促进PGI2生成,维持TXA2/PGI2在体内的动态平衡预防血栓形成,扩张脑血管,改善微循环。目前临床广泛应用治疗脑血栓的血栓烷合成酶抑制剂代表药物是奥扎格雷。临床研究证实奥扎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脑血栓,能提高疗效,同时不增加出血风险等不良反应。联合应用奥扎格雷与长春西汀,与单一用药相比,更能促进脑血栓后神经功能康复[22]。Park等[23]研究者通过大鼠模型证实奥扎格雷不仅对脑血栓有治疗作用,而且对一些有血栓形成风险的脑血管手术比如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血管内成形术等也有预防作用。研究人员分别对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栓患者和腔隙性梗死患者进行倾向评分匹配分析,平衡了接受奥扎格雷治疗(奥扎格雷组)和未接受奥扎格雷治疗(对照组)的患者的基线特征差异,比较奥扎格雷组和对照组出院时的改良Rankin量表评分和入院后出血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研究结果示奥扎格雷并没有改善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或腔隙性梗死患者的功能预后[24]。其他血栓烷合成酶抑制剂还有Isobogrel、Terbogrel、Furegrelate等,这些药物临床应用较少,其疗效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3.3 血栓烷受体拮抗剂
TXA2与受体结合后发挥生物活性,血栓烷受体在在血管生理、止血和病理生理血栓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血栓烷受体拮抗是动脉粥样硬化和脑血栓预防的一种新的治疗干预手段,目前处于临床实验阶段[25],血栓烷受体拮抗剂可作为脑血栓等治疗用药,现阶段研发的血栓烷受体拮抗药主要有特鲁曲班、伊非曲班等。
特鲁曲班是一种特异性的血栓烷受体拮抗剂,Lesault等[26]研究证实在动脉粥样硬化人群中,特鲁曲班改善了内皮功能和动脉血管扩张特性。然而,在一项具有中期结局的大型临床试验中,与阿司匹林相比,特鲁曲班未能显示脑血栓患者脑血栓事件的二级预防的临床相关性[27]。最近Lagier等[28]通过构建蛛网膜下腔出血大鼠模型证实特鲁曲班可用于预防出血后血脑屏障破坏、神经元凋亡和迟发性脑灌注不足。
NSTPBP5185是一种新型血栓烷受体拮抗剂,NSTPBP5185比阿司匹林具有更有效的抗血栓活性和更少的副作用[29],NSTPBP5185也有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30],由于NSTPBP5185具有抗血栓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特性,因此新型血栓烷受体拮抗剂NSTPBP5185是脑血栓二级预防的一个很好的候选者。
4 展 望
TXA2在脑血栓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与脑血栓形成的发生及发展密切相关,进一步深入研究环氧合酶、血栓烷合成酶及血栓烷受体的遗传特征及人群差异,研发针对性强的新的靶点药物,提高脑血栓的精准防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