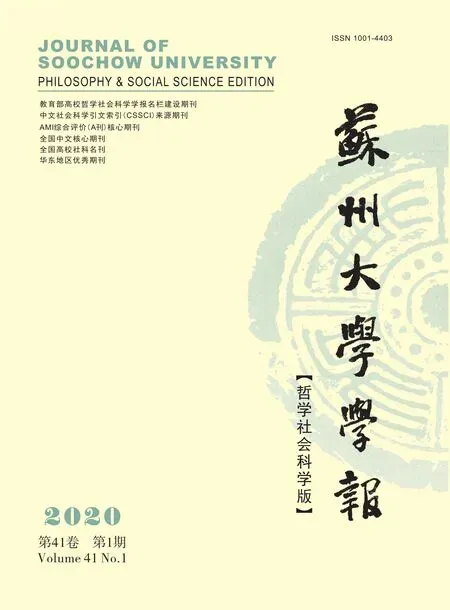荀子的“乱世之征”及其道德隐忧
关健英 郭士榕
(1.黑龙江大学 国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黑龙江大学 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汉代司马谈在谈到先秦诸子百家时指出,百家所言异路,但皆“务为治者也”。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治”,既指社会治理的方案,也包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及应然构想。思想史表明,对时代道德状况的关注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不可或缺的思考主题。作为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家,荀子揭示其所处时代的“乱世之征”,表达对于时代道德精神的关切与思考。
一
综观思想史,哲人的思考中总是充满对时代及其精神状况的深度关注,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思想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婴与晋国大夫叔向谈论时政,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季世”[1]1181。孟子在谈到春秋末期时也说这是一个“世衰道微”[2]272的时代。庄子将战国时期定义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3]1064的乱世。荀子敏锐地捕捉到战国末期的“乱世之征”,给后人留下窥见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风貌、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丰富的信息。在《乐论》篇的结尾,荀子根据其对战国末期的社会道德状况和精神症候的理解,对其所处时代冠之以“乱世”,并总结出“乱世之征”:
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襍,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4]385
汉儒孔安国释“组”为“绶”,马融解为“文”。王先谦《荀子集解》认为:“服组,谓华侈。”“襍”为“杂”的异体字,段玉裁引申为“参错之称”[5]399,意谓错乱。王先谦释“险”为“衺”,释“匿”为“慝”,“衺”与“慝”均谓邪恶不正。“瘠墨”,指先秦墨家主张节葬,以俭薄为道。荀子在这段话中,描述了战国之末的服饰、妆容、音乐、人们行为、社会风气等方面的特征。乱世中,人们服饰奢华,容色、气质趋向女性化,社会风气放荡堕落。人们普遍看重物质利益,行为放纵混乱。乱世里,音乐怪诞而失谐,文章浮华而不正。人们沉溺于物质享乐,对待逝者却俭薄失敬。这是一个轻视道德而看重勇力的时代,人们贫则为盗,富则为贼。
在荀子的笔下,这是一个浊世、乱世、末世,是世风浇薄、社会失序、道德沦丧的时代。荀子从战国时期的道德实然出发,揭示出乱世人人求利、人人争利的情形,“其志利”[4]385,“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4]296,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与孟子观点截然相反的性恶论。他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4]412,人性是人与生俱来、原生态的自然属性,生而所有,禹桀所同,无待而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4]434,人人皆有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佚、生而好利的自然本性,而这种原生态的本性是恶的。荀子认为,对利益的追求是普遍的人性,也是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他论学论治,皆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以性恶为始,以礼为宗,王霸并重,义利兼顾。他兼容法家思想元素,表现出与孔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扞格不入,其阵营归属也因之成为后世儒家内部的讨论话题。自韩愈《读荀》之后,关于荀子思想“大醇而小疵”几成定论,更有宋儒指摘其思想“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2]198。关于宋儒对荀子性恶论的批评,王先谦认为:“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荀子并非不知人性有善有恶,他之所以把求利、争夺看作是人的普遍本性并将人性定性为恶,乃是“感激而出”[4]1,是对乱世中人们趋利本性的深刻揭示,是对乱世道德有感而发的激愤之辞。
荀子年五十游学于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后适楚为兰陵令,终老兰陵。他生活在战国之末,其生卒年不可确考。史家一般认为,荀子出生在秦统一前一百年左右,他去世后十几年秦统一六国。荀子的时代正是最为动荡无序、疯狂逐利的战国“乱世”。荀子一生著述数万言,以此表达对乱世的激愤以及他的制度构想和道德愿景。正因如此,司马迁说他“嫉浊世之政”[6]1842,王先谦也认为,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4]1,其思想观点是对时代道德状况的有感而发。荀子所说的“乱世之征”,不仅是他生活的战国末期几十年社会道德的反映,也是春秋战国几百年中,中国古代社会最为频繁、最为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的道德状况的缩影。
二
思想家笔下春秋战国“乱世”可谓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变局。“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7]723-724《诗经》对当时自然界发生天崩地陷的自然现象的描写,何尝不是春秋时期社会沧桑巨变的写照。在宗法体系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1]1237。随着宗法制崩坏,民闻公室之命,如逃寇仇,公室式微,民无所依,一派“季世”景象。如晋国叔向所言:“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益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奕、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1]1183-1184。按照孟子的说法,在“世衰道微”的春秋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2]272。在齐国,权力洗牌,田氏代齐呼之欲出,社会亦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的动荡乱世。司马迁认为,在春秋的200多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究其所以,“皆失其本已”[6]2492,一个失序的、人伦纲纪缺失的社会必定篡弑横行,天下大乱。“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7]1258,伴随着旧贵族的哀鸣,新的社会阶层在崛起,谋杀篡位史不绝书,利益整合从未间断。
时至战国,连年征战愈发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加之城市发展,工商业逐渐发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私欲,社会贪利争夺之风盛行,礼义轻如草芥。孟子从儒家德治思想出发,设想建立人们之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2]256的和谐关系,但这种道德理想,在战国时代只能是方枘圆凿的迂阔之论。
据史记载,战国时期人们普遍不避法禁,人际关系恶化。日中为盗,甚至杀人越货的行为并不鲜见。基本的人伦关系遭致破坏,子有杀父,臣有弑君,兄弟争钱财,交友以求利。人们行为的动因是利益驱动,而不是仁义道德,“民之于利甚勤”[3]771,“其实皆为财用耳”[6]2473。人的贪利之心日盛,社会的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利”甚至侵蚀家庭伦理关系。《史记》和《战国策》均记载了纵横家苏秦发迹之前落魄还乡的遭遇,形象地描绘了功利之风对人伦亲情的影响,“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汉初思想家贾谊在总结秦亡教训时,指出当时社会道德所遭受的毁灭性破坏:父子分家之后,儿子向父亲借锄头农具,要看父亲的脸色;母亲借儿子家的碗瓢扫帚,也要听冷言冷语。翁媳之间毫无礼数,媳妇给孩子哺乳,毫不避讳公公;婆媳关系紧张,争吵不休。贾谊认为,商鞅变法后,“嗜利”之风充斥社会,在逐利之心的驱使下,即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要进行经济成本核算。家庭伦理关系受到侵蚀,人伦失范,几同于禽兽,乃至秦俗日败,“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亦不同禽兽僅焉耳”[8]97。家庭伦理关系尚且如此,社会道德之沦丧程度可想而知,“贾生此言,可以代表战国之民德矣”[9]37。
孟子曾形象地刻画了“齐人”为了富贵利达而毫无底线、寡廉鲜耻的“餍足之道”:他流连于坟场,乞食祭品。酒足饭饱后,又以成功者的姿态骄于世人。孟子认为,像齐人这样的寡廉鲜耻之徒在生活中比比皆是。“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2]301那些功成名就、富贵利达的人,和乞食于坟场的齐人没什么两样。他们行为下作,不择手段地攫取利益。他们令妻妾蒙羞,令世人不齿。他们为了名利富贵,毫无廉耻之心,行为丑陋令人瞠目。汉代的赵岐说,这些人“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骄人于白日”[2]301,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社会道德之沦丧可见一斑。
三
人伦道德和社会精神风貌作为社会的观念层面,是被当时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不是人伦道德决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而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时代的变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乱世”“季世”预示着一个旧时代即将终结,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社会在新旧交替之际表现出人伦阵痛,是社会变革如影随形的道德代价,也必然在阵痛中生长出适应新的时代的道德观念,也由此引发了思想家们的道德隐忧。
第一,“利”的合理性及其隐忧。“利”字在先秦古籍出现很早。《说文》曰:“利,銛也,刀和然后利,从刀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是一个会意字,从刀从禾,本义是庄稼成熟用工具收割,而有所获即“利”。从事稼穑有所收获,是人们在生产中获得的经验认识,有付出就有收获,这是人们对“利”的初始认识,主要指物质利益。据此基本含义,人们对“利”的认识逐渐深入:“利”从何而来?如何才能得“利”?如何看待自己的“利”与他人的“利”?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在这些思考中,人们逐渐萌生出关于“利”的伦理思考。
中国古人认为,“利”是天之德的体现,“利”本身不具有善恶评价的意味。但如何对待“利”,以何种手段获取“利”,则关涉道德。评价的标准看“利”是否合“义”。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概念,其基本含义为“宜”,意谓“应该”。《易》认为,天生万物,必使万物各得其宜,这是天对万物之利,君子应该法天而行,在获得利益的过程中,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天道得以体现,使自己与他人各得其所,各得其宜,《易》认为这是君子之德,此即“利者义之和也”[10]12。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辩证思维和道德智慧的观点。但是,在社会转型、利益矛盾突出的年代,“利者义之和”更多的是具有应然的性质,而不是社会道德状况的实然。
魏惠王三十五年,魏惠王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者,孟子来到大梁觐见魏惠王。(1)魏惠王,即魏侯罃。战国时期的魏国都大梁,故魏国亦称梁国,魏惠王即梁惠王。孟子的时代各诸侯国已经称“王”而不称“侯”。梁惠王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2]201梁惠王所言之“利”,主要不是他个人的私利,而是魏国的利益,“盖富国强兵之类”[2]201。梁惠王开门见山而问“利”,“言利”是事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大事,堂而皇之。而孟子,则以一句“王何必言利”,表达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重义轻利的价值立场。在充满功利精神的战国时期,孟子的“何必言利”毫无疑问是迂阔之论。几百年后,司马迁在为孟子做传的时候,即以此事开篇: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獘何以异哉![6]1839
笔者认为,令司马迁废书而叹的不是“利”本身,而是先秦社会人们对于“利”的看法。民从利之心,如水之走下,不可壅塞。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承认对合乎“义”之“利”追求,具有正当合理性。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人人“利”字当头,人人以利益为行为准则、评价准则,如果一个统治者开言即“利”,所有的治理举措都建立在“利”的基础上,那么这个社会无疑潜伏着危险。正因如此,司马迁以一个史家的洞察力,认为子罕言利,乃是从“原”的角度防患于未然。正是因为“利”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人言利,孔子“罕言利”,正是补偏救弊之举。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此之时,贪利争利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大潮,“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4]296。基于此,荀子认为,义与利,是每个人的“两有”。人人既有“好义”之心,也有“欲利”之心。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不能消灭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不要压制人们对道德的渴望,要在民之“欲利”和“好义”的两者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但总的说来应该是“义胜利”,而不是“利胜义”,“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4]502。战国末期的社会大势,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逐利之心,荀子提出的“义利两有”,兼容当时大行其道的功利观点,是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变迁的反映。
第二,“变”的观念与个人机遇。世事变易、革故鼎新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之一。先秦各家均承认“变”,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基本的事实存在。但如何看待和应对时代之变和社会之变,各家看法则不同。儒家主张“法先王”,言必称三代。荀子作为先秦思想集大成者,虽也以“先王之道”作为社会制度设计和道德构想的基本范本,但其思想总体而言,与先秦法家一致,是“法后王”的政治主张。韩非认为,“当今之世”不是有巢氏和燧人氏的“上古之世”,不是夏禹的“中古之世”,也不是商汤周武的“近古之世”。“以先王之政,治当今之民”,如同守株待兔的宋人一样可笑。韩非子认为,时代在发展,古今异俗,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1]5。
战国时期,魏文侯任用李悝,创平籴法。秦商鞅立木取信,奖励耕战。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是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实践。“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6]1765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在法律方面主要是实行连坐制度,鼓励告密者;在政治体系方面取消贵族世袭爵禄,没有军功者不能属籍贵族。商鞅变法总体精神是论功行赏,贵族与平民一视同仁。据史记载,在法令颁布前,秦国有不同意见,大臣干龙、杜挚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但商鞅认为,百姓安于旧俗,学者囿于所闻,“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秦孝公支持商鞅,新法颁行。新法行之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6]1766。可以说,先秦关于变与不变、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理论争论,积极变法的国家因“变”而强,因“不变”而衰亡的政治实践,对这个理论之争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此即汉人所言,“不变法而亡”,“不相袭而生”。[12]427因此,社会之“变”的事实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变”是先秦时代的主流观念。
对于个人而言,变动的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战国时,秦军主将白起率军大胜赵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商议合纵大计。平原君在他所养的门客中,要挑选二十个文武全才,和他一起前往楚国。经过仔细挑选,最后还缺一个人。平素里默默无闻的门客毛遂,自荐愿往,“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6]1856。这个变幻的时代给了太多锥处囊中的人以上位的机会,抓住机遇,就可脱颖而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养了很多门客,其中两人因没有军功而被大家瞧不起,众人皆羞与之同列。后孟尝君出使秦国,被秦昭王扣押。两个门客其中一人会“狗盗”之术,另一个人擅模仿“鸡鸣”。正是这两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孟尝君脱险,两个“鸡鸣狗盗”之徒从此出人头地。始自西周的分封诸侯、沿袭几百年的世卿世禄制度,在战国时期发生遽变。“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13]24位列公卿的贵族可能沦为阶下之囚,布衣平民可能发达晋身。变动不居的时代给了普通人“徒步而为相”“白身而为将”的选择可能和晋身机会。这类现象在战国时期比比皆是。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战国时期打破世侯世卿旧制,“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13]24。
第三,“不凝滞于物”的道德标准。世事之变,既有历史合理性的考量,也有价值合理性的评判。历史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者并不总是一致。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和道德现象,从历史发展的总的过程而言,是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总可以从时代大势中找到其所以然。而处在其中的人们,却在对这些社会现象价值合理性的追问中,展现了内心的道德冲突和时代忧思。
战国时,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屈原不肯随波逐流,被怀王疏远,后被流放。屈原痛恨奸佞,心系怀王,形容枯槁,披发行吟于江畔,“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表达了与奸佞、与世俗、与众人的不妥协。司马迁借渔父之口,展现了战国时代社会的主流观点:
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6]1936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身居浑浊乱世,一个人特立独行,保持自己的道德清白,是“凝滞于物”的迂腐之举。“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才是最佳生存之道。在他们看来,那些懂得并能够“不凝滞于物”的人,才是“圣人”。换句话说,与时俱变、与世推移、随波逐流,是战国时期流行的道德标准。
孟子与时人景春也曾就道德标准展开对话。景春推崇纵横家,“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孟子则不以为然,“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君子,才可称得上“大丈夫”。显然,孟子与景春关于何谓“大丈夫”,完全持不同的标准,应该说,景春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社会主流的评价标准。在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中,纵横家苏秦、公孙衍、张仪纵横捭阖,威震天下。苏秦、公孙衍主张“合纵”,苏秦曾经佩六国相印,公孙衍佩五国相印。张仪主张“连横”,游走于各国之间,亦是一时风头无两。纵横家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按照功利标准,他们是世人眼中的成功者,也是世人道德标杆下的“大丈夫”。而按照孟子的道德标准,这些纵横家阿谀权势,毫无个人操守,他们的行为乃“妾妇之道”[2]265,根本配不上“大丈夫”的称谓。
以荀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战国的“乱世之征”的揭示无疑是非常深刻的。那是一个逐利的时代,一个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6]2463对“利”的追求是人类活动的重要驱动力。与人们生生不息的逐利行为相伴,如何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规范人们逐利的行为,如何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如何处理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关系,则引发了哲人们的道德思考,成为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旧的利益格局被逐渐打破,新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时代,“利”如同一个巨大的魔咒,若水之趋下,令人乐此不疲,沉溺其中。在这样的时代中,与世推移,与时俱变,不凝滞于物,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成功者的选择。但同时这种选择所带来的道德冲突,令人纠结,也令人深思。在史家的笔下,给我们留下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重利尚利、随时而变的丰富的时代信息。如何处理好“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剧变的时代抓住机遇,如何与时偕行而不失操守,以荀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迄今仍给我们提供极为有益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