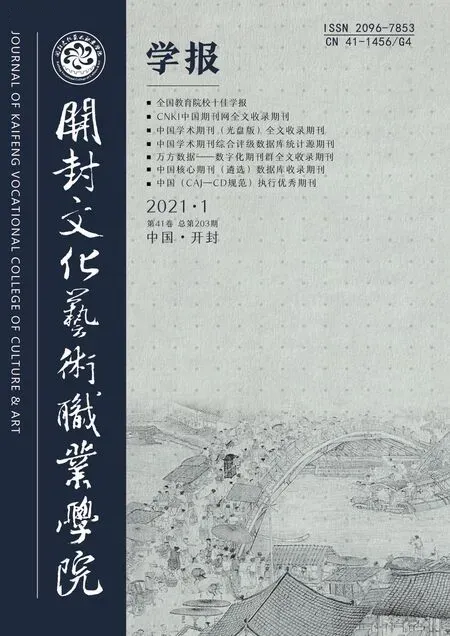葛亮小说的底层书写与叙事艺术研究
赵佳佳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1 世纪初期,底层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作家开始扎堆书写底层,虽然有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迟子建等名家的加入,但总体成就并不高。有论者指出,底层书写“不能仅仅为了满足人文关怀的需要,而应该在一种平等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对于底层人性的思考,对底层生活状态进行政治的、伦理的剖析”[1],揭示一个美丑并现的真实的底层。而如何揭示,对于技巧的拿捏就显得极为关键。
葛亮是近年来华语文坛颇受注目的新生代作家,创作了较多书写底层的短篇。他小说中的底层世界以民间为背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他笔下的底层人物,以丰富性与真实性散发着人性光芒,这些便构成葛亮的“温情底层”。他曾说:“故事是我写小说的基石。没有故事,我就基本上不想写小说了。要讲好一个故事,这就是我基本的小说理念。”[2]由此可见,葛亮非常重视小说的叙事,深入文本内部,会发现葛亮的创作的确有着独具匠心的考量。
一、平等而真诚的叙事聚焦
叙事聚焦是指“表现被叙述情境与事件的视角;据此,感知或认知的立场得到表达”[3]。视角的选择关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叙事效果的成败,在具体叙述时,葛亮选取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即儿童视角。儿童特有的单纯的思维方式使底层在他笔下不再是成人的道德评判或自带优越感的同情,“通过从成人到儿童的角色置换,以儿童的另一种眼光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从而打造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展现不易为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4]。葛亮巧妙地选取儿童视角观察成人生活,以此来体现跨越阶级的平等的写作姿态,再现真实底层。
葛亮底层书写的叙事者多由毛果充当,以旁观者姿态在平淡生活中打量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见证岁月的变迁,各个人物和故事在历史的画卷中缓缓铺开。《洪才》中以毛果的视角呈现了洪才一家的生存处境。在他眼里,洪才像“盖世英雄”,婆婆是“令人崇拜的人”,姐姐的美是“没有烟火气息的”。洪才家的小院落被葛亮赋予新的意境,犹如世外桃源,底层的生存环境被赋予一种诗意的美感。《泥人尹》《于叔叔传》同样是来源于毛果的儿时记忆,人情世故的演绎,毛果是不懂的,他只负责整理这些记忆却不加点评,但通过成人们的评议,伦理善恶自然流露。
另外,葛亮在叙事时还引入了成长视角。《阿霞》中,毛果这个大学生展现出初接触社会微妙而复杂的心思,这种心思既包含学生时代的羞涩与单纯,又有故作老练的成熟。在与阿霞的相处中,毛果也在不断审视自己、解剖自己。《阿德与史蒂夫》描写了毛果初到香港学习的经历,其置身于另一种社会环境,接触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偷渡客,虽然两人差距甚远,却因偶然的机会结为好友,因此能近距离感受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虽然随着毛果的成长,书写视角也逐渐由儿童转变为成人,但这种成长更多是生理上的,学生特有的单纯善良也与儿童视角的选择初衷一致,所以这种转变并不影响葛亮的写作立场,反而使葛亮的底层书写更富于动态与张力。
葛亮以“内在聚焦”切入底层叙事,以毛果这位能亲眼见证与倾听他人转述的见证人视角,塑造了一批丰满的底层人物,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复杂、真实、美丑并现的底层。同时,毛果的活动也与周围环境、人物构成了潜在的映衬、矛盾与对话关系,无疑加大了作者表现主题与人物的力度,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二、深情而矜持的叙事距离
故事是被讲述出来的还是被再现出来的?[5]葛亮的底层书写由“再现”与“讲述”共同完成,这几乎构成了他固定的叙事模式。《阿霞》中的故事情节以毛果在餐厅社会实践展开,跟随毛果的脚步,主人公阿霞进入读者的视线。在相处中,阿霞的奇特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作者在“再现”中埋下足够多的悬念,只待一个导火索引燃。这个导火索便是阿霞与客人的争执,由此引出阿霞的身世与经历,由旁人讲述出来。“再现”不仅将阿霞投放至“我”的视线中,而且将“我”置于大众的审视之下,并对“我”所代表的精英阶层进行审视与质问。“讲述”又将“我”与底层群体的距离拉大了,不同阶层的隔阂终究难以相容。在葛亮的其他小说里也能找到这种写法。例如,《泥人尹》由一只尘封多年的泥老虎引发毛果对尹师傅的回忆,再现了尹师傅的“今生”。而尹师傅传奇的出身与经历,同样由旁人讲述出来。寡淡的生活与传奇的经历之间,形成了可资玩味的张力。除此之外,还有《于叔叔传》,此处不再赘述。
葛亮在《七声·序》中写道:“因为时代的缘故,这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太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6]从这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作者对世上缺少传奇与神话的遗憾。在与张悦然就小说叙述立场的谈话中,葛亮说道:“小说归根到底,还是对生活的提炼,无法等同于生活本身。也就是说,适当的‘戏剧性’仍然是小说中可取的元素。”[7]所以,怎样把日常的部分变成传奇,成为葛亮的一个写作追求。由此,我们就能理解葛亮为何要在“再现”与“讲述”之间转换。日常的,归于“再现”;戏剧的,归于“讲述”。转换之间,作者饱含深情而又彰显矜持,这种若即若离的美感赋予作品极大的张力,也使故事更具真实性和艺术美感。
三、复合而舒缓的叙事时间
小说的叙事以时间为存在条件,当文本的叙述时序与故事的事实序列不一致时,称为逆时序叙述,倒叙与插叙是两种主要的逆时序叙述方式。葛亮用顺序、倒叙、插叙相结合的复合叙述方式展开他的底层书写,采用线性时间与插叙相结合的时间模式。小说的整体样貌仍遵循基本的线性故事时序,插叙的使用打破了线性的故事时序。作者并非有意玩弄创作技巧,而是为故事的叙述服务。
由于叙事视角的叙述限制,作者没有办法以“上帝视角”进入人物内心,于是用插叙处理这些叙述者无法直接得知的内容,这样的叙述方式打破了时空的局限性,沟通了过去和现在,延长了事实上的故事时间,使得故事的叙述完整而真实,也形成了叙事节奏上的美感。例如,《泥人尹》中尹师傅的身世与经历、《阿霞》中阿霞砍伤安姐丈夫的经过、《于叔叔传》中献阳的死、《阿德与史蒂夫》中阿德与曲曲的过往等,这些内容都是由故事中人物回忆插叙进来的,使主要故事暂时性中断的同时,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丰满。一个人的性格与其经历及所处环境密切相关,性格决定人生,插叙的巧妙运用,为人物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依据,也为故事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另外,文本中偶尔穿插着对感觉世界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对故事时间的推进也起到了暂时的延宕效果,同时将底层世界的别种风貌呈现出来,作者的温情自然流淌于笔尖。从作者对洪才家菜园子“世外桃源”般的勾勒,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样的美景,却在城市化的挤压下最终毁于一旦。这些内容的插入没有让读者感觉到生硬,也没有破坏故事的流畅性,减缓了叙事节奏,增添了讲述与倾听的趣味。此外,葛亮对故事的线性时间进行了碎片化处理,不是刻意营造陌生化的艺术氛围,而是为了配合他选取的叙述视角及回忆模式。由于记忆本身的碎片化,故事的展开也呈现出一个个叙事片段,在线性的故事时间轴上以散点的形式铺开,看似零散混乱,却构成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叙事结构框架。随着回忆涌出,一个清晰的底层世界也缓缓铺开,读者也随人物之乐而乐,随人物之悲而悲。倒叙与插叙的复合使用,使故事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穿梭,叙述更加真实动人,也使叙事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美感。伴随着回忆的模式,叙事节奏缓慢绵长、温情动人。
结语
葛亮的底层书写自有独特的风格,摒弃知识分子的高高在上,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深入底层书写当中。从叙事学角度切入,我们发现葛亮底层书写的诸多特色。葛亮选取了儿童成长的视角来书写,弱化道德批判,最大程度上再现真实;“再现”与“讲述”的叙述模式使作者保持深情而矜持的距离,审视的同时也在叩问自己的内心;在时间的处理上,他采用了复合而舒缓的时间模式,增添了叙述艺术的美感。葛亮对于技巧的拿捏细致到位,情感节制,不急不躁,温情呈现,所以底层世界在葛亮笔下才会是另一种感觉,一种只属于葛亮自己的感觉。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