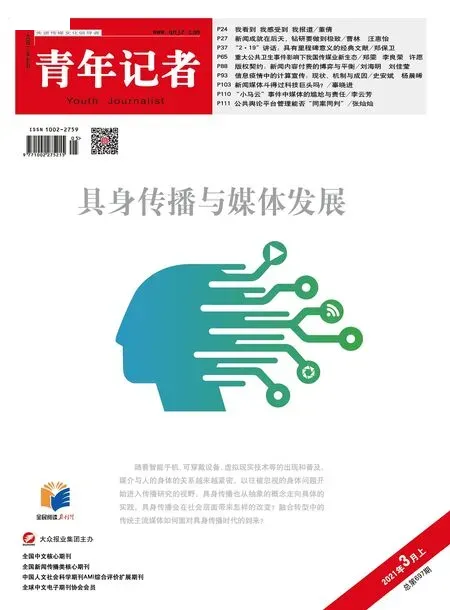智能时代人机关系问题研究的现状与进路
● 赵树金 侯瑞华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再次印证了全球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从未像今天一样被无处不在的媒介技术所包围。在国内,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迅速开展流行病学溯源调查,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应急联动机制的一面镜子。处于后疫情时代的我们,有必要从身体出发,重新思考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机关系问题。
从身体出发:思想溯源与研究现状
1.人机关系问题研究的思想溯源。关于人机关系问题的探讨,其理论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长期以来,在宗教神学的束缚之下,人的身体始终被置于一种被抛弃、被漠视和被否定的尴尬境地,人的主体性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认为人的灵魂与身体一直都是二元分化的存在。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主张“我思故我在”,重新确立“身心二分法”的思想理念。直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率先将身体从理性的压制中解脱出来,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身体即是认识的起点,明确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从古代本体论哲学思维到近代认识论、方法论哲学思维的转变,彰显了拥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身体之外客观之物的辩证发展关系。
德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视角出发,详述了物质的“上手性”与“在手性”问题,为研究人机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从现象学层面入手进一步强调“肉身本体论”,即身体是我们所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与梅洛-庞蒂不同,媒介考古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则主张要“注重硬件基础”,从传统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出发,思考了媒介技术如何重塑了人的本身。1985年,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发表了《赛博格宣言》一文,率先打破人与物质世界的自然界限,成为探究智能时代人机关系发展走向的重要思想理念。上世纪90年代,约翰·彼得斯开始重新关注人的身体地位不断下降和后退性问题,高度强调“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研究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问题具有启发性意义。更具代表性的是,以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加拿大媒介环境学者全面考察了媒介技术对人的感知觉方式产生的诸多影响,为研究新时期人机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理路。
2.人机关系问题研究的现状分析。近年来,由于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等新型媒介技术的出现,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受到挑战,引发了学界关于人机关系问题走向的相关讨论。笔者以“人机关系”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截至2021年1月20日,共检索到417篇中文文献,其中最早关于人机关系的探讨是欧阳文道发表于1983年的一篇译作——《发展中的人—机关系》,原作者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科学信息传播学者Bernard Dixon,文章敏感地意识到微电子革命发生以来,人与媒介技术关系之间发生的微妙变化,技术“既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使得我们的生活内容更加贫乏”[1]。1995年,国内学者周镇宏撰写的《人机关系新难题——高科技“副效应”警示录》与前文译作观点较为一致,集中关注了机器对人的异化问题以及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问题。2016年以后,学界围绕身体的缺席与回归问题展开了探讨。
目前,学界关于人机关系问题的探讨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其一,强调回到身体本身,相对于媒介技术、物质机器而言,主张身体传播的重要性。刘海龙(2019)从知觉现象学层面探讨了虚拟现实与身体传播的逻辑关系,强调了身体在物质信息流动中的核心地位。喻国明、郭小安、刘涛等则从媒介技术理论、修辞学、符号学、叙事学视角探讨了“作为抗争媒介的身体”如何在媒介技术变革中实现权利话语表征意涵的传达。其二,从媒介物质性、媒介技术哲学维度入手,批判性地考察人与媒介技术的本体性问题。如蒋晓丽(2018)重新挖掘海德格尔的媒介技术哲学思想,全面审视了智能环境下“人-技”之间“互构”与“互驯”的融合关系;章戈浩、张磊(2019)亦从本体论观点出发讨论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其三,以超前的未来主义视角切入,论证后人类主义时代强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伴生的新型人机关系与社会秩序重构问题,代表学者有骆正林、杨一铎等。
智能时代人机关系问题研究的不足
1.关注现象层面梳理,学理范式有待深入。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关于人机关系问题的探讨切入点虽不尽相同,但最终旨归较为一致,即落脚于为新的媒介技术给人带来的种种不适应性出谋划策,其中不少研究侧重现象层面的概念梳理,如对西方已有传播概念的本土化阐释、重要性以及某一现存问题的可行路径探索或集中于对相关传媒制度、政策层面的解读分析,看似较多的对策应用类研究似乎又缺乏真正的实际效益与学理创新。
2.侧重单一学科视角,交叉学科研究不足。当前,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中国传播学正面临一定的学科边缘化危机,尤其是关于媒介技术层面的人机关系问题探讨,如果依然停留在对西方学者理论思想的简单爬梳以及局限于单一的新闻传播学科领域,显然已无法适应我国智能媒体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亦有将传播学科边缘化、内卷化的危机。目前,我国虽有不少传播学者已注意到该问题在科学研究层面呈现出的张力不足问题,但仍然很难做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共融,如与哲学、社会学、信息技术、心理学、生物学、管理学等学科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互动。
3.研究方法略有局限,仍需不断丰富完善。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关于人机关系问题的学理探讨成果比较丰富,其中定性研究占很大比例,定量研究还需进一步规范与完善,尤其要关注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同时,应适时增加民族志研究法、深度访谈法、焦点小组法、实地观察法等,重点关注媒介技术在受众心理层面、认知层面、人际交往层面、生理需求层面等的适应性行为研究。如学者周逵(2018)使用参与式观察法,同时对若干组90后大学生群体进行了焦点小组式的深度访谈研究,探究了虚拟现实技术给人的感官系统带来的沉浸式体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智能时代人机关系问题研究的进路
1.当前人机关系问题研究的两种进路。当前,关于人机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路总体呈现两种倾向,一种研究路径从本体论维度出发,认为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但人的主体地位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如孙玮从存在现象学、媒介学、后人类、技术现象学等视角出发,认为智能化时代的“传播研究必得回归身体世界”[2],唯此才能从根本上建立传播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关联。杨保军、彭兰等在肯定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传统新闻生产方式、促进传播交流活动的同时,提醒公众要警惕将机器主体化等同于人类主体化的偏颇认识。而另一种研究路径则从认识论维度出发,强调随着人工智能、虚拟合成等技术的发展,机器之物将会越来越拥有相对的主体性,应将机器置于与人类身体平等的主体地位。喻国明(2020)认为在5G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与物质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可能会发生深层次变革,将涵盖人机同构、协同与共生三个维度,最终走向人机“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吴飞(2020)、蒋晓丽(2018)、程广云(2019)、艾志强(2020)等在相关论述中对人机协同的观点持认同态度。总体而言,两种研究路径并不矛盾,只是研究的切入点不尽相同。相对于前者的批判式思考,后者其实是站在一种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探究未来的新型“人—机”关系走向。
2.从“主奴”关系到主体间性对话的可能。奥地利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分为两重性,一是“我—它”的主客关系,即具有“主奴”性质的工具论;另一种是“我—你”互为主体性的对话性关系。当前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停留在对“人类思维的模拟阶段”[3],显然还不能挑战作为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人的主体地位,但若“不受控”的高级智能机器人出现,一定程度上会消解传统的“主奴”关系和人机工具论,进而打破自然人和智能机器人的界限,向具有人机平等和主体间性的新型“人—机”关系转变。
“未来永远待在幕后,从未找到历史的入口”[4],无论人机关系未来将会走向何处,我们都应时刻警醒,技术应为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类生活而存在,而不是将人带向幻象之外的“海市蜃楼”。总体而言,无论是当前的AI合成虚拟主播,还是3D全息虚拟歌姬的风靡,都实实在在革新着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社会公众休闲娱乐方式等,需要多学科领域研究者共同合作,努力探寻新时期智能技术对人的身体、社会文化、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的诸多革命性影响,进而揭示媒介技术作为社会肌理的重要表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