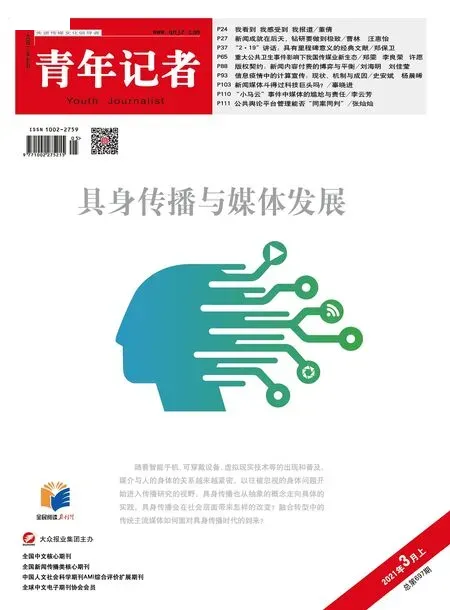3D+AI主播:伦理演进与价值引领
● 刘 霞 陈昌凤
2020年5月,新华社在全国两会启用了全球首个3D+AI合成主播“新小微”,它采用超写实3D数字人建模、多模态识别等技术,只需输入文本内容就能根据语义实时播报新闻,与前一代合成主播相比,3D数字内容的生成逼真度更高,一时间3D+AI主播是否取代真人主播的担忧再成热点。本文从历史溯源、伦理挑战与价值引领三个维度分析3D+AI主播对媒介生态的影响。
智能界面:3D+AI主播的历史溯源
3D+AI主播指在主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的智能平台上,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AI技术合成且由运动追踪设备实时驱动的AI主播。它伴随着人工智能“逻辑推理→概率推理→因果推理”这一发展脉络,经历了初创期、成长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发展阶段。
1.1956年—1959年:人工智能初创期。20世纪50年代英国数学家图灵《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提出的图灵准则与讨论可计算性的边界问题等,奠定了AI理论研究的起点。随着研究的深入,1956年“达特茅斯夏季人工智能研究会议”成为未来AI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克劳德·香农、马文·明斯基等十几位学者成为AI研究的代表人物。
2.1960年—2011年:人工智能成长期。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媒介生态变革。从1960年代符号推理系统至1980年代专家系统,AI演进在几十年间几次飞跃。1974年作为节点,之前7年启发式算法盛行,之后至1980年第一次跌入低谷;1980年后神经网络占主导,反向传播算法就出现在1986年。次年再跌低谷,直到2006年深度学习算法出现,才使得AI进入第三次发展浪潮。到本世纪初,AI推理以命题逻辑、谓词演算等知识表达、启发式搜索算法为代表(梅剑华,2018),摩尔定律以及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人们可以通过大量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来验证想法(张宏江,2020)。这一时期,AI稳步发展。
3.2012年至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期。2011年沃森夺冠、谷歌大脑的出现,助推2012年成为AI发展的重要节点,直到2016年机器人阿尔法狗(Alpha Go)基于符号逻辑算法,使用了蒙特卡洛树搜索技术和基于深度学习技术,战胜韩国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再引关注。在数据、算力与算法支持下,AI从2012年的知识图谱发展到2018年的认知图谱,研究的重心由感知智能逐步向认知智能过渡。业内AI专家普遍认为,认知图谱将成为认知智能技术突破的关键,未来让机器具备类似人的理解、逻辑与解释能力是AI发展的高级阶段。
技术演进:人工智能国内外应用实践与研究现状
2000年4月19日,虚拟主持人安娜诺娃因网上直播菲律宾飞机坠毁事件的新闻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虚拟主持人;中国最早的虚拟主持人是2001年5月天津电视台《科技周刊》节目中出现的比尔·邓,后改名字为“言东方”。随后,美国Vivian、中国阿拉娜、韩国露西雅,以及两年后中国西部博览会开幕式上推出的互动虚拟主持人“江灵儿”等相继出现。早期虚拟主持人功能相对简单,是非实时通过后台制作完成并通过电视播出的虚拟主持人,是虚拟现实、虚拟演播室和动画技术发展的结果。
2004年央视首位虚拟主持人小龙由于技术不够成熟,僵硬的外表使观众难以接受。而国外AI发展相对较快,从2011年机器人沃森在《危险边缘》节目中击败了两位真人选手,到2017年能识别人类62种人类表情的英国《早安英国》节目智能机器主持人Sophia;从2018年拥有AI对话系统的日本电视新闻主播埃丽卡,再到2019年拥有自由对话能力的美国索菲亚,在智能技术驱动下,AI技术从感知阶段逐步推进到认知阶段且呈加速发展态势。
与国外AI研究学者关注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等热度相比,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关注稍显不足。回溯国内AI主播研究进路大致有两种倾向:首先,从郑素侠《我们是否需要电视虚拟主持人》一文(2003.5)开始,“虚拟主持人可能会取代真人主持人”的讨论就未停歇。持质疑观点者认为AI主播只是一个电子影像的复制品,很难挑战人类主播的独特存在(周信达,2019);它是一种程序设定的虚拟反馈,其情绪和表达都更为程序化(孔令强,2019);人所拥有的经验、感觉和综合判断能力,是机器无法比拟的(童云,2019);与传统的播音员有明显差异,它们受自身技术特性的束缚,不具备二度创作的条件(邢梦莹、卢静);尽管新华社“AI合成主播”诞生即突破,但在不同情境中的认知互动有待加强(於春,2020)。
而另一声音则较为乐观:无论是互联网催生的虚拟主持人,还是AI技术催化的机器人主播,其现实意义都是巨大的(叶昌前,2018);AI主播通过强大的信息处理与分发能力直接进行新闻的生产和信息制造(张宗兰、赵然,2019);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机器更好地协同与服务人类(王丹;刘文燕;唐林;何强;2019)。当然,技术并非二元对立这么简单,持技术价值中立者不在少数。基于此我们认为,3D+AI主播作为智能机器内容生产的“传播者”,是多元主体传播中的重要主体,是智能平台“采编流程智能化”算法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技术赋能下媒介深度融合的可视化符号。它作为智能新闻生产平台媒体的“智能界面”,是智能采集、用户识别等智能技术内容生产的一套智能系统,未来随着“人工情感交互系统”的构建与进化,它将成为集“采、写、编、播”为一体的“超级主播”。
3D+AI主播面临的伦理挑战与价值引领
技术和技术发展的中心要素是人造物本身。人造物既是手段,也是技术目的。[1]如何更好地探索一种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协同并进之路?怎样为3D+AI主播植入正确的价值观?这些问题是AI主播面临的伦理挑战。
1.人工情感:3D+AI主播面临的伦理挑战。情感智能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工情感”的研究可以使AI主播及智能机器人的视觉形象更人性化。“人工情感”是指以人类学、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为理论基础,利用信息科学手段对人类情感过程进行模拟、识别和理解,使机器能够产生类人情感,并与人类进行自然和谐的人机交互的研究领域[2]。这一概念诠释了AI情感研究的重要方向以及未来在科学与人文交融更高平台上的新进路,它是涉及脑科学、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多技术融合研究的一门新型交叉学科。
3D+AI主播作为“人机交互智能界面”就是一种人工情感引擎驱动情绪行为的“人机交互”智能系统,外形更拟人化,更符合受众视觉愉悦的审美需求。尽管“新小微”已逼近真人主持人的状态,但远未达到真人状态。从媒介生产实践看,人工情感技术的发展还相对缓慢,无法自主完成对编辑所提供稿件的深度解读以及自如“对话”能力,AI主播“人工情感”系统构建、人机“共情”、人机传播与AI视觉感知的维度与限度均面临诸多挑战,“远未能达到自组织、自适应、自涌现的高级心智,与人类智慧程度的自主采写、编评、播报相去甚远”[3]。
由于机器缺乏人类情感“品质”和有意识的情感体验,目前仍处于弱人工智能初级阶段。因此,怎样构建“人机交互”情感认同与人机传播机制,情绪对情感的影响价值如何,这些是AI研究的重点。
2.算法偏见:3D+AI主播价值引领与伦理演进。“技术不可能独立于伦理的态势获得发展,伦理是前沿科技发展的框架与底线,伦理的反思和引导需要一直贯穿技术发展的始终。”[4]算法绝对不是完美的,它的漏洞与算法工程师的价值观、算法偏见紧密相关。对于算法偏见也可理解为“技术偏见”,除了算法工程师本身的技术水平包括从中提取数据库的技术限制、存储与处理能力、代码错误影响外,“技术偏见”主要来源于“个人”或“组织机构”对算法系统设计的前期设想与规划。实际上,“算法偏见”在算法编写时就已植入算法程序,在差序格局作用下,算法设计者自身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算法程序的设定规则,算法操作中“算法黑箱”漏洞的产生、“算法偏见”与价值观引入等应引起高度重视。
降低“算法偏见”应从降低“技术偏见”和确立“技术责任规范”“价值规范”入手,通过“责任理论”系统构建来体现智能技术在媒介实践中的责任担当。以人为本明确算法工程师、新闻从业者、社会管理者的责任与价值观才是根本。因此,我们认为,技术主体的伦理行为必须受技术主体自身的伦理意识、伦理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的约束与支配,实行“技术主体问责制”将伦理规范、价值体系内化为技术主体的自律与行为标尺,未来“人造物”的不可控风险才会降低。
总之,3D+AI主播只是一种传播工具和载体,附着于媒介之上的传播以及传播背后所追求的人与人交流的传播秩序才是媒介传播的真正意义。算法训练与算法价值观怎样引入“3D+AI主播”的表达系统?如何进行专业化规训与驯化?如何做到算法向善?这些方面的思考将有助于完善算法人性化、透明化、公开化、问责化并推进算法向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