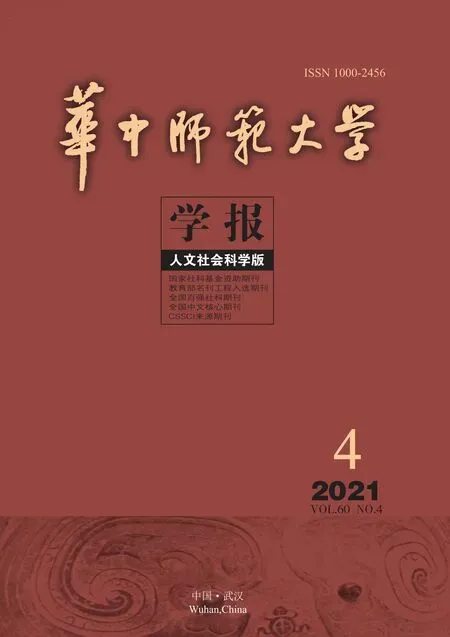论契丹文学的二元同构
和 谈 郭佳楠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契丹人曾经建立强大的辽朝,创制契丹文字,留存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契丹人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形成独特的契丹文学。契丹文学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关注和研究。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辽代文学及其重要作家进行评论,可算是较早关注契丹文学的学者。与赵翼同时的周春辑有《辽诗话》,搜集辽代诗作及相关记载,可算是第一部辽代诗歌集。其后有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与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其中涉及耶律氏文学的议论,颇多独到之处。“同光体”代表作家陈衍于20世纪30年代编辽金元诗纪事,对此领域研究亦有贡献。此后关于契丹文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辽金元文学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著作主要有张晶的《辽金诗史》《辽金元诗歌史论》,黄震云的《辽代文史新论》《辽代文学史》等;论文有祝注先的《辽代契丹族的诗人和诗作》、张晶的《论辽代契丹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别廷锋的《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花兴的《辽代契丹族文学研究述评》等。但契丹人并非随辽朝灭亡而灭亡,契丹文学也并非仅限于辽朝,其发展的顶峰乃是在元代,故而有必要打破朝代的局限,从文学本体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以便整体把握契丹文学的特征。
契丹文学从发源到成熟,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期。契丹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集中地表现出二元同构特征。当然,这是就其总体特征而言,并非绝对,如果具体到某些作家个体或个别作品,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的状态——随着契丹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种二元同构特征也就随之消失,呈现出多元一体的融合趋势,成为中华文化、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契丹文学二元同构特征的社会文化根源
这种二元同构特征,并非无端生出,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与契丹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形态有密切关系。一旦契丹人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建立自己的政权,逐渐强大,并迅速向外扩展地盘,他们就意识到,全面接受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制度,是一条捷径。就文学而言,中原农耕社会,稳定自足,重礼尚文,内敛守成,居处有常,安土重迁,利于文化之传承,故数千年来文字未有大变,而文献代代累积。庠序之学,先为贵族所享,私塾之设,则下于庶民百姓,教育渐开风气,无贵无贱,无长无少,咸得就而学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修饰其辞,以立其诚——故文学渐兴。先以《诗》播之,后以《骚》讽之,文人赋诗作文,言志抒情,酬唱赠答,自汉代至魏晋而渐渐自觉。翻译佛经,而四声完备,至晋宋齐梁始多属意声律技巧,文学之士,得为专门。文学发展至唐,则有诗歌之高峰,传奇之小说,词作之渐兴。这种积累与发展,随之而起的辽朝,是无法与之比拟的。
但是,另一方面,契丹人在建立强大政权、显示强悍军事实力的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与文学的缺失,从而催生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种民族自尊和自信,使得他们表现出兼取两种文化的二元状态。这种二元状态,表现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诸多方面。
首先是形成以语言文字二元化为主的体制。人们日常的交往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文字进行沟通。由于辽朝以契丹人和汉人居多,兼有其他民族,使用哪种语言文字作为通用语,是摆在契丹统治者面前的一个大问题。白寿彝在阅读大量材料之后得出结论说:“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①毫无疑问,双语并行的做法符合实际需要,也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当然,除了汉语和契丹语之外,辽朝治下的女真、回纥等民族也都有自己的语言,更全面地说,辽朝的语言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性特征,而以官方规定与社会约定俗成的二元制为主。就文字方面来说,则施行汉字和契丹字并行的双轨制。
与此相应,由于书写姓名、树立墓碑、登记户口、缴纳赋税、接受教育、官职升迁等需要,契丹人名最初也有两套系统,一是契丹小字,二是汉式的名和字。如辽太祖“小字啜里只”,汉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②;太宗“小字尧骨”,汉名“德光”,“字德谨”③;部分汉人亦有小字,如陈昭衮,小字王九④;韩制心,小字可汗奴⑤,这大约是汉人生活在契丹人聚居区,也同时学习使用契丹语的缘故。契丹人的名字,到后来逐渐变为只有名和字(或小字),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汉语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名字太多容易混乱,且不易记忆,故而删繁就简,与汉人名字趋于一致。
其次是实行政治经济体制的二元化。契丹立朝之初,由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观念制度的隔阂,虽然在同一朝堂之上,契丹官员与汉人官员往往无法有效沟通,契丹官员与汉人官员各站一排,各成一派,彼此语言交流还需要有人翻译,皇帝的诏敕大约需要分别用两种文字向契丹和汉人官员宣告一遍,故辽代职官中有译官、译史。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南北面官制,就势在必行,所以“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⑥。但这种二元化体制并非截然分开,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则有逐渐融合的趋势。在实际任职中,一些契丹人也任南面官,少数被信任的汉人也有被任命为北面官的情况。在经济生活方面,则是农耕与游牧同时并存。
再次是姓氏的二元化。契丹姓氏只有两个,一为耶律,一为萧。这在中国史上可谓独一无二。蔡美彪撰文认为:“辽代契丹人只见耶律与萧两大姓氏,为历代王朝所未有,也是中国各民族史所仅见。”⑦这也是契丹二元结构文化特征的表现之一。从契丹最早的族源神话开始,就只有男女二人,只有青牛白马,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契丹的社会和文化。当然,从世界各民族文化来看,都有这种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如亚当和夏娃、宙斯与赫拉、伏羲和女娲等,这与追寻人类起源的思想有关。《辽史·后妃传》有种说法:“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⑧从政治体制上看,皇族始终为耶律氏,后族(国舅帐)则基本上把持着相位,倒是符合《辽史·后妃传》的说法。这种二元姓氏体制,终辽一朝,未有改变。对此,也有官员提出改革建议,如耶律庶箴,曾上表请求增加姓氏,其文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⑨但辽道宗认为旧制不可改,未予采纳。至金朝,尽管契丹人有被赐女真姓氏者,也有为避战乱而改汉姓者,甚至金朝中后期契丹姓氏被强制改为移剌和石抹,但总体上仍保持二姓并列的状态。元朝时,有部分契丹人回改移剌为耶律、石抹为萧,也有沿袭而不改者,又有改汉姓、蒙古姓者,遂逐渐淆乱。
最后是崇文尚武并行不废。尽管辽朝建立五京,宫室形制一如中原,教育科举逐渐完备,但契丹人尚武游猎的习俗一直保持,皇帝与大臣春夏秋冬都要进行游猎,至辽朝灭亡,崇文尚武两种生活方式都一直并存。就契丹作家个人情况来看,基本上既能写诗作文,又能带兵杀伐,可谓文武双全,这与多数汉人作家颇为不同。契丹皇帝自不用说,大臣也多数文武兼备,甚至有很多女性兼习骑射。翻开《辽史》,这种例子随处可见。如耶律庶箴,“善属文。重熙中,为本族将军”⑩。耶律庶箴之子耶律蒲鲁,“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寻命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帝嘉赏,顾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鲁奏曰:‘臣自蒙义方,兼习骑射,在流辈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会从猎,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萧蒲奴“幼孤贫,佣于医家,牧牛伤人稼,数遭笞辱。医者尝见蒲奴熟寐,有蛇绕身,异之。教以读书,聪敏嗜学。不数年,涉猎经史,习骑射。既冠,意气豪迈”。契丹本重游猎,女性多习骑射,多能从军征战,翻检《辽史·后妃传》,其中既长于射御田猎、又通文墨者,有述律平(太祖皇后)、萧绰(景宗皇后,小字燕燕)、萧观音(道宗皇后)等人。契丹人在建极立朝、文教渐开之后,研读经史、崇尚文学逐步成为社会风习。
以上仅就总体而言,并不绝对代表契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这种语言文字、政治、经济、姓氏等方面的二元性特征,确实对契丹人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其文学创作,使其文学呈现出二元同构的特征。契丹文学的这种二元同构,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契丹语和汉语同时并用,存在大量使用双语进行创作的现象,这是二元并行;二是存在语言交叉结合的双语合璧诗文,这是二元共生;三是诗文思想内容及情感倾向的兼容,一方面向慕并吸收汉文化,杂儒释道思想,另一方面又表现契丹民族独有的情感、文化等内容,这是二元混融。
二、双语创作与翻译的二元并行
由于汉语使用群体数量较大,故最为通行,用汉字书写与创作的范围也最广。契丹文字创制之后,就逐渐广泛地被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是制敕诏令、章表奏疏、外交文书等官方公文,北面官系统的官方公文必定使用契丹文字,至于内容和写作方式,则模仿汉文,总体来说,主要是仿唐朝的公文,所不同者,仅仅在于文字、语法顺序、表达技巧等方面。这些方面,从存世的契丹小字作品中即可看到端倪。
第二是日常文书,如书信、碑铭、序跋、记传等,其内容与汉文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史料记载来看,契丹字较早用于刻纪功碑,以彰显皇帝和将官的武功,如天赞三年九月,“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契丹皇帝、皇后、王公大臣去世之后的哀册、碑文(墓志铭)往往有双语并用的情形,可能是先用汉语写成,再翻译为契丹文字。从目前出土碑刻文字识别的情况来看,有不少是契丹语和汉语并行者。
第三是教育机构颁行的教材——主要是翻译并撰写儒家典籍的传疏。《辽艺文志》载,道宗曾颁定《易传疏》一部、《书经传疏》一部、《诗经传疏》一部以及《春秋传疏》和《五经传疏》,并于“清宁元年,颁赐学校”,其后,“道宗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颁经及传疏”。毫无疑问,道宗所颁定的经及传疏,绝不是汉文写成,否则不至于大书特书记录在史册中。再者,辽太宗入汴,尽载后晋图书、医、乐师、百工等而去,汉人教育机构本已发达,实在无须道宗亲自“颁定”经书传疏。这种翻译,当有文字润色修饰,有契丹文人的创造在其中,且教材之编写,兼有撰述,普及范围较广,故在提高契丹族整体文化水平方面作用巨大。
第四是除教材之外,翻译汉文的其余著述。据《辽史》记载,辽太子耶律倍曾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皇帝诏萧韩家奴“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据《契丹国志》载,圣宗“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等读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辨鴂录》一卷,不著名氏,契丹译语也,凡八篇。”辽代对汉语经史子集翻译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契丹人翻译最多的是佛经,从史料记载来看,契丹人崇佛,曾大量翻译、刻印佛经。此种翻译,既忠于原著,又有个人的理解与创造,不同于简单的双语字句对照,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第五是诗文创作。自契丹文字创制后,就曾用来创作诗文,不管耶律倍的《海上诗》是双语合璧诗还是用契丹语翻译的汉语诗,都算是最早出现的契丹文文学作品。至于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则更是契丹语诗歌的代表作。《金史·选举志》载,考选国史院契丹书写一职,“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汉字书史译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诗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以契丹字出题”。因金朝多沿袭辽朝制度,金朝国史院契丹书写考试,竟然要求必须用契丹字作诗一首,可见对用契丹字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视。当然,由此也可以推断辽朝更是如此。就史料记载的诗文集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契丹文字创作,但是,更多的诗文还是用汉文进行创作。
除此之外,契丹字还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记诸部乡里之名、镜铭、符牌、旗帜、金银铜和瓷器上的标识等等。
综上,汉人的汉语创作与契丹人的契丹语创作同时并存,形成文化与文学的二元并行状态。
同时,很多契丹文士兼通双语,他们分别用契丹语和汉语进行创作,就他们本人而言,也显示出二元并行的状态。如创制契丹字的耶律突吕不,“幼聪敏嗜学”,“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耶律鲁不古,“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毫无疑问,他们当然精通双语。另如太子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宁王耶律只没“通契丹、汉字,能诗。统和元年,应皇太后命,赋《移芍药诗》”,“赋《放鹤诗》”;耶律学古,“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耶律蒲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应诏赋诗,立成以进”,“父庶箴尝寄《戒喻诗》,蒲鲁答以赋,众称其典雅”。
至金朝初年,女真字尚未制成,士人兼通契丹语、汉字者较多。即便女真字制成之后,也并未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有很多人仍然能用契丹语和汉语写作,契丹人如移剌慥、移剌斡里朵、移剌成、移剌温、耶律恕、萧永祺等人即是。
从目前出土的哀册和墓志看,双语并行还有一种特殊形态。如辽兴宗仁懿皇后、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哀册,有契丹字和汉字各一合,都是分别用契丹小字和汉字写成,其内容完全一致。还有契丹字和汉字刻在墓志同一面者,如《许王墓志》,右边用汉字书写,左边用契丹字书写。之所以用两种文字书写,具体原因难以坐实,但笔者揣测,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用两种文字刻于石上,以求不朽,其意义和作用远胜于纯用一种文字;二是辽朝管辖契丹人和汉人,政治体制采取南北面官制,使用两种文字正是这种体制的具体表现,由此可显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三是辽朝官方用语用字本来就是契丹字和汉字同时并用,哀册文的做法只是当时的习惯而已。
三、双语合璧的二元共生
关于双语合璧诗文,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笔者根据所见到的材料,试作界定。所谓双语合璧诗文,是指在诗文中嵌入两种语言,二者的内容与形式较好地融为一体。这对于作者的要求比较高,首先是要会两种语言,其次要掌握诗文的创作要求,并能按照相应的写作规则进行创作,第三是要实现两种语言的切换与交融。
严格地说,双语合璧诗往往囿于语言的隔阂以及格律的要求,水平一般不太高。再加上阅读理解的困难,传播范围也不广,所以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
根据袁行霈先生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契丹文学史上最早的双语合璧诗是耶律倍的《海上诗》,但王静如、清格尔泰、刘凤翥等一些契丹文专家考释契丹小字“山”对应汉语的“戊、己、金、黄”等字,“山”字上有一点的契丹字可释读为“金、黄”等汉字。而汉语的“王”“可汗”“皇”,就目前释读情况来看,在契丹语中均未见写作“山”的例子,所以《海上诗》是否算作双语合璧诗,可能还不好下定论。
契丹文中存在大量的汉语借词,这是无可置疑的,如“皇帝”“皇后”“太尉”“翰林学士”“论语”“尚书”“楚辞”“泰山”“黄河”“长安”“洛阳”“孔子”“孟子”等涉及官职、书籍、地名、人名之类的专有名词,契丹语中本来没有,只能从汉语中原样翻译借用。这与汉语借用“葡萄”“苜蓿”“龟兹”“吐鲁番”等词的情况相类似。但汉语历史悠久,本身词汇丰富,这些借词已经转化为汉语的一部分,不好断然认定汉语中凡用这些借词就是“合璧”。但是,契丹字的原字字形借自汉语的偏旁部首,契丹语的相当一部分词借自汉语,这样就必然导致契丹语文学创作中掺杂大量的汉语词汇、汉字字符,与汉语借用“苜蓿”等词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就本质而言,契丹语文本身就是以二元构词为主,这是我们强调契丹文学中双语合璧诗文的关键所在。
既然契丹语中有如此多的汉语借词,那么在其诗文中,契丹语词与汉语语词交织在一起,同时又符合契丹语的语法要求,符合“双语合璧诗文”规范,且创作这些诗文的作者,多精通契丹字和汉字,如上文所述,故此结论可以成立。
其所以称二元共生,还因为契丹语词与汉语借词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组合起来,形成规范的短语(或词组)、有序的句子,共同表达某种意义,或生成某种新的意义,因而具有共生性。
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语音、语义和语法结构与汉语都不相同,所以在表达中就有民族的独特性。洪迈《夷坚丙志》卷十八载:
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结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
以现在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进行比较,可知这则记载比较符合实际情况:阿尔泰语系的诸语言与汉语语序不同,常会出现词序颠倒的情况。汉语用一个字即可表达,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有时则需要几个词才能表达出来。
除了契丹语中的双语合璧诗文外,宋人也有以契丹语入诗而作双语合璧诗者,刘攽《中山诗话》载余靖出使契丹所作诗云:
夜宴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感勒。
微臣雅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
诗下有小注曰:“设逻,厚威也”;“厥荷,通好也”;“感勒,厚重也”;“雅鲁,拜舞也”;“若统,福祐也”;“铁摆,嵩高也”;“可忒,无极也”。这是一首很特别的诗,张振谦认为,“余靖此诗并非单纯的、严格意义上的‘胡语诗’,而是契丹语和汉语双语合璧之作,作者将契丹语用‘音译’的方式通过汉字写入诗句中”。
宋人以契丹语入诗而作双语合璧诗的情况并非个案,沈括《梦溪笔谈》亦载“契丹语入诗”之事:“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貍。’”其下注云:“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似小木罂,以色绫木为之,如黄漆。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豚子而脆。”
由余靖和刁约的这两首诗可以看出,要想做到双语合璧,既要懂所用词语的意思,还要符合平仄押韵的要求,把两种语言较好地安排在一首诗中,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四、思想文化的二元混融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前言》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用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些用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常常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融合在汉语种文学的整体系统中。”少数民族无论用汉语进行创作,还是用母语进行创作,其诗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基本上具有这种二元混融的特性,他们在情感上对汉文化向往,又保持着对本民族特色及文化的自尊和自爱,而这两个方面又借助于文学作品的形式,自然地交融在一起,所以呈现出二元统一的状态,共同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些表达契丹风俗的诗文,明显体现出思想文化的二元混融,如耶律良在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游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兴宗亲自出题,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道宗即位后,“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十分明显,秋猎、捕鱼、射熊、放鹰,均是契丹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渗透着契丹人的思想观念,而用汉赋的形式进行创作,则融进了儒家思想劝讽的内涵。这类作品,既在语言形式上进行交织,又在思想文化上发生互融,是二元混融形态比较典型的代表。
契丹人本无所谓的正统思想,但在接受汉文化之后,逐渐认识到这种思想文化在稳固政权、统治人民、树立权威等方面的作用,所以通过各种途径树立辽为正统的观念,如圣宗耶律隆绪作《传国玺》诗,把后晋所献的所谓“秦玺”奉为至宝,认为可以“千载助兴王”,这很明显是自秦汉以来强调的皇权至上、“君权神授”思想。但细细品读这首诗,又颇觉其稚拙:“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似乎说只要拿到这方玉玺,契丹就是正统;“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只要守好这块传国宝,国家就永远昌盛。从汉民族的思维特点来看,大约不会写这样的诗。这种简单、直接、显豁的思维方式,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直率豪爽性格与游牧文化形成的内在因素之一。
再如萧观音的《伏虎林应制》:“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毫无疑问,“应制诗”这种形式、七绝诗的格律以及汉字载体,是汉文化的直接体现,但从思想内容及语言表达方式来看,却是契丹民族所独有的。《辽史·营卫志》载秋捺钵之地:“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由于契丹女性所受束缚相对较少,她们中有很多人娴于弓马骑射、带兵作战,如辽太祖皇后述律平“有雄略”,自能领兵作战,室韦来袭,“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太宗皇后“虽军旅、田猎必与”;景宗皇后“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耶律隆庆之妻秦晋国妃“颇习骑射”。萧观音本人也颇习骑射,此诗是随道宗游猎时作,语言恣肆,境界阔大雄奇,气势如疾风骤雨,“风格奔放豪迈”,“反映了契丹人张狂性格”。萧瑟瑟的诗歌也具备这种慷慨清劲之风,如《讽谏歌》之“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以及直言不讳的特点,如《咏史》之“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都反映出契丹女性不同于中原女性的诗文言说方式。除此之外,萧观音《应属和道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破除华夷界限,表现了华夷同风的大一统思想,正是契丹族基于政权和民族问题进行思考后的文学表达,也真实反映出契丹人对于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契丹文章所涉内容庞杂,凡公务之军国、政事、外交、律令、教育、徭役、民生,以至个人书信、杂记、墓碑等,涉及思想也各不相同,或儒,或释,或道,又有契丹生活风俗、文化习尚。仅就单篇文章来看,或以一种思想为主,如涉及佛寺僧众塔铭等,则一般只关涉佛教思想,但就契丹文整体而言,则表现为多种思想并存。
当然,思想文化之间并非全是和平交融,其中也有矛盾与冲突,有一篇北面林牙耶律昆谏阻南京留守高勋种水稻的文章,就体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思想差异,文章题名为《上言乞止南京疏畦种稻事》:
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由而入?
高勋是汉人,有较浓厚的农耕思想,见南京(今北京)有很多空地,便打算种水稻,但契丹人世代以游牧为生,考虑骑马的道路是否通畅,故认为引水种稻,到处是水田,马不得过,万一反叛,则难以进入。就局部来看,这是思想文化的冲突,但就契丹文学文化整体而言,亦是二元混融之变化形式,即所谓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其实所谓的文化思想差异,本质在于思考问题的视角不同。
这种思想文化的二元混融,到辽兴宗、圣宗时,速度加快,中华文化在统治者上层和知识阶层已基本普及,出现了统一体制与文化的呼声,如著名诗人萧孝忠向兴宗奏曰:“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这种二元统一,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对于辽代的文化,白寿彝先生指出:“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并又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不但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余论
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认同中华文化,学习汉语,学习儒家经典及其他诸家的思想,使用汉语进行创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要向前追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当在周穆王时期,《史记》《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西王母,居住在昆仑丘,可能是西域母系氏族社会的部落首领,她用汉语作的四言诗,一直流传至今。公元前60年,汉朝置西域都护府,其后西域诸王多派质子如扜弥王子赖丹和莎车王子延等到长安学习典章制度和文化,生活于当地的塞人、羌人、乌孙人、匈奴人等也多学习汉语,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族汉化程度最深,明元帝拓跋嗣即位之初,命博士祭酒崔浩用三年时间给他讲解《诗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著作,其后他曾撰《新集》三十篇,汉语水平已远非普通人可比。而孝文帝则更进一步,迁都洛阳,改汉姓,穿汉服,用南朝典章制度修改北魏制度,鼓励与汉人联姻,极大推动了民族融合进程,其后鲜卑后裔文人辈出,与此皆有莫大关系。在同一时期,西域高昌亦置学官,为学生讲授《诗经》《论语》《孝经》,这些情况,从大量的出土文书中可以得到印证。大唐盛世,万方来朝,无论粟特昭武九姓,还是契丹、回鹘等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用汉语写作诗文,都是当时风尚影响的结果。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并延续至辽代。辽代以后的金、元、清三代,在女真、蒙古、色目、满等族群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大体经历了类似的阶段,因而具有共通性,是一种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契丹文学的这种二元同构特征,又有不同于女真文学和蒙古文学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契丹文学创作建立在辽代社会政治体制二元化、姓氏二分、双语并用等基础之上,因而具有独特性,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之处。
综上,从双语创作的二元并行到双语合璧的二元共生,再到思想文化的二元混融,这三种状态,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思想,构成契丹文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这三个主要阶段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其中,二元并行是前提和基础,二元共生是二元并行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必然结果,二元混融是最高形态,由二而一,合二为一,统一于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这个整体之中。契丹文学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契丹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展现出契丹文化与汉文化、契丹文学与汉文学同构于中华文化、中国文学的过程,也充分证明了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多元融合与统一。契丹文学与文化的二元同构,是各民族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生动案例与典型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量。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互通交融,形成了兼容并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
注释
⑦蔡美彪:《试说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