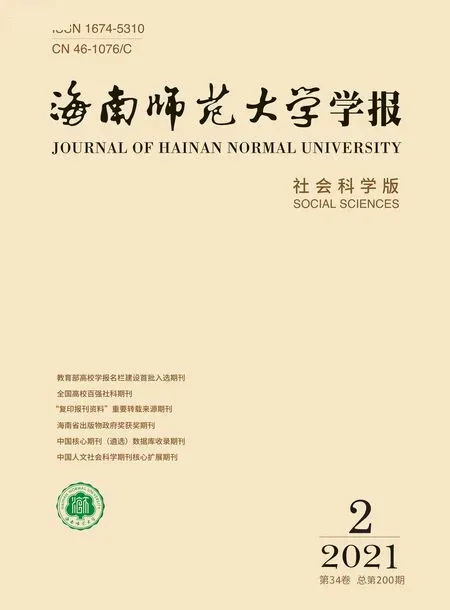语境转换与诗人的“隐现”
——穆旦在1950—1977年的文化命运
李蒙蒙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与时代诗歌主潮之间的距离,穆旦独特而鲜活的现代诗质受到忽视与排斥,其丰富的灵魂世界和主体精神受到压抑,20世纪40年代曾在诗坛享有一席之地的现代派诗人穆旦退隐,直至去世前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地下诗歌”,同时其译诗引起良好的共时接受效应,并与诗歌创作形成互补。本文以穆旦1950年回国至1977年去世这一段时期内的文化命运为研究范畴,考察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的合法化问题、穆旦在新中国成立后诗歌创作被批判的状况、其译诗的接受效应等,并探讨穆旦诗歌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变迁与多元价值。
一、“现代派诗人穆旦”的遁形与有限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开始以新的历史视野与价值尺度重新整合和评判现代文学遗产,对一些不合时宜的旧人和旧文进行选择与删汰,并重建现代文学的经典谱系。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的部分诗作以及解放区诗歌被奉为新的诗歌经典,而“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七月派”“中国新诗派”的诗歌则被排除于经典序列之外。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由于鲜明的现代主义风格、强烈的欧化色彩、陌生晦涩的语言、对自我的痛苦探索,以及象征与隐喻手法的复杂性等,都与时代主流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拒斥、对阶级性与现实性的重视、对明朗健康的诗风的要求之间形成对立,因而失去存在的价值与传播的渠道,遭到文学史、诗歌史、新诗选本的遗忘和遮蔽,“现代穆旦”在大陆文学场中几于遁形。
其一,穆旦在新中国文学史中的存在状况。文学史的任务之一是对一定时空范围内出现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公正客观的记录与评述,从而为文学经典化提供依据,但文学史却常常为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所左右,呈现出被遮蔽、过滤和改造后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的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都以左翼文学为叙述主流,对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风格过于强调,“艺术谈得极少,而且几乎抹杀了五四以来许多新诗流派存在的意义与历史地位,甚至否认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对当时某些重要的作品一字不提”(1)唐湜:《闲话新诗的“放”与“鸣”》,《文汇报》1957年5月29日,第3页。。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在处理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诗歌时,都将袁水拍和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放在重要位置,从而简化了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诗歌创作的多样性。而作为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重要的青年诗人,穆旦及“中国新诗派”诗人则被排除于文学史的合法空间,其在1978年之前的大陆文学史论著中基本都是处于缺席状态。
其二,穆旦在新中国诗歌史中的存在状况。新诗史的写作肩负着重建新诗经典秩序、定位新诗资源、为当代诗歌发展寻求合法性的任务。自1949年至1979年整整三十年间,并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新诗史著作,仅有少数的篇章执行着替代性功能。如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是建国后首次对现代诗歌流派做出梳理与定性的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史”的意义。在严格的“左”“右”阵营划分之下,与“人民诗歌”差距较大的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未获得入史的资格,在本该被“特写一笔”的时候被完全忽视。《新诗发展概况》是“大跃进”时期由几位北大青年学生集体撰写的新诗史,其革命性更强,等级排序更为严格,在介绍国统区诗歌时提到,“在抗战爆发前就已疲弱了的现代派诗风,又在死灰里冒出白烟。其恶性发展就是穆旦、杜运燮(‘中国新诗派’)之流,非常起劲地零售着他们脑海里一团团颓废、模糊的印象……这些寂寞地在反动王朝末日出版一两期丛书的‘南北才子’,也没有什么艺术‘才能’,不过是发一两声哀号的先朝遗少罢了”(2)谢冕:《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虽然其叙述中流露出某些偏激色彩,但这是在当时语境下较为罕见的对20世纪40年代穆旦及“现代派”诗风的提及,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其三,穆旦在新中国诗歌选本中的存在状况。选本是作家作品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选录本身即承载着相应的价值判断功能。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是专门性的新诗选本,该选本秉持“新的人民诗歌”的理念,选取了26位诗人的82首诗歌作品,具有排座次的意味。其中着意选取阶级立场明确、现实主义色彩鲜明、格调单纯明朗的诗作,而20世纪40年代为臧克家所熟悉的“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的作品却由于不合规范而被普遍漏选。这既与穆旦等人诗作的“非主流”因素有关,又呈现出不同主体间诗歌观念的差异,以及人事关系、个人处境等的复杂考虑。针对当时“中国新诗派”等的被冷藏,1957年,唐湜曾在《闲话新诗的“放”与“鸣”》一文中呼吁历史的公正性,表示“除少数极端反动的流派外,大部分至少在诗的艺术的发展上是有过一些贡献或影响的。对于它们,应给予正确的历史的估价”(3)唐湜:《闲话新诗的“放”与“鸣”》,第3页。。
最后,“现代派诗人穆旦”在新中国大陆文学场中也有过几次非常有限的公开存在的机会,如1950年平原社出版唐湜的《意度集》,其中收录的《穆旦论》是20世纪40年代极有分量的穆旦专论,并且在《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一篇中也提及了穆旦。1957年9月5日,田之的《“人民文学”反右派斗争获初胜——剥露唐祈、吕剑的原型》一文在批判唐祈时曾提及“中国新诗派”和穆旦的名字。但是,上述少量的引述基本未引起关注,也未能将“现代派诗人穆旦”从历史的盲区中拖拽出来。
相较而言,20世纪50至70年代的香港地区由于文化传统、接受观念、研究范式等的不同,对新诗的认知与评判在某些方面似乎更为客观,既为穆旦的共时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补足空间,同时也为新时期穆旦被“重新发现”奠定了基础,呈现出穆旦诗歌在不同地域间的价值浮动现象。
其一,不同于当时大陆新诗选本的“严挑细选”,香港的部分新诗选本较为真实地呈现了新诗史的本来面目,再现了一批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优秀诗作,还原了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坛位置。如1974年张曼仪、黄继持、黄俊东等合编的《现代中国诗选(一九一七——一九四九)》在选录标准上以艺术价值为重,兼顾文学史地位,对于不大受注意的个别优秀诗人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与推崇,共选取了110 位诗人的代表作品,其中收录了穆旦的《赞美》《诗八首》等九首诗歌;并且编者在《导论》部分将西南联大诗人、《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诗人群的注重社会责任与艺术性、将个人情志与大众情志相结合的诗歌探索视为20世纪40年代新诗的重要构成;同时将这批诗人划分为以郑敏和穆旦为代表的“从哲学的思考开始,通到时代与社会”和以杜运燮为代表的“以刻划社会现实为主,而加理性的综括”两种类型;在与郑敏的比较中指出,“穆旦多的是生命的紧迫感与矛盾的张力。他的自我探索与自我完成的历程走得比郑敏要艰困,他的内心世界的展开是与他对外在世界的观察同时推进的。语言方面,穆旦比较欧化而略显晦涩”(4)转引自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1页。,其对穆旦诗歌创作的理解是较为恰切的,具有为穆旦及这一群体正名的意味。1975年,尹肇池等编《中国新诗选——从五四运动到抗战胜利》注重呈现“伟大民族在伟大时代中的历史经验”(5)尹肇池:《中国新诗选——从五四运动到抗战胜利》,香港:大地社,1975年,第Ⅱ页。,入选诗歌以反映历史主流及有一定艺术成就的作品为主,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报贩》等七首诗歌入选。
其二,不同于当时大陆文学史对穆旦的忽略,香港文学史对于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的存在状况或稍作提及,或做出明确肯定。1978年,林曼叔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在述及“十七年”诗歌时,指出“穆旦是比蔡其矫资格更老的诗人,在卅年代,他写下了大量的诗作”(6)林曼叔:《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香港: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第233页。,将穆旦与“现代”时空之间建立关联。1978年,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将穆旦标举为战后踏入诗坛的值得注意的新诗人,并对20世纪40年代穆旦诗作给予了200多字的评论,以“意境清新,想象活泼……情意飞翔”(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第227页。等词语来阐述其创作风格,并对《诗八首》做出“风格独异”的较高评价。另外,在作品的刊载与出版方面,“在大陆十年文化浩劫期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刊在香港成了热门货,好多出版社都私自翻印了这类书刊”(8)王一桃:《香港暨海外的“臧克家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2期。;20世纪70年代穆旦的诗集《旗》《穆旦诗集(1939—1945)》和《探险队》都曾以影印版的形式在香港流传。穆旦在香港新诗选本与文学史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记忆”的有效延续,为下一阶段的穆旦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由于语境转换所带来的区隔,以及“左翼”文学话语的影响,曾在20世纪40年代有过非凡艺术探索的青年诗人穆旦被时代遗忘,其所代表的新诗理念与范式也遭到拒斥,这不仅阻碍了穆旦诗歌的传播接受进程,“阻塞了‘异质性’艺术渗透、比较、冲突的通道,也切断了新诗已经积累的部分经验”(9)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新中国诗人穆旦”与时代的深层关系(新的诗歌创作——批判/默许)正在重新建构和展开。
二、“新中国诗人穆旦”的共时批判与“潜经典”创作
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作品无缘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经典系列,他曾长期聆听时代的声音,并反思自己的创作,“唯有选择‘新事’,才有可能将‘旧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点”(10)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在“百花齐放”文学热流的影响下,穆旦发出了无愧于时代和自己的独特声音,却因不符合主流文学的预设,而受到来自诗界权威和普通读者的共同批判。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厄运,诗人穆旦沉默了将近20年,直至1975—1976年创作出一批被后世称为“中国新诗的宝贵财富”(11)黄万华:《中国现当代文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的“地下诗歌”。本小节通过分析穆旦1957年发表的诗作与“时代经典”之间的距离及其所受到的批判,以及穆旦“地下诗歌”的“潜经典”特质,来考察“新中国诗人穆旦”的共时存在状况与接受程度。
首先,新的“时代经典”的确立及其“质”的规定。“时代经典”是相对于“永恒经典”而言的,它是指作家作品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打造之下,在某一时期被共时读者接受并奉为典范,而随着语境的流转,有可能因精神意蕴、审美内涵等的不足而被“去经典化”。新中国在认证“时代经典”时,对于诗人的身份、诗歌创作的思想主题、价值观念、题材选择、修辞方法、情感基调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20世纪50至60年代政治抒情诗由于主题的宏伟、趣味的高尚和诗情的明朗等质素被确立为新时代的经典诗歌范式,郭小川、贺敬之、闻捷也被树立为新的典范诗人。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非主流往往是对立存在的,在一批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审美要求的作品被指认为“时代经典”的同时,也有部分思想内涵丰富、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但因不符合国家民族意志和新的人民文艺建设的要求而遭受贬斥,以确保人民文学的“同质性”。在这种创作氛围与机制中,诗歌的书写范畴与言说对象“必须面向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以往基于城市文明背景的诗歌观点和语言策略是不适用了,不仅抒情观点不行,表现形式与技巧也不行”(12)王光明:《中国当代诗歌观念的转变与政治抒情诗的经典化》,童庆炳、陶东风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8页。。因此,穆旦在新中国的诗歌探索及其创作价值遭到理所当然的批判,其诗歌的传播接受进程也遭遇挫折。
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臧克家、徐迟的约稿之下,穆旦在《诗刊》《人民文学》上贡献了一批“探索性”作品。从整体上看,穆旦已做出了有限度的调整,以试图寻求主流的认可,但是其以往的诗歌经验与表达方式又不自觉地渗露出来,在“有我”与“无我”、晦涩与平易、虚构与真实、暴露与歌颂、忧郁与明朗等方面形成了与主流诗歌之间的截然对立。穆旦先锋性的精神探寻与异质表达招致主流话语的严厉批判。1957—1958年,约有11篇文章涉及到或专门针对穆旦诗歌进行批评,从批评人员的构成上看,既有邵荃麟、徐迟之类的文艺官员,也有郭小川这样的知名诗人,更有工人、战士之类的共名读者,在这几方面的共同作用之下,穆旦诗歌被贬损为充斥着“洋腔洋调”的坏作品,穆旦连同他对时代的表达一起遭到拒绝。这一时期对穆旦诗歌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将诗歌内容的理解机械地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使得穆旦对现实的理智认识、对“新旧自我”决裂的真诚表现被极大地简化。如戴伯健认为《九十九家争鸣记》反映出穆旦对于现实和政治的不满、影射与歪曲。李树尔和黎之认为《葬歌》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我改造的修正主义态度,本质上是“以埋葬为名,来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13)李树尔:《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么?》,《诗刊》1958年第8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是“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污蔑”(14)黎之:《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与反党逆流》,《诗刊》1957年第9期。。在两者的共同阐释之下,穆旦作为异己分子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其二,几乎所有的批判文章都涉及到穆旦诗歌晦涩难懂、朦胧模糊的问题,并将这一问题与现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趣味相关联,从而质疑穆旦诗歌能否为人民服务。如1957年,安旗在《关于诗的含蓄》中指出穆旦最近的作品晦涩难懂、令人不知所云,并认为这类晦涩诗来源于现代主义。(15)安旗:《关于诗的含蓄》,《诗刊》1957年第12期。1958年,邵荃麟在《门外谈诗》中将穆旦的诗歌语言称为“沙龙式”的语言,并将其与穆旦的思想意识相关联。(16)荃麟(邵荃麟):《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第4期。徐迟在《南水泉诗会发言》中将穆旦的诗界定为“典型的西风派”,并指出其“平衡把我变成一棵树”一句隐晦而又糟糕。(17)徐迟:《南水泉诗会发言》,《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 第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65页。《诗刊》刊载的《“工人谈诗”小辑》和《“战士谈诗”小辑》中也用“看起来比天书还困难”(18)周用宁等:《工人谈诗》,《诗刊》1958年第4期。,以及“读之不入口,听之不入耳”(19)刘瑾瑜等:《战士谈诗》,《诗刊》1958年第7期。等话语来描述对穆旦诗歌的阅读感受。其三,将穆旦对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表现视为一种灰暗低沉或消极反抗的情绪,这类批判的矛头往往指向穆旦的《葬歌》一诗。如1958年,李隆荣《谈谈新诗》认为穆旦的《葬歌》情调阴暗、意绪消沉(20)李隆荣:《谈谈新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C1期。;郭小川《我们需要最强音》以穆旦的《葬歌》为负面例子,号召将这种“知识分子的有气无力的叹息和幻梦”(21)郭小川:《我们需要最强音》,《谈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98页。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划清界限;《战士谈诗》也指出穆旦的诗“调子低沉情绪灰暗,听不到我们时代的声音,摸不到我们时代的脉搏,不知道抒发的是什么感情”(22)刘瑾瑜等:《战士谈诗》,《诗刊》1958年第7期。。不同于上述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批判之声,1978年,林曼叔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中率先对穆旦20世纪50年代的创作进行了客观评价,并对《葬歌》的价值做出相应的肯定:“在近二十年来,穆旦的诗作并不多,可以说他的创作的旺盛期已经过去。从他有限的诗作中,可见他一贯的诗风,有明显欧化倾向,诗句读起来有点晦涩,但他写作的态度不会虚假,他会将他的内容深切地表现出来,像《葬歌》便是这样的一首诗作”(23)林曼叔:《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第233-234页。。总之,穆旦1957年的诗作虽未达到真正的审美经典的高度,但是其所具备的丰富性与独立性是超越于当时主流文学的一般创作水准的,我们不能以后设视角苛求诗人,而应当看到这些诗作在当时的超前性,以及诗人以最大限度发出自己声音的努力。
在遭受激烈的文学批判和一系列政治厄运之后,诗人穆旦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选择“隐退”,诗神无踪,直到1975年和1976年才创作出一批颇有水准的“地下诗歌”。这些“地下诗歌”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的“潜经典”,是荒原时代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拥有一定程度的经典质素和在未来时空中被指认为诗歌经典的可能性。文学经典往往“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品格。它常常提出……某种根本性的问题”(24)黄曼君:《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穆旦“地下诗歌”思想的穿透力与超越性即符合这一经典特质。这些诗作涉及到理想、自我、权力、情感、异化、智慧等永恒的话题,包含着作者对时代荒谬性的审视,对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个体悲剧的洞察,对个体价值与人性内涵的关注,对良知、人格与灵魂的坚守和对理性精神的呼唤,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极具思想史意义,“它们既是过去文明的见证,又对后来的时代发挥着持续的影响”(25)贾振勇:《文学史秩序·经典·权力》,《东方论坛》2005年第5期。。同时,穆旦“地下诗歌”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成熟性和原创性特质。穆旦晚期的诗艺更趋精湛,在继承现代派诗歌内质、吸收浪漫派手法及古典诗艺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兼容式”的创作新变,形成了一种蕴藉深厚的新的抒情模式。具体而言,穆旦的“地下诗歌”既保持着知性写作、象征隐喻、内心独白、视角转换、戏剧化等技法的现代性,又追求亲近大自然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浪漫性,也注重诗歌意境与节奏韵律的古典性,从而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不可复制的原创性,既不同于已有的新诗写作范式,也区别于同期诗歌的创作质量,呈现出丰厚的诗性内涵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真正的文学经典往往能够在时间淘洗中摆脱无名状态,在重读时代时展现其应有价值,穆旦的潜在诗作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公众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当代文学史且被重点阐释,甚至获得专节论述的资格,成为“地下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在许多“时代经典”被逐渐遗忘的同时,其仍被持续传播和阐释着。
总之,穆旦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创作为主流话语所拒斥,穆旦及其诗歌生命被无情斫伤,而20世纪70年代穆旦“地下诗歌”创作中一批审美经典的问世,为其诗歌写作历程画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事实上,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穆旦还有另一重身份,即“译者查良铮”,这一身份为穆旦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与表达方式。
三、“译者查良铮”译诗的接受热流与潜流
诗人身份与译者身份在穆旦身上实现了有效的互补,当诗人穆旦被迫隐遁时,翻译家查良铮以杰出的翻译文学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其艺术生命再次焕发出光彩,并且一度形成了“只知查良铮,不知穆旦”的特殊现象。总体而言,查良铮的翻译生涯由苏联文学理论翻译、普希金诗歌翻译、英美诗人诗歌翻译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潜在翻译四种类型构成。就影响度而言,其所译的文学理论读本因为理解的透彻与译文的精准,而成为通用教材;其所译的普希金、雪莱、拜伦等一流诗人的作品,更是因为传神达意、译笔流畅、语言凝练、精粹典雅、诗味浓厚等特征,而成为诗人译诗的典范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深深滋养和影响了几代读者,并惠及无数当代作家和翻译家,其中尤以查译普希金诗歌的影响力最为强烈和久远,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曾引起良好的共时接受效应,以下将专门探讨查译普希金诗歌在当时的接受效果。
1954年,查译普希金《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陆续出版,因其对苏联文学的译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且其积极浪漫的格调与时代要求、读者趣味相契合,更因其译诗的高质量和对本国人民语言习惯的兼顾,使得查译普希金诗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广泛而持久的接受热潮。首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查译普希金诗歌的读者范围非常广泛,“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工农大众、党员干部到知识青年,人们为查译普希金而激动,而感叹”(26)王宏印:《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 380-381页。。如查译普希金诗歌深受当时中学生和大学生读者的欢迎,成为流行的课外读物,被反复摘抄传诵,许多读者都能背诵其中的部分篇章。学者赵毅衡曾回忆道:“五十年代的大陆少年,凡如我那样喜欢做浪漫梦者,手里必然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27)赵毅衡:《下过地狱的诗人》,《作家》2003年第4期。。同时,查良铮译诗也满足了其它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在工人读者群体中也有一定的接受度,查良铮曾回忆道:“工厂里三十多岁的工人师傅,在南大开门办学去时,问老师们认识不认识这译者(并不知我在南大),他想见见”(28)穆旦:《致杜运燮六封》,《穆旦诗文集2散文、书信、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在对查译普希金诗歌的广泛接受过程中,读者的阅读视野得到开拓,文化结构得到丰富,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译者查良铮与诗人普希金的名字被共同镌刻于读者心中,查良铮译诗的成就与贡献获得民间的普遍认同。其次,在“文革”期间,查译普希金诗歌也曾以隐秘流播的方式,为当时迷惘彷徨、备感压抑的青年读者带去了无尽的慰藉与鼓舞,使他们获得了新生的信念感。当时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争相阅读、传抄查译普希金诗歌,并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感,在阅读中收获了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的渴望、对人类美好情感的珍视,并在寂寥黯淡的岁月中培养了积极向上的生命情怀与高贵不屈的灵魂。正如当时的知青孙志鸣所言,“普希金的诗在那些年月里象甘泉一样滋润了我心灵的沙漠。因此,我深深感激这位俄国诗人和他的译者查良铮先生”(29)孙志鸣:《诗田里的一位辛勤耕耘者——我所了解的查良铮先生》,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最后,查译普希金诗歌对知识青年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启蒙的作用,为这些青年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做出了重要的铺垫。查译普希金诗歌以优美动听的旋律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在反复吟咏中产生了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并尝试开启自己的创作之路,“读着这样的译诗,不能不使人有一种激情和憧憬,因而就产生对诗的向往和钟爱。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读了这样的诗后,成了诗歌爱好者以至诗人的”(30)杨开显:《穆旦百年:春到人间燕归来》,《光明日报》2018年2月2日第14版。。赵丽宏也对查译普希金六本诗集的启蒙作用表示充分肯定,他曾直言:“我后来写诗,和当初这几本诗集有很大的关系”(31)赵丽宏:《回忆和祝福》,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上海市编辑学会编:《我与上海出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45页。。除了兴趣的培养之外,查译普希金诗歌也凝练为重要的精神资源与文学资源,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一定的文学养料与储备,并在文学创作方法、思想、观念、语言等方面对其产生了积极的正面效应。如王小波曾在《我的师承》中谈及在20世纪60年代读到查良铮所译的《青铜骑士》时所产生的震撼感,“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作好”(32)王小波:《我的师承》,《王小波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页。,并且在文学语言方面,查良铮的译诗也在王小波创作之路上扮演了引领者与示范者的重要角色,对王小波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是突出的,其成就也是不朽的。20世纪50年代,查良铮出版的文学理论翻译和诗歌翻译作品向读者输送了宝贵的世界文化精粹,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得到了读者群体的普遍而持久的接受热遇。而穆旦20世纪70年代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翻译,则因为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之间构成一定对抗,而成为未能出版的“潜在译作”,但其对文学审美性和自我主体性的坚守以及对于艺术初心的艰难回归则隐含着重要的价值,成为一个时代的先锋,并且其影响力也在新时期得以重现和验证——《唐璜》《英国现代诗选》《丘特切夫》等译作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出版,并引发了新一轮的阅读热潮。同时,在政治压力的裹挟之下,穆旦这一时期由诗人到译者之间的身份转换、由“作”到“译”的写作变迁及其所带来的复杂效应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这一转型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与诗歌史意义。穆旦通过“以译代作”的特殊形式,在政治与时代的夹缝中,艰难地探索文学传达主体的艺术追求与真情实感、实现“文艺复兴”的有效途径,可谓变相地延续了自我的创作生命。同时穆旦的晚期译作因坚守其对“一生所认定的诗歌价值的深刻理解、高度认同和心血浇铸……预示着文革后期一次诗的真正觉醒和回归”(33)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6期。,既构成了与主流诗学的隐性对抗关系,又对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链接作用。
其次,这一转型也是复杂的文化语境中个体生存姿态与生存策略的特殊表征。穆旦以“查良铮”的身份重生,转而从事翻译事业,虽属无奈之举,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场域、承担文化建设和启蒙的使命提供了特殊通道,穆旦以此在时代洪流中完成了自我实现与价值确证。“通过译诗,他再次‘被点燃’,或者说,他再次把自己‘嫁接到那棵伟大的生命之树上’”(34)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6期。,从而避免了被扭曲或变形的厄运。更进一步而言,这一转型是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特隐喻。穆旦的“潜在译诗”以彻底的反叛和“激流暗涌”的姿态彰显着知识分子清醒独立的精神立场与高贵不屈的人格力量,其对独立的精神姿态与个人自由意志的葆有,对批判与怀疑、内省与反思的理性精神内质的延续,其强烈的知识分子性和持续的精神探索均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成为建国后知识分子命运研究的突出个案。因此,穆旦的文学转向具有深刻而复杂的意味,无论是对于穆旦个人的命运史,还是对于中国现代诗歌史,抑或是对于思想文化史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总之,“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35)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第10页。。
综上所述,在政治与诗学关系失衡的时代,由于受到一元化既定成规的束缚,批评家只能用同一种政治性和阶级性话语来阐释和评说创作现象,穆旦丰富的灵魂世界和主体精神受到压抑,其独特而鲜活的诗质也被忽略和遮蔽。新时期以来,随着权力话语的调整,文学的自觉意识逐渐回归,文学研究观念由阶级性向审美性过渡,穆旦其人其诗才又重新从历史的尘霭中被挖掘出来,再度进入到读者的阅读接受视野中;并且在文学现代化标准的张扬和新诗现代性追求的烛照之下,穆旦诗歌中曾被有意遮蔽的现代性、异质性与反叛性等质素得到重新发现和强调,其诗歌的价值意义得到充分挖掘和彰显,穆旦在文学史上的身影也愈发高大起来,被指认为是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