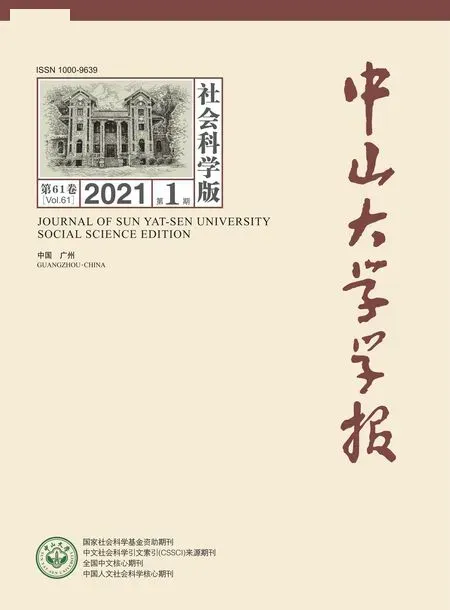《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
——以《诗经》“逑”“仇”为例
李林芳
《毛传》和《郑笺》对《诗经》的训释常有差异。对于差异之由,前人多用郑玄据三家之说改易《毛传》予以解释,如陈奂谓“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例不外此二端”①陈奂:《郑氏笺考征》,《续修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1页。,而较少关注到其他层面的原因。然而现有研究已逐渐认识到传统所谓三家之说多有不可靠处②详见马昕:《三家〈诗〉辑佚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783—795页。,这就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毛郑差异的根源。本文即以《诗经》中毛郑对于“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尝试从更为根本的文本层面入手,探察二家异说的成因。我们将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毛诗》本身的文本层次问题,说明毛郑所据文本容或有异,及可能的考察方法。继而全面梳理文献材料,包括传世和出土文献,探究字形与词义的变化发展状况,推求可能的文本面貌与理解来源。最后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毛郑文字与训解上的差异和差异产生的原因③本文所引诗皆取自《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嘉庆本),2009年。。
一、《毛诗》的层次
经典由于形成较早,且受众众多,在流传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变易。随着后人不断的注释、校改、传抄与刊刻,其文本面貌就在这其中不断发生变化,并形成不同的层次,叠加于今天所能见到的文本之上。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已指出经典古籍有着“多层次的复杂重叠构成”,并以《诗经》为例,认为该文本历经孔子编定、四家传授、《郑笺》注释、《经典释文》注释、《毛诗定本》编撰、《毛诗正义》编撰等,故于宋代合刊时,至少重叠了六个层次①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81页。。每一层都对原先的文本面貌有所改动,并最终汇积到今天所见《十三经注疏》的《毛诗正义》之中。
所以,若欲见到更早期的文本面貌,在缺少直接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便需由此层次逆推,仔细分析与每一层次相关的文献,从中寻求线索,以从今见文本中剥离出更早的文本层次。而对于《毛诗》文本来说,我们所能见到的早期版本非常有限。今见最早的刻本为宋刊经注附释文本②参见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9—421页。,已属最晚的文本层次了。敦煌本《毛诗》虽有白文本,但据其首题“诂训传”等语可知其实从经注本中抄出;亦有兼抄《毛传》《郑笺》者,故知亦为经注本,所以最早也只能是第3 层次的文本了③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21—425页。。至于其他出土文献,如阜阳汉简《诗经》已证实非属《毛诗》和三家诗系统④详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阜诗》属于哪家”节,《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31页。,安大简《诗经》与《毛诗》在国风排序、篇数、篇次、章次和字词方面都有一定差异⑤参见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其中认为“简本与《毛诗》应是两个不同的先秦古本”。,清华简中与《诗经》相关的部分亦与今见《毛诗》在文本上有着明显不同⑥参见李锐:《清华简〈耆夜〉续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黄甜甜:《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诗经〉之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故皆不能归入《毛诗》本身的文本系统中,只能留为旁证。
若欲考察《毛诗》可考的最早而确切的样貌,我们只能通过研究《毛传》和《郑笺》注释,从细节中发现《毛传》所据的《诗经》文本和《郑笺》所据的《诗经》文本的特征,从而将《毛诗》的早期样貌从今天的已被多重叠加的《毛诗正义》中剥离出来。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更早时期的用字习惯,通过字词关系的变化来排除某些可能和确定某些可能,以期最终判定毛郑所见的《毛诗》文本的相关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剥离文本层次的方法,清代学者已经在其校勘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段玉裁校《毛诗正义》时就经常据注疏文字改校《毛诗》正文,并提出了“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的卓越理论⑦《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而在今天,有了更多的出土材料后,我们就能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开展这一工作,并得出更为细致和可靠的结论。赵培《毛传郑笺所本之〈诗经〉面貌管窥——以〈曹风·鸤鸠〉为例》即是较早的相关研究论文。该文运用出土材料,通过考察字形历时演变的方法来断定毛郑各自所据的《曹风·鸤鸠》的文本面貌⑧赵培:《毛传郑笺所本之〈诗经〉面貌管窥——以〈曹风·鸤鸠〉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在本文中,我们将继续运用这一方法,并将字形演变与词义演变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以期从文本的角度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毛郑异解做出解释。
二、毛郑习诗注诗的年代
为了更好地运用出土与传世文献材料来解决《毛传》与《郑笺》中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毛与郑的时代。郑玄的活动年代相对比较清楚。据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郑玄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⑨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7,97—100,190—194页。,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后始笺《毛诗》⑩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7,97—100,190—194页。,卒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享年74 岁⑪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7,97—100,190—194页。。故郑玄习诗和注诗的年代应在东汉末期,其注释应更多地反映东汉晚期的特征。
至于《毛传》作者生卒年份及习诗的时间,史籍并无明文记载。按今见最早的关于《毛传》作者较为详尽的记述,主要见于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的经典传承谱系之中①分别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70 页。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页。。若据之推算逐代间隔,则《毛传》作者为毛亨,似应出生且习诗于战国末期,这可能也是清代陈奂、俞樾等学者认为毛公是六国人的原因②《诗毛氏传疏·叙录》:“数传至六国时,鲁人毛公,依序作传。”(陈奂著,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页)《古书疑义举例·两字对文而误解例》:“毛公,六国时人,犹达古义。”(俞樾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4页)。
但是现代学者较不同意以上观点,不认为毛亨为荀子弟子,甚至以为荀子未传《毛诗》;而上述文献记载的谱系互不一致,有《毛诗》后学伪造之嫌,目的是藉以自重③详见马银琴:《荀子与〈诗〉》,《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相应的关于《毛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学者认为“成书于前155—前145 年间,作者为毛公”④赵茂林:《〈毛传〉成书及定型考论》,《诗经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我们认为,虽然陆疏和《经典释文》的记述难以确信,但《毛传》作于西汉初应是问题不大的。《汉书·艺文志》记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⑤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汉书·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⑥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88《儒林传》,第3614页。,郑玄《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⑦《毛诗正义》,第561页。。由此可知,《毛诗》作者应与河间献王的所处时代相近,后者于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受封,在位二十六年卒,故《故训传》之作者亦应主要活动于此时。考虑到秦建立距这一时期(前155)相去仅66 年,故其作者生于战国末期亦有可能。由于《毛诗故训传》的作者名姓难以考实,古来即有较多争议,且这并非本文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故文中一沿前人习俗,只以“毛公”代称。
《毛诗故训传》在写成后应又经后人的不断增补,其中部分内容可能晚至西汉末期⑧赵茂林:《〈毛传〉成书及定型考论》,第184—199页。其中认为:“故《毛传》的定型当在哀帝建平元年至元帝元始五年间。”(第199页)。总结上文,毛公应是一位出生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的人物,其所习诗和所著的《毛诗故训传》应更多地反映先秦时期的面貌,其中也会夹杂一些晚至西汉末期的成分。郑玄则是一位东汉末期的学者,其所习诗和所著笺应更多地反映东汉晚期的面貌。这一判断将是我们下文进一步分析毛郑所据《诗经》文本面貌的基础。
三、先秦至两汉“逑”“仇”字形和词义的变化
今传《诗经》中共出现“逑”字两次,“仇”字四次⑨未计“执我仇仇”,因“仇仇”为联绵词。。其中,《毛传》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把“逑”和“仇”训为“匹”,《郑笺》则释为“怨耦”⑩以下二例除外:1.《大雅·民劳》:“以为民逑。”传:“合也。”笺:“合,聚也。”2.《小雅·宾之初筵》:“宾载手仇。”《毛传》:“宾许诺自取其匹。”仍将此“仇”训为“匹”。而《郑笺》:“仇读也。”以为假借。。如《周南·关雎》“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郑笺》“怨耦曰仇”。关于两字之间的关系,前人多认为是音同义近,相互通用。如段玉裁:“逑仇古多通用。”⑪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页。王力:“按,在匹耦的意义上,‘逑、仇’实同一词。‘仇’古音如‘逑’。”⑫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9页。至于为何诗中毛郑释义似相违戾,则以为此二字“浑言则不别”“析言则异”①①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逑”字下段注,第74页。,“对言则异,散言则通”②②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2,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并多以为毛是而郑非③③ 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2,上册,第32页)、陈奂《诗毛氏传疏》(第3—4页)、《毛诗郑笺平议》(黄焯著,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页)皆是。。以上皆为从传世文献中得出的结论,已指出二字联系密切。若再考以出土材料,对于二字的关系则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按西汉以前的出土文献中未见“仇”字;至于“逑”字,楚简中已可见到,为“日逑月相”,对应于今本的“日就月将”,应非“匹”或“怨耦”之义。但是,毛郑所训字所记录的词却早已有了。今考以先秦诸出土文献,将其中所有“仇”“逑”声(二字声韵调皆同)并表示“匹”义或“怨耦”义的字形,及后来在对应传世文献中写作“仇”“逑”字形的字依声符分类,可得下表。另外,由于毛郑对诗中“逑”“仇”二字释义有异,故将涉及诗句的文字单列出来,以便观览比对。
至于其余战国文字字形,或从“求”声,或从“九”声,皆与“”声相近①参见陈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33,24、34页。,且意义相同。其中中山王鼎的“”字可以认为是采用不同声符记录同一词的字形,而《清华简五·殷高宗问于三寿》的“九”字则或可认为是通假字。
至于{仇}这两个义项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应该是引申关系,并且是从“匹”义引伸出了“怨耦”义。首先,汉语里有不少类似的从两者相对发展为敌对、仇怨含义的词。如“敌”,《说文》“:仇也。”段玉裁注“:相等为敌,因之相角为敌。”④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24,90页。又如“雠”,《说文》“:犹也。”段玉裁注“:心部曰‘:应,当也。’雠者,以言对之……又引伸之为雠怨。”⑤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24,90页。这种类似的平行引申关系皆可以作为{仇}义发展的佐证。其次,字形的变化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证据。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仇}的字形皆从“辵”旁,俱为“匹”义。到战国文字中,该词则改为从“戈”旁,且主要为“怨耦”义,这即是词义变化而对字形进行的改易,从中正可见词义引申的方向。
而在进入汉代后,{仇}的写法则发生了变化。遍检今所见汉代简帛碑石文字,可得如下诸例:

⑥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⑦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⑧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⑨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⑩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⑪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⑫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1,113,114,122,86,88,139页。⑬ 白海燕:《“居延新简”文字编》,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03,603页。⑭ 白海燕:《“居延新简”文字编》,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03,603页。⑮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4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134页。⑯ 马衡:《汉石经集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总结上文,若将{仇}的字形和常用义项的发展情况依时代变化作一整理,可得以下图表(不太常用的字形与义项放于括号内):

下文将在此基础上讨论{仇}的字形替换与常用义项的变化对毛郑所据《诗经》文本和所做注释的影响。
四、再论传笺对{仇}释义上的差异及成因
前文俱已述毛公所习诗应更多地反映先秦时期的面貌。从今见战国文字的情况可知,他所习《诗经》文本中的{仇}应尚未写成“仇”字形,可能是从“”声或从其他近似读音声旁的一个字。尽管不能说战国时一定没有“仇”字形,但我们认为毛所见诗{仇}写作“仇”字形的可能性非常小,有以下原因:1. 今所见战国及之前文字中尚未见“仇”字形,至汉后方大量出现。2. 在今见战国文字中,从“”声的字占到绝大部分,从其他声符的字形都比较少,仅一二见。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文表格中呈现的战国时期的引诗内容,乃至于安大简的《诗经》内容,其中{仇}字形皆以“”为声符。据此,虽然尚不能完全确定《故训传》成书时的文字面貌,但综合考虑毛所习《诗经》中文字的样貌及今本《毛诗》中尚存“逑”字形的状况,可以推断《故训传》在最初写定时其中的{仇}也不作“仇”形④若假设《故训传》中{仇}皆作“仇”形,则后作“逑”形者乃汉人所改。可前已论述汉代常见的{仇}乃从“九”声,这种由常见字改为不常见字的情况比较难以想象。。
与毛公时的情况不同,郑玄笺诗时所据本的{仇}字形应已作“仇”了。其中,《国风·兔罝》《秦风·无衣》《小雅·宾之初筵》《大雅·皇矣》诸篇中的{仇}今本皆写作“仇”,此不必细论。而对于《关雎》的“君子好逑”,我们认为郑玄所据《诗经》中此“逑”字亦可能作“仇”,理由如下:1. 如前所述,汉时从“九”声的字形更加普遍,在《诗经》文本的流传过程当中很容易将{仇}的其他字形改为常用的“仇”字形。前述诸{仇}皆由其他字形改为了“仇”字形,则此处的{仇}也有极大可能性被改易了字形。2.《经典释文》记“君子好逑”句有异文“仇”。3.《礼记·缁衣》:“君子好仇。”郑玄注:“仇,匹也。”⑤《礼记正义》卷55,第3582页。应本自《毛传》训诂⑥关于郑玄采传注礼,参见杨天宇:《郑玄〈注〉〈笺〉中诗说矛盾原因考析》,《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此正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郑玄所见毛本《诗经》作“仇”。4.《郑笺》笺释“君子好逑”一句为:“怨耦曰仇。”
以上从字形演变角度说明了毛郑各自所本《诗经》中{仇}的用字状况。下面则从{仇}义变化的角度对毛郑的释义作出说明。
《毛传》将{仇}解释为“匹”,从今见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可知此释的来源是非常早的。又据《郭店·缁衣》和《上博简一·缁衣》,其中记录的孔子话语明确将{仇}释为“匹”,可知毛对该词的释义也是有所传承的。郑玄将{仇}改释为“怨耦”,可能是受了当时语言的影响所致。根据前文对{仇}字形和词义的分析,可知在战国之后“怨耦”便成了{仇}的常用义项。遍检今传先秦两汉典籍,“逑”字形已极少使用①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的“逑”字,除“惟逑鞫也”(《尔雅·释训》“急迫”义)、“旁逑孱功”(《说文》“逑”聚敛义引《尚书》文)和引诗外,皆为“匹”义,用例为《史记·封禅书》“诸逑之属”,《太玄经·》“俟逑耦也”,《汉书·扬雄传》“乃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再考虑到传世文献中“仇”字形皆用为“怨耦”义的状况,这一现象似是字形经过整齐后的结果。;排除引诗、通假和人名这三种情况,“仇”字形皆为“怨耦”义,极少例外②例外为《春秋繁露》:“偶之合之,仇之匹之。”(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11页)。所以,郑玄见“仇”字并释之为“怨耦”,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语言状况及学者对“仇”字字义的理解的。因而本文认为,郑玄所见《诗经》文本作“仇”字形,再加上{仇}的常用义项发生变化,导致了郑玄将《毛传》的诂训“匹”改为了“怨耦”。
《郑笺》改易《毛传》共有两种类型。《经典释文》引郑玄《六艺论》:“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③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卷5,第119页。具体到“君子好仇”这一句上,考虑到“匹”义与“怨耦”义的密切关系,以及《礼记·三年问》“则失丧其群匹”句郑玄注“匹”为“偶也”④《礼记正义》卷58,第3609页。,则此处郑玄应非欲完全不同于《毛传》;或许这里的笺释只是对毛的“匹”义加以限定,以“更表明”此处的“匹”应是“相怨之匹”而已。
总之,通过考察出土材料,分析字词形义演变,可以发现毛郑二人所据文本是有所不同的,兼之词的常用义项也在发生变化,这反过来影响到二家对具体字词的训释。该认识还能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诗经》学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如段顾对毛郑文本的争论、三家说归属、毛郑义来源及优劣等。这些都有待结合更多的出土材料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