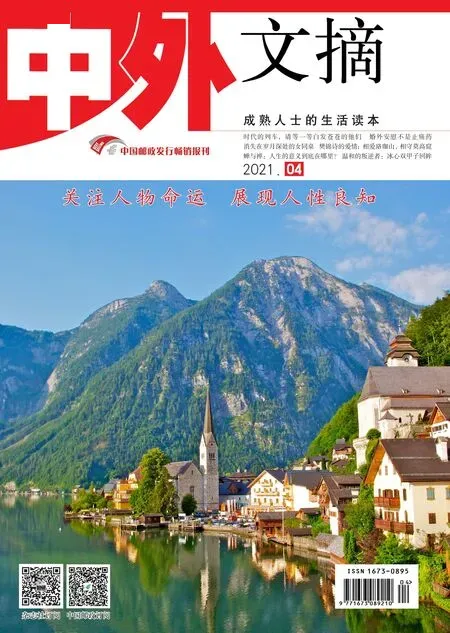汪曾祺的写作之道

汪曾祺先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出道甚早却大器晚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斯人已逝,其作品却愈发熠熠生辉,成为打动人心的经典。
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为人为文,我喜欢汪老一以贯之的真诚朴素,惊叹他观察描述平民百姓和生活细节的温馨细致,佩服他下笔如有神的不羁才气。庸常岁月读汪,是爱好,也是习惯,更是享受。他写人物,写地方风情,写花鸟虫鱼,写吃喝,写山水,写掌故,惯于淡淡着墨,却又有那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回甘独特的韵味。汪老著作给我带来的阅读快感和审美情趣,历久弥深,挥之不去。
观察世间百态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所谓阅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传统的读书,即读纸质图书。二是观察、记录、思考生活现象,即“从无字句处读书”。合二而一,就大致具备了写作所需的积累。
先说后者。汪曾祺在谈到沈从文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从文自传》中的一段文字:“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他之所以尤其在意《从文自传》中的这几句话,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告诉了我们,一个人要写出优秀的作品,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从1920 年 出 生,到1939 年考入西南联大,汪曾祺在高邮生活了19 年,他也从故乡嗅到了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从小就喜欢用一双眼睛去听去看,将各样的风俗人情、各种印象气味,留存在心里——高邮小城的人和事,始终是他小说创作的起点。
比如汪老就读的小学,原是佛寺的一部分,几乎每天放学,他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从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他总喜欢东看西看——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
除了家和学校,汪老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作“东大街”的街。那里曾经是高邮的繁华地段之一,属于城乡结合部,是联系城乡的水陆码头,是粮食、柴草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汪老曾回忆:
我熟悉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我熟悉中药的气味,熟悉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我熟悉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我熟悉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这种观察世间百态的习惯,从他小时候看父亲作画,至暮年在玉渊潭散步,汪曾祺持续了一辈子,并源源不断地从中汲取多种鲜活养分,受益不浅。
汪曾祺曾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正是因为秉持这样的写作态度,汪曾祺写花鸟虫鱼、美食美景,写凡人凡事、旧时掌故,其中充满着对小人、小事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对个体生活温情脉脉的打量。
阅读和积累
再说读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话有力地见证了阅读与写作的关系。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而写作的素材往往又来源于阅读中的间接感受。汪曾祺笔下呈现出的汪洋恣肆的文学世界,都是他博览群书的结果。
祖父汪嘉勋曾亲授汪曾祺读《论语》,教他写“初步的八股文”。父亲汪菊生在当地画画颇有名气,他从小就喜欢站在一旁看父亲作画。四五岁时,嗣母就教汪曾祺背诵《长恨歌》等古典诗词曲赋。上学后的寒暑假,家里请来老先生,为他开小灶,讲授古诗文。汪曾祺的国文成绩突出,一枝独秀,其来有自,画画亦颇了得。
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高北溟先生教汪曾祺国文多年。高先生很有学问,为人正直。他很喜欢汪曾祺,汪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老师所授的古文中,少年汪曾祺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与汪曾祺的气质相近。汪曾祺对高北溟感情颇深,他晚年写成的著名短篇《徙》,即为显证。
汪曾祺读的高中,是江苏名校——江阴的南菁中学。据汪老介绍,那是一座创立很早的学校,历史悠久。此校重数理化,轻文史,但他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相合”。
童年、少年时期,汪曾祺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成分,主要是打下了诗词曲赋和古文的坚实功底,受用终身。
读高二时,侵华日军占领江阴,高邮告急。汪曾祺随祖父、父亲离城,到庵赵庄避难,在那里住了约半年——这段经历,成为汪氏晚年成名作《受戒》的蓝本。借住小庵时,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日后,他说这两本书改写了他的人生,引他走向了文学道路,“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
1939 年夏秋之交,汪曾祺如愿以偿地考取了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汪曾祺都在泡茶馆、逛图书馆,看翻译的文史哲著作,尤其是小说。外国作家中,他受影响较大的是俄国的契诃夫和西班牙的阿索林。汪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他还读了一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他看不上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莫泊桑、欧·亨利,认为他们的作品要么厚重笨拙,要么离奇做作。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影响,那时写就的小说《复仇》和《小学校的钟声》,就有意识流的味道。晚年时的汪曾祺回顾这一段时期,认为年轻人写东西要多尝试,浓丽华美都不为过,不要一开始就流于平淡。但他也主张,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要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
1950 至1958 年,来到北京的汪曾祺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当编辑。因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风收集民歌,这让他有机会接触阅读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他说:“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因为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我大概读了上万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置”。他又多了一大块养分和积累。
也许是居住条件所限,汪曾祺藏书不多。但他终生喜欢阅读,跟他对烟、酒、茶的嗜好一样,至老靡衰。早年在昆明教中学时,他的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晚年在京剧院编剧本,单位的藏书被他翻了个稀巴烂,床前放一凳子,上面堆了一大叠书。
曾有位北京的青年问汪曾祺:“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汪答曰:“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并劝这个年轻人要广泛地吸收。汪曾祺阅读的一大特点,是特别喜欢看杂书,他自称看杂书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所用的时间,要多得多。
汪曾祺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讲草木虫鱼的书他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花镜》。讲正经学问的书,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也觉得好看,如《癸巳类稿》。他也爱读书论、画论,如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有些书无法归类,如《洗冤录》,至于《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类的著名笔记,更是他身边的常备读物,不在话下。
汪曾祺总结过读杂书的几种好处,不吝金针度人: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融入自己的笔下。这是我的一点经验之谈。青年作家,不妨试试”。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
兴趣与表达
汪曾祺是个特别注重个人兴趣、讲究表述方式的作家。
当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从文教创作,反反复复讲的一句话是:要贴着人物来写。很多学生都不大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照汪曾祺的理解,老师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需和人物相协调,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写农民。
闻一多也开了三门课:楚辞、古代神话、唐诗,他也都选了。直到晚年,他还对闻先生讲楚辞的开场白津津乐道、记忆犹新:“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闻一多讲神话,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连工学院的学生,都穿越大半个昆明城区,赶过来听课。汪曾祺尤其喜欢听闻一多讲唐诗。他充当枪手,代替同学杨毓珉写了一篇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闻一多夸赞:“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汪曾祺很早就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后来又领悟到,民间文学,包括戏剧,对书面语言的表现方式,很有帮助。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与散文的界限。老年时,又想提高京剧唱词的文学性。他认为:
小说就是回忆。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结构的原则是:随便。
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
对于小说的语言,汪曾祺认为,语言一方面承载着小说本身,另一方面小说也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表现内容,内容依赖语言。另外,语言和思想交融,无法把两者剥离开来。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在他看来,作为小说家,书面语言要少写,要在方言和民间文学中寻找语言的滋养。
又说:
我认为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琢磨,去思索,去补充。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包世臣论书以为当使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宋人论崔颢的《长干歌》“无字处皆有字”。短篇小说可以说是“空白的艺术”。办法很简单: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会更大了,传达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短了,其实是长了。少了,其实是多了。这是很划算的事。
汪曾祺的创作没有鸿篇巨制,《受戒》《异秉》等都是短篇小说,这一点,连汪曾祺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写不出来大作品,写不出来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但在汪曾祺看来,短篇小说的灵魂恰在其“短”,要做到短而精,短而深,短而有神,需要有高超的叙事技巧。
汪曾祺不擅长编故事,不习惯虚构,尤其不喜欢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他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大都有原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构思、发掘、剪接、拼合,加工添料,移花接木。他对各种生活细节尤为关注,记得十分真切。他一再强调:修辞立其诚。
他的写作习惯是:动笔之前,深思熟虑,先把结构、段落,包括用哪个词最适合,都想个差不多。然后聚精会神,一气呵成,很少再修改。他的手稿通常相当干净。想好了,就写,随时能进入状态,又随时能退出。写一阵,该做饭做饭,该参加活动就参加活动。事情做完了接着写,思路和状态一点都不受影响。这种功夫,这等火候,可谓炉火纯青。
知父莫若子。汪朗曾谓乃翁:“爸爸很少用华丽的辞藻,更不用一般人不熟悉的词句唬人。他所重视的是语感,是用词的准确性。他写的东西,就像高明的工匠做出的家具,材质不见得名贵,但是各个卯榫全都严丝合缝,很见功夫。”
汪曾祺是名副其实的“文体家”,对表述方式,开头结尾,起承转合,非常考究。写《徙》,开篇描述歌声,试过多次,都不满意。后来,如有神助,劈头便是:很多歌消失了。找到感觉,一挥而就。也有写到中间,涌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细节,比如《大淖记事》,他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鬼使神差来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这正是所谓“神来之笔”。写到这里,汪曾祺流下了眼泪。他强调说:“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
汪曾祺觉得,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是要不断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他的小说背景基本不外乎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只有这几个地方他住得比较长。
人间烟火味
有人称汪曾祺为“最后一个士大夫”。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汪老当然有个性、有闲情逸致,但他又是个相当平民化、人间烟火味浓厚、极有情趣的人。他的作品,亦复如此。他自许:“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说:人家写过,我就决不这样写。他坦言: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呼吁:“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他期待:自己的写作“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人间送小温”。
性情的温和与骄傲,对生活的随意与用心,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写作态度的无可无不可与不离不弃,文字的典雅考究与接地气,无处不在的悲悯与一种不可遏止的生命的内在的欢乐,在他的身上和笔下得到奇妙的融合与统一,浑然无间。他的语感,他的文字,是当代汉语文学精致与美妙的结晶。
此情可待成追忆,世上已无汪曾祺。作为读者,没能看到汪老更多更好的作品,包括说好了的《汉武帝》、那么多随风散佚无从收集的书简……难免心存遗憾,意犹未足。不过,转念一想,人生的最后17 年,汪曾祺用生命爆发,与时间赛跑,写出了那么多精良优美的文字,奉献给汉语文学一份无与伦比的成果,出了20 多种集子,已经极其难得。我辈实在应该欣幸、感激、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