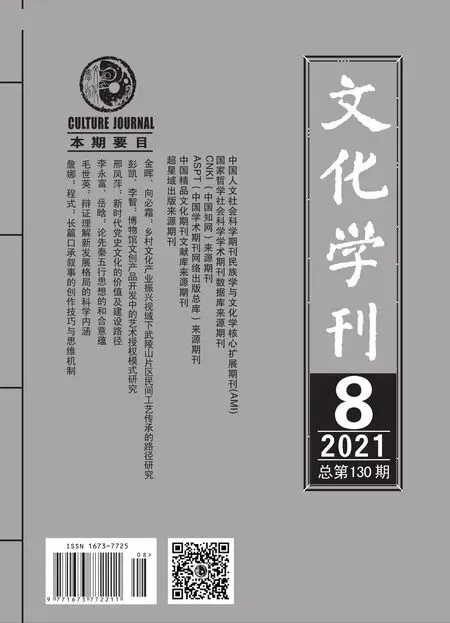从“息妫未言”看《左传》的女性话语体系
陈立芳
息妫,又称“息夫人”,是《左传》里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女性之一。因女性的美丽而引发纷争的故事在《左传》中不在少数,如著名的“骊姬之乱” “夏姬之乱”,息妫也是如此,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在《左传》的叙述体系里并未把其简单地划归 “女祸”之辈。在以男权为主宰的春秋时代,“息妫未言”究竟是对命运刚烈的抗争,还是无奈的沉默,在历史的文本书写和文学的价值重构之间,都给人留下了诸多遐想。
一、“女祸论”下春秋女性沉默的声音
“息妫”之文首见于《左传·庄公十年》: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1]。
蔡、息两国先后娶于陈国,息妫在出嫁途中经过蔡国,蔡侯却称其为“吾姨也”,言语轻佻激怒息侯。于是息侯向楚献策,借楚之力伐蔡,实则引狼入室,挑起了楚、蔡、息三国之间的征战,最终导致息灭亡,蔡沦为楚国附属的结果,楚国图霸之势由此而始。
引发这场纷争的关键是蔡侯称息妫为“吾姨也”的行为。息妫,作为蔡侯妻子的姊妹,蔡侯却未加礼敬,而是“止而见之,弗宾”。杜预对“弗宾”的注解为:“不礼敬也”。日本奥田元继《春秋左氏传评林》曰:“‘止而见之’,含蓄许多轻亵不可言者”[2]。究竟“弗宾”的行为是否仅此一句轻佻之语,还是有更多“不可言”处,左氏一贯冷静克制的笔墨并未详述。后世评家中也有质疑息妫“失礼”的观点,如王系《左传说》:“且妇人无外交,夫人之行,必有送者。蔡哀虽固欲见,夫人可辞,送者亦可辞,而皆不闻也。”认为息妫原本“可辞而不见”却见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番评论大有后世道学家们对春秋女性的苛责之意,实不足取。
其一,春秋时期所谓的“妇人无外交”并无绝对。相反,在《左传》里可以看到许多有着杰出政治才干的女性,如颇具外交才能的文姜,文采斐然可赋《载驰》的许穆夫人。事实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秩序混乱,却也给了女性更多机会参与政事。王系所言“妇女无外交”并不尽然。
其二,春秋时期“过邦之礼”是过境他国的惯常仪节,在这种情况下息妫出见并未违礼。[3]在《仪礼·聘礼》中可见对“过邦之礼”的解释:“若过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誓于其竟。”[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曰:“陈都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蔡都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故息妫由陈至息必过蔡。”[5]无论蔡哀侯对息妫是言语不敬,还是未行“过邦之礼”,都是失礼的行为。再从左氏以“君子曰”为代言的一段评述看:“《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则左氏对蔡侯的批评态度显而易见。
回到息妫的首次亮相,我们在文本中无从获知这个人物的品行个性,而仅有“她很美”的模糊印象。在这里,女性角色自身的语言是沉默的。
仅因“美”便引发动乱和纷争,类似的事件在《左传》中还有许多。比如,桓公元年传载宋华父督路遇孔父之妻,见色起意杀夫夺妻、弑君为乱。更为极端的例子是被视为“女祸”典型的“夏姬”。据宣公九年传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君臣三人同与夏姬淫乱,甚至穿着夏姬的内衣“以戏于朝”,可谓荒诞至极。楚灭陈后,楚庄王与其弟均欲纳夏姬,楚大夫申公巫臣屡次谏言:“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弒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然而,申公巫臣前番还在义正言辞地谏言楚王,转身自己却暗地谋划带夏姬出奔齐国。林纾在《左传撷华》里就尖锐地评论:“然巫臣竭其全副精神,及数年区画,全注夏姬身上。[6]”这里,女性的美被视为“不祥”和带来祸乱的原因,而冠冕堂皇说出一大篇“淫为大罚”的男性,实际却道德沦丧,自己既不相信也不奉行所谓的“明德慎罚”。女性的命运在男性的权力之间几经辗转且毫无自主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夏姬作为引发纷争的故事主角,在叙事语言里却同样是缺席的。我们几乎看不到她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只能通过男性视角猜度夏姬的“美”或“恶”。此外,来自其他女性的评判更让夏姬因美而“恶”的罪名看上去理所当然。晋国大夫叔向是羊舌氏的子孙,素有贤名,想要娶巫臣与夏姬的女儿,他的母亲马上出来劝阻。叔母把夏姬的罪名列为“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认为“甚美必有甚恶”,甚至连同夏姬的孩子,也天生继承了母亲的“恶”,并预言这个孩子会带来家族的灾难:“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结局正验证了这种预言,叔向受祁盈之乱牵连,羊舌氏终被灭族。李惠仪在《<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中就指出:“《左传》中有一些例子,因果关系并非不言自明。因此《左传》刻意把美丽放荡的女人铺写出来,把她们视作事件发生的‘充分理由’。……运用这套理论解释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假如一个人行为正直,他的家族怎么会惨淡收场?[7]”叔向因娶夏姬之女导致灭族之祸,女性在《左传》的叙事体系里扮演的角色似乎就是告诫君子们:远离“甚美必有甚恶”的女人,哪怕是她的女儿也不能靠近。
回顾《左传》里那些因美而“恶”的女性,会发现无论是引发三国纷争的息妫、让华父督“逆目而送”的孔父妻、还是“甚美必有甚恶”的夏姬,其实根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她们的遭遇反映的恰是春秋时期宫廷女性们险恶无比的生存状态:在一夫多妻制下,宫廷中为了争夺王权而引发的混战无一不充斥着血腥和杀戮,女性的生存与她们的丈夫、儿子荣辱共存,牢牢相连,或者说,女性完全依附于男性,斗争中的失败者面临的只有屈辱甚至死亡。《左传》里这种混乱的悲剧随时上演,如夫死子亡不得不哭着“大归”母国的哀姜,因自己无宠、子也无威的子叔姬,因野心而终致被杀、陈尸朝堂的戎子……这些女性在权谋斗争中或许并不都无辜,但把祸乱的因果简单推给女性,却是中国几千年来“女祸论”者的习惯罢了。鲁迅先生就曾说:“我一直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话。……向来的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到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8]。”美是原罪,息妫们别无选择,也无处辩驳。
二、礼制之下,春秋女性话语的有限表达
与美丽放荡的夏姬相比,息妫的美实难与“恶”相联。她给世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段“息妫未言”的故事。据庄公十四年传:
楚子如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继息侯向楚献策借楚伐蔡之后,蔡侯也如法炮制,“绳息妫以语楚子”向楚王赞誉息妫的美丽,楚王心动,“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息妫作为战争的战利品入楚,被封夫人,并为楚王生二子。这里左氏对息妫的一段描述颇令人玩味。按庄公十年传云,楚败蔡于莘,以蔡侯归是在庄公十年,在庄公十四年提及灭息之事当是追叙前文。杨伯峻注曰“此当是前数年之事,此年息妫则已生二子矣。”已生二子的息妫却仍“未言”,原因何在?按杨伯峻梳理,前代学者对息妫“未言”的注解主要有三:
其一:息妫“未言”,杜预注曰:“未与王言”。魏禧《左传经世钞》评曰:“息妫辱身尤能报仇,亦女中之杰。即其不言,想见坚忍之志,惜欠一死耳。”魏禧认为息妫“不言”是坚忍之志,但没能以死决绝,在今天看来此种评语尤显冷酷,并不足取,但也可见其观点同杜注一致,息妫“未言”即没有与楚王说过话。
其二:息妫“未言”,乃未先言。也就是息妫入楚从未主动开口说话。息妫入楚后即为楚王生下二子,两三年间却未说一字,似乎不符人情实际。杨伯峻引《礼记·丧服四制》曰:“礼,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认同郑玄注:“言谓先发口也。”
其三:俞正燮《癸巳存稿》以未言为守“心丧礼”。《尚书·无逸》云:“昔在殷王高宗,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但这里的“三年不言”之丧礼,当为嗣王为先王的守丧之礼,不应为夫人之礼。可见,俞之论点并未可靠。
此外,钱钟书还提出了第四种观点,认为息妫“未言”含义类同僖公十三年传:“齐仲孙秋聘于周,且言王子带,事毕,不与王言,注:‘不言王子带’”,乃息妫不愿与楚王再谈及息为蔡构害之往事,“言之无益,不如无言”[9]。以上四者多从文字训诂、礼仪考辩的角度对息妫“未言”加以解释。再看前代学者的评注中也有类似魏禧认为息妫“惜欠一死”的道学家言论。如吴曾祺《左传菁华录》:“息妫一言,而蔡侯为虏,亦足以见亡夫于地下矣。虽失节之妇,吾有取焉。”把息妫“未言”视为“失节之妇”的羞愧心里,似乎息妫不死便是“失节”,此类评注已近乎“恶意”。
那么,息妫所言“事二夫”是否就违礼呢?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女性在征战之中往往如物品般被抢夺、被转让,在婚姻上根本没有自主权。同时,这个时期还未形成宋明时期那样的女性贞洁观,对女性再嫁也未有明确的礼法限制。就像夏姬辗转三嫁一样,息妫的遭遇可以说非常普遍。还有在春秋时期频频出现的“烝”“报”现象,也反映出当时的礼制并不反对妇女再嫁。顾颉刚先生在他的《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里对此有过专门考辩。这样看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息妫 “事二夫”并不违礼。
不违礼,却不意味着“礼”会对女性宽容。《左传》里随处可见“礼”对女性行为道德的种种规定。比如恒公十八年传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杨伯峻注曰:“意谓男各有妻,女各有夫,宜界限谨严,不得轻易而亵渎之。”僖公二年传曰:“女子,从人者也。”按《仪礼·丧服》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凡此种种都在强调女性如同男性的附属,没有独立人格可言。再如,昭公二十六年传曰:“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婉;妇听而从,礼之善物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柔而正、慈而婉、听而从”、是男女有别、是三从四德。其实,《左传》反复出现这些“礼”的声音,与左氏欲“以史传经”的作传主旨是一致的。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中认为:“孔子试图以写作正视时局的混乱与暴虐。左丘明则试图通过解释《春秋》来澄清混乱的阐释,恢复《春秋》的‘真意’”。因此,左氏常把人物命运、国家兴衰都纳入“礼”的体系中评判,对女性人物也是如此,合不合“礼”便可预示她们命运的吉凶祸福。比如,文公四年传记载的哀姜,鲁国未按应有的礼节迎娶,便注定了她未来的悲剧结局:
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
按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曰:“恒三年传例:‘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敌国上卿送女,则逆女当然,故传以卿不行为非礼[10]。”依礼,鲁国应由上卿迎接哀姜,而实际上却“贵聘贱迎”,这种“卿不行”的违礼之举直接预示了哀姜的命运:夫亡子杀,自己无奈哭着 “大归”母国。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女性因守礼而受到奖赏。比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侯战败归来,路遇辟司徒之妻,其妻先问君、再问夫,因有礼而受封赏土地。可以说“礼”是春秋时期对女性的道德评判标准,甚至这点也得到了女性自觉的认同和遵循。比如襄公九年传记载的鲁宣公夫人穆姜,不仅与卿大夫叔孙侨如通奸,而且屡次谗害季、孟二氏。这样的人临死前却极为清醒地忏悔,认为自己“四德”皆无,“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吊诡的是,在道德混乱的时代,毋论女性守不守“礼”,“礼”其实都未能给到她们切实的保护。这便是息妫们的艰难之处:女性在婚姻里毫无自主的可能,只能被掠夺被侮辱,“一女二夫”虽未违礼,但在当时社会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规定和女性的自我认知中,依旧意味着屈辱和不贞。春秋初期,陈、蔡、息三国同属“汉阳诸姬”,利益交织,命运同体[11]。三国通过婚姻取得联盟,并不奇怪。息妫在此背景下嫁给息侯,历经了国亡被虏的坎坷命运,最终的归属却是让她遭受亡国之痛的楚文王。再嫁哪怕于礼不背,却改变不了被侮辱、被掠夺的事实。息妫们的“未言”或“言”,展现的恰恰是那个时代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唯一可以抗争的或许仅是对掠夺者反问一句:“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三、文本之下,春秋女性真实的声音
《左传》里记录了两百六十多位春秋女性,或许息妫的特别并不在她的美丽,而在她不愿迎合的姿态。在男权为绝对主宰的春秋时代,大多数女性的声音都被压抑、被遗忘,也有少数于左氏的文本书写中保留了下来。于是,前文中“未言”和“惜言”的息妫,却在庄公二十八年的传文里有了一段近乎愤怒的哭诉: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
庄公十九年,楚文王因伐黄之役负伤而卒。庄公二十三年,息妫次子熊恽继位。“子元欲蛊文夫人”这段出现在庄公二十八年。那么,即便按息妫入楚即生子来算,此时成王也未到二十岁,羽翼未丰,而楚文王之弟令尹子元当权,息妫在楚宫的生存境地可以想见。在“子元欲蛊文夫人”句下,孔颖达疏曰:“昭元年传,《周易》:‘女惑男谓之蛊’知蛊谓惑以淫事也。”子元为得到息妫,不仅“置馆于侧”,而且习万舞吸引美人关注,可谓费尽心机。前文中息妫再嫁楚文王,被封夫人,至少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而此处左氏仅用“欲蛊”二字便尽显子元的猥琐和不堪。如果说面对楚文王,息妫是以“未言”的沉默来反抗,那么面对子元的猥琐,她只好以楚文王的名义,用近乎悲愤的哭诉警戒子元。且不论息妫是真的对楚文王追忆难忘,还是为了阻止子元不得不采取自保策略,从后文看这么做似乎有效:子元幡然悔悟,感叹一个女人都能不忘报仇,自己一介男儿岂能甘拜下风:“妇人不忘袭雠,我反忘之!”子元出兵伐郑,到底是因息妫的哭诉发挥了作用,还是为了取悦美人而故作姿态,蒋铭《古文汇钞》里有一段评注可谓切中肯綮:“勉强出师,聊以解嘲。其意专在速归蛊文夫人耳。至无功而还,身陷大戮,天道罚淫,信不爽也。”果然,据庄公三十年传载:“楚公子元归自伐郑,而处王宫,斗射师谏,则执而梏之。”在“而处王宫”这句下面杜预注曰:“欲遂蛊文夫人”。息妫的哭诉,显然效力有限。
今天,无论怎样从文字训诂、礼制考辩、或者文学解读上分析,传意本身和后世解读之间,都永远存在时间沟壑。我们难以还原息妫的声音,正如把“息妫未言”解读成女性意识的觉醒很可能就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钱锺书便认为《左传》“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显然,无论是“甚美必有甚恶”的论调,还是以“礼”作为评判女性的标准,左氏的这种“添枝画叶”都有着自己的话语体系,每一位读者又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隐含在文本叙述背后,春秋时代女性们微弱的声音终于还是穿越千年,余音回响,让后世有了走近她们的可能。
四、结语
《左传》塑造了许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但她们的声音往往在传统的“女祸论”中被淹没,在男权为主导的“礼制”包围下被压抑,又在文本书写与解读中被不断重构。“息妫未言”展现的恰恰是那个时代女性话语权的丧失。抛开“女祸论”的传统偏见,方能理解何以在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礼”依旧对女性有着严苛的主宰,这也是穿越《左传》文本书写,走进历史真实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