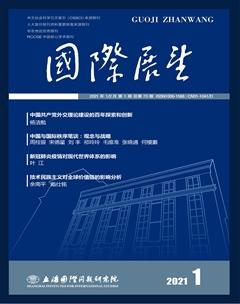“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内容摘要】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 四方安全对话 印太战略 三边合作 地区秩序 东盟方式
【作者简介】 刘阿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20)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1-0088-22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1005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或“四方对话”)机制沉寂多年之后于2017年再度“复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在此之前,虽然它们之间的三边和双边合作取得了进展,但四方对话和联合行动却未出现。对于该机制的重启,既有充满担忧的批判性观点,又有乐见其成的积极评价。无论如何评价,该机制都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和政策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演变,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与2007年的首次出现相比,重启的机制具有哪些新特点?经过三年的演进,它对地区以及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前景进行研判,并进一步分析在新的地缘战略形势下,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再次出现的地缘战略安排。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复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实际上,四国合作最早始于2004年12月。彼时,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促使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快合作,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救援行动。在当时合作的基础上,2006年,安倍晋三在其当选日本首相几个月前,首次以“民主国家的集合”之名提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概念,[①]得到了另外三方的响应。2007年5月,利用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议之机,四国官员低调举行了会晤。同年9月,美、印在“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中将澳大利亚、日本与新加坡纳入,实现了首次扩容。
Quad的出现引起了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分别与其目标指向及主导国有着最大安全关联度的中国和韩国的关注和担忧。作为对这种关切的积极回应,2007年11月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明确表示,澳不会再次提议针对中国的四边对话,四国会议是一次性的。[②]随着澳大利亚的退出和安倍晋三的辞职,Quad的合作也隨之搁置。
此后十年间,尽管四方对话和联合行动没有出现,但四国内部的三边和双边合作却取得了进展。三边对话被认为是夯实双边并进一步拓展四边关系的工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始于2002年的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和2011年开始的美、日、印三边对话,特别是2015年日、印、澳首次举行的三边战略安全对话,被看作是“加强了一种‘四边式伙伴关系再次出现的重要趋势”[③]。在双边层面,除了美日、美澳传统同盟关系得到加强外,日澳之间也建立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2+2”)定期会晤机制,实现了所谓的“辐—辐”联系,促进了双边防务合作的持续升级。更值得注意的双边关系动向是美、日、澳三国分别与印度关系的跨越式发展。自2007年以来,美、印签署了数个军事、情报合作协议,提升了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2014年9月,日、印建立了“特别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并于2016年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日本首次在防止核扩散这一核心外交政策原则上做出妥协;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印澳战略关系迎来大发展,双方签署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并于2017年建立“2+2”对话机制。与此同时,三边和双边的实质性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也在增加。[④]此类联合行动显然超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同盟体系,在四国间建立了多重合作关系,提升了协作能力,并反过来为更深入的政治互信奠定了基础。[⑤]
伴随三边和双边互动的强化和升级,Quad于2012年12月再次正式成为各国政府层面讨论的问题。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建议美、日、澳和印度合作,“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广阔的……民主安全菱形。”[⑥]2017年11月,在东亚峰会举行之际,美、日、澳、印四国外交官举行了十年来的首次会晤,会后各自发表声明,表达对Quad的支持。美国宣称,与日、澳、印的“四边磋商是美国推进地区接触的新里程碑”[⑦]。澳大利亚认为,“Quad对于澳大利亚和地区都是一个重要的合作平台”[⑧]。相对而言,印度对于Quad的态度更加谨慎,但也表达了对“印太”区域内更大的多边合作的期待。四国迄今已举行了六次会晤,不仅将会晤级别提升到外长级,而且不断扩展新议题,既包括对各自“印太”地区愿景的讨论及对地区秩序原则的重申,也涉及具体的海洋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协作领域。
Quad的新发展基于其固有的历史轨迹,因而此次其再现被称为“Quad 2.0”。自重启之日起,对Quad的评价主要有两类。一是充满担忧的批判性观点,认为Quad将无法显示作用和发挥影响。一方面,虽然四国之间在利益上有共通性,但鲜有迹象表明它们具有协调一致的战略优先目标,即使是美国也未必始终将遏制中国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由于Quad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其理念的分裂性和对抗性不仅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而且也得不到地区内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的支持。[⑨]二是乐见其成的积极评价。一些学者认为,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过去十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中国力量的增强及其在领土诉求上的立场是四国之间加强联合的关键驱动因素;此次Quad的重启是以“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对地区事务频繁的讨论和协调行动为基础的,必将使四国合作进一步加强。[⑩]中国学者往往以更加理性和特有的中国视角对Quad的重新活跃进行分析,认为四边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明显有针对中国崛起之意,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峻挑战,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尽管Quad未来仍面临一些挑战,但中国应警惕其战略意图并审慎加以应对。[11]
二、“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
相较于十年前的稍纵即逝,Quad此次三年多来的发展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并对地区战略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加以认真分析与研判。
(一)新版“四方安全对话”的特点
第一,Quad升级版具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即与中国对抗。这与十年前的Quad具有明显的区别。此种变化源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是为了阻止美国进入(印太)地区”。[12]次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继续追求军事现代化,以便在短期内取得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定义为国家威胁,而美国的国防任务之一就是以“扩展同盟和伙伴关系为主要战略手段”,达到“维持印太地区力量对比优势”的地缘战略目的。[13]2020年5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罗列了所谓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领域“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将中国界定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和美国生活方式造成威胁的国家。[14]美国是四国中唯一直接将中国贴上“敌手”标签的国家,并将Quad称为“一个绝对恰逢其时的想法”。[15]
相应地,其他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的担忧。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国,日本对中国“威胁”的渲染一开始就出现在安倍晋三“民主安全菱形”的提议之中,并一再扬言要关注中国在亚洲的军事能力和意图。日本2020年度《防卫白皮书》用整整34页分析中国军力,声称中国军力快速增强,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升级,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影响。[16]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正在上升到与美国相匹敌甚至在某些时候高于美国。”[17]“自2016年起,主要大国在促进其战略偏好和寻求发挥影响力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包括中国积极寻求在印太地区更大的影响力。”[18]为谋求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上升也相当警惕,并不断强调两国之间力量的“不对称性”。显而易见,虽然尚未形成一个明确针对中国的同盟,但四国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以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为目的。四国形成的菱形地缘分布具有一种潜在的地理优势,使其能够作为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合作机制,协调各方战略,阻止中国以地区“霸权”国家出现。[19]
第二,“民主价值观”成为Quad秩序构建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认为,“所有的Quad成员都是民主国家,这是其最突出的特点。”[20]这一点其实与十年前并无不同,之所以在今天被突出强调,是因为新版Quad试图以“民主价值观”作为整合、构建地区秩序的战略抓手。首先,以价值观为基准界定朋友和敌人。早在2007年Quad首次出现前后,美国战略界就大张旗鼓地讨论过“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声称要建立一种民主国家间的协调一致,在欧亚大陆及以外地区加强自由民主体系,以应对非民主国家造成的问题或威胁。[21]“四方对话”不仅被定义为“世界上四个最大的民主国家”间分享关于地区安全看法的平台,强调四国价值观的共通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协作关系和相互信任,而且在国家间关系中以价值观为标准,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分野,并以此确立对立的战略思维。其次,凸显“民主价值观”对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各种场合都被美国大力渲染。在2017年11月第一次会议之后美国发表声明称,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原则,四国伙伴承诺加强合作,并将继续讨论进一步加强在“印太”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22]在2019年1月印度瑞辛纳对话中,首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表示,Quad“有着25年渊源的生机勃勃的关系……在过去70多年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为我们所有国家带来了和平与安全……”[23]Quad被看作是民主伙伴国家为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而进行磋商的重要手段。通过在所谓“共同的民主价值与原则”基礎上寻求建立“印太”地区秩序,Quad实质上打破了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奉行和持续推进的开放的地区主义进程,将地区国家以价值观划线,渲染地区存在所谓“自由”和“压迫”两种秩序之争。[24]
第三,Quad构成更宏大战略,即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5]在2007年四国首次会晤之后,安倍晋三就在印度国会发表了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宣称“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正形成一种自由与繁荣之海的动态结合。”[26]这可谓“印太”的粗浅表达。十年来,随着自太平洋西海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广袤区域日益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心,这一区域的“印太”标签和所谓“印太战略”更为世界所熟知。Quad的重启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不仅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而且在理念和效用上协调一致。一是推动对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FOIP)理念的认同。这一理念由安倍晋三于2016年首倡,之后得到美国的强调和支持。在2018年6月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四国均阐述了各自的“印太”理念,“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尊重国际法等成为共同要素,FOIP理念得到了Quad所有成员国的支持。[27]二是成为践行“印太战略”的重要方式。“印太战略”的实施有赖于盟国与伙伴的支持,为此美国正在重新赋予其盟国活力、加强与伙伴国的联系纽带。在美国同盟体系的支持下,Quad以更大的灵活性、相对低的交易成本和自愿而非约束性的承诺方式,加强美国对伙伴国的非对称性控制,并防止其被拖入不希望介入的冲突之中。[28]
第四,加大对发展和治理的投入,以配合战略实施。自第二次会议开始,四国在声明中特别列出了“发展和互联互通、良治、地区安全(包括反恐和防扩散)、海上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等内容,尤其强调“可持续的、私人领域主导的发展、海上安全和良治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29]。
目前,四国已经在“印太”地区开展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美国共同宣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设电网;在“印太”商业论坛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确认三国将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即实施“蓝点网络”计划。四国在“印太”区域内的总援助额已经达到数百亿美元。[30]有学者甚至称,迄今为止Quad所进行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扩大了成员国之间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合作范围。[31]此外,四国投资与发展合作还着眼于追求特定的“标准”。2018年11月,第三次Quad会议表达了对透明度、真实需要和可持续债务负担的关切。次年5月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美国主办了四国+印尼政府官员会议,讨论了需要通过透明的金融来进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同时强调新的基础设施融资计划。[32]透明、高质量、与国际标准一致、利用私人机构等“标准”也在2019年Quad会议时成为四国共同的关切,四国表示要继续协调一致和密切合作,确保可持续的私人领域的发展、海洋安全以及良治。[33]可以说,Quad 2.0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十年前的经验教训,议题设置更加多元,其目的在于全方位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意欲从更深远和全面的角度发挥地區作用。
总之,与十年前相比,Quad 2.0保持了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价值观基础,并在美国的战略引导下,将中国作为现实威胁因素,以促进四国间开展密切和全方位的地区合作,具备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基础。[34]
(二)新版“四方安全对话”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各领域合作加强了四国间的战略联系,提升了国家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四国频繁的军事演习、战略对话、技术协议和协调行动,有助于培养合作的习惯、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过去三年中,四国间的军事活动、信息与情报交流快速增长,创造了历史新高。自2018年美、印举行首轮“2+2”对话后,四国中的每两国之间都确立了“2+2”对话机制,与已建立的三对三边对话机制相互补充,加强了彼此间的战略沟通。美、日、澳、印战术协作能力也在提高。美、印、日“马拉巴尔”和美、澳、日“护身刀”从双边演变为三边联合军演后规模不断扩大,参加演习的武器水平和装备通用性持续提升,三国海军的整合度和协同作战能力日渐加强。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印度一改之前态度,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使四国协调得以强化;美国也在考虑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空中力量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进行联合训练,并寻求提升四国海上力量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第二,在既有合作基础上,四国纷纷将战略触角拓展至更多的议题领域和更广阔的地理范围。正如美国《亚洲再保证法》中所称:“美、澳、印、日四国间的安全对话对于在印太地区应对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战是关键性的。”[35]“四方对话”被视为“印太”地区地缘战略的倍增器,是实现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首先,Quad在议题领域将合作重点置于“高政治”领域——南海。四国或以“自由航行”为名派遣军舰在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或以所谓“南海军事化”为借口,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扩建与防御设施建设。[36]对于华盛顿来说,Quad实践了美国“印太战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总体安全目标。[37]其次,基于Quad的三边或多边协调开始积极向“低政治”领域扩展。2018年7月,美、日、澳宣布建立“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同年11月三国签署《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共同动员和支持私营部门在“印太”地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强数字互联互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美、日、印则在三边对话框架下设立了基础设施三边工作组,并就开发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达成意向协议。[38]在发展领域,美国借Quad升级之机加大对湄公河次区域的投资,强化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2020年9月,美国会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湄公河五国,将2009年建立的“湄公河下游倡议”合作机制升格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既有的35亿美元地区性援助的基础上,今后几年再投入数十亿美元,并宣称要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密切合作,对冲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39]
Quad的重启也为其非主导成员国扩展地区战略创造了条件。由于历史问题,日本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一直有限,这被日本很多右翼政客视为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高科技强国的地位不相称。Quad的恢复强化了日本在谋求地缘政治大国方面的野心,使其有机会将经济与军事技术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和战略影响。日本借与澳、印进行频繁军事演习之机在南太平洋、南海海域和印度洋海域进行军事力量投放演练。2020年6月,日本更是修改《信息分享法》,允许与澳大利亚、印度以及英国分享情报,并在防卫省设立新机构,用以在东盟和太平洋群岛事务方面加强与印、澳的协调。[40]此外,从“亚太”扩展到“印太”本身是基于一种现实判断,即印度将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美国鼓励“印度作为一个主导性全球力量和更加强大的战略和防务伙伴出现”[41]。印度通过与日本加强海上安全协调,进一步将触角延伸到西太平洋区域。澳大利亚外长佩恩(Marise Payne)也坦言,澳期待“今后更加密切地与印度接触来支持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伙伴”[42]。印度洋与南太平洋的结合是印、澳两国都希望看到的战略拓展。澳大利亚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强调在印度洋的利益,包括保护所谓“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和搜救区域、离岸领土和关键的海上通道”,为此计划在国防设施上投资10亿美元,以期在西澳大利亚部署小型护卫舰、离岸巡航舰艇以及潜艇。[43]
第三,在外交上释放政治信号。四国以团结一致的方式表达共同的利益诉求,具有一定的外交象征意义。[44]在各自的声明中,四国均表达对共同议题的关注,从最初聚焦地区安全议题,如遏制朝鲜核武器项目、海上安全等,到后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发展;同时在理念上也显示出相当大的共性,即强调在“印太”地区促进一种基于规则的秩序、促进地区内的自由价值观。四国对于理念原则的支持和针对特定议题所进行的小多边联合行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一定的“弱结盟”特點。[45]这是“一种松散的地缘战略联盟,各国关注中国对其利益的潜在挑战,但却不以有强制力的同盟机制来刺激中国。”[46]因此,虽然Quad以表达决心的象征意义以及实质性行动强化了其特定指向的威慑价值,但四国仍不期待将Quad提升为正式的军事联盟。相反,它只是表达了在与第五国(也许是中国)发生紧张关系或军事冲突时,四国至少做好准备相互帮助。[47]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种形态会在短时间内发展为正式的多边同盟机制,Quad释放的一致性政治信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止步于象征意义,对实质性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较为有限。[48]
第四,加强美国在地区同盟框架及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性作用,以此回应美国衰落之说。Quad从两个方面体现了美国的主导性。一方面是体现了特朗普政府[49]所认同的同盟形态,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地区同盟的演变趋势。Quad符合特朗普总统蔑视多边主义、抱怨盟友和伙伴“搭便车”、坚持“公平分摊责任”的态度。[50]“(让)盟友(和伙伴)为美国可持续的地区战略接触贡献更多”显然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51]美国要求地区盟友和伙伴对其安全作出更多贡献,Quad正是澳、日向美国政府证明它们承担各自安全责任的一种方法。[52]另一方面是维持美国在同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从地缘位置还是从战略力量而言,四国的结合都将对区域内的力量均势产生影响。美国需以“印太”地缘概念为基准,在中美竞争的大视野下维持甚至加强对地区同盟体系和具体安全事务的主导权。通过鼓励次级盟友即各个“辐”之间选择性地彼此合作,Quad对正式、长期的双边同盟发挥了有效的补充作用,其排他性也保持了美国对亚太双边同盟框架一贯的控制力。同时,借促进盟友和伙伴间的沟通互动,美国向其盟友和中国显示决心,加强对那些所谓受到中国“威胁和霸凌”的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支持。[53]
三、“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走向
Quad重启是地区战略框架的显著变化。尽管其特点也对地区安全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迄今为止四国尚未发表共同声明或联合公报来展示对未来的共同规划,更不用说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或设立共同的协调机构。从其缘起背景和演变轨迹来看,Quad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内生性制约、特定成员国的作用和地区战略环境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Quad的内在局限性决定了四国难以形成更加紧密的同盟型关系
第一,共同目标飘忽不定。较之十年前,虽然Quad整体的安全目标相对更加聚焦于中国,但“四国之间没有能够共同分享的、单一的关键性国家利益”,[54]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共同优先目标。安全因素构成了同盟战略产生的最初和最主要动机,但是,安全利益并非国家的唯一利益,尤其是在当前地区安全认知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即使日、澳、印三国均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单一双边关系,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多排在第二位,甚至超过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美国的地区盟友还是印度这种非盟国,考虑到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依赖,都不愿看到与中国的关系过度紧张,均试图避免正式的多边安全承诺。[55]换言之,Quad这种伙伴关系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从属于其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只有当地区冲突涉及使用武力的时候,四国才会寻求一种更新的目标。即便如此,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将把它们的全部努力放在利用现有的双边安全同盟,以回应一个主要的、小幅升级的军事活动。[56]
第二,威胁认知差异。在缺乏共同的、相同程度的战略威胁感的前提下,四国之间相互依赖不足,“亚洲版北约”的形成绝非易事。一个国家通过观察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来评估其“品格”(忠诚或不忠诚),尤其是当一个国家评价另一个国家是否支持非条约义务时,具体的国家行为将是一国判断另一国忠诚与否的标准。[57]澳大利亚是2007年制约Quad发展的主要原因。陆克文曾在回忆录中详细阐述了当时澳大利亚退出的考虑,包括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历史包袱、未来两国与中国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以及这种“四边同盟”方式会给澳美双边同盟带来的影响。这些质疑仍然是今天Quad 2.0需要面对的问题。印度政策精英依然对澳中关系未来进展顾虑重重。而澳大利亚内部对Quad价值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致,一旦新政府执政,政策延续性可能生变。[58]为了避免成为“反华急先锋”,印度曾连续三年拒绝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军演,印澳关系也被认为是四组双边关系中的最大的短板。当然,四国之间的地缘战略算计将因时、因地、因事而发生变化,但国家间战略上的不信任将是持续的影响因素。
第三,政治环境变化对主导国领导意愿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一方面倾向于在西欧和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却加大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和介入。“印太”作为美军地缘政治的重中之重,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军事战略精心经营的目标区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美国在经过长期酝酿后正式推出“印太战略”,并对Quad进行升级改造。Quad 2.0与十年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美国大力推动并主导了这一演变过程,以期在诸如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南海问题上,突出Quad在军事方面的作用。[59]然而,美国政治周期的变化同时也对Quad的发展提出了挑战。2021年的新政府如何看待这一安全安排,以及以何种方式展现领导意愿,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四国对于Quad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的官方解读并不相同。[60]印度和澳大利亚更多将其看作是“印太”地区众多多边安排之一,不愿对其赋予任何特殊意义。[61]因此,雖然美、日最初希望将Quad的合作级别提升至部长级,但印度一直反对。[62]随着后续发展,也许这种姿态会有微调,例如,2020年11月举行的“马拉巴尔”军演变身成为四国联合的形式,但是,无论是从参演装备和人员规模,还是从官方和媒体的宣传来看,联合演习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可以说,只要印度等国依然避免将四国合作塑造成为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联盟,这种低层级合作就不会有实质性改变。面对“不情愿的参与者”,即使美国也不急于将Quad转变为一个“反华集团”。[63]
(二)印度的影响
链条的力量受制于其最薄弱环节,即所谓的“木桶效应”。在Quad中,印度是公认的最弱一环,在某种程度上,Quad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印度的态度。印度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力量最弱,与其他三国相比,印度海军及整体军事力量是最弱的一方,印度的武器系统并非依赖美国,短期内无法实现与其他三国在军事上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其合作意愿最弱,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而且高度重视“战略自主性”。[64]作为四国中唯一没有与美国缔结同盟条约的国家,印度认为,与一个大国结盟会将自己置于另一大国的对立面。莫迪特别强调,“印度不会把印太地区看作是一个战略或一个成员有限的俱乐部,也不是一个试图寻求主导的集团,更不会直接反对任何国家,印太的地理定义本身就不能如此。”[65]虽然印度与美、日、澳的安全联系的深化促进了Quad的回归,但是,印度对Quad的看法具有多面性,既希望借其平衡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影响力,又不愿支持Quad获得更大的地区主导权,更未表明已准备好在南海或西太平洋区域与其他三国共同采取实质性军事行动。当被问及四国是否要建立一种常备军事任务集团或设立一个联合司令部时,大部分印度受访者给予了否定回答。[66]这意味着未来Quad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发展成有制度约束力的多边联盟体系。
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印度有可能越来越重视Quad的战略作用。首先,Quad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军事实力。美、日有着先进军事技术,与Quad的合作将帮助印度在广阔的印度洋区域获得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从而增强实力。2017年的日印《防务装备与技术转让协议》和2018年的美印《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使印度在国防科技和军事技术转让方面获得了两国支持;2019年美、印又签订重要防务协议,印度将从美国采购系列先进武器装备。其次,作为“东向政策”升级的一部分,印度希望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Quad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小多边平台。澳大利亚的战略位置重要,在信息收集和潜艇战力等海洋军事技术能力上不容小觑。印、澳之间在2015年建立了年度海洋对话、2017年建立了“2+2”会晤机制,并在近三年中加强了互动;2018年,印、澳空军相互加入对方的空中和海上军事演习,双方战术协调不断增强。再次,印度是Quad成员国中唯一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的国家。2017年上半年中印“洞朗危机”与下半年Quad的回归并非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2020年两国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冲突虽然结束了军事对峙,但此类事件无疑强化了印度国内主张警惕和制衡中国的强硬派立场。面对两国实力上的差距,Quad被印度寄予更大的希望用于遏制中国。[67]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印度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无论是中印矛盾、印巴矛盾构成的现实威胁,还是对保持在孟加拉湾甚至整个印度洋区域战略优势的渴望,都可能促使印度以更大的决心参与Quad。当然,这种决心更多来自其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对互惠伙伴关系的期待、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而非被动地被Quad牵制。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所称,“印度的愿景……必须通过自己的叙事和理念,找到更加清晰的表达方式……关于利益扩展,印度真正能发挥影响的地区仍然是印度洋,这一事实没有改变。”[68]可见,尽管在战略上存在重视Quad的动力,但印度仍将以自己的节奏进行具体的政策安排,而印度对Quad的承诺无疑将决定四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限度。
(三)次区域战略空间能否容纳Quad的成长
东南亚的历史表明,没有东盟的支持和参与,地区政治或军事合作框架常常无法发挥持续的影响力。东南亚处于印度洋、太平洋两洋交汇点,是Quad的关注区域,也是采取行动的核心区域。这一对话机制最初就引起了东盟的注意。东盟对Quad的认知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一是东盟特有的政策偏好,即“东盟方式”。由于东盟自身的多样性,其对Quad针对特定目标的安全同盟形式并不认同,也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Quad的排他性合作特点,显然不符合东盟包容、开放的地区合作理念。二是对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担忧。如同担心Quad被用作对中国进行“软遏制”一样,东盟国家对于这个新多边集团可能损害其在地区的中心地位和团结一致表示疑虑。[69]一些分析认为,只要东盟仍然以亚洲地区主义的驱动力量自居,任何正式的四国安排都将遭到其反对。[70]虽然美、日、印、澳均处于东盟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架构之内,但考虑到以东盟为中心建立的亚太多边机制在处理如南海问题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现实,[71]Quad将拥有比“清谈馆”更多的军事能力和实质性举措,可能在安全领域产生更大影响,甚至削弱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主导性地位。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亚洲多边主义秩序的建设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东盟能否保持其地区中心地位并重新证明其能力,无疑是一种考验。[72]随着《东盟印太展望》的发布,东盟已经接受了“印太”这一事实,说明其外交未来将致力于在更大的地缘空间中纵横捭阖。对Quad的价值,东盟各成员国之间存在迥然不同的观点,反映出当前地区战略环境的复杂性。[73]Quad之所以对某些东南亚国家有一定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希望进一步扩展海上军事能力,以期在海洋和陆地领土争端中争取最大利益。Quad成员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技术能力、先进的装备以及后勤和训练技术,已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加强军事关系的目标,如越南等国纷纷加强与美国、印度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则是从经济利益和地区治理考虑,Quad成员国的市场巨大,各国宣布的对东南亚次区域和落后国家的投资计划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例如,日本提议的湄公河发展援助得到了泰、越、柬、老、缅等国家的支持。2020年3月,四国官员讨论了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新西兰、韩国和越南首次加入,形成了“4+3”对话模式。在可见的未来,东盟国家根据不同领域有选择地与各个区域外国家进行合作,已成为一种趋势。[74]新加坡对Quad的评价有一定代表性。2018年5月,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称新加坡至少现在不会加入“印太战略”或Quad,因为Quad并没有完全回答各国对于“东盟中心地位的疑问”。[75]可见,只要Quad仍然在功能、理念和制度建设上存在损害东盟中心地位的倾向,东盟主导的次区域战略空间将无法容纳其成长与发展。
综上所述,Quad混合了局限性和成长性两类因素,其发展前景有待进一步观察。可以肯定的是,Quad机制化的机会并不大。虽然美国公开声称,华盛顿的目标是将“四方安全对话”组织正式化,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组织,用结构化的方式吸引“印太”地区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以共同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仍需要其他成员国的坚定意愿和积极配合才能实现。[76]显然,从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发展到一种事实上的同盟仍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目前Quad既无可能也无现实条件转变为一个机制化的行为体。[77]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调查显示,虽然四国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接受将定期的部长级会议作为首脑会谈的补充,但在是否支持建立某种永久性的Quad秘书处并由四国轮流担任主席这个根本问题上,各国反应不一,大多持怀疑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Quad充其量只是一个缓慢的“聚合”而非快速机制化的过程。[78]
四、中国的应对
作为中国周边最具争议的地缘政治安排之一,Quad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是随着中美紧张关系加剧,Quad针对中国的功能有可能被逐步激活,对此中国需更积极和审慎应对。可以说,当前决定Quad前景的最大單一因素仍然是中国。为了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应努力从战略角度影响Quad的发展。
第一,针对Quad的内在局限性,应进一步扩大各国的威胁认知鸿沟。美、日、印、澳四国间正式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成反比。在“印太”国家中,在与中国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之间寻求平衡的做法日益盛行,尤其是后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显得更加脆弱已是不争的事实。[79]因此,保持经济手段的影响力,并将冲突限制在一种可控的范围内,无疑是中国外交亟须达到的目标。
中国需要不断扩大澳大利亚和印度“两面下注”的空间。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促使两国放弃Quad这一小多边安全合作方式,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地鼓励它们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并强调两者并行不悖,而非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更不能主动迫使两国更深地依赖Quad。虽然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结构性难题,中、澳之间也有需要认真对待的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总是会把自己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永远的战略优先选项。通过在多个伙伴之间“两面下注”以维持战略自主,已经成为此类国家战略的共同特点。中、印两国同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成员,有着畅通的政治沟通渠道。在洞朗危机后,中、印领导人利用各种多边场合频频会晤和互访,不仅稳定了两国关系,而且建立了军方热线,并完成了第一个安全合作协议,以防止“双边分歧激化为对双方都不利的敌对关系”[80]。同样,在2020年发生边界冲突后,中印双方经过多轮会谈,逐渐稳定了边界局势。中、澳两国经济联系依旧密切,对澳大利亚来说,其政府意识到在两年的龃龉不断之后,需要“重启”与中国的关系。[81]提升中国与印、澳的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增加政治交往,有助于削弱Quad安排对它们的吸引力。
第二,在四国行动的核心区东南亚,应进一步推动以东盟为中心的“包容性地区主义”机制建设。从四国不断强调东南亚在“印太”地区及“印太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可见,Quad希望通过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认可而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和“可信度”,毕竟南海问题是促使四国重启合作的一大动因。但是,即使是越南这样强硬的声索国,对于Quad的任何“反华”集团标签都相当敏感,“Quad+”在地区内依然遭到相当大的抵制。[82]当认同政治从社会个体、群体上升到主权国家对自身的认同、对他国的排斥,其内在冲突就更加令人担忧。如果认同政治在一个社会内部已经造成了冲突,其必然也将导致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83]有鉴于此,中国应继续秉持包容、开放、合作的地区主义理念,倡导地区和平主义;应进一步强调该地区的未来决不能由所谓的“民主四国”来决定,因为以价值观为合作基础、以针对某一国为合作目标的地区主义不但不符合地区内大部分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会使东盟所推动建设的地区和平机制的努力付诸东流。面对“印太”地区所经历的深刻、激烈和不稳定变化,唯一有利于所有国家的选择是继续坚定支持包容、开放、合作的地区主义理念,创新性地发展地区机制中的东盟中心原则,积极推动“和平地区主义”机制建设。
总之,鉴于Quad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结 束 语
由于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得以在最初四边对话的基础上重启。这一发展固然体现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规划和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Quad 2.0会比其前身更加成功。鉴于各方利益重点和威胁认知的差异妨碍了集体行动的有效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若要发挥预期作用,其内容和形式均有待充实和提升。虽然它会像世界上其他话题一样“一时引人耳目,转瞬归于平寂”[84],但Quad作为“印太”地区内重要的战略变化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领域(如南海),Quad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有着遏制中国意图的安全集团,Quad将进一步恶化地区战略环境,并可能导致区域内部关系紧张的零和竞争状态。未来,无论是从各国不尽相同的利益重点和威胁界定,还是该集团中最弱一方对于组织发展的决定性制约作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对其接纳的程度来看,Quad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将是其最大制约因素。中国应积极主动运筹和平外交政策,化解Quad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努力争取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Shinzo Abe,Towards A Beautiful Country, Tokyo: Bungei Shunju, 2006, p. 160.
[②] Frank Ching, “Asian Arc of Democracy,”The Korea Times, April 24, 2008,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opinon/2008/04/171_19480.html.
[③] John Nilsson-Wright,Creative Minilateralism in a Changing Asia: Opportunities for Security Convergen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India and Japan,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July 28, 2017, p. 18.
[④] 关于四国间双边关系的演进,详见屈彩云:《双边视角下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第37—50页。
[⑤] Patrick Gerard Buchan and Benjamin Rimland, “Defining the Diam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CSIS Briefs, March 2020, p. 4.
[⑥] Lavina Lee, “Abe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and New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The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30, No. 2, December 2016, p. 1;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20—21页。
[⑦]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7, p. 46; 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A Free and Open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November 4, 2019, p. 6.
[⑧] Lowy Institute,The 2019 Lowy Lecture: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ison, October 3,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2019-lowy-lecture-prime-minister-scott -morrison.
[⑨] 关于Quad的批判性观点,主要参见Michael D. Swaine,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 2018,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u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 -pacific-strategy-pub-75720; Huong Le Thu ed., “Quad 2.0: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Revived Concept,”Strategic Insights,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14, 2019, pp. 1-26; Benjamin Zala, “Taking the Potential Costs of the Quad Seriously,” in Andrew Carr ed.,Debating the Quad, Centre of Gravity Series, No. 39,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Canberra, March 2018, pp. 19-22; William Choong, “America under Trump Lacks Commitment to Compete with China in Asia to Defend th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ugust 13, 2018,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18/08/america-under-trump.
[⑩] 关于Quad的期许性观点,详见Jesse Barker Gale and Andrew Shearer,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CSIS Briefs, March 2018, pp. 1-4; Ian Hall, “Meeting the Challenge: the Case for the Quad,” in Andrew Carr ed.,Debating the Quad, pp. 12-15; Arzan Tarapore, “The Geopolitics of the Quad,”Commentar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geopolitics -of-the-quad.
[11] 張洁:《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59—73页;张力:《“印太”视域中的美印日澳四边机制初探》,《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第1—8页;陈庆鸿:《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进展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6期,第44—52页。
[12]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46.
[1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pp. 2, 4, 9,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14] White House,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 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1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ranscript of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8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2, 2018, https://dod.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 /Transcript-View/Article/1538599/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plenary-session-of-the-2018-shangri-la-dialogue/.
[16] 《專家点评:日本2020版〈防卫白皮书〉煽动“中国威胁”》,央广军事,2020年7月17日,http://military.cnr.cn/ycdj/20200717/t20200717_525172166.html。
[17] 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November 2017, p. 25.
[18]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 July 2020, https:// defence.gov.au/StrategicUpdate-2020/docs/2020_Defence_Strategic_Update.pdf.
[19] Arzan Tarapore, “The Geopolitics of the Quad,”Commentar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geopolitics-of-the-quad/.
[2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8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2, 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Transcripts/Transcript /Article/1538599/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plenary-session-of-the-2018-shangri-la-dialogue.
[21] 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September 27, 2006; 刘阿明:《民主国家同盟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96页。
[22] Heather Nauert, “Australia-Ind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the Indo-Pacifi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state.gov/australia-india-japan-u-s -consultations-on-the-indo- pacific/.
[23] Jim Garamone, “Commander Stresses Importance of Indo-Pacific Partnership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9,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 1727679/commander-stresses-importance-of-indo-pacific-partnerships/.
[24] 陈庆鸿:《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进展及前景》,第52页。
[25] Wu Shicun and Jayanath Colombage,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Chinas Response, 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 October 2019, p. 5.
[26]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August 22, 2007, https://www.mofa.go.jp /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27] Huong Le Thu, “ ‘Indo-Pacific: (Re-)revise and Resubmit,” Australian Naval Institute, https://navalinstitute.com.au/indo-pacific-re-revise-and-resubmit/.
[28]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019, pp. 232-244.
[29]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Japan-Australia-India-U.S. Consultations,” June 7, 2018,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2062.html;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s,” November 15, 2018, https://www.state.gov/u-s- australia-india-japan-consultations-2/; 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s (‘The Quad),” May 31, 2019, https://www.state.gov/u-s-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s-the-quad/.
[30] Gwen Robinson, “Southeast Asia Gains New Leverage as China and US Battle for Influence,”Washington Post, June 14, 2019, https://washingtonianpost.com/magazine/money/ southeast-asia-gains-new-leverage-as-china-and-us-battle-for-influence/.
[31] Nina Lebedeva, “Why Is the US-Japan-Australia-India Format Being Revived?” Astute News, February 5, 2019, https://astutenews.com/2019/02/why-is-the-us-japan-australia-india- format-being-revived/.
[32] Asia Development Bank, “New Tools for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of Event, May 4, 2019, https://www.adb.org/annual-meeting/2019/events/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3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s (‘The Quad),” https://www.state.gov/u-s-australia-india-japan-consultations-the-quad/.
[34] Jesse Barker Gale and Andrew Shearer,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p. 4.
[35] 115th Congress,S. 2736-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https://www. 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2736/text.
[36] 李金明:《在南海遏制中國:印太战略的根本目的》,《学术前沿》2018年8月(上),第16页。
[37] Wu Shicun and Jayanath Colombage,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Chinas Response, p. 8.
[38] 刘飞涛:《美国“印太”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策略》,《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3页。
[39] Michael R. Pompeo, “The Mekong-U.S. Partnership: The Mekong Region Deserves Good Partners,” Press Statement, September 14, 2020, https://www.state.gov/the-mekong-u-s -partnership-the-mekong-region-deserves-good-partners/.
[40] “Japan Defense Ministry to Create Post for ASEAN Affairs,”The Japan Times, June 28, 2020,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6/28/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defense- ministry-asean-post/.
[41]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46.
[42] Marise Payne, “Address to the Raisina Dialogue,” January 9, 2019, https://www. 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speech/address-raisina-dialogue.
[43] Aakriti Bachhawat, “Australias Indo-Pacific Pitch: Whats in it for the Quad,”The Strategist, February 5, 201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ustralias-indo-pacific-pitch- whats-in-it-for-the-quad/.
[44] Jame Curran, “All Shot and No Powder in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East Asia Forum, January 27, 2018,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1/28/all-shot-and-no-powder -in-the-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
[45] Darren J. Lim and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4, 2015, pp. 696-727.
[46] John Hemmings, “A Reborn Quadrilateral to Deter China,”The Interpreter,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November 9, 2017,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 reborn-quadrilateral-deter-china.
[47] Derek Grossman, “The Quad Is Poised to Become Openly Anti-China Soon,” Rand Corporation, July 28, 2020,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e -openly-anti-china-soon. html.
[48]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9, p. 22, http://www.cscap.org/uploads/docs/CRSO/CSCAP%202019%20 Regional%20Security%20Outlook.pdf.
[49] 因為Quad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全面复活并发挥影响的,而且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Quad的存在及影响在后特朗普时代大概率会延续下去,因此从论证逻辑上说,尽管美国进入政府更迭的阶段,但是文中的一些表述或判断仍无法避开“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
[50]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Vice President Pence Announcing the Missile Defense Review,” January 17,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 -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vice-president-pence-announcing-missile-defense-review/.
[51]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 241.
[52] “Pax Trumpiana-Americas Allies are Preparing for a Bumpy Ride,”The Economist, December 17, 2016,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16/12/17/americas-allies-are- preparing-for-a-bumpy-ride.
[53] Daljit Singh,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Shades of a New Cold W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une 24, 2020, https://www.iseas.edu.sg/media/commentaries/sino-us -strategic-competition-shades-of-a-new-cold-war/.
[54] Nick Bisley, “Is There a Problem with the Quad?”China Matters Explores, July 2018, p. 1, http://chinamatters.org.au/wp-content/uploads/2018/07/China-Matters-Explores-July-2018-The-Quad-1.pdf.
[55] Joel Wuthnow, “U.S. ‘Minilateralism in Asia and Chinas Responses: A New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8, No. 115, 2019, pp. 133-150.
[56] Jeff Smith, “Why the Quad Wont Ever be an Asian NATO,”The Strategist, January 24, 201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why-the-quad-wont-ever-be-an-asian-nato/.
[57] Iain D. Henry, “What Allies Want: Reconsidering Loyalt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4, Spring 2020, pp. 45-83.
[58] Lalit Kapur, “The Indo-Pacific Enigm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1, 2020, https://amti.csis.org/the-indo- pacific- enigma/.
[59] Derek Grossman, “How the U.S. Is Thinking about the Quad,” Rand Corporation, February 7, 2019, https://www.rand.org/blog/2019/02/how-the-us-is-thinking-about-the-quad.html.
[60] Jesse Barker Gale and Andrew Shearer,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p. 4.
[61] Simi Mehta,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A Way Forward,”Policy Forum, July 25, 2019, https://www.policyforum.net/the-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a-way- forward/.
[62] Derek Grossman, “How the U.S. Is Thinking about the Quad,” https://www.rand.org /blog/2019/02/how-the-us-is-thinking-about-the-quad.html.
[63] Derek Grossman, “The Quad Is Poised to Become Openly Anti-China Soon,”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e-openly-anti-china-soon.html.
[64] 何珵:《美日印三邊合作升温的背景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第30—31页。
[65]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 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66] Patrick Gerard Buchan and Benjamin Rimland, “Defining the Diam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p. 2.
[67] Derek Grossman, “The Quad Is Poised to Become Openly Anti-China Soon,”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e-openly-anti-china-soon.html.
[68]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Keynote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Indian Ocean Conference in Maldives,” September 3, 2019,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 Statements.htm?dtl/31915/Keynote_Speech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at_Indian_Ocean_Conference_in_Maldives_September_03_2019.
[69] William Choong, “Quad Goals: Wooing ASEAN,” The Strategist, July 11, 2018,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quad-goals-wooing-asean/.
[70] Lavina Lee, “Abe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and New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pp. 1-41.
[71] Sarah Teo and Bhubhindar Singh, eds.,The Future of the ADMM/ADMM-Plus and Defence Diplomacy in the Asia Pacific, RSIS Publications, February 23, 2016, p. 2,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idss/the-future-of-the-admmadmm-plus-and-defence-diplomacy-in-the-asia-pacific-2/.
[72] Seng Tan, “Consigned to Hedge: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January 2020, pp. 131-148.
[73] 关于东盟国家对Quad看法的相关民调,详见Huong Le Thu, “Southeast Asian Perceptions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October 23, 2018, https://www.aspi.org.au/report/southeast-asian-perceptions-quadrilateral-security- dialogue。
[74] Ankush Ajay Wagle, “How will ASEAN Balance a Tug of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US-led ‘Quad in the Indo-Pacific?”Jakarta Post, October 24, 2018,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8/10/24/how-will-asean-balance-a-tug-of-power-between-china-and-us-led-quad-in-the-indo-pacific.html.
[75] Vivian Balakrishnan, “Singapore not Joining US, Japan-led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r Now,”Strait Times, May 14, 2018,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ingapore-not -joining-us-japan-led-free-and-open-indo-pacific-for-now-vivian-balakrishnan.
[7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puty Secretary Biegun Remarks at the 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um,” August 31, 2020, https://www.state.gov/deputy-secretary-biegun- remarks- at-the-u-s-india-strategic-partnership-forum/.
[77] Huong Le Thu,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ASEAN Centrality,” in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eds.,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SEAN, p. 99.
[78] Patrick Gerard Buchan and Benjamin Rimland, “Defining the Diam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p. 2.
[79] Max Fisher and Audrey Carlsen, “How China is Challenging American Dominance in Asia,”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3/09 /world/asia/china-us-asia-rivalry.html.
[80]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9, p. 21.
[81] Lai-Ha Chan, “Hedging or Balancing?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s Differing China Strategies,”The Diplomat, July 14,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hedging-or- balancing-australia-and-new-zealands-differing-china-strategies/.
[82] Derek Grossman, “The Quad Is Poised to Become Openly Anti-China Soon,”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e-openly-anti-china-soon.html.
[83] 鄭永年:《认同政治与时代大冲突》,《联合早报》2020年6月30日,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200630-1065167。
[84] 南博一:《王毅回应“媒体炒作印太战略”:各种话题像浪花转瞬归于平寂》,澎湃新闻,2018年3月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