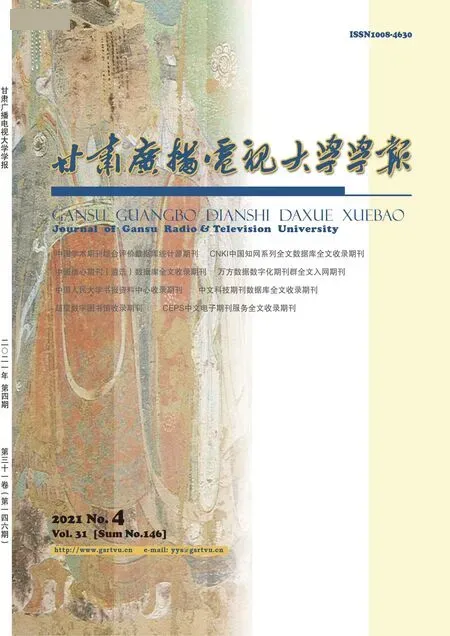蒲松龄文章的文体特征
——兼与《聊斋志异》小说文体进行比较
杨 超,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清代的蒲松龄素以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享誉古今,并不以骈、散文写作名世,历来研究蒲松龄的文章论著中也较少提及其于《聊斋志异》之外的创作。但实际上,据蒲松龄世孙蒲庭橘所撰《〈聊斋文集〉志》记载,清代《聊斋文集》收录蒲松龄骈、散文“共计四百余篇”[1]428,经后人递相摭拾,1998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盛伟编《聊斋文集》收录文章已增至六百余篇,其中赋、传、记、引、序、疏、论、题词、文告、婚启、行实、祭文、杂文等“诸体皆备”[1]428。王士禛评蒲松龄之文“卓乎成家,可传于后世无疑也”[2]541。清人朱子青亦题辞评其文“苍润特出,秀拔天半,而又不费支撑,天然夷旷,固已大奇;及细按之,则又精细透削,呈岚耸翠,非复人间有”[2]541,可见聊斋之文不仅数量众多,兼备众体,且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一、应用类文体中的民本思想
文学产生之初即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因而中国文人历来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及应用类文体的写作。孔子曾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3]110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其中的“言”,指的是有外交之用的辞令,孔子认为晋国成就霸业,郑国攻陷陈国,外交辞令起了重大作用,充分肯定了实用性文体的价值。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4]159,标举文章的政治实用功能,又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4]158四科八体论,其中奏议、书论、铭诔三科六体皆为应用文体,并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4]158,对应用类文体的审美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此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中也为事务文书等应用类文体正名:“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实焉。”[5]460可见刘勰虽偏爱文学性文体,但也反对文人徒追求浮华辞藻而忽视事务文书等应用类文体的写作。又在《程器》篇中强调:“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5]720认为为文要经纶政务,文学创作的才能也应发挥于应用类写作方面。于此方面,蒲松龄也在《〈古香书屋存草〉序》中道:“自古文人,多为良吏,可以知弦歌之化,非文学者不能致也。”[2]37在充分肯定文学经世致用之社会作用的同时,也表达了文章须有益于民生教化的要求。
清初蒲松龄因家境贫寒而长期在缙绅人家坐馆谋生,其间便代当地的缙绅名流写了大量实用性文章,蒲松龄在《聊斋文集自序》中曾说:“吾邑名公钜手,适渐以凋零,故搢绅士庶,贵耳贱目,亦或阙牛而以犊耕。日久不堪其扰,因而戏索酒饵,意藉此可以止之;而远迩以文事相烦者,仍不少也”[2]1。蒲松龄所作虽多是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但他也曾是贫窭大众的一员,饱受生活贫困与科举失意之苦,深刻关切并同情同样苦难深重的百姓,因而其应用类文体的写作中也包含着浓厚的民生意识。除其在做知府幕僚期间代人写了诸如《代王侍读与布政司何书》《正月七日上总督麻(代孙蕙)》等反映民情、为民请命的公文之外,他自己的文章也体现着旧时代知识分子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境遇、同情百姓疾苦的民生意识。据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记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淄川接连发生了水灾、虫灾、饥荒等,蒲松龄写下《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在这些篇章中,蒲松龄不仅记录了自然灾害之景象,更用大量笔墨写出了灾害引发的民生凋敝、哀鸿遍野、盗犯横行之惨状:“家中粟盈斗,钱盈贯,箱有完衣,目即莫敢暝,防少懈,白刃加颈矣,故有朝而素封,夕而丐食者”[2]18,“去岁道有弃儿,慈者犹或收育之,今则号嘶路侧无顾者”[2]22,“去年天作孽,邑绝贫民;今年再作孽,邑无富民。今年之天,又作来年之孽,恐邑少生民矣!”[2]22蒲松龄更在《救荒急策上布政司》一文中提出诸种赈灾救灾之策,字里行间透露着他以救民为己任的民本思想。
蒲松龄不仅悲悯于百姓所受的自然灾害之苦,对于官弊病民现象也表现出为民请命的自觉意识。康熙四十八年(1709),淄川县新任漕粮经承康利贞“妄造杂费名目”[2]132,盘剥百姓,民不堪命,然而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邑中已革漕粮经承康利贞,厚赂新城已罢刑部尚书王士禛(渔洋)、同邑进士谭再生(无竞)为之关说,复其旧职。合县闻之皆惊。先生愤然致书王士禛,并同张益公致书谭再生,直陈此事。据此可知当时乡宦之行为与先生关心合县人之利益也”[6]57。蒲松龄愤然连书《上王司寇书》《与孙艾文转示吴县公》《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三封书信,“直陈此事”[6]57,为民奔走呼号。在《上王司寇书》中,他直陈“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虐民,以肥私橐,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2]130,进而劝王士禛与淄川知县“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则浮言息矣”[2]131。在《与孙艾文转示吴县公》中,蒲松龄愤然反诘:“小民有尽之血力,纵可盈取,橐役无底之贪囊,何时填满?官不知为民贼,而视为良臣,牢不可破,如何如何!”[2]132又于《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中痛批康利贞欺官虐民的行径:“想一啖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购之也,闻者莫不失色!”[2]132其为保护淄川百姓的利益奔走呼号,彰显蒲松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蒲松龄在书、序、疏、呈中也表现出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心。《〈药祟书〉序》体察山村百姓“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2]35之苦楚。《粟里建桥疏》关注农村基础建设之不足,呼吁“共发微愿,创小桥以便行旅”[2]92。《请表一门双节呈》以一腔热血为淄川妇女王氏的贞烈之节求“一字褒扬”[2]239,以彰其德行,树淳朴民风。甚至在《与邑侯张石年(嵋)》《又与李希梅》等私人书信中,蒲松龄也在为涉及百姓的种种琐事而筹谋。总之,蒲松龄在各种体类的应用性文章中,都表现出对清初百姓生活的关注,以及对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状况的同情,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民本意识。
二、聊斋文的骈体书写
清代被视为骈文复兴的朝代,“有远承唐宋、超迈元明的气局”[7]19。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及为人做幕的应酬需要,蒲松龄的大量文章都以骈体书写,且其甚长于骈文写作,“豹岩太史目以单行之神,作排偶之体,一切开阖动荡,音韵铿锵,无不脍炙人口,神妙不亚六朝;渔洋司寇,亦称可与陈其年相伯仲,非寻常流辈可及也”[2]542。蒲松龄的骈文,大多为应酬往来而作,其代孙蕙所拟《十一月二十三日贺济南太守》《十二月初六日贺曹太守署淮阳道印》《二月二十二日答徐山卓书》等都是典型的应酬文字。这些文章以“伏以霜节高悬,四履慰甘棠之愿;星标孤峙,五马生绣豸之辉”[2]167一类的恭维语开头,以“谨恪将乎芹悰,聊鸣欢于贺燕,仰希叱茹,不禁荣施。临禀曷胜瞻切忭舞之至”[2]167之类套话结尾,是标准应酬文字的体式。此外,蒲松龄也用骈文写作了诸如《重修玉谿庵碑记》《募建西关桥序》《贺周素心生子序》《〈我曰园倡和诗〉跋》《唐太史豹岩先生命作生志》等大量碑记、序跋等应用文。
以骈文体式写作官府公文、应酬文字等应用文的传统由来已久,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道:“从当时(六朝)的文集来看,除诗赋的明显骈化以外,举凡一切公牍文如诏、令、表、疏,和一切应用文如碑、铭、诔文、祭文,以及书信之类,已经都用骈体了。”[8]155到了宋代“举凡一切官府文书如章、表、制、诰等,均用此体,并且四六句的格式更严,更趋于定型化”[8]147。宋以后,“所谓散、骈之争虽然还几度起伏,但骈文只在公文、应酬文中还可以逞其余技”[8]162,而蒲松龄不仅用骈文形式写了诸多应制之文和官府公文,还把日常生活琐事引入骈文的书写范围,扩大了骈文的题材,为骈文增添了趣味性。如《为花神讨封姨檄》开篇即控诉风神“飞扬成性,忌嫉为怀。济恶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类含沙”[2]370,之后以“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忧,反借渠以解愠;楚王蒙其蛊惑,贤才未能称意,乃得彼以称雄。沛上英雄,云飞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2]370一系列典故责斥封氏狐媚邀宠,日益恣肆,以趣味之笔表达出作者憎恶豪强、同情弱小之心。在《责白髭文》中,作者以戏谑之笔责怨髭神:“官有汝则致恶于大僚,士有汝则取厌于文宗。冯唐于焉淹蹇,颜驷因而飘蓬。嗟汝白髭兮胡不情?汝宜依宰相,汝宜附公卿,勋名已立,尚不汝惊。我方抱苦业,对寒灯,望北阙,志南溟;尔乃今年一本,明岁一茎,其来滚滚,其出营营,如褦襶之客,别去复来,似荒芜之草,铲尽犹生,抑何颜之厚而不一頳也?”[2]375通过写与虚幻髭神的辩论,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垂老无成的忿懑。
骈文写作历来注重辞藻华美、对偶精妙、音韵铿锵等形式,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片面追求文采,缺乏真实内容情感的弊端,正如褚斌杰先生所言:“它却往往以形式和技巧的追求来掩盖空虚贫乏的内容。”[8]155刘勰也曾在《丽辞》篇批评此类骈文“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5]589。而蒲松龄的骈文克服了徒事形式而缺乏内容、情感不足的积弊。《陈淑卿小像题辞》用近千字深情缅怀陈淑卿,“所恨离奢会促,孙子荆怨起秋风;可怜乐极哀生,潘安仁悲深长簟!香奁剩粉,飘残并蒂之枝;罗袜遗钩,凄绝断肠之草!半杯浆水,呼小岁之儿名;一树桃花,想当年人之面。”[2]104情浓意切,融入了作者无限情怀。《公祭西河王粹中先生》中以骈文形式述王粹中生平经历:“呜呼!自古及今,人谁无死?行路伤心,独我夫子!窃于立雪之余暇,悉平生之逸轨。生困苦而艰难,质聪明而秀美。其就傅在垂髫之年,而入泮犹弱冠之士。学洛纬而濂经,文蛟腾而凤起。设绛帐于颜山,倡绝学于范水。济济者半出门墙,英英者悉为桃李。”[2]314还表达出了深切的惋惜和痛心:“何文人国士,偏逢百罹?少陵每多险阻,仲宣乃有流离。旻天不吊,灵椿萎矣!闵凶再遘,庭萱摧矣!杂英满地,扬风吹矣!忧刀割肠,架衣悲矣!茕茕一身,形影相依。遭逢若此,真所谓有一无两,不可思惟者矣!”[2]314全文在兼顾骈文形式特点的同时,具有感人肺腑的情感力量。另《祝辞》控诉贪官恶吏于民之害,“设宏霸一日不死,则床寝难安;脱鱼宏半载犹留,则人民欲尽”[2]367充满填膺之义愤;《赌博辞》警劝赌博倾产亡家之危,“门前宾客待,犹恋恋于场头;舍上烟火生,尚眈眈于盆里。忘餐废寝,则久成入迷;舌敝唇焦,则相看似鬼。”[2]369讽刺警戒意味尤甚。总之,蒲松龄骈文写情者,情感充沛感人;描事者,内容广博真实,在兼顾文辞华美等骈文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丰富了骈文的表现内容,为骈文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三、聊斋文“尊体”特点与《聊斋志异》“破体”之比较
《聊斋文集》与《聊斋志异》虽同出于蒲松龄之手,但二者却表现出不同的文体意识。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评价《聊斋志异》文体:“《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妮之词,媟押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之?又所未解也。”[9]472虽是批评之语,却一语道破《聊斋志异》对传统文言小说体例的突破,“一书而兼二体”[9]472点明了《聊斋志异》的破体特点。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也道:“此书即史家列传体也,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10]924虽认为《聊斋》之体“弊实有之”[10]924,但也肯定了《聊斋志异》“有乖体例”[10]924的破体特点。鲁迅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点明了《聊斋》在文体上的突破与创新:“《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11]167认为此书写神仙鬼怪故事,形式上“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1]167,完全打破了传统志怪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内容上“易调改弦”[11]167,不同于传统志怪“发明神道之不诬”[11]41的套路,这样的文体创新突破传统,打破窠臼,因而“读者耳目为之一新”[11]167,既指出了《聊斋》的破体特点,又对此予以了充分认可。
不同于《聊斋志异》对传统文言小说体例的突破,聊斋文则表现出鲜明的尊体特征。正如刘勰在《通变》开篇所言:“设文之体有常”[5]519,即特定的言说内容要放入特定的文章体制中,且文章体制的安排有一定的规范。其书信诸如《与李淡庵》《又呈崑圃黄大宗师》均“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5]456“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5]456,为“心声之献酬”[5]456;奏笺如《上孙给谏书》《上王司寇书》等,“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5]457;《徵毕信涉逸老园诗启》《邀景夏孙学师饮东郭启》等启文“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5]424;《责白髭文》《为群卉揭乳香劄子》等杂文“发愤以表志”[5]255“渊岳其心,麟凤其采”[5]255,等等,聊斋它的诸种文体皆合各体之大要,写作方式体现出尊体为文的特点。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关于文学尊体有云:“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5]514他认为创造新颖的文意,要以学习经典,通晓文体文情为基础。蒲松龄曾投身举事,又作为坐馆先生教导学生潜心举业,学习儒家经典自然不必多说。蒲松龄又在《聊斋文集自序》中说自己“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2]1,张元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中也记载,蒲松龄落第之后“肆力于古文”[6]72,可见其对古文经典的重视。王士禛在《题〈聊斋文集〉后》言:“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弇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觚家论文正宗,谓不若震川之雅且正也。聊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奥峭,又非拟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2]541也从侧面肯定了蒲松龄对前人经典之作的学习。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司文郎》中借僧人之口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10]743表达了对“卓然成大家”[12]351归有光的推崇。正是在学习古文经典,通晓古文文体文情的基础上,其文章才达到“颖发笤竖,诡恢魁垒,用能绝去町畦,自成一家”[6]72之成就,亦即《风骨》篇所言“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5]514之境。但其实不论是聊斋散文之尊体还是《聊斋志异》之破体,都是殊途同归,正如《柳泉蒲先生墓表》中所云“要归于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7]72。
综上所论,蒲松龄作为有清一代文学大家,其文学成就的光辉不应仅集中于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虽曹丕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4]158,但蒲松龄实可谓通才,其文章创作不仅兼备众体,各体皆具特色,且能在尊其体例的基础上,拓宽题材表现领域,融入主体思想倾向,并以鲜明的个人特色为多种体类文章的创作注入新鲜活力。其文章中表现出的儒生情怀上承杜甫,其写作大量的骈文下开清代骈文之“复兴”之势。研究蒲松龄各体之文,对于研究清代文学发展源流及中国文学文备众体的民族特点,无疑是极具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