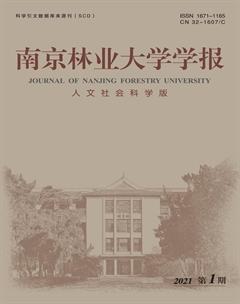论古典园林艺术在东晋的新变
张鹏举 梁海
摘要:东晋是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新变期,表现为:在形制上出现了由“巨丽”到“精巧”,由“营国之制”到“翳然林水”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东晋时期不仅园林布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设置,而且在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还将园主“乐情”的生活取向融入居住环境,园林的审美价值逐渐从实用价值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在功能上则加强了寄情山水、赋诗作文,放松心志、体认生命的士人情趣。这说明随着园林形制在东晋时期的日益精巧化、雅化,园林中的文化因子不断地得到了增加。这时的园主更加注重园林在寄情山水、放松心志和体认生命等精神层面的功能;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由“炫富”到“隐逸”、由“比德”到“畅情”、由“崇俗”到“尚雅”的嬗变。说明当时的园林不再是园主们物质上的需要,也不再是他们家藏的外漏,而是真正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家园,成为他们心灵上的栖息之地。这时的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怀着一颗平静之心,恬然怡然、欣然悠然,冥视六合,真正实现了园与人、身与神的合一;这些变化都表明园林审美功能在东晋上升到了首位,并呈现出个性化、士人化的审美倾向。
关键词:东晋;园林形制;园林功能;园林观念;新变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可见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充满矛盾的嬗变期。不仅如此,魏晋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还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史上重要的新变期,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除了皇家园之外,私人园(包括皇族宗室的园林、权臣贵族的园林、士人和平民百姓的园林)和宗教园林(包括寺庙园林和道观园林)等新的园林形式开始出现,园林的形制、功能和审美观念等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對后世园林创作手法、建造理念的发展和格局的演进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东晋在魏晋园林史上又最为独特,诚如杜牧所言:“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东晋时期无论是园林风貌,还是园林审美风尚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亮点。因此,我们以古典园林艺术在东晋的新变为视角去管窥这一变化。
一、园林形制之变
东晋时期,古典园林艺术在形制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园林规模和园林格局两个方面。其中,就园林的规模而言,主要表现为由“巨丽”逐渐走向了“精巧”;而从园林的格局来看,则突出表现为由之前的“营国之制”到东晋时期的“翳然林水”的嬗变。
(一)园林规模:由“巨丽”到“精巧”
秦汉时期的园林以宫苑为主,受先秦理性精神的影响,多表现出一种情感中的理性美。这时的园林多如汉大赋那般规模宏大、范山模水、巨丽无比,以体现大一统帝国笼盖宇宙的气魄和力量。“百代皆沿秦制”,汉魏时期随着国力的式微,皇家宫苑已明显不似秦皇汉武时期那般规模宏大了,但由于此时的统治者依然幻想通过恢弘的宫苑向世人展现其“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威仪,仍然追求通过奢华巨丽的宫室、巍峨辽阔的苑囿来体现皇权的独尊,再加之,这时的皇家园林多是在前代宫苑遗址的基础上增饰而成的。因此,此时的皇家园依然延续着秦宫汉苑“观夫巨丽惟上林”的营建理念,仍然追求秦汉“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混一宇内”的大美气象。正如《晋书》所记载的那样:“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伎巧。”由此可见,汉魏时期皇家园林的规模虽已不似秦汉那般“包举宇内”“气吞八荒”,但仍然“范山模水”巨丽无比。
然而,由于东晋是在“永嘉之乱”中仓促立国的,外有强敌之忧、内有门阀之患,国力孱弱,再加之建国初期东晋统治者一心想着克复中原,返还旧都,无心偏安于“江南一隅”,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宫室营建,只是在三国时吴建邺旧址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修葺。再加之,江南秀美的自然地理环境、发达的庄园经济与士人审美文化,使得这时的皇家园林多追求精致,改变了汉魏统治者在暴富心理和膨胀的私欲驱使下“尽情罗列、排设,而不知小中见大、知微显著,咫尺间见层峦叠嶂、烟波浩荡”的局面,出现了“以小见大”的构园手法。此时的皇家园从规模上讲与魏晋时期的恢弘巨丽相比明显小了许多,“精”“雅”成为东晋皇家园的基本特征。
在私人园方面,汉魏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得“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存进之路”。世家大族的势力迅速崛起,如西晋的王戎、石崇和潘岳等人,“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必备”,广占良田,大兴庄园。但是,这时的庄园更多的是以经济功能为主,往往规模宏大,闭门为市,以满足园主奢靡物欲的需要,可以说毫无精巧可言,园林中的审美也充斥着横流的物欲。
东晋时期,由于时人广受“魏晋风度”的影响,伴随着“人”的不断觉醒,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一改秦汉时期理性美的主导地位。士人们在慨叹着人生之短促、生命之无常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对生命的无尽留恋和对人生的强烈欲求,开始将自己的心思、眼界转向了自然,“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找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再加之,他们大多财资丰厚,不必为生活担忧。因此,这一时期自然山水独立的审美价值更加凸显,士人们雅好自然、纵情山水,非常向往那种草木芳菲、清静闲适的园居生活。他们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社会转向自然,就遨游山水,放情丘壑”,纷纷兴建园林别业,引得文人、名流争相效仿,使得不少文人园得以兴建。又由于这些园主大多是精通艺文的士人,他们往往亲自参与园林的选址和设计,使得他们的审美趣味、个人喜好都融入园林的规划、布局中。这时的私人园不再承载物质生产的功能,真正成为士人寄情山水的审美对象。与之相似,受东晋士人清雅审美风尚的影响,此时私家园的规模也较之前代小了许多,显得较为精致。
综上所述,东晋时期无论是皇家园还是私人园的规模都出现了由“巨丽”到“精巧”的变化;同时,园林格局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二)园林格局:由“营国之制”到“翳然林水”
汉魏时期,由于深受儒家“成人伦,助教化”思想的影响,儒家理性化的审美意识更是在皇家园的格局规划中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无论是皇城的规划还是皇家园林的设计处处都要体现出尊卑、高低的不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逾越,无论是单个建筑还是各个建筑之间的平面布局都要突出皇权的独尊地位,体现着“美善合一”的审美原则。正如园林家考证的那样,当时的都城邺城“是一个长方形的城市。……一条从正中的正阳门引申出来的路直对王城的宫殿,形成了明显的中轴线。北部中央建宫城,大朝所在宫殿位于宫城中央”。由此可见,邺城分布格局以王城为中心、宫苑沿中轴线呈“左祖右庙”的对称分布,以体现“营国之制”。“营国之制”的营建原则不仅体现了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威仪,也体现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园林格局中的支配地位。
到了東晋时期,都城的布局虽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受到魏晋“以玄对山水”的清雅之风的影响,此时的园林布局不仅开始较为灵活地根据地形的不同进行规划,更是将园主“乐情”的生活取向融入园林等居住环境中。比如,《世说新语·言语》中就有东晋名相王导营建建康城以“纡余委曲,若不可测”为总体规划的记载。“纡余委曲,若不可测”的园林设计理念不仅体现了王导个人的价值选择和审美品位,更是整个东晋园林格局设计理念和园林审美风尚的自然流露。不仅如此,这时皇家园林的设计也远不如汉魏时期那般威严肃穆了。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的简文帝的“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的故事。晋简文帝能够在自家皇宫内苑中体会到“翳然林水”之趣,可以与逍遥于濠、濮之间的庄子一样冥心于物外,这说明此时的华林园的格局绝不像魏晋宫苑那般呆板凝重,已经有“妙造自然”的诗意。毫无疑问,此诗意化的审美境界在秦汉那种追求“营国之制”的皇家园林格局中是难以找寻的。
总而言之,王导营建建康城的时候,敢于打破深入人心的“营国之制”的格局,根据建康“负山带江,九曲清溪”的地形,把都城建造得迂回曲折、深不可测。简文帝的皇家宫苑也已不再一味追求园林的“比德”功能,而是将“翳然林水”的士人化的审美情趣融入其中。这些都证明了无论是出于主观的审美选择,还是由于被动地接受魏晋清音的洗礼,东晋时期无论是皇城的规划还是皇家园林的格局都已经融入“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士人化审美韵味了。
除了作为主流的皇家园林之外,私人园的格局在东晋时期也发生了由“室宇宏丽”到“尽幽居之美”的士人化倾向。如上文所述,汉魏时期由于门阀旺族攀附于皇权,他们享有很多的经济、政治特权,往往“财产丰积”,有足够的财力去经营自己的庄园,如《晋书·石崇传》中关于石崇金谷园“室宇宏丽……冠绝时辈”的记载。再比如,潘岳的《闲居赋》中对其园物质之丰饶、楼宇之豪奢有大量炫耀式的描写,等等。或许石崇、潘岳等辈纯属个案,没有充分的代表性,这些文学化的作品也有夸大其词的成分,然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仍能从上述描写中管窥出当时世家望族庄园的片貌,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不难读出当时以石、潘等人为代表的世家望族的审美水准。就像潘氏《闲居赋》为我们呈现的那样,一方面这些庄园往往依托大片山林川泽,规模宏大,可以为这些士族们奢靡的生活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此时的私人园更多的是满足园主现实的物质欲求,背负着一定的经济生产职能。所以此时的私人园虽然规模很大,但物欲充斥其中,在物欲的遮蔽之下此时的私人园林虽然也有独到的审美功用,但审美价值还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审美价值仍是实用价值的附庸。
然而,东晋私人园风格呈现出了与上述石崇、潘岳等辈“错采镂金”的豪奢的私人庄园的明显的不同。如果说,东晋时受简文帝和王导等决策层审美趣味的影响,皇城和皇家宫苑呈现出了“翳然林水”的审美风格,那么,此时的士人们也不仅仅再满足于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与攀比,他们开始更多地追求“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的悠游生活,追求“清水芙蓉”的自然之美,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上的宁静与自由。可以说,“简约玄澹”已不仅是魏晋玄学的审美品格,而且更成为东晋私人园清新雅丽的园林格局的美学风格之一。我们难以忘记谢灵运始宁别墅远离世俗生活,“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的清新雅致的自然环境,我们更醉心于王羲之兰亭“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清幽之貌,而陶潜安然自得于“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宁静陋室更是传唱至今,令无数人心向往之。
由上述分析可知,东晋时期中国古典园林的规模、格局都呈现出了士人化、雅化趋势。这种焕然一新的园林为士人们娱游宴饮、谈玄清禅、赋诗作文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二、园林功能之变
园林规模和格局在东晋的士人化嬗变直接引发了园林功能的变化,使之不仅成为士人游山玩水、赋诗作文的艺术欣赏对象,而且成为士人们放松灵魂、体认生命的心志栖息之地。
(一)嬗变为寄情山水的艺术欣赏对象
诚如上文所言,汉魏时期的园林往往规模巨大、闭门为市,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生产和安全防卫系统,其经济价值遮蔽了审美价值,物质功用超过了精神功用。但是随着士人参与到园林的设计中,园林形制日益精巧化、雅化,园林中的文化因子不断增加,园林逐渐成为士人们游山玩水、赋诗作文的艺术欣赏对象。这里仍以西晋石崇的金谷园为例,石氏的金谷园可以说是这一园林功能由以经济生产为主向以审美体验为主嬗变时期的典型。一方面,它兼有一定的经济生产功能;另一方面,又可以说金谷游会把中国式游园活动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东晋士人争相效仿的典范。如通过石崇《金谷诗序》的描写可以看出,金谷园“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的自然环境十分的优美,同时,由“莎桑”“乌椑”“繁石榴”“众果竹柏药草之属”也可以看出,金谷园仍以经济生产职能为主,审美价值仍旧从属于实用价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园林的审美功能也在逐渐地提高,园林的审美价值也逐渐地得到园主的重视,而且此时已经开始出现形式多样的园林游赏活动,游宴、赋诗、欣赏乐舞等园林活动也逐渐成为常态。
东晋时期,园林已经摆脱了经济生产职能,成为游山玩水、饮酒作乐的物质载体和谈玄论佛、赋诗作文的艺术欣赏对象。前文提到的谢灵运、王羲之和陶渊明等人已经彻底摆脱了物欲对其精神的束缚,不再将物质的满足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而是将自己关注的重点转向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王羲之携群贤好友醉心于兰亭的清幽风光,写下了《兰亭集序》这一震铄古今的名篇,其“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至今仍令人感到惊艳。
通过对比《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我们不难发现,兰亭禊会中傍水赋诗可以说是对金谷游会在游园方式和文化行为上的传承。但是二者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对比金谷游会中的“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与兰亭禊会的“无丝竹管弦之盛”,可以看出金谷的富贵之气和兰亭的清幽之美,金谷的游者多是沉醉于歌舞声中寻欢作乐,而蘭亭的游者更多的是陶醉在兰亭“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优美景色之中“畅叙幽情”。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变化,一则表明此时园林的审美价值已经彻底摆脱实用价值的束缚,园林审美成为最重要的园林功能;二则表明园林审美心理在东晋时期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随着游者审美能力和文化品位的提高,此时园林真正成了游山玩水、赋诗作文的艺术欣赏对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观赏对象。
虽然石崇及其好友在金谷园中,一边游山玩水、欣赏歌舞,一边喝酒赋诗、怡然自得,为中国式游园活动树立了范式,尤其是其“或不能者,罚酒三斗”不仅直接影响了王羲之的兰亭禊会,更是为中国园林的人文特征奠定了基调,影响深远。但是这仍难以掩盖金谷游会奢侈豪阔中流露出的富贵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只是具有了士人游园活动中的某些文化因子。这时的园林对于园主来说仍是经济功用大于欣赏价值、物质意义大于精神意义,此时的园林更多的是园主物质财富的载体,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精神的寄托,所谓的游园活动也掺杂着园主炫富的心理。如果以康德的无功利审美标准来评价,这一时期的园林显然还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园林,这一时期的游园活动也不是真正审美意义上的观赏活动。因此,可以说金谷园和金谷游会只是园林嬗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标准意义上的园林是由兰亭和兰亭禊会最终实现的。因为在兰亭禊会上兰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放松灵魂、体认生命的心志栖息之地,成为游者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二)嬗变为体认生命的精神家园
标准意义上的园林在东晋时期最终形成,使园林不仅成为物质方面的艺术欣赏对象,更成为游者精神上的家园。在兰亭禊会中,王羲之与“群贤”在陶醉于兰亭清幽的自然环境放松灵魂的同时,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中不由自主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感受到了茫茫宇宙的浩瀚与深邃,他们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中体悟到了宇宙之真义,进而敏锐地意识到了人生匆匆几十载,在浩瀚的宇宙面前犹如沧海之一粟,流露出“曾不知老之将至”的清悲意识,发出“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慨叹。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悲观失望,而是“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即通过将自己内化于自然山水之中,进而达到与自然山水的和谐共生的“终焉之志”来化解郁结,来体认生命。这时的游园活动才真正上升为纯粹的生命体悟,这时的欣赏者才真正地与作为欣赏对象的兰亭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种境界或许正是李泽厚先生在《美学四讲》中所说的“悦志悦神”的境界?或许是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所说的“天地境界”?亦或许是中国美学所孜孜以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
通过对比金谷集会与兰亭禊会我们不难发现,与金谷园中游者更多的是感叹时光之易逝、富贵之难留不同,王羲之及群贤更多的是感慨宇宙之浩渺、人生之微渺,并能通过山水欣赏化解郁结,从而将自己的思想境界由世俗的荣华富贵上升到宇宙人生的哲学高度,使自身的审美体验由体认生命的“园人和一”达至“天人和合”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东晋时期园林的审美功能最终形成、新的园林及园林活动开始大规模出现,“经营园林成了社会上的一项时髦活动,出现民间造园成风、名士爱园成癖的情况”。但无论是园林规模和格局的改变,还是园林审美功能在东晋的加强,都根源于园林审美观念在这一时期的新变。
三、园林观念之变
东晋时期园林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由“炫富”到“隐逸”、由“比德”到“畅情”和由“崇俗”到“尚雅”等方面。
(一)由“炫富”到“隐逸”
东晋士人的出处观对园林审美观念的加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魏晋时期的士人大多追求的是汇通名教与自然的“朝隐”,他们试图“将自然代表的超脱与自由融人名教代表的束缚与秩序之中”,但往往又沉溺于世俗的羁绊中无法自拔,汇通名教与自然的想法多以失败而告终,这体现在魏晋士人营建园林时的炫富心理上。而东晋时期士人们在主张出处同归的“朝隐”的同时,也讲究出优处劣,改变了魏晋时期名教即自然的出处观,崇尚“隐逸”。例如,谢安和邓粲的先隐后仕遭到时人的讥讽,王羲之辞官之后“尽山水之游”“遍游江南郡,穷诸名山”,受到时人的追捧。再加之,这一时期的士人由于大多拥有世代沿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反而能够将心思放在自然山水之间,追求放情丘壑的“隐逸”生活。这一出处观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了士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仍以西晋的潘岳和东晋的陶渊明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例如潘氏在上文提到的《闲居赋》中对其住所“张公大谷之梨”“溧侯乌裨之柿”“房陵朱仲之李”等炫耀式描写。可以思考一下,为何潘氏要对自己家中丰饶的物产运用赋的形式,不惜以大量华丽的辞藻对之进行不厌其烦的描述?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潘氏难掩其对自家园圃环境之美、品物之盛的盛赞心理背后其实是其肤浅的“炫富”心理及在遭贬失势之后谪居家中的浮躁心态在作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陶渊明在遭贬之后,虽身居陋巷,却写下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而我们透过陶渊明的诗句更多的是读出其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世俗生活的厌恶之情和对想要挣脱樊笼、返还自然的“隐逸”生活的向往。这不仅反映了二人对待物质需求的不同态度,更体现了二人不同的人生境界。此一追求诗意化栖居的变化无疑为中国古典园林在东晋出现雅化的趋势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这时“隐逸和园林不再单单是避世的处所,更是士大夫体认‘天人之际最理想、最和谐的胜景”。
(二)由“比德”到“畅情”
皇家园林的“比德”功能,明显是受到了儒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思想的影响。如《汉书·高帝纪》中萧何解释之所以把未央宫建造得壮丽无比的原因说成“非令壮丽亡以重威”。可见萧何正是想通过未央宫宏大的规模和格局来体现“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达到用宫苑来“比德”的目的。再比如,何宴在《景福殿賦》中“莫不以为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饬不美,不足以训后而永厥成”的论述。这些都和上文中邺城宫城之所以建在邺城中轴线上、大朝所在宫殿建在宫城正中的高台上一样,都是出于“营国之制”的“比德”目的的考虑。同样,在私人园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深受儒家三纲五常、尊卑有序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也极其讲究建筑之间的结构布局,也体现着长幼、尊卑、主客等伦理秩序。也就是说,在园林中不同建筑之间的布局更多的是出于伦理的需求,审美功能在园林格局的规划中还处于辅助的地位。
东晋时期,园林的“比德”功能在园林的规划尤其是皇家园的规划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是这一时期由于融入了更多的自然审美观念,使得皇家园、私人园都出现了“精致化”“简约化”“雅化”的趋势。这一审美趣味的新变之所以能够透过园林体现出来,主要由于当时的人们虽然注重园林规划中所体现的人伦关系,但是受魏晋名士清谈观念逐渐流行的影响,人们尤其是士人阶层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园林的审美、“畅情”功能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园林营建理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才使真正意义上的园林审美“文化-心理”在东晋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例如《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王子敬(王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王子猷(王徽之)偿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可见,东晋名士由于受清谈风尚的影响,远离世俗名教思想的羁绊,开始将审美作为最主要的价值追求。
总之,简文帝置身于华林园郁郁葱葱的林木怀抱中,钦慕庄子于濠、濮之间逍遥自得的境界,顿觉飞鸟走兽都会自觉地来和人们亲近的翳然之情,王羲之的寄情于兰亭山水之间、献之悠游他人之园“旁若无人”、王徽之“比竹而居”的任诞、自由……这些无不是透过园林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表达游者欣然、恬然、怡然、悠然之情,这些“悦志悦神”的审美境界,如果没有清幽的园林环境,没有名士“情本体”的自然流露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吴功正所言:“中国色彩的园林文化审美心理只是在六朝才真正形成,汉魏以前的园林心理还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审美心理。这一审美心理在六朝产生以后便不改东流,泽被后代。”
(三)由“崇俗”到“尚雅”
不同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并非相同。由于不同审美主体人生阅历的不同、知识结构的不同、艺术情趣和人生境界的不同,自然会有雅俗、高低之别。同样,同一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同理,从审美观念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作为上层建筑也必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改变。东晋园林审美观就发生了由“崇俗”到“尚雅”的变化。东晋时期由于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再加上清谈之风的流行,使得东晋士人对自然山水充满了向往之情,这时园林的审美功能上升到首位,成为士人们体察天地、品味山水、谈玄清禅、娱游赏会的主要场所,成为他们洗涤俗世污浊、澄澈心灵的精神栖息之地。因此,这时的园林审美观念出现明显的雅化趋势,我们仍可以通过东西晋士人间不同的审美品位的对比发现这一嬗变。
例如《世说新语·汰奢》中有很多关于园主穷奢极欲、奢阔成俗的记载:“石崇厕,常有十馀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王君夫以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石崇在与王恺等人斗富、摆阔过程中,一味展示其“侯服玉食,穷滋极珍”的豪奢,甚至不惜以杀人这一庸俗可恶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权势和淫威,这与上文提到的简文帝、王羲之、王徽之、陶渊明等人的风雅相比相去甚远。
再如通过潘岳《金谷集作诗》中对石崇金谷园奢丽的描写:“王生和鼎宝,石子镇海沂。……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莎桑,后园植乌椑。灵圃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池,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诉北行迟。扬桴抚灵鼓,萧管清且悲。”从中可以看出这时的金谷园还只是显示园主身份、地位和权势的标签,作者对众果丰硕的描写也有很大的庸俗的物欲膨胀心理在其中。而透过王羲之《兰亭集序》对兰亭周边环境的描写,可以看出兰亭“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带给人们一种“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的心旷神怡的审美体验。
通过对比金谷之“富贵”与兰亭之“清雅”不难看出:东晋时期士人园更多的是强调顺应自然、托志畅情,成为沐浴心灵的栖息地,呈现出“恬淡”“清雅”之美,它已经完全摆脱了靠园林格局之气派、品物之丰盛来满足园主夸富心理的“奢俗”“艳丽”之美的层次,东晋园林“不是物质的需要而是精神的安顿,建造的是精神家园。怀着一颗平和、虚静之心,恬然怡然、欣然悠然,园人和一,冥视六合,身内与身外融汇一体。构园之心视园林为心灵的寄托之所、心智的栖息之地,又视为艺术的欣赏对象。它在园主眼中不是家藏的暴露,而是情怀所由寓示的对象存在”。这才真正体现东晋园林的园林精神和审美观念。
四、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东晋时期发生了新变。就园林实践活动而言,正是在东晋时期中国古典园林的形制日益精巧、清雅,园林的审美功能也逐渐上升到了首位。随着园林审美功能日趋增强,园林逐渐成为士人娱游赏会、赋诗作文的艺术欣赏对象,成为他们放松灵魂、体认生命的心志栖息之地。就园林美学自身的理论发展而言,在东晋时期“畅情”“尚雅”等园林审美观念最终形成,产生了“清”“幽”“雅”等一大批园林审美范畴,为唐宋园林美学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影响至今。总之,东晋园林艺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处于中国古典园林由先秦的奠基期向隋唐的鼎盛期的过渡阶段,无论是从园林建造的实践方面,还是从园林美学的理论发展角度来看,在整个中华园林史上都占据着十分独特的地位。东晋时期的古典园林艺术以其个性化、士人化的审美倾向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史上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责任编辑 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