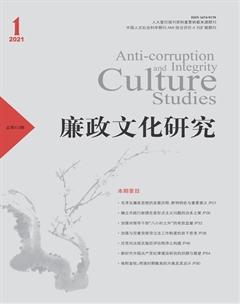现象·动因·治理:“微腐败”问题研究综述
蔡文成 林兆扬
摘 要: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微腐败”的治理成为腐败治理的焦点,“微腐败”研究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就整体现状而言,论文数量可观,成果丰硕;从研究角度来看,主要论题聚焦于“微腐败”的概念、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社会影响和治理措施等方面;就研究趋势而言,“微腐败”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针对性、系统性等研究态势。尽管“微腐败”研究还存在理论深度不足、实证研究较少、比较研究欠缺等问题,但是,研究的主题、问题、方法、成果等为腐败治理研究拓展了内容和形式,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指导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微腐败”;文献;议题;评析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1)01-0082-08
“微腐败”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和腐败类型。如若放任发展,“微腐败”终将成为“大祸害”。近在眼前的“微腐败”不同于远在天边的“大腐败”“巨腐败”,相较于“老虎”而言,人民群众对“苍蝇”的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阻滞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割裂了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侵蚀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败坏了一方乡风民情,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扫清的障碍。目前学者们对“微腐败”的概念、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治理对策进行了研究,“微腐败”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特殊性、广泛性和长期性特点,故而对“微腐败”的研究需要挖掘理论深度,治理方法需要因地因时制宜,研究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
一、 概念:“微腐败”的内涵辨析
“微腐败”的概念辨析,即明确什么是“微腐败”。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五个角度对“微腐败”进行定义:一是行为主体的角度;二是行为客体的角度;三是行为性质的角度;四是行为发生场域的角度;五是行为影响程度的角度。
(一)从行为主体角度定义:行为主体的公职身份是定义“微腐败”的核心要素
“微腐败”也是腐败,它的主体和一般腐败行为具有共性,即都为公职人员。萨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而违反社会公认规范的不良行为;[1]胡鞍钢认为,“微腐败”是一种藏匿在看似合理的表面下而形成的腐败现象,它在纪律红线和法律底线的边缘游走,主要体现在一部分公职人员借以人情交往的名义,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2]夏红莉在宿州纪委的支持下,以当地部分县区单位负责人、纪检组长,乡镇党政班子成员、纪检书记、村“两委”班子成员、党代表和群众代表为对象进行了广泛调研,发现半数以上村居干部涉及“微腐败”问题,拉帮结派,为官不为。[3]
(二)从行为客体角度定义:小微权力是“微腐败”区别于其他类型腐败的标志
“微腐败”是一般腐败的一种亚型,二者是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微腐败”的“微”体现在权力的小微性上。李靖、李春生认为,基层官员的“微腐败”就是基于小微权力而发生的腐败行为;[4]周师认为,“微腐败”是一般腐败的一个面向,“微腐败”体现的是个性与特殊性,而一般腐败则体现出共性与普遍性特征。“微腐敗”和一般腐败不能并为一谈,“微腐败”有其特殊表现形式——即“微腐败”的客体是小微公权力;[5]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对另一种腐败亚型的研究分析指出,之所以强调“微腐败”概念中权力的微小性,是因为这一要素是区分“小官巨贪”(或“小官巨腐”)这一易混淆概念的重要标识。
(三)从行为性质角度定义:以权谋私的行为性质是定义“微腐败”的关键所在
“微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抓住以权谋私的本质,就抓住了这一概念的牛鼻子。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认为,腐败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6]戴夫·沃克曼和阿伦·科特利伯认为,对腐败进行区分的有效途径应当是衡量参与者数量,“大腐败”需要利益集团内部多人协同完成,并进行利益分赃。但“微腐败”一般是个人收受贿赂或利用职权便利谋得私利;[7]邹东升认为,以权谋私是腐败的实质,不论是大贪巨腐,还是“微腐败”皆无例外;[8]任中平、马忠鹏认为,“微腐败”同“大腐败”一样,都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9]
(四)从行为发生场域角度定义:发生在基层是定义“微腐败”的基本前提
基层是“微腐败”行为产生的特定场域,基层范围广泛。纵向来看,包括县级以下的行政机关,横向来看,包括居民自治组织、街道办事处、企业、学校、医疗机构、连队、社会组织等任何存在公共权力的基层单位。李威认为,“微腐败”主要是指基层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从事违纪违规、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10]周师认为,不能将“微腐败”与一般腐败一概而论,“微腐败”有其特殊表现形式,即“微腐败”发生在基层,主体是基层领导干部;[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基层连队、高校、精准脱贫战略下的贫困村、特定乡镇等场域为研究焦点,展开对这些场域“微腐败”现象的研究。
(五)从行为影响程度角度定义:小而直接的影响是定义“微腐败”的重要标志
“微腐败”的“微”还体现在影响的微小性上,但是这种微小的影响在可感受性上绝不等同于大官巨腐的影响,是人民群众能切身感受到的。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伯里安·艾尔伍德指出,亚腐败是一种本身并不完全廉洁的行为,它介乎于权力的清廉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并能够维持在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史云贵认为,“微腐败”可以分为吃拿卡要、公款私用、圈地卖地、私办企业、截留冒领、私养情人和染黑涉黑七大类;[11]余雅洁、陈文权认为,“微腐败”是指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人员利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力及职务便利在小事上以权营私或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失,一般涉案金额在 3 万元以下的违纪违法行为。[12]
上述学者的理解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各有侧重,丰富了国内外对“微腐败”定义的研究理路。“微腐败”是一种社会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违纪违规或违法犯罪的行为,其内涵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微腐败”的主体是公职人员,客体是小微权力,本质是以权谋私,发生场域是基层单位,影响小而直接。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微腐败是一种基层公职人员利用其所掌握的小微公共权力谋取小利,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具有广泛性、隐蔽性、逐蚀性的一种腐败行为。
二、 形式:“微腐败”的类型分析
归纳“微腐败”的表现形式,是研究“微腐败”问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鉴于“微腐败”的特点,要深化对其认识,就必须对其外延进行充分的研究和科学的分类。目前学者主要从物质利益和个人作风两个角度对“微腐败”行为进行分类。
侧重于从物质利益角度分类的学者强调,“微腐败”主要应包括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或亲友谋取经济或其他物质利益的行为,他们认为“微腐败”是一种主动作为。邹东升、姚靖从五个方面归纳了“微腐败”的表现形式:第一,贪污;第二,收受贿赂;第三,优亲厚友;第四,违规收费;第五,怠忽职守。[13]余雅洁、陈文权将“微腐败”的表现归纳为七种类型:第一,吃拿卡要;第二,雁过拔毛;第三,优亲厚友;第四,收受礼金;第五,公款消费;第六,违规挪用;第七,懒政怠政。[12]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个人作风角度出发,指出个人工作、生活作风糜烂,思想堕落也应归为“微腐败”,他们认为“微腐败”也可以是一种消极不作为。殷路路、李丹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微腐败”的表现形式:第一,在资金管理使用方面虚报套取“动歪经”,歪曲政策“谋暴利”;第二,在政策制定执行方面优亲厚友“送人情”,吃拿卡要“争民利”;第三,在干部思想作风方面作风漂浮“走过场”,意识淡薄“不作为”。[14]近几年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许多学者已将“语言腐败”这一新概念引入“微腐败”研究的范畴,“语言腐败”作为思想作风败坏的新样态,已被学者们归纳为“微腐败”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习近平对“微腐败”做出如下表述:有的搞雁过拔毛,挖空心思虚报冒领、克扣甚至侵占惠农专项资金、扶贫资金;有的在救济、补助上搞优亲厚友、吃拿卡要;有的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执法不公,甚至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代言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习近平对当前基层官员“微腐败”做出的概括涵盖了物质利益和思想作风两个方面,这表明,多维全面地归纳“微腐败”的表现形式,是未来研究的基本方向。
综合来看,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优亲厚友、收受礼金、公款私用等直接获取经济或物质利益的行为是“微腐败”行为的重要类型,也是绝大部分“微腐败”行为的普遍表现形式。但是,“微腐败”不仅仅表现在违规违法获取物质利益这一层面,懒政怠政、涉黑涉恶、作风糜烂、渎职以及“语言腐败”等恶劣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同样也构成“微腐败”,却难以被认定。就目前学术界对“微腐败”的分类情况看,在界定“微腐败”时,个人思想和作风问题将会占有越来越多的权重,这也预示着对“微腐败”问题的研究在逐步深入,剖析角度更加全面丰富,有助于为新时代全面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三、 成因:“微腐败”的生成机制探析
“微腐败”为什么会发生?对“微腐败”生成机制的研究是新时代廉政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认识“微腐败”的成因,对于从理论层面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在实践层面提出有效治理措施具有双重意义。通过探析法律法规、社会文化、监察制度和主体态度与“微腐败”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了对“微腐败”的认知,为党和国家多角度综合施策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法律层面:法律法规不完善为“微腐败”的产生创造了空间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开端,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违纪违规行为就会有恃无恐,违法犯罪活动就会恣意横行。李双清、刘建平认为,“微腐败”是基层法治环境现状不理想的集中体现,消极的法治环境是基层“微腐败”产生的根源所在;[1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16]2016年起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将挪用公款罪的起刑点数额调整为3万元。现行法律条款的这种原则性规定难以对贪污数额微小或者表现为道德、作风问题等的“微腐败”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同时也使得腐败分子在违法邊缘的灰色地带有恃无恐,打法律的“擦边球”。
(二)文化层面:落后文化残余为“微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多依靠宗族关系、血缘关系和圈子关系进行维系,简言之,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由于乡缘、学缘或业缘而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小圈子在中国社会中屡见不鲜,基层更加普遍。这种小圈子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排他性,极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卜万红认为,传统政治文化是基层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微腐败”产生的政治文化基础存在广泛,包括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当中的宗族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伦关系、家庭秩序和社会关系网络、家长制传统、官本位意识和全能主义等。“微腐败”形成的文化机理根系深厚,一些封建落后思想、特权思想以及圈子文化依附于现代政治架构之中,影响着政治主体的思想和行为。[17]
(三)制度层面:监察制度缺位使得“微腐败”成为了社会顽疾
在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权力的自由裁量范围较为灵活,上级领导部门和监察机关很难对基层公职人员的失范行为做出有效的监督和准确的裁定。周师认为,乡村地区基层干部及公职人员纪律意识淡薄、权力过分集中和有效监督的欠缺是造成乡村“微腐败”的原因;[18]定明杰、史健认为,基层领导干部的选拔甄别机制失衡、基层公务员对自我行为和思想的调节机制失效以及监督机制失灵是导致我国当前基层腐败难以消除的重要原因;[19]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基层公职人员的薪资福利制度不完善会对“微腐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较低的薪资水平、不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诱使公职人员向利益伸手,不敢或没有机会谋取私利的则“破罐子破摔”“得过且过”。
(四)主观层面:主体价值观扭曲为“微腐败”的蔓延注入了催化剂
个人价值观的扭曲对“微腐败”行为的助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层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唯利是图、作风败坏;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漠不关心,容忍纵容。邹东升、姚靖从三个方面对乡村“微腐败”的生成原因做了论述:第一,对“微腐败”的惩治力度过小;第二,村民对“微腐败”的容忍度较高;第三,村民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13]李靖、李春生将“微腐败”的生成机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微腐败”的潜藏期,“微腐败”发生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包括掌握公共权力、渴望物质利益和受到诱惑;第二阶段是“微腐败”的酝酿期,行为主体着手寻找机会完成腐败行为,包括获得动机和达成“同盟”;第三阶段是“微腐败”的激发期,这个时期是腐败发生的时期。[4]
总的来看,“微腐败”的生成机制是个综合复杂的过程。“微腐败”行为的产生并不是单一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微腐败”生成机制的研究,明晰了法律法规不完善是根本原因,落后文化的腐蚀是深层次原因,监察制度缺位和主体价值观扭曲又加剧了这一现象的蔓延。取得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就必须形成多元一体、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而形成这一体系的前提是明确“微腐败”行为的生成机制。因此,对“微腐败”行为生成原因的研究,有助于突出完善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加强社会文化建设,强化监察体制建设,提升个体思想道德素质和公民意识,为治理“微腐败”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
四、 影响:“微腐败”的后果评析
“微腐败”会引发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对“微腐败”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毋庸置疑,“微腐败”轻则违纪违规,重则违法犯罪,会对社会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微腐败”究竟会对哪些领域产生消极影响?诸多学者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集思广益,从现代化进程、党群关系、人民利益和社会风气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评估了“微腐败”所引发的消极影响。
(一)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实现善治的国家,必然要以良好的政治生态为基本前提,“微腐败”破坏了基层的政治生态,进而破坏了社会政治生活。俞可平指出,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善治的首要前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对于社会政治生活而言,恰如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对于居民的日常生活一样重要;[20]李有林认为,“苍蝇扑面”使得政治生态恶化。“小事弄权”这一违纪行为本身将产生严重的“污染”效应,容易影响整个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所以不容轻视。“蚁贪行为”致使国家整体治理成效遭到弱化。反腐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发展。[21]
(二)破坏政府形象和党群关系
政府公职人员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做人民的公仆。“微腐败”违背了这一宗旨、原则和角色定位。俞可平提出警示,“微腐败”已经导致政府公信力缺失,公共权威丧失,人才逆向淘汰等恶果。李威认为,事小多发,损坏干群关系。“微腐败”行为往往发生在离群众最近的基层一线,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导致群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损坏了干群关系,与党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22]李有林指出,“小腐微腐”可能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若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滥用职权,抢占民众利益,无论其具体的数量大小如何,都会严重影响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21]
(三)损害人民切身利益
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微腐败”使得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帕累托最优”,至少也应当让绝大多数人获益。但是在“权力拜物教”的影响下,人民群众常常面临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窘境。杜治洲认为,基层公职人员负责着各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他们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时本应该是“马上办”“尽快办”,但现状却是“等等看”“拖着办”。此外,一些地方公职人员在落实惠民政策的过程中欺上瞒下,大打折扣。惠民资金“惠官不惠民”“不跑不送不给办”等问题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增添了负担,也给人民群众的感情造成了伤害。[23]
(四)败坏社会风气
端正的社会风气为培养“四有”青年和推进社会主義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氛围。李威认为,“微腐败”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与公信力遭到侵蚀。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休戚相关,若任凭“微腐败”大行其道,基层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纷纷效法,势必败坏当地的社会风气,更有甚者对其他地区造成消极示范;[22]罗清认为,“微腐败”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如果自身思想政治觉悟低下,无视纪律和法规,腐化堕落,将对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干扰,妨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4]
综上所述,学术界已充分认识到了“微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微腐败”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政府形象、党群关系、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风气已然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可见,“微腐败”对社会的贻害不是一丝一毫,也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广泛而持久的。若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提出整治措施,做不到抓铁有痕、踏石有印地贯彻落实治理方针,小腐败终将质变为大祸害。学者们对“微腐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作出的科学全面的评析,对分析“微腐败”演变的形势、核查可能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提出治理措施以及预估未来的整治力度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五、 治理:“微腐败”的整治对策分析
如何科学有效地整治“微腐败”?这是研究“微腐败”问题的价值旨归。当前学术界普遍倾向于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社会风气和个人思想觉悟四个向度提出治理对策。学者们通过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从强制措施到思想道德教育、从强化传统模式到注重方法创新,全方位、多层次地为整治“微腐败”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立法制规向度
通过政策和法律实现控权、限权和规训用权者来预防和矫正公职人员的失范行为是整治“微腐败”的核心逻辑。邹东升、姚靖认为,学习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推动国内立法工作,对于细化、量化法律裁判标准,预防和惩处“微腐败”至关重要。[25]如2016年10月,韩国颁布实施的《金英兰法》,详细规定了十五种涉及“微腐败”的行为以及法律后果。又如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公职人员不得接受20美元以上的礼物,全年累计不得超过50美元,且不得接收礼金及有价证券等;芬兰法律规定公务人员接收超过20欧元以上的礼品,超出部分即使是食品也须上交;在新加坡接收一元钱都是违法。萧鸣政、李净认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顶层设计和国内反腐败斗争的基层实践有机结合,才能使“微腐败”的治理卓有成效。[26]
(二)纪法衔接向度
国法是任何人都不能触碰的底线,党纪党规是党员干部不能逾越的红线,党规党纪的法制化和法律法规灵活实施是治理“微腐败”的有力抓手。学者们普遍认为,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次,深入学习和落实2017年10月和12月颁布和实施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 试行) 》,这是细化、量化、制度化治理“微腐败”的又一关键步骤。邹东升认为,要将权力置于“密网固笼”下,并且加强党纪党规的精细化管理。[8]党纪与国法的衔接推进是十八大以来治理“微腐败”的成功经验。[25]
(三)清风正气向度
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为打击“微腐败”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2018年,赵乐际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探索开展县(市、区、旗)交叉巡察、专项巡察等方式方法,着力发现并尽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见到实效;[27]吕永祥、王立峰基于对当前治理“微腐败”过程中的现实困境的研究,提出了三点应对措施:第一,通过对监察人员进行培训与对内设机构进行整合,来提升县级监察委的腐败治理效能;第二,通过采取异地交叉巡察和报请提级管辖等手段,以排除基层执法过程中人情干扰;第三,将基层“微腐败”治理与“清扫黑恶势力、铲除保护伞”专项工作结合起来。[28]
(四)思想道德教育向度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充分调动人的主体性是防范和消灭“微腐败”的内在动力。必须坚持提升基层公职人员思想道德水平和喚醒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并举。李威认为,要为思想道德教育创建生动的载体;推进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化、常态化;树立典型模范,基层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正能量,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10]余雅洁建议,开展全民反腐败教育,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治理“微腐败”的斗争;[12]还有部分学者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指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助长了“微腐败”。大多数群众一方面在面对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选择隐忍,另一方面,在社会往来中又无时不在效仿“礼尚往来”的交际模式。增强群众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是治理“微腐败”不能忽略的重要一环。
总体来说,学者们基于对“微腐败”的概念、表现形式、产生原因的研究,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对策建议,总的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基层范围广,情况复杂,目前学者们提出的策略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还不能很好的做到因地制宜,二是缺乏对行政成本的综合考量。这对“微腐败”研究的实践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未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六、 前景:“微腐败”的研究趋势
立足于本篇综述对“微腐败”问题的系统考察可以发现,在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这一领域研究成果颇丰,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显著增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角度更加新颖,视域更加广阔,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需要挖掘研究深度。学术界对“微腐败”生成机制的研究,大多流于表面,学者们普遍偏重于对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探讨,比如法律法规不完善、检查机制缺位、落后文化侵蚀和个人思想道德水平滑坡等问题,但是忽略了对于行为主体本身的研究,比如主体的心理机制在“微腐败”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又比如主体原生家庭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这就容易导致对“微腐败”生成机制的研究产生断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对策则会失去针对性,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最终流于形式。二是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诸学者集中力量针对某一个切入点进行深入演绎和推理,不断丰富概念的内涵与理论的外延,使得理论层面的研究更加综合全面,更加层次化、精细化,但是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和实证调研。目前,鲜有学者就“微腐败”治理的成效给出确切的数据支持,也很少有学者就其提出的治理措施的行政成本给出明确的统计结果。例如有学者提出利用“互联网+”“5G”和“大数据”技术进行监察,但却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实证调研结果来证明其对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使得对“微腐败”的研究陷入“以理论论证理论”的困境。三是需要加强比较研究。从横向来看,一方面学者们对不同基层单位和不同地区的“微腐败”比较不足,另一方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微腐败”比较不足;从纵向来看,对不同时期、职级、年龄和性别的“微腐败”缺乏比较。从社会学的角度考量,不同社区的群体,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对不同社区的“微腐败”的研究就不能等量齐观,必须在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力求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当下,对“微腐败”问题的研究空间还很广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廉政建设必将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理论界对“微腐败”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第一,研究视角更具多样性。学术界与时俱进,开辟崭新的研究视角。学者们逐渐开始拓宽“微腐败”概念的外延。比如“语言腐败”等新概念已开始被引入“微腐败”的研究范畴;又比如“互联网+”“5G”和“云计算”等新技术逐渐被纳入“微腐败”的治理策略研究之中;学者们还开始从心理发生机制的角度推演“微腐败”的生成逻辑。第二,研究目标更具针对性。学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加注重研究的实践价值。学者们将会聚焦某一地区或某一基层单位,展开对这一具体范围内的“微腐败”的研究,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组织机构运行状况和乡风民情等具体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给出切合本地区实际的对策。第三,研究体系更具系统性。学界与时偕行,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学者们不再将“微腐败”作为一个孤立的议题进行研究,而将其放在更宏大的战略层面研究。学者们由单纯研究“微腐败”问题开始转向研究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微腐败”,农村精准脱贫工作中的“微腐败”,高校工作中的“微腐败”和基层部队的“微腐败”。
综上所述,对“微腐败”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是新时期进行伟大斗爭的重要任务。自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对廉政建设的研究。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进行研究还是在实践层面提出建议,我们都必须与时俱进,重视理论知识的创新,更要尊重实践经验,力争构建一套多元一体,完善规范,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诚然,在对“微腐败”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亟待完善,因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不断完善“微腐败”研究的学理基础和方法体系,还要充分借鉴国外研究和治理的有益成果,总结我国研究和治理经验教训,对我国目前基层“微腐败”状况作出科学的评定,进而探索出推动基层反腐败斗争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美)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玉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54.
[2] 胡鞍钢.隐性腐败更应关注[J].当代经济,2001(6):7.
[3] 夏红莉.基层“微腐败”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对宿州市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调研报告[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5):1-4.
[4] 李靖,李春生.我国基层官员“微腐败”的生成机理、发展逻辑及其多中心治理[J].学习论坛,2018(7):58-64.
[5] 周师.“微腐败”概念辨析[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9(2):75.
[6] Bank W.Helping Countries Combat Corruption:The Role of the World Bank[Z].Washington DC:World Bank Group,1997.
[7] 周琪.西方学者对腐败的理论研究[J].美国研究,2005(4):38-55.
[8] 邹东升.“微腐败”的治理经验和路径[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3):127-135.
[9] 任中平,马忠鹏.从严整治“微腐败”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以四川省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为例[J].理论与改革,2018(2):49-58.
[10] 李威.基层“微腐败”的危害及治理建议[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6(6):42-45.
[11] 史云贵.哪些基层腐败令人深恶痛绝[J].人民论坛,2017(5):14-17.
[12] 余雅洁,陈文权.治理“微腐败”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有效途径[J].中国行政管理,2018(9):105-110.
[13] 邹东升,姚靖.村干部“微腐败”的样态、成因与治理——基于中纪委2012到2017年通报典型案例[J].国家治理,2018(2):4-12.
[14] 殷路路,李丹青.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行为分析与精准治理[J].领导科学,2018(12):10-12.
[15] 李双清,刘建平.基层“雁过拔毛”式腐败生成的法理透析与防治对策[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2-87.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17] 卜万红.“微腐败”滋生的政治文化根源及治理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17(6):63-69.
[18] 周师.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干部的“微腐败”及其治理路径[J].理论导刊,2018(1):55-57.
[19] 定明捷,史健.我国基层腐败特点及其生成机理解析[J].观察与思考,2016(9):75-84.
[20] 俞可平.走向善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7.
[21] 李有林.从“小事弄权”看微腐败的大祸害及防避对策[J].领导科学,2019(10):9-11.
[22] 李威.治理基层“微腐败”的对策建议[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6(6):62-65.
[23] 杜治洲.改善基层政治生态必须治理“微腐败”[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11):37-38.
[24] 罗清.新时期农村“微权力”腐败形势与对策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9(1):189-190.
[25] 邹东升,姚靖.新时代微腐败治理的纪法衔接[J].理论探讨,2019(1):128-134.
[26] 萧鸣政,李净.铲除基层腐败滋生的土壤[J].人民论坛,2017(5):20-21.
[27] 赵乐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J].中国纪检监察,2018(2):11-15.
[28] 吕永祥,王立峰.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实践价值、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43-50.
责任编校 张煜洋
Manifestations, Causes and Governance: a Synthesis of “Micro-
Corruption” Research
CAI Wencheng, LIN Zhaoyang (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With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y being further deepened, “micro-corruption” has come to the center of corruption treatment, relevant studies becoming the hotspot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s a whole, such research articles are numerous, achievements considerable;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research topics are focused on the concept, manifestation, origin, consequence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as regard its development, such studies will be more varied, pertinent and systematic. Problems can be found in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depth, scarcity of empirical studies and insufficient comparative studies. However, research topics, issues, methods and outcomes have expande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micro-corruption” treatment, and provided guida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for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nd are thus of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icro-corrup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issues; review and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