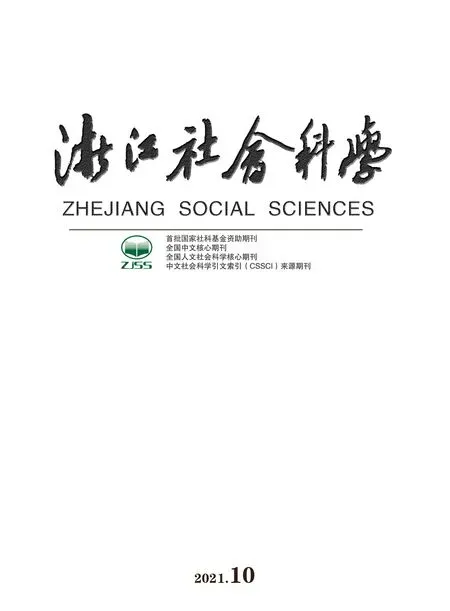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 王守仁
内容提要 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如一些批评家所言“过时”或“枯竭”,而是在向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形态发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也有很多建树,出现了“新现实主义转向”,从新的角度审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探索质疑传统观念、范式和认知,显示出这一研究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以中文和外(英)文为载体,两个知识体系应该是对话的关系,互为支撑。以莫言、阎连科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方面对世界现实主义做出贡献,促使中国外国文学学者的现实主义研究融通中外,在全球学术空间进行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的创新。
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与虚拟既彼此依存又对峙交锋的时代。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平台、虚拟现实技术、 移动科技不断提升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和探究自我的阈限,挑战人们对真实的传统认知。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当下更加渴望在千变万化、 虚实难辨的人间万象和浩瀚宇宙中把握确凿可信、无可辩驳的真实。从风靡全球的真人秀节目、凸显普通人视角的自媒体兴起,到不久前天文学家们调集遍布全球的毫米/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通过合成照片终于解锁了宇宙黑洞的“庐山真面目”,人类一直试图挣脱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描绘的幻象枷锁,接近真实的光明。这份对真实孜孜以求的渴望与探究同样涌动在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20 世纪中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摹仿论》中论述西方文学对真实进行诠释或“摹仿”的传统,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圣经文学、司汤达到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思潮风靡学界,真实作为一个形而上的“绝对”①观念,首当其冲成为解构的目标。进入21 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退潮,人们把目光放到后现代主义之后,要超越后现代主义,重新审视文学与真实的关系。②谢尔兹(David Shields)2010年发表的《真实的饥饿:一份宣言书》在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有史以来的每一次艺术运动都在寻找将艺术家所认定的真实更多偷偷带入艺术品中的路径。”③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洗礼的当代文学呼唤着更加深刻、多变的表现方式,以回应当代社会对真实的“饥渴”。回顾检视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历史,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文学揭示真实的认知价值,在守正的基础上推进文学理论话语创新,不无裨益。
一
英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于1719年问世,距今已有300 多年历史。根据韦勒克(René Wellek)的研究,“现实主义”(Realism)这个术语用于文学批评,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剧作家、诗人席勒1798年致歌德的书信。④现实主义在19世纪成为西方文学主潮,涌现出司汤达、 巴尔扎克、狄更斯、爱略特、托尔斯泰、亨利·詹姆斯等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巨匠。进入20 世纪,现实主义相继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冲击。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批评家发出“现实主义已死”、“现实主义过时了”的声音,人们曾一度质疑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认为其表现手法单一,不足以描写战后复杂的生活现实,对现实主义前景持悲观态度。特别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转向”后一批理论家质疑语言指涉现实的功能,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后现代主义解构“现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冲击。但是,现实主义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所谓“现实主义过时论”(the obsolescence of realism)⑤、“现实主义之死”的预言站不住脚。
语言是现实主义作家传递其对现实感知的工具,其指涉现实的功能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的诗学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战后西方思想界出现“表征危机”,语言符号不再作为一种可靠的表征手段,无法“真实”“客观”地表征客观现实。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具有任意性,它不能反映世界或客观现实,不接受指涉现实世界的要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关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客观存在则用括号括起,予以悬置。巴特(Roland Barthes)将语言视为独立于现实的封闭系统,将文学定性为“一种言语活动”、“一种符号系统”,割裂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对于现实,话语不负任何责任:最现实主义的小说,其中的所指物毫无‘现实性’可言……(现实主义文论中)所谓的‘真实’,只不过是(意指作用的)再现符码而已。”⑥巴特认为文学仅仅属于言语活动,否认语言的现实指涉功能。米勒(J.Hillis Miller)呼应巴特对于语言意义的论述,提出现实主义文本是进行自我指涉的,而无法突破语言的封闭系统去指涉历史现实。⑦
当然,语言与客观现实、文学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真的如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可以被割裂。语言的表意功能以及其指涉现实的功能是日常生活交际的前提,也是所有文学文本借助语言这一媒介进行传情达意的基础。首先,从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来看,语言是用于社会交际的符号体系,是传递意义的工具。语言的这一基本功能使得语言可以指涉现实,与客观世界保持一致性;语言这一媒介交际的内容与读者的生活经验相关,具有可信性。其次,这种将语言以及文学视为独立于客观现实的封闭系统的看法忽略了文学的社会根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由社会存在决定。语言是架接文学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桥梁,如果剥夺语言作为桥梁连接之功能,那么所有书写都没有任何认知价值,文学的存在依据也就消失。此外,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虽然强调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沟壑,但是他也认可语言赋予事物以意义,也就是说,人们在言说某个对象的同时也在言说中建构一个意义世界,它包含言说者/叙述者主观认识和态度。现实主义文学符合索绪尔所描述的语言建构的世界:现实主义作家在言语/书写的过程中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又浸染言说者/作者的主观认识;也就是说,作家们在清楚认识到文学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的前提下,使用语言这一表意工具反映客观现实。因此,我们承认语言受使用者主观意识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影响语言指涉现实。
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对象是客观世界,而我们平常生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现实主义所模仿的现实确实存在”⑧。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小说就是回应现实”,“如果书不反映真实,这本书便没有任何价值。文学从文本到文本是一个可耻的谎话连篇的过程……什么浪漫主义、虚无主义……我都不信……”⑨现实主义文学在其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创作特征,卢卡奇将其总结为真实性、典型性和历史性。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1888年恩格斯在写给作家哈克奈斯小姐的信中曾这样点评其小说《城市女孩》:“你的这部小说不够现实主义。在我看来,除了细节的真实,现实性暗示的是对典型环境的忠实的再现”⑩。典型环境是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应能集中体现某些根本性的特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现实超越了细节层面,是具有典型性的现实,典型性意味着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革命导师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述对我们观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现实主义文学拥有“灵活、宽泛、不稳定、彻底开放”⑪的内涵与外延。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简单的同一概念,相反,它立足于历史语境,其含义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发展。现实主义文学试图展现真实世界的微模型,在有限的叙述中展现一个足以补充历史现实世界的平行现实。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性也体现在与处在历史进程中的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是一个因语境以及主体的不同而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发展、变化的内在发展机制,永远在挑战并超越旧时普遍的文学模式,并在超越陈规的过程中,或是改革旧有表征方式,或是创造新鲜的手法表现历史现实。早在1961年,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 一文中提出现实主义是一个“时期概念”(period-concept)⑫,将现实主义视为历史的、阶段性的文学事件。作为“西欧本原性现实主义”⑬的19 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有其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性边界,现实主义本身在20 世纪继续发展、演变。现实主义与现实有关,现实主义的真实是对现实存在的认同。20 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复杂的社会生活既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给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主题。特别是战后现实主义作为在19 世纪已成系统的现实主义诗学的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有着多种外在形态的“复数”概念。这种变革与创新的“复数”现实主义体现在世界各国涌现的众多现实主义,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自觉现实主义、地域现实主义、主体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等。这表明现实主义没有停滞凝固,而是在向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形态发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二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形态不一,流派纷呈,具有表现题材、真实标准、叙述手法多样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也向纵深推进。20世纪上半叶,卢卡奇与布莱希特曾围绕现实主义展开论辩;60年代初,韦勒克和格林伍德就现实主义概念进行学术交锋; 当代学者继续就现实主义诗学进行探究,对传统观念、范畴、认知方式和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展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现实主义如何反映现实、 追求真实始终是人们关注和探究的课题。客观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描写的对象,也是创作的基础。在说明现实主义可以而且应该表现客观现实时,我们可以引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阿尔都塞在他著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一文中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生存的真实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征”。意识形态是“想象的”,并不对应于现实,但是,他又指出:
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并非对应于现实,换言之,它们构成一种幻觉,同时我们也承认它们确实暗指现实,只要经过“阐释”,便能在想象的表征世界背后发现那个现实的世界(意识形态=幻觉(illusion)/暗指(allusion)。⑭
现实主义文学与意识形态具有类似的特征,两者都是想象的,并不对应于现实,但是正如阿尔都塞所言,虽然现实主义是虚构的“幻觉”,但同时也“暗指”现实,在想象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背后能够发现客观现实;反过来,客观现实一直被假定为现实主义文学世界的参照物。
阿尔都塞在文章中提出了独创的“意识形态/主体”说。他将个人视为“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的主体:意识形态从无数的个人当中征召主体,赋予意识,将其改造为属民。在阿尔都塞称之为“询唤”的过程中个人对意识形态作出反应,辨认意识形态提供的整体图像后,获得一种认同感。⑮作品的“真实”同样也被意识形态化:真实是认同意识形态后获得的。作品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期望: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对世界是怎样这种认识的期望是受意识形态制约的。因此,“真实”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因时代和作家而异。“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再现绝对客观存在的生活本来面目,每个作家竭力把握和表现的,仅是他感受到的那个相对真实的生活本来面目。”⑯
韦勒克认为艺术不可能脱离现实,而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如此,它的目标是追求真实,但是他强调这是“一种更高的现实,一种本质的现实或一种梦幻与象征的真实”⑰。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再现/反映连贯自主的现实,另一方面日常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跳板”(springboard),现实主义又基于日常的认识与经验。⑱所谓“跳板”不仅暗示现实主义文学以日常现实为基本素材,也指出现实主义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与沟壑,需要跨越,以跃上更高的层面。
摹仿冲动和对外界现实的关注是现实主义诗学的根本,但是这种摹仿并非简单的复制,现实主义文学是作者主观意识参与的创造性再现的结果,它所追求的并非是与历史现实零距离的“逼真感”,而是一种“本质的现实”,是来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艺术现实。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现实主义文学能动地反映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其能动性包含着作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现实主义文学被视为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一种行为,一次实践”⑲。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当代文学理论界就文学本质及其与社会关系思考得最为深入的学者之一。在《文学事件》(2012)中,伊格尔顿将阅读文学作品比作为心理诊疗室中发生的场景:这是一个与现实生活分离、高度仪式化的表演空间,诊疗病人(叙述者)对一个刻意隐身的心理分析师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梦境,而心理分析师(读者/阐释者)则试图透过病人的讲述把握病人的问题症结。不论讲述的内容是否真实发生,在心理诊疗室大门内,受到关注的只是叙述话语在病人表演活动中的作用;同样,在文学作品中,“真相并非直接指涉[外部世界],而是指一段陈述在更广阔的虚构情境中体现的功能”⑳。伊格尔顿接着指出,正如心理分析师不只关心病人的梦境内容,还更关注通过病人的讲述策略和口误来挖掘其无意识一样,文学分析也不应止步于对“梦文本”(dream-text)的语义解释,而要进入对“梦创作”(dream-work)的话语策略分析,挖掘作品内暗涌的社会动因。“梦文本”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独立性,而只是在“梦创作”的复杂层面,现实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才进入作品。伊格尔顿虽是针对所有文学创作,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阐释对现实主义创作最为适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现实主义的优势:现实主义作品既成功维持了艺术“梦境”的整全,又没有丧失社会批评的力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十年,国外学者对现实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012年《现代语言季刊》 推出《边缘的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s)专辑,关注当今世界经济核心国家之外的边缘地区、 半边缘地区的现实主义发展。艾斯蒂(Jed Esty)与莱(Colleen Lye)撰写长文,将文学批评领域研究方法发生的新变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转向”(“new realist turn”),认为这是继“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后文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向。2013年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出版《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对以福楼拜、左拉、托尔斯泰、加尔多斯、 乔治·爱略特等人为代表的19 世纪现实主义进行再思考,在此基础上建构现实主义新理论。詹姆逊对现实主义的思考是从情动维度切入,他将情动视为现实主义时间性迈进的动力。同年比尔克(Dorothee Birke)和布 特(Stella Butter)主 编《当代文化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政治、媒介构造》文集,从全球视角讨论英国、德国、爱尔兰、苏联、塞内加尔、土耳其、美国等国家的现实主义,涉及小说、戏剧、电影、摄影、绘画、纪录片、电视新闻等多种媒介,我应邀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期刊为该文集撰写书评,讨论其跨国界、跨媒介、跨学科特征。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小说》期刊推出《世界性现实主义》(Worlding Realisms)专辑,刊登9 篇学术论文。作为21 世纪的学者,撰稿者们“对如何超越19 世纪状况和欧洲空间的世界性现实主义进行探索”,即在时间上不再局限于19 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在空间上打破以伦敦-巴黎为地缘轴心的世界文学模式。
当代学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颠覆了传统认知,有助于我们突破固化思维的框架,启发我们去思考和发现当代现实主义研究各种新的可能。如莫里斯(Pam Morris)借鉴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言理论,提出了 “转喻式现实主义”(metonymic realism)的理念。雅各布森分析话语的发展沿着两条语义路径进行,即选择轴上的相似性和组合轴上的相邻性,前者是隐喻方式,后者是转喻方式。传统现实主义追求真实是基于主体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相似性,因而属于隐喻式现实主义。在转喻模式下,局部通过相邻性原则与整体建立关联,雅各布森还将“举偶”(synecdoche)纳入转喻,这意味着局部可以代表整体。转喻式现实主义跳出主体/客体分离所产生的“二元化对立”,从主体/客体融合的假设出发,文本与世界的关系遵循相邻性原则发生关联,成为其组成部分,从而消解了语言与现实的沟壑。
三
对于国外当代现实主义的研究进展,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自然十分关注,与此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丰富和发展现实主义研究,并形成中国特色。
现实主义在五四前后被引介到我国,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作家、批评家和译者最早使用的是“写实主义”,1932年瞿秋白提出将现实主义取代写实主义。他在翻译《高尔基论文选集》后写的序言中指出:
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而他对于现实主义的了解是这样的!他——饶恕我把他来和中国的庸俗的新闻记者比较罢——绝不会把写实主义解释成为“纯粹的”客观主义,他不懂得中国文,他不会从现实主义realism 的中文译名上望文生义的了解到这是描写现实的“写实主义”。
“写实”和“现实”,一字之差,却蕴含深刻含义。现实主义中的“现”也可理解为“显现”,揭橥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瞿秋白此处谈及外国文学翻译的“中国文”使用,也涉及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外国文学”顾名思义,“外”字当头,有别于中国文学,指外在于中国的世界各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是在中国语境下研究世界各国文学,隐含了中国主体立场。目前大部分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是以中文为载体,这个知识体系是为中国读者服务,“为了繁荣、 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体”。就现实主义而言,中国学者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积累起丰富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外国文学研究还有一个以外(英) 为载体的知识体系。据统计,“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的英文期刊占96.17%,“艺术与人文学科引索引”(A&HCI)中的英文期刊占75.26%。两个知识体系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而话语是有动机和目的的交流方式,隐含意识形态、 社会历史文化、学术传统规范等。以中文为载体的外国文学研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受叙者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读者,必须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和阅读期待,而以英文为载体的外国文学研究是面向国外的英语读者,有不同的目的、功能、语境和价值。“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术走出去,发出中国学者强劲的声音。在这方面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优秀学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提高了中国学术的国际显示度。鼓励用英文写作,并不意味着中文论文不重要。文秋芳呼吁要重视“以中文为载体的学术创新”,避免“洋文至上”倾向。李宇明从“三世界”视角来看语言的功能,即发现新的世界图景,保存旧日世界的老图景,转述新世界,通过翻译获得世界新图景。“只有前沿科学家(包括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才能发现新的世界”,“首先描绘新的世界图景”。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语言在描写新世界,努力“增加中文的国际知识供给”,使中文成为原创知识的载体,这是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实施“中文首发”制度的意义:新知识的创造在中国,载体是中文。
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两个知识体系因其各自的学术传统、互文指涉、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同而存在差异,两者虽然自成一体,但不应该自我封闭、相互排斥,而是要展开对话、互为支撑,“使中英文和中外知识同步双向循环”。语言作为知识载体必须在多维度对接契合,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文学的产生、 流通和接受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形成文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文学性”。叶兆言曾说:“一个中国作家,他要是说自己不看外国小说,没有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那一定是在骗人。”但受影响并不等同于一味模仿重复。2012年莫言因其作品“将幻觉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融合在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新闻稿将hallucinatory realism 说成“魔幻现实主义”,这是明显误译。早在1980年代,莫言就自觉地与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保持距离: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
……
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
莫言发现靠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太近,就没有了自己。他逃离这两座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成功地创造、开辟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区,“幻觉现实主义”具有他自己的特色,而这归功于他深入扎根供他生长的土壤。同样,阎连科也一直在积极探索现实主义,既有理论的思考,也有文学创作实践来支撑。他在21 世纪提出了“神实主义”的理念,其小说《炸裂志》和《风雅颂》成为神实主义代表作。阎连科对神实主义进行界定,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阎连科常用的一个比喻——“神的桥梁、实的彼岸”——体现出当代现实主义的一个发展路径,不仅仅是形式上(桥梁)的变革,相应的也有在内容上对现实(彼岸)的不懈追索。
以莫言、 阎连科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突出成绩,是扎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国历史传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他们对世界现实主义做出贡献,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既提出了新的命题和任务,也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即我们不能脱离中国文学的丰富实践研究外国文学,而是要从中汲取滋养,并用外(英)文阐发中国作家文学创作,将学术成果放在国际平台上传播和交流,通过议题设置、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在全球学术空间进行现实主义理论话语创新。新时代要求我们处理好以中文作为载体的知识体系和以外(英)文作为载体的知识体系的关系,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使我们的现实主义研究因扎根中国而富有原创性,因独立思考而具有思想性,因融通中外而富有活力和生机。
文学是虚构的,但正是通过虚构可以揭示真实,而现实主义最能体现文学的这个特点。现实主义文学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同时,它的反映现实不是对现实做机械的翻版,而是兼顾艺术的审美与对“知识或真理”的认知,并且在反映生活现实的过程中介入历史进程。现实主义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伍德(James Wood)在《小说机杼》结尾时指出现实主义具有“生活性”(lifeness):“页面上的生活,被最高的艺术带往不同可能的生活。”真正的作家必须抱有这样的信念,“小说迄今仍然远远不能把握住生活的全部范畴”。蒋承勇在强调重视“19 世纪现实主义这份厚重的文学资源”时确定的第一个“有待深入研究与发掘”的问题便是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念”。如此看来,无论是当代作家也好、文学研究者也罢,我们依然还在追寻和探索现实主义的漫漫征途上。现实主义文学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将不断拓展疆域,开辟广阔天地,推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而现实主义文学研究本身也将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不断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
注释:
①王守仁等:《英美文学批评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0 页。
②Klaus Stierstorfer,“Introduction: Beyond Postmodernism-Contingent Referentiality?”,in Klaus Stierstorfer ed.,Beyond Postmodernism: Reassessments in Literature,Theory,and Culture,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03,p.9.
③David Shields,Reality Hunger: A Manifesto,London: Penguin Books,2010,p.3.
④René Wellek,“The Concept of Realism in Literary Scholarship”,Neophilologus,45.1(December 1961),p.3.
⑤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London: Routledge,1971,p.4.
⑥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 页。
⑦J.Hillis Miller,“The Fiction of Realism”,in Lilian R.Furst,ed.,Realism,London: Longman,1992,p.287.
⑧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 Road”,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 Road,London:Routledge,1971,p.26.
⑨《“我的小说就是回应现实的召唤”——访菲利普·福雷斯特》,陈丽萍/文、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024533601133173&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1年5月21 日.
⑩Ren Wellek,“The Concepts of Realism in Literary Scholarship”,Neophlogus,Vol.54,No.1 (1961),p.5.
⑪Andrzej Gasiorek,Post-War British Fiction: Realism and After,London: Edward Arnold,1995,p.14.
⑫René Wellek,“The Concept of Realism in Literary Scholarship”,Neophilologus,45.1(December 1961),p.2.
⑬蒋承勇:《五四以降外来文化接受之俄苏 “情结”——以现实主义之中国传播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4 期。
⑭⑮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62.
⑯杨金才:《廿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命运》,《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5 期。
⑰René 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224.
⑱Damian Grant,Realism,London: Methuen,1970,p.59.
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