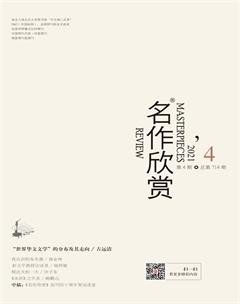元好问诗歌通释三则(九)
查洪德
关键词:颍亭 壬辰 癸巳 青城
《颍亭》
颍上风烟天地回,颍亭孤赏亦悠哉。春风碧水双鸥静,落日青山万马来。胜概消沉几今昔,中年登览足悲哀。远游拟续骚人赋,所惜匆匆无酒杯。
颍亭,在登封颍水上游。颍水发源登封,东南流入淮河。本诗写作时间,或说兴定三年(1219),或说正大二年(1225)。诗中情感比较复杂,作于兴定三年的可能性不大。此诗解读起来有些困难。诗人来到颍亭游赏,原本以闲静心情玩赏山水,但心情突然变坏,满心的悲哀与烦恼,不知如何排遣。
诗的前四句赏景。“颍上风烟天地回”,颍上,颍水之上。风烟,这里指风景。天地回,言颍上风景,颍水风涛壮阔,可以回转天地。杜甫《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巫峡秋涛天地回。”赵彦材解:“盖言秋涛之势,可以回转天地也。”“颍亭孤赏亦悠哉”,孤赏,独自游赏。悠哉,悠闲而从容。“青山万马来”,写山势如万马奔腾而来。古人多以马喻群山,宋周紫芝:“谁知隔岸山,万马日奔赴。”(《送孙求仁官黄冈》)
下四句诉怀。胜概,美丽的景色。消沉,消逝,逝去。“几今昔”有二义,一为“多少时光”,如“一片青山几今昔,百年华屋记生存”(元好问:《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一为“今昔几”之倒装,意为“古往今来有多少”,如“流水浮生几今昔”(元好问:《九日登平定涌云楼故基楼即闲闲公所建》)。此处当为第二义。足,多。“中年登览”句用《世说新语》“中年伤于哀乐”语意。“远游拟续骚人赋”为“拟续骚人《远游赋》”之倒装,“骚人”指屈原,屈原有《远游赋》。
诗人由前四句的赏美景突然转到了后四句的诉恶怀,是什么刺激了诗人内心敏感处,使得情怀转恶了呢?诗人心境不会无故变坏,在心灵深处有着潜在的根基,因外境触动而诱发。在诗中寻找,只能是上四句与下四句的衔接处“万马来”三字,将原本“亦悠哉”的心境,推向了“足悲哀”。
心灵深处的根基应该是两个方面的,诗人没有揭明,读者不易觉察。第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把诗人所在地颍川和眼前景象——群山奔赴如“万马来”,与当时诗人的身份结合起来看就明白了。颍川,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标志性符号,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显著信息:隐逸(相传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不受而逃去。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事见晋皇甫谧《高士传·许由》)和战争。目前对元好问心情造成冲击的,是战争:“颍川,四战之地。”《后汉书·荀彧传》载,荀彧颍川人,“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大难。宜亟避之”。元好问恰恰是来此避兵的,这无疑很影响他的心情。眼前群山奔赴如“万马来”,这是壮美景色,而当时真实的蒙古军万马,随时可能到来,是元好问要躲却躲不了的战争威胁。这应该是诗人“足悲哀”的一个方面。“胜概消沉”的不幸,历史上曾有多少,而眼前颍亭与颍上美景,或许又面临“消沉”的危险,这无疑引发了诗人更复杂的思绪。从“远游拟续骚人赋”看,袭上心来的“悲哀”,还与他在朝遭受排挤的不愉快经历有关。屈原《远游》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时俗迫厄,在元好问“中年”时,首先应该是兴定五年的科场风波,这年元好问中进士,但知贡举的礼部尚书赵秉文,因大力革除科举之弊遭到攻击而“致仕”,元好问愤然“不就选”。再后來,元好问权国史院编修,在国史院因种种不愉快,郁然告归。这诸多的不如意,袭上心来,他想摆脱,于是想到屈原,效法屈原赋《远游》。最后一个问题:赋远游与酒有什么关系?屈原的《远游》,并非身游,而是“托配仙人与俱游戏”(王逸:《楚辞章句》),是精神进入恍惚状态的精神漫游。没有酒,怎么进入这样超忽的状态?不能赋“远游”,也无法驱除心中的悲哀与烦忧。如此解读,或许可得诗人之心。
这首诗最受称赏的,是“春风碧水双鸥静,落日青山万马来”一联,两句动静关系的处理、色彩的调配、柔与刚的和谐,确实难得。出句应是借鉴了黄庭坚“风波春水一双鸥”和陈国材“碧波春水一双鸥”,经点化而出彩。张养浩《同乡友宴会波楼》第二联“春风碧水双鸥没,落日青山万马来”,全用此联,只将“静”换成“没”,后来苦难居上。仔细玩味这一联,“落日”对“春风”,完成情绪的转换,不见用力不着痕迹。另外,后人讲律诗章法,认为这首诗仅颔联对仗,是律诗的一种变格。在我看来,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胜概消沉几今昔,中年登览足悲哀”,也可以说是对仗。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选三)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其二)
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其三)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其四)
题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壬辰,即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这一年是金朝多难且走向灭亡的关键一年。正月,蒙古军围汴京,金援军与蒙古军战于禹州三峰山,大败。四月,金遣曹王为人质求和,蒙古退兵。七月,蒙古使者到汴京,令金哀宗去帝号称臣,金军杀蒙古使,和议绝,蒙古再围汴京。“壬辰十二月”,一个特殊的时间,历史需要记住这一时间。这个月,城中粮尽援绝,瘟疫流行,金哀宗亲征河朔,突围东去,兵败后退守归德(今河南商丘)。此即所谓“车驾东狩”。车驾,特指皇帝的车马,这里代哀宗。东狩,东去巡狩。狩,打猎,也特指君主冬猎。古代皇帝出征、在境内巡行,都称狩,皇帝出逃、被俘,也称狩,是一种隐讳的表达。即事,就当前事物、情景所感而作。
这组诗五首,既不写“壬辰十二月”,也不写“车驾东狩”,写的是这一时间和这一事件“后”的汴京城。“后”字标志着,一个被皇帝抛弃的国都,危在旦夕,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最后的破灭。元好问具有强烈的存史意识,这也体现在他的诗中。这组诗写在一个特殊时期:金哀宗东去之后,新年已过,崔立叛变之前。这时汴京城,在蒙古军的包围中,被死亡的气氛笼罩着。情势如此,一般人顾命不暇,而元好问还用诗笔记录下当时的情况和自己的心理活动。此后经历城破,囊中之物尽失,一命仅存,又被羁管聊城,颠沛流离,这诗却保存下来,可以说诗与生命同在,而这组诗是那段特殊历史最真切、最直接的记录。第一首说看到车驾匆忙走了,自己也渴望“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最后一首说汴京已经不能继续待下去了,希望能够尽快离开;中间三首写这期间的汴京,后人关注的也是中间三首。
先说第二首。第一句“惨淡龙蛇日斗争”写天下势,也是眼前事,化用了杜甫的“干戈虽横放,惨澹斗龙蛇”(《喜晴》),突兀而起,阴风飒至。“惨澹”即惨淡,形容凄惨酷烈、天昏地暗。龙蛇,即龙与蛇,用指争逐天下的双方。《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起兵时曾于泽中斩大蛇,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之十二:“屠钓称侯王,龙蛇争霸王。”这里借指金、蒙双方。日,日日。这句意为:天地因日复一日的战争而惨淡无光。第二句“干戈直欲尽生灵”补写“斗争”的残酷。干戈,盾牌和戈戟,这里借指战争。直欲,简直要。尽生灵,灭尽生灵,言战争之极端残酷。第一联从大处起,得笼罩之势,以下接写天下战局。
第二联上句接首联上句,因“斗争”而“山河改”,下句接首联下句,“干戈”不已而“草木腥”。“高原水出”是陵谷变迁的形象表达,用来指社稷倾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百川沸腾,山冢翠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里化用其意。“山河改”暗用杜甫“国破山河在”(《春望》)句意,而今不仅国破,山河也“改”了。“战地风来草木腥”句化用杜甫“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等句,写战争之残酷,血雨腥风。以上四句写战争残酷,以下四句写人之无奈。“精卫有冤”句用神话中精卫填海故事。《山海经·北山经》:“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瀚海,浩瀚的大海。这句表达虽力量微小但誓死复仇的决心。包胥,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吴国攻破楚都,申包胥到秦求救,秦不允,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事见《左传·定公四年》和《史记·伍子胥列传》。这句说,自己欲如申包胥那样去哭秦庭求援也已无泪。实是说已无处求援。这联说,面对危局,自己虽有精卫填海之志,但求援无处,哭亦无泪,这是第三联。第四联,“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当今何处找挽救危局的“并州豪杰”,能扶大厦于将倾!并州,古地名,治所在今太原,广义上并州泛指河朔一带。并州自古多英杰。莫拟,没有人打算。“分军下井陉”,《资治通鉴》载,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十月,出帝被契丹所掳,驻守并州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闻讯,“声言欲出兵井陉,迎归晋阳”。井陉,即井陉口,河北井陉东北井陉山上之井陉关,太行八隘之一。这两句是说,在皇帝蒙难之际,没有人像并州豪杰刘知远那样急难勤王。
在第二首做全局的扫描之后,第三首落实下来做具体描写,从诗人自身的感受写来。
首联“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点明困居围城已两个年头。金天兴元年(1232)三月,蒙古军围汴京,攻城十六昼夜,城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四月和议成,围解。五月汴京大疫,七月再度围城。十二月,哀宗出逃。郁郁,忧伤,沉闷,心情压抑。“愁肠饥火”,围城绝望无奈,故言“愁肠”;城中食尽,忍受饥饿煎煞,是为“饥火”。这一联写围城中的惨相和百姓的苦难。元好问在围城中度过新年,困居中生活之艰难,用“日相煎”三字概括。“日相煎”提領以下三联,分别从三个方面写“相煎”,展示诗人精神的痛苦。
第二联写无人为国谋,让人绝望。“焦头无客”句用焦头烂额与曲突徙薪之典,事见《淮南子·说山训》汉高诱注。《后汉书·霍光传》所载较详:“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移突,“徙薪”与“曲突”之省略。突,指烟囱。“更为曲突”是说重新把烟囱做成弯曲的。这句是说,金朝缺乏有先见远谋之臣,不能防患于未然。“曳足”即拖着脚缓步行走,用《后汉书·马援传》事。马援率军南征五溪,“三月进营壶头(山名,在今湖南沅陵东),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共船”即同船共谋,用南朝宋刘裕事。东晋安帝时,桓玄篡逆,何无忌劝刘裕除桓玄复兴晋室,“高祖(刘裕)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乃与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之计”(《宋书·武帝本纪》)。这句是说,当此危难之际,没有人像马援那样尽力,没有人像刘裕那样谋划复兴大计。上下两句,“无客”句说文不能谋,“何人”句说武不能战,如此金朝还有什么希望?这是绝望之“煎”。
第三联:“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兵死鬼,死于兵刃之鬼。《淮南子·说林训》:“(战)兵死之鬼,憎神巫。”高诱注:“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杀之。”“元”同“原”。地行仙,佛教所谓十种仙之一,语出《楞严经》,这里当借指地仙,犹言人间神仙,比喻闲散享乐的人。《新五代史·杂传·张筠》:“筠居洛阳,拥其赀,以酒色声妓自娱者十余年,人谓之地仙。”又朱弁《风月堂诗话》:“刘几筑室嵩山,号玉华庵主。每乘牛吹笛,使二妾和之,人目为地仙。”这两句说,战场上“兵死鬼”日益增多,享乐的“地行仙”故态不改,如此现实,使人悲愤,是愤恨与无奈之“煎”。
最后一联写到诗人自身:“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元好问南渡后初居三乡,后徙登封,在汴京西南。“三月”非实际时间,用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句意。“落日孤云”典出陶潜《咏贫士》诗:“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李善注:“孤云,喻贫士也。”此句化用其意,言其穷困中思念家人。孤居围城,亲人信断,牵挂与担忧,是悬望之“煎”。第二三联心忧天下,第四联悲叹家身。自身的孤苦和对家人的牵挂,也煎熬着诗人的心。三重煎熬,把“日相煎”落在实处。
第四首,诗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安慰自己的心灵。他希望战局翻转,绝处逢生。战争之所以称作“风云”,就因为战局往往变化莫测。杜牧《题乌江亭》诗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幻想绝地逢生的人都怀有这样的心理,元好问也一样。不过元好问有自己的思考。
第一联,“万里荆襄”句是说,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到天兴元年(1232),金与蒙古在今湖北、河南交界一带数次大战,金兵主力丧失。荆襄指今湖北江陵、襄阳,泛指这一带地区。“汴州门外”句,指蒙古进围汴京,城外一片荒芜。荆榛,荆与榛,都是灌木,泛指丛生灌木,荒芜残敝。曹植《归思赋》:“城邑寂以空虚,草木秽而荆榛。”这两句说,因荆襄战败,汴京被围,成为战场,满目荆榛。诗人回顾战争历程,为自己寻找立论依据:汴京被围,是因为襄阳之变(其实是三峰山之败),“万里荆襄入战尘”使得“汴州门外即荆榛”。在金人看来,三峰山之败是偶然的,因为战前金军占有明显优势。有偶然之败就没有意外之胜吗?
第二联就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所做的推想:以哀宗的雄才大略,一旦神龙入水,定能播云弄雨。何况他已冲出重围,出离池中,在更广阔的天地,当有机会施展雄才,恢复故国。蛟龙,传说中的两种动物,居深水中,蛟能发洪水,龙能兴云雨,用来比喻风云人物。《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今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蛟龙失水,困于池中,一旦得云雨则能兴其风浪。当时人们相信金哀宗乃有为之君,有重整河山的希望,李俊民《和王李文襄阳变后》二首其二:“蛟龙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垄上人。”即此意。虮虱,虱子和虱子的卵,是极细微之物。“虮虱臣”比喻芥微之臣,唐卢仝《月蚀》诗有“地上虮虱臣仝告愬帝天皇”之句,这句是“地上虮虱臣空悲”的混装,是诗人自喻,说自己这样卑微之臣只是空自悲哀而已。与神龙般的皇帝相比,自己卑贱而微小,悲哀只是小人物的悲哀。在诗里,他似乎已经模糊了幻想与真实的界限,战局的翻转好像真的那么可期。这一联对金国的复兴寄予希望,其实不过是自慰。他甚至已经在设想复兴后,怀念挺身而出救难的英雄。令他失望的是,这英雄今在何处呢?这是第三联,其意境似真似幻,有些像李商隐,给读者的理解带来了一定困难。
“乔木他年怀故国”是“他年怀故国乔木”之倒装。“故国乔木”语出《孟子·梁惠王》:“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古人在都城外种植树木,因此用乔木象征故国。“喬木”这里隐指拯救国难之“世臣”。这句设想战事平定,金国复兴,那时追怀今日,怀念故国,怀念为国赴难的旧臣。“野烟何处”句用唐昭宗《菩萨蛮》词句。唐乾宁三年(896),李茂贞犯京师,昭宗被华州韩建迎至郡中。他登楼西望,思长安而不得回,作《菩萨蛮》词云:“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这联意思是,救难之臣,他年会被怀念,而今在何处呢?现实是没有人起而救难。显示了诗人对于时局,在幻想的希望与冷峻的失望之间迷茫。
最后一联“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说自己虽然衰老,但大乱年代,还会有用于世,天下还需要我。华发,花白头发,言衰老。沧海横流,指海水泛滥,喻时局动荡。晋殷仲堪《答桓玄论四皓书》:“天下,大器也,苟乱亡见惧,则沧海横流。”要,需要。这句是说,大乱年代,时代还需要我。设想重整河山,自己还会出力。晋范宁《谷梁传序》:“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不是元好问太过天真呢?不是。在绝望中,人总是需要信念的支撑,哪怕这信念是梦幻般的。从组诗的第五首看,他心里明白,这希望是虚无缥缈的。
这组悲凉之作,历代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其沉雄笔力,不知征服了多少人。清人沈德潜说:“遗山诗佳者极多,大要笔力苍劲,声情激越。至故国故都之作,尤沉郁苍凉,令读者声泪俱下。如‘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之类,于极工炼之中,别有肝肠迸裂之痛。此作者所独绝也。”(《宋金三家诗选·遗山诗选》卷首批)赵翼则说:“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车驾遁入归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瓯北诗话》)这类诗,发挥杜诗精神,继承杜诗传统,为元好问赢得了崇高的诗史地位。
如果说这组作品有什么不足,那就是用典过多,造成理解的障碍。诗句费解,便是缺陷。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沈德潜评元好问金亡之际诗:“愁惨之音,皆泪痕血点凝结而成。”(《宋金三家诗选·遗山诗选例言》)这样的作品,岂止是血与泪?仅仅有血与泪,不足以成就经典。除了血与泪,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的,是以卓越的见识做深刻的历史反思。癸巳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元好问跟其他金廷旧臣一起“出京”,被驱赶到青城。这短短几里路,却是他们命运悬崖式的跌落。在此历史时刻,元好问写的诗如果只有血与泪,那也太浅薄了。汴京一破,尽管流亡朝廷还在,金朝已名存实亡了。国灭之际,一个有思想有见识的人,不仅仅只感受亡国之痛,更会反思亡国之因、亡国之渐。这首诗正是如此。
癸巳,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这年四月,金汴京守将、西面元帅崔立向蒙古军献城投降。四月二十九日,蒙古军将金朝旧官羁押出京,暂居南青城,几日后(五月三日)北渡河羁管聊城。元好问在其中。出京时,元好问写了这首诗,记录了这个惨痛而哀伤的时刻。
祸福往往起于毫忽。当征兆初萌时,人们多不在意。待祸端已成,悔之已晚。“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是养患之初。这两句可以看作是跨句倒装,本为“当时初捐宴赐金,塞外南牧已骎骎”。当时,何时?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距金太祖立国的收国元年(1115),仅仅41 年,金立国刚几十年,就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失败求和,以“宴赐”名义,向北方边境各部输送大批钱物,《金史》多有“宴赐北部”“宴赐诸部”的记载,“初捐”的时间在海陵王正隆元年。章宗明昌二年(1191)起,五年一宴赐。当时正当所谓“大定明昌五十年”的“盛世”。以“宴赐金”的妥协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定,那绝对是养虎遗患。而那时的蒙古,已经“南牧已骎骎”,野心勃勃。此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整体上无疑是金强蒙弱。但金之朝野,对“南牧骎骎”的蒙古缺乏足够的警觉。南牧,南下牧马,实指游牧族南侵。贾谊《过秦论》:“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骎骎,马疾速奔驰貌。陆机《挽歌》之一:“翼翼飞轻轩,骎骎策素骐。”这里以马奔驰之疾形容蒙古扩张之快与野心之盛。
第二联:“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灞上是地名,即霸上,在西安市东、灞水西高原上,故名。《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文帝到霸上、棘门劳军,各营将官均自往迎送,文帝直驰而入,唯细柳周亚夫营地,戒备森严。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 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此借指金军涣散松懈状态。神州陆沉,指中原沦陷。神州指中原地区,这里指金之故土。“陆沉”言陆地沉陷水中,比喻国土沦陷。《晋书·桓温传》:桓温“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宴赐金”的失误,“真儿戏”的涣散,对“南牧骎骎”的失防,终于导致“神州陆沉”的后果。“只知”“谁谓”,是强调未能见微知著的失策,而非对结局的惊奇与意外。诗的前四句二十八字,以高度的形象概括,勾勒了一部亡国简史。如此笔力,堪称非凡。事已至此,悲哉痛哉!
诗的后四句写亡国之痛。但此时的深痛大悲,哪里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第三联“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因为其情无可言说,其痛无法描述,只能引用典故,以设问的方式来述说:假如丁令威看到此时的汴京城,他“应有语”,但他会说什么呢?华表是树立在广场或路口处的标柱,上有横木。陶潜《搜神后记》载:“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铜盘人去”典出《汉晋春秋》,指汉武帝在京城长安造金铜仙人,上有承露盘。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魏明帝青龙元年(应为青龙五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其诗有句:“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汴京城破,金名存而实亡。元好问和金铜仙人一样,国亡且被迫离开国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两句用典,表达难以言说的哀伤。现实绝不仅仅是“城郭如故人民非”的变迁,那是天翻地覆,天崩地坼,“何不学仙冢累累”足以表达此时的心情吗?远远不足。那又如何表达呢?无以言表。“应有语”但无法想象他会有何语。故国倾覆,自己又被迫离开国都,连无心的金铜仙人还“忆君清泪如铅水”,何况有情的人,此时此刻,何以为怀(何心)呢?岂止是“清泪如铅水”?其痛其悲,难以描述。“泪痕血点”,不足以言其深痛大悲。除了痛与悲,诗人的内心还有什么?还有无奈、失落,和彻底的幻灭。
亡国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现实,可又不能不接受。“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天意从来高难问,也不会因人的不能接受而改變;而那两度见证亡国的青城,依然如故,人间的悲剧还会上演,青城还会继续见证。青城当指南青城,原为宋代斋宫名,在南熏门外,为祭天斋宫。元好问自注:“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宋、金两次城破国灭,青城都曾见证。刘祁《归潜志》载:“大梁城南五里号青城,乃金国初粘罕驻军受宋二帝降处,当时后妃、皇族皆诣焉,因尽俘而北。”《金史·哀宗本纪》:“天兴二年四月癸巳,崔立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及诸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诗题“出京”,结句却是“留着青城阅古今”,多么奇特的结尾!它展示的是诗人之眼“通古今而观之”(王维语)的大境界。
诗的题目是“出京”,“癸巳四月二十九日”是个特殊日子,表明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离京,而是国灭人去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此国难之际,追思导致今日“出京”的历史成因,是出京所思。如此“出京”,何以为怀!是出京所感。所思,成一部亡国简史;所感,写一腔亡国之痛。读这首诗,我们感受的不仅仅是千钧笔力与高超技法,更有史学家的卓识、哲学家的深邃、诗家的真情。这些都凝聚于八句五十六字之中,成就了中国诗史的不朽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