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年谱》本不该是我的第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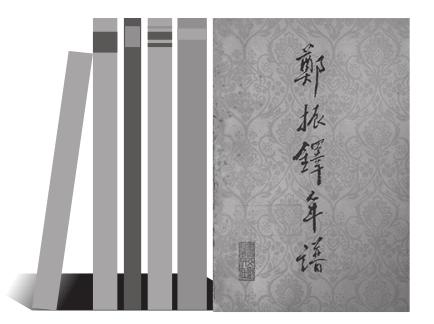
我这辈子出的第一本书,是1988年書目文献出版社(对这个社名我很留恋,也非常喜欢,可惜这个名后来改过好几次,先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后又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我觉得还是“书目文献”最雅)出版的《郑振铎年谱》。但是,我本来更早应该出版的第一本书并不是这本年谱,而是《郑振铎研究资料》。我必须从这本未刊书稿开始说起。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有点遗憾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作为当时全国最早的研究生在复旦大学就读。那时我已经开始研究郑振铎先生。那年头,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很热门的。但当时很多“现代文学”专家,几乎都还没有认识到郑振铎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举个例子吧,当时有很多专家开会研究,要组织撰写出版一套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丛书,胃口很大,反复推敲搞了个几十位作家的名单(包括其实没什么可写,而且到最后也写不出传记来的作家),约了很多人来写,最初就根本没有想到郑先生其人。(后来这套丛书中有了我写的一本《郑振铎传》,但那是我写好以后努力说服出版社收入的,并非专家原计划里就有。)不过,大概因为郑先生生前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创始所长,所以当时社科院文研所的一个非常宏大的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里面,倒是列入了《郑振铎研究资料》一种的。我当时只是个学生,虽已发表了一些有关郑振铎研究的文章,但谁也不会想到找我。这本书,是他们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理论读物编辑室主任余仁凯编的。有一天,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余主任叫住我说,我看到你发表了好几篇研究郑振铎的文章,社科院交给我编郑先生资料的任务,但我对郑先生没有研究,而且我工作也太忙,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个任务的话,我就向他们提出来转给你好吗?我当然很高兴地答应了。
这个国家级社科重大项目国家是投了不少钱的,可是你知道吗,我承担这个重大项目下的一个子项目,那到我手里是多少经费呢?现在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100元。我当时就领了这100元开始工作了。(后来,有关同志觉得不好意思,又要我打报告再申请了200元。所以,我第一次得到学术研究基金是很早的,比很多同龄人早得多了;但最早得到的基金只有100元,一共300元钱。)好在,那时我们国家还比较穷,物价也比较低,人的欲望也不高。
我非常努力地按时按要求完成了《郑振铎研究资料》书稿。如果顺利的话,完全可以在毕业前就出版。大约有50来万字,那是他们限制的字数,本来我觉得应该搞得再多一点,因为郑振铎的资料非常丰富。那时复印机还远没有普及,照相机也是稀罕物,书稿所有的内容都是手抄手写的,包括我的父亲也辛苦地帮我抄写了不少(现在想起来,我还非常感谢先父,也觉得很对不起他的)。我交稿后,社科院文研所的领导就转交给了这套丛书的一个编委“审读”。可是非常纳闷的是,她迟迟不作处理,理由是她有其他的工作,太忙。本来,所谓的“审读”也就是看看符不符合体例和要求,其中大部分内容(如作家生平自述、创作自述、文学主张、研究者对作家的评论等)其实根本就不用多看。但人家就是拖着不看。我除了写信询问外,好几次出差到京,都到她家里去问;后来我又上京当了博士生,更去她家好多次(当然,我也从没想到应该提一点什么礼物送去)。后来,连她的忠厚的爱人(也在社科院文研所工作)在一旁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曾当着我的面对她说,你就快点帮小陈看看吧。但她就是一直拖着。我向文研所领导也反映了,他们说没办法,也不好换人。过了好久好久,她总算“审读”完了,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书稿才交到这个大项目的负责人马良春那里。老马倒是非常爽快的,立刻就作了批示通过,并将书稿给了福建某出版社,因为郑振铎就是福建人嘛。
不幸的是,由于被长期拖延耽搁,这部书稿错过了出版的机会。此时的出版界已很不景气。出版社大概认为,既然是国家重大项目,有很多经费的,可是给他们的出版补贴却太少了,于是就不愿出。该社的编辑与我也认识,他就坦白地跟我讲,书稿是编得好的,但如果你另外搞不到经费的话,出版就“想也不要想了”。又过了多时,我也就绝望了,把书稿也要了回来。此前,我又曾向社科院文研所提出,在那大项目下再编选一本《彭家煌研究资料》(他们原计划中没有),得到他们批准立项,并已着手进行,也因为我怕做了白做,没有继续做到底。但我想,自己对《郑振铎研究资料》下了这么多功夫,包括老父亲也为我费了很多力,难道就这样白干了吗?因为书稿里面,本来就按要求有我撰写的《郑振铎生平活动大事记》《郑振铎著译年表》等,但因为限于丛书体例与字数的规定,比较简单,所以我就想不妨利用这些资料,另行撰著(我拒绝用“编”这个字)一本《郑振铎年谱》吧。就这样,本来《郑振铎研究资料》应该是我的第一本书,可惜却石沉大海。
撰著《郑振铎年谱》完全是我的“自选科研项目”,没有“立项”,没有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但我乐此不疲。就在我反复修订当中,一次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文献》杂志编辑部去玩。我是他们的作者,当时的主编刘宣先生很看得起我,常对我说他在编杂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男(指我)一女两个十分努力的青年人。我向他谈起了我的《郑振铎研究资料》,和正在撰写中的《郑振铎年谱》。不料他顿时双目发光,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为郑先生写年谱好啊!郑先生对我们北图也是有恩的,相信你这么多年认真研究,质量一定会好。你完成后拿来,我推荐到我们社出版!”就这样,我这辈子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书目文献出版社的《郑振铎年谱》了。我永远感谢已故的刘宣老先生。
我的《郑振铎年谱》书稿交到出版社去时,刘老已经退休了。该书的责任编辑是贺敬美。老贺人非常朴实,我在京读书时常到他办公室和他家里聊天。他的哥哥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延安革命诗人贺敬之,时任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但是老贺在我面前从不提他哥。我提起了,他还跟我说,我哥是我哥,我是我,我不沾哥哥的光。当时,书目文献出版社刚创办不久,编辑的经验也不足,书的装帧印刷有时不那么好。例如我的这本书,印好后他们才发现在封面、书脊和扉页上都没印我的名字。他们肯定觉得很不好意思,于是就把“陈福康编著”五个铅字沾了油墨,像盖图章一样,不辞辛劳地一本本手工打印在扉页上。尽管如此,我仍然非常喜欢这本我请郑先生老友郭绍虞、李一氓先生题签题词的,封面朴素无华,而且没有印我名字的书,一本厚厚700页,却仅售4.60元的书。一本赶在郑振铎诞生90周年、牺牲30周年时出版的书。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的故事。还有一些余闻,亦可一说。
此书出版后,很快就卖完了。而我仍继续不停的研究郑振铎,又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也发现了有些地方原先记述不准确,所以我不断地做着修订。我曾向出版社试探提出再出修订本,但当时他们确有困难,没有积极回应。一过又是十多年,原社领导和编辑也都退休了,这时,我们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版形势也好转了。我的修订工作有幸列入了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科研项目,这样,按学校规定我就可以把修订书稿交给本校出版社出版了。可是没想到的是,山西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张继红兄听说我在修订这部年谱,立即主动表示希望在他们社出版。又没想到的是,在我即将交稿之际,北图出版社(即原书目文献出版社)的当时我还不认识的殷梦霞编辑(现已是该社总编辑)来电话谈别的事,得知我这一书稿已修订完成,当场表示还是应在她们那里再版。我对北图出版社一直感恩在心,但我已与山西古籍出版社谈好了,怎么办呢?殷梦霞说没关系,她们郭社长与山西古籍出版社张总是老朋友,打个电话就成。我想起听张总说过,山西古籍社是个小出版社,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而我这本书又赚不到什么钱,因此我对殷梦霞说,只要张总同意,我就没意见。过了没几天,殷梦霞来电话说,他们社长亲自给张总打电话了,但张总不愿“割爱”。修订本于2008年郑先生诞生110周年、牺牲50周年时出版。书从一册变成了两册。
但我仍是继续不停地研究郑振铎,又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又发现了有些地方原先记述不准确,所以我仍旧不断地做着修订。在学界友人的年谱专著修订工作获得国家基金立项的启示和鼓励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领导和科研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便也尝试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竟幸运地也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在我的修订增补工作正式启动以后,曾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多家著名出版单位的编辑和领导主动向我索要书稿,表示可以安排出版。对此,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我深深感受到,近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对社科研究和出版的投入之不断增大,使社科研究和出版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我又深深感受到人们对郑先生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的。我的第二次大规模修订的《郑振铎年谱》,最后还是给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那是当过我多本书的责任编辑的李振荣兄主动向我要去的。于2017年出版,书又变成了厚厚的三册,成为第二年纪念郑先生诞生120周年、犧牲60周年的献礼。
我的这部书,先后荣幸地获得过第三届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第十四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第八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作者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郑振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