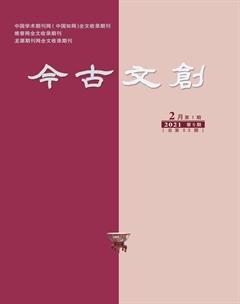浅析琼籍华人文学的原乡书写
【摘要】 琼籍华人文学的“原乡”书写,究其本质就是“离散”书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书写。“原乡”书写就成了旅居国外的华人一种潜在的精神追求,祖国、故乡、文化、童年、母亲、爱人等是“原乡”依附的几个重要物象。
【关键词】 琼籍华人;文学;原乡;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5-0028-03
基金项目:2020年度海口经济学院校级科学研究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琼籍华人文学研究》(编号:HJKY(ZD)20-08)。
“原乡”是指旅居国外的华人对中国故土的称谓,通俗上指的就是故乡。对于个人而言,家乡是目前居住的地方,故乡是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原乡是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所谓“原乡”即“原色本乡”,意味着传承着祖先的历史记忆和原味生态环境。文学上的“原乡”书写,究其本质就是“离散”书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书写。“原乡”书写就成了旅居国外的华人一种潜在的精神追求,祖国、故乡、风俗、文化、童年、母亲、爱人等都是“原乡”依附的几个重要物象。
一、琼籍华人文学中的中国符号(意象)书写
琼籍华人虽然已经离开故土,但他们血液里仍然流淌着中国的文化传统,逢年过节及重大节庆活动他们仍然要舞龙舞狮、敲锣打鼓、贴对联、燃放鞭炮、吃饺子、走亲访友、包红包等习惯。这些在居住国国民看来怪异的行为举止,就是华人难忘的乡愁具体表现,也是本地原住民永远也不能理解的,这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环境熏染结果的文化的差异性,琼籍华人以各种行为阐释着自己的汉文化身份。
华人自古以龙的传人为傲,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与象征,龙这种神话中的神物,是多种动物器官的结合物,这也象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经过千年融合而成的一个生命不息的稳固的伟大民族。从龙的形体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多民族相容后的包容痕迹,更应该理解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拼搏精神,龙成为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也成了海外琼籍华人对原乡最朴素的追忆。
温瑞安的散文一再以中国符号显示历史记忆的无所不在,他在其散文《龙哭千里》里以“龙”为题,第十一段写道:“记得那个笑起来总露出兔子牙的小女孩儿吗?他曾笑着说:‘你扬眉的时候,就像……就像……一条昂然抬头的龙’。”虽然这一段话只是假设性叙述,然而里面所提到的“折翅的龙”“困龙”“郁结万载的龙”“郁龙”都不是快乐的龙,都是困境中苦苦挣扎的龙。这里的“龙”只是个喻体,他所暗喻的是多元社会中不受重视甚至受到压迫的华人与中华文化。
在《八阵图》中,作者强化了《龙哭千里》的不满、无奈与恐惧:我是龙啊龙是我我是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周遭还是无天无地无边无际无岸无涯无远无近无生命的黑暗。”压抑、苦闷、彷徨、恐惧、无助溢于言表,29个“龙”字的连用喊出了“压在垃圾箱底下的龙”的悲哀与愤恨。“周遭的黑暗”亦即是当时的大环境。
华人南来,漂泊是他们的命运,被压迫是其宿命。属于南来华人第二代的子弟,作者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深深感受到民族文化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国度里被人压迫,被人歧视,内心不满之情油然而生。知识分子由于环境所迫,自我流放。这样的一群人,就是一群被边缘化的特殊群体,他们不但遭受原住民的排挤,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没有话语权,文化上被流放。“与拒绝被同化”同时产生的是文化承担的意识。这个议题出现在点题的第六段。这段写哥哥和一群朋友从外国旅行回来时带了很多书,海关人员不解地看着这群年轻人。后来他们为此而在车上大笑。其实大笑之后又是怎样的心情呢?段落后半段如此叙述:“你们都是驼子,高大的驼子,蹲着都比别人高大的驼子;你是守着绿洲的沙苇,为母体抓取每一份暖土吸取每一点养分的根须;你是拜星者,你是一具不完整的血婴”。这个句子写出了作者对本族文化被压迫和被轻视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承担意识,是旅居国外的华人共同的心酸体验。
长城蜿蜒万余里,是中国神物“龙”的实物呈现。长城是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大明王朝千年来阻挡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一道屏障,是保卫中原农耕民族的铁血卫士,它见证了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象体现,琼籍华人流落海外,以长城精神手足相扶、互帮互助,聚集而成的“唐人街”“中国城”就是最好的证据。
潘碧华的《我会在长城上想起你》这篇文章,是作者到中国旅游的经历,可它不属于介绍式的游记,抒情、发思古之幽情才是文章的重点。文章开端呈现了空旷辽远的远景,以及作者抒发激动振奋的心绪,而这份敬仰的心情是長期以来对中国的想象、仰慕,进而关怀、呵护中华文化。这份想象,来自从小到大读过中文的经历。潘碧华听老师讲,“从远古的尧舜到近代的抗日”英雄人物事迹,以及惊天动地的战争场面。老师朗诵唐诗、吟咏宋词的悲伤情调,已深深感染了作者。古诗里的战士出关,家人妻儿的断肠遥望,就像老师14岁离开家乡(中国)来到马来半岛,“悠悠地度过了四十年”,和亲人失去联络的哀痛和遗憾。因此,作者以长城意象结合了老师的哀伤或历史伤痕,是“永远缝补不好的遗憾,日日夜夜扯痛你(老师)的心灵……
长城本来就象征、显现中国古人的伤,从建筑长城到修复长城,工程浩大而艰巨,人民死伤人数是现实情景的创伤;文章里老师经历的是远离故土的伤,只身移民南洋而最终无法回中国。相对于第一代华人移民的爱中国情结,潘碧华为第三代华人,已是土生土长。以此观察,他的中国想象是结合本地经验的,所以这份(充满想象的)倾慕中国文化的心绪是必然的,也是“短暂”的。“必然”是因为长期受到华文教育、中国文化的熏陶,“短暂”是因为他的现实生活情景是在马来西亚。
《我会在长城上想起你》这篇文章显现了作者对于中国的抒情印象,她是如此描写长城:长城,一条历经沧桑的飞龙……以千年气势凌空而来,这曾经命丧千万人的长城,曾经阻挡外族侵犯的长城,浩浩荡荡地向前延伸……连绵无尽衔接而去的是悠久灿烂的历史,源源而来翻滚席卷的是血泪交加的声音……就文字语言而看,不乏亮丽的中国图像,长城与“飞龙”象征千年来的历史文化,对照的句式、动态性的用语(凌空、延伸、连绵无尽、翻滚席卷等)显现了作者看到长城的浩瀚与翻腾的情感,亦是激动而久久不息的。
以温瑞安和潘碧华为代表的华人,用他们手中的笔书写着对文化中国的感伤记忆,这就是乡愁的最真表达。
二、琼籍华人文学中的故乡书写
作为琼籍移民的华人对故土的思念,主要表现在家园情结上,用文字回忆着对故乡的眷恋。
王哥空是个重乡情的人。20世纪新加坡人都还记得,王哥空当外勤记者期间,曾为琼海人莫履瑞在海南街开的“瑞记鸡饭店”写过一篇报道,盛赞海南鸡饭的味道好极了,此文在《新都日报》刊登出来以后,被《海峡时报》(英文报)转载,莫履瑞老板好不高兴,亲自把该文剪贴在饭店门口,影响所及,不仅新加坡人,而且马来西亚、印尼、日本以致欧美游客,对“瑞记鸡饭店”都不胜神往,趋之若鹜。自此莫履瑞的财源滚滚而来,生意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以至成为星洲屈指可数的企业家。
琼籍华人女作家李忆莙,祖籍海南省文昌市,现任马华作协副会长,曾任《马华文学》主编。作为华人的后代,李忆莙没有先辈们漂洋过海、为生活打拼的艰难困苦,她对祖辈所生活过的故土天生就有一种莫名的欢喜。海南岛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祭祀庆典、风俗民情在她的笔下涓涓流淌,最终汇聚成一篇篇精美爱读的文化散文,不舍的是作者的家园情结。文昌乡下的祠堂、老树、小吃、祖屋、牌坊、老井历历在目,岁月悠悠,祖辈下南洋的艰辛成为历史,但渗入血脉的文化记忆却永远成为她的标志。
在其自传性的文章中写父亲早年在老家文昌乡下结了婚,生了三个女儿,后来为了生计,结伴乘船来到马来西亚半岛,后来再也没有回去……
父亲后来在槟城新娶了母亲,母亲第一胎就生下了哥哥,而那个在文昌老家的父亲前妻,“我”的大妈,居然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自己也是一个有儿子的母亲,自己的儿子在槟城,心里想着嘴巴里成天念叨那个自己从未谋面的“儿子”。
上一辈的人,没有抱怨,有的只是理解与宽容。那个年代的女人都是认命的。父亲的前妻,就是“我”的大妈,名字叫陈孟莲,是父亲未出国前在文昌老家娶的妻子;而“我”的母親是父亲后来在马来亚新娶的妻子。父亲的背井离乡不回头,大妈的翘首企盼、包容认命,充满着辛酸与无望。“我们”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相携相助,李氏宗亲的血脉相系,让家族的血脉亲情延续流淌。这些都铭刻在了作者的心里,让她的回乡探亲之路混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与伤感。在祖屋里,看到父亲亲手栽种的椰子树,坐上父亲坐过的雕花酸枝椅,睡在父亲的睡过的低矮砖石房里,她做到了回乡探亲的的夙愿。
李忆莙的作品中详尽阐释了中国人在亲情、习俗、宗教、庆典、饮食、建筑等方面的文化。琼籍海外华人与故园的深厚情感基于传统的中国文化。
三、琼籍华人文学中的诗词书写
从琼籍华人作家创作方面看,一系列具有原乡意向的书写符号常常出现在其作品中,包括中国的传统诗词歌赋、风景名胜、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等,这些带有显著中国元素的书写标志着对汉文化的望乡。
温瑞安的散文一再以中国符号显示历史记忆的无所不在,他的散文《龙哭千里》全文长达近万言,共分十七段,内容丰富,主旨在揭示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社会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的处境以及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年,在面对种种不公平对待的心理反应,以及因而孕育形成的民族文化承担意识。由于这样的一个主题,本文的中国性或中国属性特别浓厚。作者在文中明引和暗引了许多诗词和具有典故的词语,目的不外乎表达他对中华文化的钦慕,热爱。例如第一段的“抬首,仍是八千里路云”源自岳飞的《满江红》;“举杯相邀”乃是李白的《月下独钓》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缩减;“杨柳岸边”乃是柳永名篇《雨霖铃》中“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浓缩;“悲欢离合的月,阴晴圆缺过的月”是蒋捷诗句“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和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句子“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叠合使用。
何乃建先生的《稻花香里说丰年》这篇文章是以辛弃疾的《西江月 · 夜行黄沙道中》的第二句作为题目,点出农人与自然,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操作之间的互动,并融抒情、言志、描述于一炉对水稻做出深情的礼赞。诗人以饱满的想象力和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倾墨而出。对于自然环境的描写,作者多以比喻、对比和比拟的积极修辞手法绘之;对于内心的感慨,则一问一答、反问、引用、排比等手法言之。在文体上,本文虽是散文,却渗入诗歌的形式,形成互文的特点。
琼籍海外华人无论身处何方,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方法传承着自身的汉文化,追忆着自己祖辈走过的过往,这也是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恩。说到底,这就是对原乡的眷恋与不舍,也是其书写乡愁的源泉。
参考文献:
[1]王春煜、庞业明.星洲三人行[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
[2]马峰.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莙论[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7(12).
[3]扈彩霞、翟莉.美国华裔文学视域下华人的文化心理嬗变及其历史成因[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4(10).
[4]刘征.华人到处有花踪[D].陕西师范大学,2015(5).
作者简介:
关德福,男,甘肃靖远人,本科,副教授,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