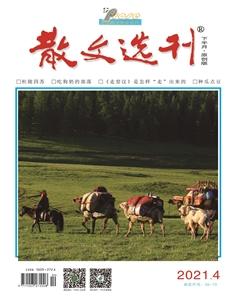邵洵美:柔美迷人的春三月
符利群

光绪八年(1882),《中俄伊犁条约》签订者之一、浙江余姚籍外交官邵友濂带着一大家子迁往上海定居。
二十四年后,邵洵美出生于上海斜桥邵府,与末代皇帝宣统同岁。余姚于他只是长大后每年一次扫墓祭祖的远乡。
邵家始祖,北宋哲学家、易学家邵康节本名邵雍,生前多次授官不赴,所以死后谥号“康节”。北宋以降至近现代的幼学启蒙读本上,多半印有他的一首诗作,“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简洁直白,朗朗上口,轻而易举地表达了一种文理皆通的基本学问。
八百多年后,邵雍的一支后裔定居余姚。邵家在余姚这块江南名邑建筑房屋,购置田地,最多时达到一万多亩。城郊那些肥美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都是邵家佃户。后来邵家另辟两千多亩土地,在城外东北角建庄屋一座,捐立邵氏义庄,庄屋大门上有光绪御书匾额“旧德先畴”,这是令邵家十分荣耀的一桩事。邵家后来又创办邵氏小学,其族裔子弟免费就学。1930 年,邵洵美将学校改名康节小学,以之纪念始祖邵雍。
邵氏义庄的田地收入主要用于办学开支,接济生活困难的邵氏族人。虽是私有财产,邵友濂还是订下了严格的义庄管理条款:不得由邵姓人氏管理义庄……经营得法,生息有度,这使得邵家的产业越来越大,据说最盛时余姚镇上半条街都是姓邵的。
光绪五年(1879),邵友濂随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赴俄国重订《伊犁条约》。此前一年他随吏部侍郎崇厚赴俄谈判,崇厚在庞大的俄国身躯力压下将主权一让再让。邵友濂急报朝廷,朝廷震怒,后改派曾纪泽,邵仍为随员。在漫长艰难的谈判过程中,曾纪泽据理力争,邵友濂则在异国的每一个夜晚埋首撰拟谈判文牍,不厌其烦地字斟句酌每一句行文措辞,既不能强硬,更不能卑微,每一句话等同于一寸国土。经过长达半年艰辛的谈判交涉,终于收回伊犁地区,但仍有大片国土划归俄国,且赔款900 万两银子。挨了人家一巴掌还得给人家赔笑脸,衰败的晚清甚至连一件遮羞的青布衫也无法给予它的臣子们。
邵友濂回国后改任苏淞太道兼江海关道,这相当于苏州上海两市市长。这一年,41 岁的邵友濂将一大家子从余姚乡下接到上海定居,开始了斜桥邵家的上流社会生活。依赖于余姚老家雄厚的资产,加上邵友濂为官多年的资本,邵家正如花园里枝繁叶茂的树木,悄无声息地滋长财富。
盛宣怀创办的实业多在上海,与地方长官邵友濂是近邻。儿女因缘遂成为他们在花香四溢、绿树交荫的庭院里喝茶时津津乐道的内容之一。他们很快说定了亲事,盛宣怀的四女儿盛稚惠嫁给邵友濂的小儿子邵恒。盛宣怀有心栽培女婿,给了他轮船招商局督办的美差,却没料到,自己挑了个扶不起的阿斗做女婿。邵恒除了生下儿女,毕生精力用于吃喝嫖赌。盛宣怀愤怒地革掉女婿的职。
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着“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衔着银调匙出生于邵家占地七亩的花园洋房。那时他的名字叫邵云龙。花木扶疏、曲径通幽的邵家花园外,还有许多银楼、影院、当铺等产业。在镇江有两家当铺,其中那个叫“忠裕当”的当铺,有九十九间房,木柱皆用楠木,据称值十五万银洋之多。此外,邵家的产业多得邵云龙从没弄清过。
有一年,上海杨庆和银楼的经理来邵家花园,向邵云龙汇报“大批存户前来挤兑”,请求如何处理。这时邵洵美才知道,自己是这家大银楼的大股东。他硬着头皮去处理这桩他没兴趣也不内行的事,然后发现,带头挤兑的是自己的姐姐。姐弟俩均不知道银楼是自家的。银楼由此倒闭,所幸归还储户存款、支付职员遣散费后还有八万多银洋。他们的父亲笑嘻嘻地拿走四万块银洋,又兴冲冲地扎进麻将馆、大烟铺、跳舞场、跑马厅,以及所有能找到乐子的销金窟。
在父母教养无方的富贵门庭里出生长大,邵云龙竟然没有沾染上赌毒之气。这似乎源于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诗墨气质。多年以前,当一周岁的他被母亲抱着抓周时,细嫩的手指抓住的是桌子角落的秃头狼毫笔,这令他的老祖母为之黯然,认为孙子将来只能是拿笔杆子的清苦命。长大后的邵云龙常绕开麻将声响喧嚣的客厅,来到祖父的书房,探幽他所感兴趣的事物。墨香幽幽的书房里,窗外的竹影在书桌上印出浅淡而摇曳的细碎影子,邵云龙学着他从未见过的祖父的样子提筆临帖,研读诗文,从书柜里好奇翻阅祖父与李鸿章、盛宣怀、曾纪泽等人的书信……书卷诗墨像窗外的竹影潜入书房一样,缓慢而深刻地烙进他的骨子。
会跳舞、赛马、打高尔夫球的邵恒对儿子最大的教益,是将他送进圣约翰中学,当然,他原本的宗旨是让儿子学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样更容易混迹于上流社会。圣约翰良好的英文环境,将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邵云龙熏陶成了中西学通融、才情满溢的优秀青年。在上世纪20 年代富家子弟留洋风潮的影响下,圣约翰中学毕业后,邵洵美选择了欧游道路。
这之前,邵云龙有了生命中第一次爱恋。他爱上了自己的表姐,也就是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少年恋情令他将自己的名字由云龙改成“洵美”。1925 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就读伊曼纽学院经济系。课余他醉心于英国文学,读高思、罗捷梯、莎士比亚、雪莱,欣赏街头的雕塑,教堂的穹顶的彩绘,悠长的笛声,逼真的绘画艺术……欧洲文艺愈加催化了邵洵美身上的艺术气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大批留学欧洲的文艺青年,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蒋碧微、刘纪文……两年后邵洵美回国,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盛大,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证婚。邵盛联姻成为十里洋场上海滩轰动一时的话题。
祖上护荫,家财庞大,满腹才华,织交广泛,加上浓厚的文艺情怀,使邵洵美有足够的财力与精力投入到读书、写诗、编杂志、办书店、出版书籍等这些毫无经济收益的事情上。而在邵洵美看来,这才是他一生为之付诸心血的事业,“我不能像其他富家子弟,只知将莫名其妙由祖宗传下来的钱一个个用光,而不想去运用天赐给自己用以求生的手和脚。”他这样说。
最早的时候,邵洵美认为凭借就读过伊曼纽学院经济系的专业知识,自身累积的文学素养以及对文学的热衷,办书店搞出版并非困难的事。他像他的父亲热衷于赌博那样,以赌徒般的狂热投入到出版业。从1928 年到1950 年的22 年中,邵洵美办了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创办《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等十多种刊物。他像写抒情诗那样,随心所欲地开办一家又一家出版社,出刊一本又一本杂志,为无数知名文人和不知名的业余文艺爱好者提供发表作品的平台,支付一笔笔润笔费,根本没有考虑过投入与产出比。投入越来越庞大,产出越来越低迷,到后来入不敷出,只得又像他父亲拿走母亲的陪嫁那样,以妻子的陪嫁作为资本投入到出版业,结果毫不意外地打了水漂。
这个时期,邵洵美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夏衍等等一大批人出了书。在华洋杂陈、多元并存的上海滩,胡适、叶公超、潘光旦、林语堂、沈从文,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鲁少飞,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文艺派别各异的朋友,均成为邵家花园的座上宾。邵家花园的厅堂整日酒樽交错,高朋满座,各种最新鲜、最犀利、最富權威性的文艺话题,常常自邵家花园飘然飞逸在上海滩的上空。
邵洵美与鲁迅的交恶,导致了他长久以来在中国主流文学史上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一个抨击另一个“文人无行”,“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生意,人人想做,所以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一贯疾恶如仇的鲁迅,哪容得邵洵美这般讽诮,当即回击对方“捐班”,“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要登文坛……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
同为绍兴府同郡的浙江文人,邵洵美与鲁迅原本可以成为亦师亦友的同道知己,但身处异常复杂而微妙的历史大背景,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了彼此不屑。
邵洵美有足够的资本与精力将文学玩得团团转,写诗、著文、办杂志、开书店、印刷、出版以至发行,他似乎什么都懂,什么都沾边。他不必像诸多热爱文学而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那样为稻粱谋,更不必像白薇、萧红、萧军那样,捧着呕心沥血的书稿,跑到热心提携文学青年的鲁迅先生家中,向他恭恭敬敬地请教文学疑惑,请他指点人生迷津。优渥富足的上层生活,留学英伦的人文背景,文风轻柔、唯美、艳丽,“(如)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笔触极少伸向底层平民生活,挥金如土、呼朋唤友的少爷作风,施惠众多,而难免树大招风,论诗不及徐志摩,论文不及沈从文,论翻译不及施蛰存……够了,这一切,足够让笔下“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鲁迅深恶痛绝。而将文学看得十分纯粹唯美的邵洵美,对不断打破文学美感而构写苦难、重建文学新秩序的鲁迅,同样有某种傲慢与偏见。
许多年后,鲁迅以他影响中国文学、思想以及政治领域的力量,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难以超越的标杆人物,他早期对邵洵美的评价,成为后者一生无法卸去的心灵重荷与阴影。特殊年代的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令主流文学史不给予邵洵美以应得的话语权,当是意料中事。
事实上,正如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后来所说,鲁迅先生去世于抗战之前,他对邵洵美抗战时期的爱国行为无从评价。
1938 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邵洵美的美国情人项美丽将其翻译成英文,邵洵美迅速将英文版在《自由谭》发表并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同时又自掏腰包出版500 本《论持久战》单行本,开着汽车,别着小手枪,带着法国保镖,在寒气逼人的冬夜,穿过上海滩闪烁着诡异光泽的大街,将书投进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他嗅到了危险迷人而令人兴奋的革命气息……
二十年后,这个将脑袋别在裤腰上发送革命书籍的诗人,以“反革命罪”被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年后出狱。曾经坐拥大观园般的花园洋房,此时只有一间狭窄阴暗的小屋。为谋生计,盛佩玉只得带着小儿子投靠南京的女儿邵绡红,邵洵美则住在离婚的大儿子家。曾经一起共享邵家花园繁花如锦的少年夫妻,如今白苍苍视茫茫分居两地而遥望不得。曾经豪掷千金只为换得书生意气交游的诗文生涯,如今成了夫妻间通信时“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8 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这般辛酸的描摹……
终其一生,邵洵美只有盛佩玉这位从少年时结缡的妻子,且恩爱一生。如同弦乐里滑入一个意外音符,1935 年,美国女作家艾蜜莉·哈恩来到中国,结识了邵洵美,两人一见钟情。邵洵美为其取中国名“项美丽”。两人公开同居,项美丽自由出入邵家。邵家始终视项美丽为朋友,亲昵地称她为“蜜姬”。
这段“三人行”极富戏剧性的是,盛佩玉从来没有嫉妒过丈夫的美国情人,邵洵美不曾有过遗弃糟糠另娶新人的想法,项美丽也同样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念头。项美丽因《宋氏三姐妹》而饮誉海内外,后还将与邵洵美的情缘写成书,直截了当地称邵洵美为“我的中国丈夫”。邵家花园里,阳光透过绿荫洒下碎银般温柔的光光斑斑,一个男人与两个爱他的女人像一只茶壶配两只茶杯,无比融洽地度过了许多温婉美好的下午茶时分……这样的情事,放在当今,亦是令人惊叹。
这些已是三十多年后,顶着一头斑白头发,虚弱地靠在床上的邵洵美,剧烈咳嗽喘息后,在苍白的新月透过窗棂照进淡淡光泽的时候,记起的一些碎裂旧事。或许他还细细琢磨着,新月这名字多好啊。或许,他的灵魂随着新月飘向许多年没有去过的余姚老家,那里有大片大片的金黄色稻谷,在十月淡金色的阳光微风里,像黄浦江上的浪花一样缓缓地涌动,涌动……
1968年5月5日,留下了一首“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的诗后,邵洵美带着被肺源性心脏病折磨成一身枯槁的躯体,离开了人世。曾经在布置精雅的书房里摆设着“估价五千金以上的希腊女诗人沙弗像真迹,用20 万金镑在伦敦拍来的史文朋的手稿”的新月派唯美诗人,留下的是一堆窘迫的债务:欠医院四百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六百多元,还欠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