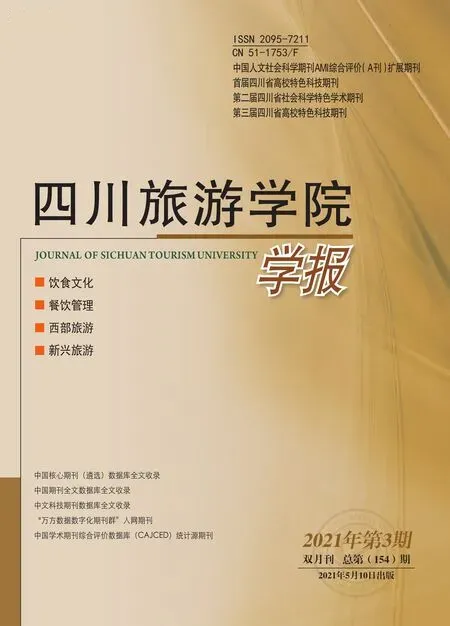乡村振兴战略下川东土碗菜的传承与创新※
李 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2)
川东土碗菜是流行于嘉陵江以北的达州、广安、巴中、南充等地的乡土菜,它以土碗为形式载体,兼容蒸、扣、炒、熘、浸、烩、炸等烹饪技艺,包括卤菜、蒸菜、炒菜、干锅、泡菜、小吃等菜品样式,具有乡土气息浓郁、江湖口味厚重的特点。川东土碗菜归属于川菜下河帮,自成体系且多元发展,一般以九大碗组合,约定俗成乡村田席,以传统烹饪技艺,体现百格百味的川菜内涵,以不拘一格的融合创新,满足了大众消费者的需求。从生态的角度,川东土碗菜的“土”,突出了乡村“文化根性”,体现了乡土风味的生态品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川东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下里巴人”的传统“食性”,既有食具、食材等考古发现,又有合菜、辛辣饮食习俗的遗存,饮食文化成为解密川东人文地理的一把钥匙。从经济的角度看,川东土碗菜并不囿于乡村市场,也赢得了城市大众消费市场,构建了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川东土碗菜的传承与创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川东土碗菜为抓手,加快川菜产业发展,促进产商文旅融合发展,对于推进川东地区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川东土碗菜的活态传承
作为四川饮食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川东土碗菜的活态传承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根基。土碗承载食性,反映了川东人的性格和气质;田席凝聚乡情,增添了乡村生活的仪式感;烹饪传承匠心,表达了城乡生活智慧与文化认同。
1.1 土碗承载食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食性特征,作为文化生态条件之一,给予文化的形成以重要影响。”[1]川东土碗菜代表了劳动人民的食性特征,反映了川东农民的群体性格特征。他们热情友善,古道热肠,请客吃饭,倾其所有;他们勤劳粗放,重吃不重穿,即便是上不得正席的食材,也能捯饬得像模像样;他们爽直泼辣,敢爱敢恨,充分展现了火锅里的江湖气、土碗里的大乾坤。川东农村人性的觉醒与回归,为川东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川东土碗菜的饮食文化传承,成为川东农村是否留得住乡愁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川东土碗菜链接着川东的农耕文化,每一种食材都有农耕文化的依托和支撑。有的地方通过大空间的体验方式去呈现,例如南充市西充县古楼镇高家沟村就是以“中国西部有机农业公园”的农业体验方式,表现土碗菜的生态性;有的地方通过小空间的展陈方式去体现,例如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长滩河村就以村史馆展陈九大碗的取材及形制。另一方面,川东土碗菜承载着川东的地方文化,包括空间形态的民居文化和时间形态的节庆文化。川东乡土民居形制如“撮箕口”,中间是院坝,是坝坝宴的场所,正门外有檐廊,檐廊下有晒架,悬挂玉米、海椒、腊肉等,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川东民俗节庆的饮食颇有讲究,正月十六“游百病”,户外登山带凉卤;八月十五“中秋节”,团团圆圆打糍粑;腊月初八“杀年猪”,邻里乡亲“吃庖汤”。总之,川东土碗菜的多样内容和形式,增添了民俗节庆活动的喜庆气氛,民俗节庆活动的鲜活体验,丰富了川东土碗菜的饮食文化内涵。
1.2 田席凝聚乡情
“田席是清代中叶开始的在四川农村流行的一种筵席,因常设在田间院坝而得名。最初的田席是秋收后农民为庆祝丰收宴请相邻亲友而举办的,后来有所发展,凡是婚娶丧葬、迎春祝寿甚至栽秧打谷等活动都要举办类似的酒席。”[2]川东的田席又称坝坝宴、九大碗、流水席,其本质上就是土碗菜的组合搭配,体现了朴素实惠、肥腴香美的特点。田席作为川东农村一种正式的筵席,不能简单地从经济消费上研判其档次,在乡村社会交往活动中,田席不仅仅满足了乡民口腹之欲,也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文化仪式。符号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转化器’,将世俗日常生活转变到一种全新的或者更高层次的关联之中,使得原本日常的事物由此得以改变。”[3]从邀请、排座、送客,到敬酒、请菜、谢厨,田席特有的仪式感起到了凝聚乡情的重要作用。
在川东农村社会生活中,田席就体现出“转化器”的功能。首先,田席对于传统秩序的强调,巩固了亲情。田席常用方桌条凳,有上席、陪席的座次之分,长幼有序,主宾有别,一般请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尊贵的客人坐上席,内戚之间论辈入座,一般辈分高的坐上席,内外戚同桌,则以外戚为客,舅舅坐上席。旧时川东田席要喝“转转酒”,陪席中的劝席者斟满一碗酒,从上席左位开始饮酒,向右依次传递酒碗,共饮一圈后,由上席左位长者或贵宾执筷指向筵席中间说一声“开船了,船开不等人”,田席正式开始。劝席者引导宾客敬酒,也是遵照席位顺序,先祝长者寿,再叙亲友情。席间夹菜敬酒,嘘长问短,其乐融融。酒到酣畅处,也有划拳行酒令的粗放场景,江湖气一展无遗。其次,田席对于乡人的尊重,增进了乡谊。川东人吃酒席要“绷面子”,聚首田席自然要给足面子,乡亲邻里之间通常借孩子的称呼,将对方抬高一辈,交换信息绝不吝啬对他人的赞赏,大快朵颐也不忘答谢“大师傅”。乡民之间的互相尊重,满足了交际的共性心理需求、消解了家长里短嫌隙、巩固了地缘关系和人际纽带。再次,田席表达的感恩之心,强化了乡村互助合作的关系。劳动力是农耕经济的基础,农忙时节,抢种抢收,村民之间结成互助组,解决了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田席酬谢乡邻的鼎力相助,表达的是一种感恩之心,难掩疲惫却又盛情难却的场景,让乡村充满温情。
1.3 烹饪传承匠心
川菜传统烹饪技艺入选四川省省级非遗名录,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川菜传承人的汗水与匠心,表现了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与文化认同。川东土碗菜的非遗传承体现了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一方面,川东土碗菜作为川菜下河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以整体的形式呈现。例如广安华蓥的坝坝宴、巴中恩阳的十大碗、南充仪陇的客家水席等,将炒、煮、蒸、扣等川东菜烹饪技法充分发挥,体现了川东土碗菜兼容并蓄、大方粗犷,不拘泥于材料、器物的整体风格。土碗与土菜的完美结合,顺应了食材与器物的本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乡土菜的鲜味与温度。另一方面,川东土碗菜不乏地方标记的个别菜品,例如达州宣汉麻辣鸡、广安盐皮蛋、巴中枣林鱼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地理标志菜品,体现了历史悠久的匠心传承,承载着一方百姓的集体记忆。还有一些地方名小吃、泡菜、调味品的制作技艺也被列入非遗名录,例如开江的豆笋制作技艺等,也是四川饮食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整体的筵席、个别的菜品,还是川菜调料,都要致力于川菜非遗的活态传承。川东土碗菜的乡土根基、蓬勃生命力,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动力。首先,川东土碗菜是乡村社会的产物,是川东人的集体记忆。“传统技艺只有与社会生活需求相联系,个人经验才能被社会认同和接受,转化为集体记忆。非遗传承是以个体传承者为纽带和载体的集体记忆的再生产过程。”[4]乡村旅游者之所以流连于乡村,是因为那里有儿时的味道,挥之不去的乡愁,个体经验情感在体验中转化为集体记忆。[5]扎根乡村的川东土碗菜,实现了集体记忆的价值重构。其次,川东土碗菜的传承机制,保留了传统技艺的内核,也适应了现代生活的需求。从单一师徒传承机制向分工与职业化传承机制的演变,让川菜成为大产业。川东土碗菜不再拘囿于乡村,传统味道的标准化生产,为川东土碗菜的连锁经营创造了条件,川东土碗菜成为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再次,川东土碗菜体现了五方杂处的大融合。川东土碗菜烹饪技艺杂取众长、不拘一格,将“百格百味”的川菜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川菜非遗传承融会贯通地域、阶级、族群差异,体现了不同凡响的文化整合力。
2 川东土碗菜的创新发展
大胆用料,敢于创新,是川东土碗菜最显著的特点。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川东土碗菜的创新品质熠熠生辉。土碗菜风靡城市,践行了生态优先理念;家庭餐桌革命,节省了人的时间和精力;川菜融合创新,缔造了大众餐饮业的奇迹。
2.1 土碗风靡城市
费孝通先生描述了近代中国的乡土本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土”逐渐摆脱了土气的贬义,衍生出生态、地方特色的词义。在乡村旅游的语境中,“土、野、俗、古、洋”的特质,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人们对于“土”的向往,甚至掀起了回归之旅的热潮。川东土碗菜以土碗为时尚,传递了浓浓的乡味,契合了乡村振兴的时代需求。在川东农村,土碗菜成为农家乐的标配。为了营造“土”的氛围,增强乡村旅游的体验性,有的农家乐开辟了可供食客采摘的菜地,并采用光伏驱虫灯等生态科技展现食材之“土”;为了增加食材“土”的附加值,有的农家乐放养猪、鸡、牛、羊,并通过林下经济、生态循环理念阐释食材之“土”;为了体现“土”法烹饪技艺,有的农家乐坚持以柏枝熏腊肉香肠、以柴火灶烧鸡贴馍。川东农家乐的实践证明,以土碗承载土香土色的土菜,更能激发食材的鲜香与游客的食欲。
在生活节奏相对较快的城市,川东土碗菜也受到打工族的欢迎。首先是快,川东土碗菜以蒸扣为主,“蒸笼+土碗”的备菜模式节省了食客等待的时间,烹饪的分工协作更适应了城市的快节奏。其次是丰富,走进城市的川东土碗菜花样繁多、琳琅满目,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口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再次是经济实惠,川东土碗菜门槛低、分量足、好吃不贵,受到城市大众消费者的青睐。创新加快了川东土碗菜的发展,在线下实体店,川东土碗菜馆突出农耕文化的创新,磨盘小径扁担桥,土布轩窗玉米墙,方桌条凳,土碗土菜,此桌方罢,彼桌又起,深得乡村流水席之妙,也有市井文化气息,构建了不一样的饮食文化空间。
2.2 家庭餐桌革命
20世纪90年代,以家庭替代餐为标记的餐桌革命在美国悄然兴起,并风行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家庭替代餐(Home Meal Replacement)是一种家庭外进行制作家庭内消费的饮食解决方案,以家庭外购熟食、调理半成品和加工配菜的方式,以期尽量减少家庭备餐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工作量。”[6]近年来,家庭替代餐在中国发展迅猛,由阿里巴巴重构的新零售业态盒马鲜生整合了超市、菜市场、餐饮店、快递的功能,将家庭替代餐做到极致,并入选“2019福布斯最具创新力企业榜”。“盒马鲜生现象”是现代城市生活的缩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食材的新鲜和生态,自觉抵制隔夜菜、转基因食品,但又无法追溯源头、千挑百选,也不想为配餐而耗费大量时间,这为选择家庭替代餐创造了条件。智能科技的创新更是打通了家庭替代餐流行的最后一个关节,人们将配菜放入多功能料理锅,然后输入菜单,多功能料理锅就能自动烹饪主人想要的菜肴。家庭替代餐适应了城市的快节奏,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健康饮食需求。
家庭替代餐客观上带动后厨工业化和标准化升级,川东土碗菜进军商超美食城势不可挡。在商超柜台或餐车中,顾客可以自由选择热气腾腾的土碗菜直接食用,也可以选择营养搭配的食材或半成品现场加工或者打包带走。川东土碗菜的食材和用料都可以标准化生产,作为家庭替代餐还有生态性强、大众化程度高的优势,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市场。比如城乡接合部的选址,有利于川东土碗菜新鲜食材的及时供给。而根据销售垂直订货的经营理念,不仅保证了食材的渠道和质量,而且减少了食材变质的库存损失。
2.3 川菜融合创新
川菜能调众口百味,贵在融合创新。从川菜烹饪技艺来看,不拘一格博采众长,乃铸川菜之魂。例如客家名菜梅菜扣肉与川菜融合,就发展为脍炙人口的咸烧白,保留了梅菜扣肉的传统食材与客家菜的咸甜风味;川东土碗菜又创造性地加入泡辣椒,以肉片卷成筒状,做成龙眼咸烧白,形成了咸甜辣的地方风味。川东土碗菜的压轴之菜品碗,融合更加复杂,创新愈发大胆。将猪肉剁成肉蓉,以鸡蛋均匀涂抹肉蓉,蒸制切片后,覆盖于焯过水的木耳、豌豆尖之上,以红油调汁浇淋肉片之上。整个制作过程融蒸、焯、浇汁等工艺,从中可见湖北肉糕、粤菜烧汁与川菜合菜技艺的融合,创造性表现了品碗的香软嫩滑与层次变化。
从川菜品牌输出来看,融会当地菜系的创新,则为川菜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市场。相比于其他菜系的高端定位,川菜的根系在民间,也迎合了大众消费者的口味。川菜北上进入北京,便有了京派川菜宫保汁的配方;川菜下江到了上海,便有了一点也不辣的海派名菜香酥鸭;川菜下海去了深圳,便有了上汤娃娃菜的咸香。改良后的川菜似乎少了川菜的味道,却保存了川菜的灵魂,延续了川菜融合创新的本质。从川菜文化的角度,正是这种以人为本、有容乃大的文化品质,使得川菜成为八大菜系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菜系。英国美食作家扶霞·邓洛普认为:“川菜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一道菜肴中大胆融合很多不同的风味,一顿饭中能尝到千奇百怪的丰富滋味。”[7]事实上,川菜在国外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关键在于调味技术,走出国门的川菜馆,除了特有的麻辣味道,甚至能够很好地应用西方的黑胡椒、番茄酱等调料,烹饪出符合西方人口味的菜肴。川东土碗菜大多化身川菜小餐馆,分布在国内大小城市,不断融合创新的家常味,突破了众口难调的局限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餐饮业的奇迹。
3 川东土碗菜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
3.1 乡村产业链条化
川东土碗菜以食为天,直接关系到民生之本。由土碗菜带动的产业覆盖一二三产业,呈现出体系化发展的趋势。首先是第一产业,川东土碗菜密切联系“菜篮子工程”,带动了蔬菜产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其次是食品加工业,包括川菜调味品、泡菜、休闲食品的工业化生产,一般依托原材料基地布局,带动地方就业以及经济发展。再次是餐饮服务业和旅游业,川东土碗菜是餐饮产业的金字招牌,不仅得到本土群众的认可,也能吸引外来游客品尝美食、体验美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是基础,以土碗菜助推乡村振兴,还需不断完善和夯实产业链,促进产商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从农业延伸的产业链主要以农业为载体,强调“一村一品”,配套种养循环、电商、餐饮、乡村旅游业;从食品加工业延伸的产业链,注重生产、流通渠道的拓展,通常采取“接一连三”的方式,即配套种植基地、工业旅游等;从乡村旅游业延伸的产业链,突出管理服务的品质,通常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塑造乡村景观、强化文化体验、推送乡村美食及特产。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决定了产业链的模式及功能,产商文旅深度融合与差异化发展并不矛盾,反而突出了主导产业的特色。川东土碗菜虽以区域泛称,却能因地制宜、因产业而异,走符合市场规律及自身发展规律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3.2 乡村文化本土化
川东地貌山高水长,造成“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差异,广大乡村即使饮食习惯趋同,在饮食文化上仍然存在差异。例如广安华蓥山村民喜食腊猪蹄,华蓥山阳的村庄日照充分,农家乐相对密集,每近年关,家家户户将猪蹄悬挂于晒架风干晾晒,煮出来的猪蹄汤色白而味浓。而华蓥山阴的村庄,因为日照相对不足,常将猪蹄悬挂于厨房灶台的上方熏干,煮出来猪蹄汤色灰白且多了一些烟熏味。也有邻近的村庄,因为历史移民的因素,保留了一些原乡的饮食习惯,而导致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川东土碗菜助推乡村文化振兴,还需坚持乡村文化本土化,深挖地缘文化、历史文化、移民文化,提炼饮食文化的精华,推出具有文化特色乡村菜品,满足多元化的消费者需求。强调乡村文化本土化,并不是一味索求“奇异文化”,而是顺应乡村文化肌理,探寻自然生长的、有温度的文化。乡村文化本质上是人的文化,许多真善美的文化细节、充满怀念与温情的味道,也会在乡土打上烙印、形成口碑,进而影响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
3.3 乡村生态效益化
乡村振兴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川东土碗菜最大的优势是食材的生态性,实现绿色发展关键在于生态性的价值转化。首先是发展有机农业,种养生态食材,这一阶段以投入为主;其次是销售生态食材,体现一部分生态效益;再次是烹饪生态菜品,体现生态价值;最后是消费过程中实现增值效益。从川东土碗菜的生产、销售、加工、消费过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生态效益,但绿色发展理念却贯穿始终,也只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才可能真正实现乡村生态效益化。以川东土碗菜助推乡村生态振兴,还需考量相关产业对乡村环境的影响,将生态占用、生态环境损耗纳入效益评估,客观评价川东土碗菜的生态效益。
3.4 乡村人才专业化
在川东乡村社会,厨师是体面的职业,红白喜事请厨师还有约定成俗的礼仪。就做土碗菜而言,川东群众多有发言权,家庭“煮男煮妇”也时常露一手厨艺,但谈不上专业化。川东土碗菜擅长家常味,却并不等同于百姓家常菜,还需要培养专业化的人才。从川菜非遗的角度,乡村厨匠就是专业化的人才,不仅具有熟稔的烹饪技艺,还有着敢于创新、精益求精的匠心。从川菜产业链的角度,川东土碗菜助推乡村振兴,还需要培养种植能手、管理人才、营销策划等各方面的人才,健全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体制机制。人才专业化也是后厨工业化、标准化的重要保障,是川东土碗菜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品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3.5 乡村组织常态化
乡村组织常态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乡村振兴的主体并非分散的个体农民,而是且只能是组织起来的农民。”[8]川东土碗菜助推乡村振兴,还需引导农民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社、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川菜非遗传习社、餐饮行业协会等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川菜产业,以乡村组织振兴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例如,通过蔬菜专合社的技术和市场整合,发展生态蔬菜基地;通过劳务合作社和川菜非遗传习社,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培养专业技师和非遗传承人;通过餐饮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拓展川东土碗菜的市场渠道等。乡村组织常态化,就是要强化乡村组织功能,确保乡村组织的常规运转,只有让农民真正受益,才能真正激发乡村组织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