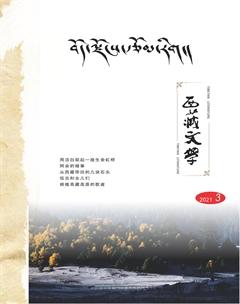安住宗果苍穹的赤子纯真质朴的吟唱
孔占芳
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作家们几乎都有散文的创作,比如,阿来的《马》、扎西达娃的《西藏女人》、央珍的《拉萨有条八廓街》、色波的《墨脱四日行》、班果的《归于雪山》等等。甚至有散文结集出版,比如龙仁青的《马背上的青海》、梅卓的《走馬安多》、白玛娜珍的《西藏的月光》《生命的颜色》《拉萨的雨》等。其中雍措的《凹村》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奖,开辟了藏族作家汉语创作在散文领域的首奖成就。
但就整体的创作体裁而言,小说和诗歌成就斐然,散文创作体量较小,专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就更少了。究其原因,散文对“真”的要求无疑提高了创作的门槛。正如近年非常流行的“非虚构文学”,散文也有“非虚构”的特征,内容上要求实有其人其事,情感上也要求真情实感,即说实话、说真话,揭示真相,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其二,散文从诗歌脱胎而来。冯骥才说:“中国文学史诗歌成熟在前,散文成熟在后,诗歌对文字的讲究影响到散文,在我国的文学史中,散文达到的水准太高。”①因此,要想在这样的高度上有所建树,难度很大。
正是在这样的写作境遇中,久美多杰的散文创作显示出了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对故乡赤子般纯真质朴的吟唱中,安多农牧区改革开放以来藏族的生活、情感、心理、追求、教育、文化、民俗、宗教、信仰、生态等等,真实地呈现出来。最为可贵的是,以不要忘记学了很久的母语而开始创作的初心,让久美多杰保持了记日记般的散文写作方式,这成就了他的散文因记录细小的日常生活细节,而成为安多藏民族社会变迁的史实性记录,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发自内心对故乡和民族赤子般的热爱以及藏语言文学专业的历练、藏文创作和藏汉翻译、藏文化研究等,又使他的散文创作带上藏民族创作的思维特征、与生俱来的幽默风趣以及学理的思辨,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
久美多杰的创作分汉语散文、诗歌创作,藏语散文、诗歌创作,藏译汉三种。本文所论散文是由作家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藏译汉翻译集《久美多杰散文集》和2016年出版的汉语散文集《故乡与远方》里的作品。
一、安多农牧区村落生活的真实记忆
久美多杰的散文从开笔,就与中国传统散文一脉相承,描写故乡普通藏族民众的喜怒哀乐,以赤子的纯情和学理的哲思,活脱出安多大地上藏民族鲜活纯真的生命,细微处见人性,笔端流淌真性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智趣,成为谱写安多藏人社会生活的别开生面的文学篇什。
久美多杰的文学创作所记录的社会生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他抱着不要忘记学习过的母语和汉语而练笔的微小目的,以近乎记日记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他对社会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笔触所及政治、经济、教育、民俗、生态、民族团结等方方面面,成为安多农牧区村落生活的真实记忆和历史见证。
在他的散文中呈现青海多民族聚居的现实。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据官方资料统计除珞巴族外,青海有55个民族。但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交流的情形在青海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作品中较为少见,久美多杰在他的散文中被记载了下来。《我的小学》真实地记录了村庄里多民族聚居的时代印痕。藏族、汉族、回族等各民族在一个村子里共同生活,相互依存。其中“10户回族人家是由政府安排从县城搬迁到我们村里的。我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又一户户返回城里去了。”多民族杂居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我”的一年级到四年级汉语和数学老师都是回族,村里人叫他“阿加老马”,“阿加”是藏语大哥的意思。这种多民族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中国多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写于2014年的《唐生发的“中国梦”》里,作者的扶贫对象唐生发所在的平安洪水泉乡,“有十五个村,居民以汉族和回族为主。据当地一些老人讲,这里以往住着很多藏族人,他们的祖先也是藏族,现在全部汉化了……这里有一座清真寺,建筑艺术除了伊斯兰特色明显外,还有汉族、藏族文化元素在里面,被认为是青海清真寺建筑史上一绝。”这个绝,就是民族文化的融合。
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走,作者的胸怀越发开阔,家园的情感升华为家国的情怀。在西安,他写下情感至纯的《金城公主》,一千三百年前,“阿姐在地球之巅,能看到草地、农田、山谷、平原以及江河湖泊。一旦烽烟升起,每当战火燃烧,阿姐就成为一名谁都不可替代的超级消防员,让所有族群免受灾祸之苦。”他深情赞美:“美丽智慧的阿姐,善良慈悲的阿姐,我们的金城公主啊”,“越想念就变得越美丽,越美丽思念也就更深切。”
在延安,他想起村里老人们讲的一个故事,“一名红军战士,恰恰来到了我们村。最初,他给村里一户人家帮忙干活,后来,就给另一户当了女婿。时间一长,这位红军战士不但能种田犁地、骑马放牧,而且学会说藏语,纯粹成了一个藏族人。我还没有出生,他就去世了。我估计,他可能是到过我们村的第一位汉人。”(《在延安想起宗果》)
《花的瓣》是作者对族人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状描,是他深沉的家国情怀的深切表达。不丹“被飞扬在众神路边的经幡”,“没有补丁的母语”那么熟悉;锡金“高大的佛塔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对世界的宽容和对自身处境的无奈,在街市上熙来攘往。”“锡金那充满尊严和思念的双眼,在雄伟宫殿的墙壁上遥望着北方。”拉达克“从小被人掠夺的孩子”,“依然古老的村庄留在山谷,依然飘香的糌粑坐在屋舍,依然传统的服饰镶在身上,依然熟悉的微笑印在脸庞,依然亲切的母语含在嘴里……”,“当初的列城,如果没有走得太远,也许还能找到回家的路。”还有,“想写一封信给巴尔蒂,问候那里的兄弟姐妹。”“想告诉小孩,你们也是雪域的子女啊!和我血脉相通骨肉相连。三十个字母完好无损,四个韵母半点不缺,正在等你们来高声诵读。想告诉未来:没有拉达克和巴尔蒂,阿里三部名不副实,一只雄鹰折断了两只翅膀。”作者对同胞饱含深情,用最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内心的思念和祝福,题记饱蘸家国胸襟:“我有一朵太阳一样灿烂的花朵,一些花瓣现在飘落在山那边;我有一朵月亮一般圆满的花朵,一些花瓣如今飘落到河对岸。”
在写作中,久美多杰逐渐从关注家园的“小我”走向关注家国、关注人类命运的“大我”,但根还在民族文化的大地上。
2004年,作者因工作需要对小学教育做调研,《青海湖以南的春天》真实记录了青海贵南、同德、兴海、共和、恰卜恰牧業区的教育现状。中铁乡长说,“校舍紧张、布局结构不合理,以及资金短缺等问题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青根河寄宿小学在“无垠的荒野里,最远的学生来自五十公里以外;微弱的灯光下,最小的孩子才满六岁。”同德县“阿血尔教学点仅有两间教室,年轻的编外女教师,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她兼任藏语文、汉语文和数学三个科目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严苛自然环境和教育困境面前,渴望知识和浇灌知识的顽强生命撼动了作者的灵魂,他用诗一样的语言为这些坚韧向上的生命歌唱:“唐格木沙漠的沙尘像数以万计的奔马涌向了塔秀草原。”但是,“牧民们还是骑着摩托车,冒着风沙把孩子送到了学校。老师们的眼神,如民歌一样高亢。”尕群寄宿小学里,“牛粪烧红了炉子,教室里弥漫着春天的诗意。一双双天真的眼睛,在咀嚼藏文字母的同时,也在啄食着aoe和ABCD。”“握粉笔的大手和拿铅笔的小手,像一朵朵含羞的格桑花。”“青根河寄宿小学宛如一列火车,满载着希望行进在高寒地带。”回到工作单位,“我又想起了海拔3000米以上草原深处的老师们,以及他们那一张张被紫外线晒伤的脸,那一双双冰凉而有力的手和顶天立地的腿。”我们看到藏民族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坚韧的生命力量。
二、对故乡家园的纯情赞美与深切感恩
对故乡家园的赞美与感恩,是大多数作家文学创作的缘起,久美多杰也不例外。宗果是久美多杰的胞衣地,也是他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最为频繁的一个词,是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的一个农牧业村,是他出生、成长、写作的精神家园。作家在《这儿离黄河不远》中考证出宗果的区域和名称来历。“在青海湖以南,黄河以北”,历史上属于郭密部落,“以前的汉文史料中,这一地区被称为溪哥,其实就是藏语赤嘎的谐音,赤嘎现在的汉文名字叫贵德。”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宗果、溪哥、赤嘎不断变换着出现,散文集《故乡与远方》就是写给宗果的歌。久美多杰将散文秉承的真情实感在文学作品中加以实践,使他的散文成为故乡生活的真实记录,他也成为时代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和见证者。宗果的山川地理、宗果的自然风景、宗果的家人邻里是久美多杰散文里的主角,是他情感神经中枢区,他将自己对家园的挚爱之情倾注在文字里忘情地赞美。
在宗果,天空高远,土地干净。春天的上午,梨花像刚出生的小羊羔一样好奇地东张西望;夏天的中午,所有风都躺在树叶上,像母亲怀里的婴儿一样安静地睡觉;秋天的下午,太阳穿过云层,像一个风尘仆仆的路人,带着小小的忧伤,等待月亮的抚慰。冬天,雪山重现雄伟,草地孕育新梦,村落炊烟袅袅,河水结冰后就像一条条哈达,把吉祥凝固在门前,不让流淌。(《这儿离黄河不远》)
将春天始开的梨花比喻为小羊羔,将结冰的河流比喻为哈达!多么新颖的比喻,多么神奇的思维!作者用藏族人特有的思维,取藏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象成譬,不仅生动形象,极富画面感,而且有浓浓的藏文化气息,“宗果”成为文学画廊里一个独具藏族文化特色与底蕴的文学名词。
奶奶是这个精神家园中最为温馨的回忆。奶奶去世后,作家时常怀念。“奶奶的怀抱成了我们演练航行的最初港湾,奶奶的脊背沦为我们学习飞翔的第一跑道。”“宗果的每一天早晨,炊烟是山村里最美妙的舞蹈。我多么希望再一次见到这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用无限的慈爱点燃那美妙的舞蹈,迎接全村第一缕阳光的动人情形。”(《三个人》)
《清晨》中,夏天的故乡“狗在充满牛粪味道的炊烟中吓唬天上最后一颗星星,远处的流水一阵阵流入耳孔。……八九只小羊羔,相约麦田旁边的山坡,一边闻着桑烟,一边欣赏草尖的露珠。马蹄莲静如她那蓝色的花朵。”这一方田园牧歌的诗意家园,就是作者迷恋的故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恬静、惬意、温馨、自在、安宁,坐落在21世纪初青藏高原一个偏僻的河谷。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最惬意的心灵感受,家园是诗人的精神归属地,而感受如此强烈,则是因为对比。作者对故乡的痴迷,正是因为他“离开”后的情感依恋和“远观”的审美效应。《我的小学》中作者明确“我也是读完三年级以后再没有上小学。爸爸托人通过关系把我和四年级仅有的两名同学送进了县民族中学。”从此,“城里人”是他生活的常态,回乡,是学习、工作中的休整。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中,“审美”就成了对故乡的视角。从情感上,他不愿故乡被城镇化、现代化,他需要心灵的栖息地,以安放身心。从理性上,他也不愿故乡由农牧业文明转变为城市文明。城市文明让人类充满焦虑,失信、尔虞我诈、冷漠、隔阂,这些是与人性相悖的,令人痛苦的,是心灵的紧箍咒。在城市中生活,人心是紧缩的,心门是关闭的,人是孤独和寂寞的,一切都在变动中,声色犬马,人心浮躁。心灵安放地在哪里呢?唯有故乡!这是游子们渴望纯朴的农牧业文明的心理基础。
作者也思考人为什么一再书写故乡,他认为单个的人是渺小、脆弱的,需要借力故乡,才能坚强。“孤单的我们,亦非大力金刚手菩萨。远方,因此站满了用笔思念故乡的游子。”为什么将故乡写得那么美,因为“从远方思念故乡,故乡是地下涌出的清泉。”作者也清楚地知道故乡是赤子之情过滤掉了杂质。故乡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对母性的深切依恋,纯情质朴的歌唱是对人生来处的深深感恩,这是久美多杰散文的一个精神向度,也是文学的精神向度。
三、对生态环保的真切关注和担忧
与现代化的警惕同时进入久美多杰眼帘的是生态环保问题。现代化与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逐渐显现出来,成为作家们关注与担忧的问题。《世纪末的话题》《雪线以下》《还我衣服》《在宗果河滩怀念森林》《宗果的河》《果洛夏天的雪》等,都是久美多杰生态文学的篇什。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散文中记录下家园环境恶化,生态受到威胁的真实情况。
我生活多年的村庄正在荒凉。大山变得丑陋,溪水日渐干枯;孩子们孤单地长大,成人都无力地倒下。从哪儿飞来的怪鸟,在到处传播莫名的疾病。很多牛、羊、马、骡、驴陆续离开田园走向远方,只有那棵站立了五百年的大树守望着故乡破败的房屋。(《远方在哪里》)
作者在雪线以下行走。眼里所见尽是生态的恶化。青海湖是最美的草场,可是一味追逐经济利益,草原被开垦,“草原上的耕地仿佛是打在我们心灵上的补丁。”生态遭到破坏,狂风袭来。作者带着愤怒斥责、痛惜:“看着子民们用粗糙的手接过一叠钞票后,便把自己仅剩的根据地拱手让给那些黄鼠狼一样的人去糟蹋;看着越来越多陌生的面孔狰狞地用利刀划开草地的胸膛,并活活剥去一层绿色的皮;看着魁梧的农用机械大叫大喊与瘦弱的牛羊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的母亲湖——赤雪杰姆又一次哭泣。”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染白青海湖双鬓的竟然是钞票!”
他的工作地恰卜恰“是藏语两条河的意思”,但现在“只看到一条瘦削的蛇,艰难地蠕动在宽阔的河床上,给饥渴的沙石讲述曾经大河向东流的故事。”他行至塔拉(蒙古语草原)滩,正值下午,“饶干村在荒漠腹地一动不动,天空急促的呼吸中,沙尘在自由活动。一泓泉水,在离饶干村26公里以外含情脉脉;一辆运输生命之源的马达声,在沙漠深处匍匐了一整天。一群牛羊,望穿天边一朵流浪的云,而雨,却像一封家书迟迟不肯邮来。一名男子和她的小女儿泽瑟,站在那堆坟墓般一天天逼近自家后墙的沙丘上,浑浊的目光里缺乏夏天的内容。”
作者不仅记录下自然环境遭到人为破坏,而且痛析生态恶化的原因。《在宗果河滩怀念森林》是一篇很鲜明的生态主义文学作品。一场暴雨导致故乡宗果村庄一半农作物被洪水冲走、被泥石流覆盖。“我想:宗果连续遭受的这些自然灾害,既不是神祇发怒,也不是妖魔作怪,而是与特殊的地址构造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作者反思村庄近年因为外迁人口猛增,对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和采集牲畜严重超载,乱砍乱伐,“遭到了大自然的警告和报复。”他担忧,“现在,生态危机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的家园落入沙尘与洪流之手,人类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他还对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发出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敢担当。《还我衣服》以水獭、狐狸、豹子、老虎等各种动物交谈的新奇叙事视角,揭露了人类钩捕、投毒、用金钱购买等方式对动物犯下的罪孽。
作者不仅仅是生态恶化现实观察者和记录者,也是一位绿色环保的倡議者和建构者。当他看到草原的干旱、荒凉与饥渴,他真诚地祈愿:“如果生死由己,来生我只愿做一条溪流,每天沿着这片荒漠的伤口,静静地淌过,让饶干村重新看到南飞的大雁又像诗一样从容地流向远方。”这样的赤诚来自草原的赤子,情真意切,为之动容。
难得的是久美多杰对生态恶化问题的关注和书写的情怀,最先源自藏族自古就有的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禁忌或教义的力量,与国家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接轨,焕发出生态文学新的精神向度。
四、对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幽微哲思
久美多杰的文学创作独具藏民族思维的理性思考,充满着理趣,散发着智慧的光焰,闪耀着学者性的理论功底和论辩力量。他的三分之一作品闪耀着观察宇宙人世的理性思考,启迪着读者的心灵和理性思维。《远方在哪里》《一个步行者的梦语》《我的安多》《不要叫我爸爸》《九月之旅》《时间如鱼》《从柴达木走过》《新年的日记》等等篇什,都是他对宇宙人生的幽微探思。
《远方在哪里》是久美多杰对宇宙、人生、创作进行思考的总汇和结晶,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语言的形象、准确、流畅,境界的阔达,堪称久美多杰散文中的精品。在“梦语般的文字”里,作者以散文诗的形式与节奏,构筑《萨迦格言》般名言警句的大厦。作者竭力穿透纷繁驳杂的世界,思考宇宙、家国、人生、人性、价值、追求、理想、爱情、恋人、村庄、城市、生态、真诚、伪善、梦境……
他像一位哲人一样思考。人生,在于辛勤耕耘:“犁铧行走在天空中,太阳把种子撒进田野里。汗水从眼前流过,大路在离我最近的远方渐渐出现。”生命,没有贵贱,众生平等:“游鱼不是大海的奴隶,飞鸟不是天空的仇敌。父母般的太阳周围,一切生命没有尊卑。”“关注地球的现在与未来,在远方,人的工作没有贵贱,贡献不分大小。”有追求就要行动:“从现在起,我将不再等待——穿上雪山,我要修行一百年,邀请自己的导师、医师和琴师永驻我的心尖拈花微笑。”“我要作心的奴仆,我要作脚的主人。从故乡的河边出发,我要以鞋为友,去寻找自己的远方。”因为“远方是时间的化身,它教我们如何辨别过去和未来。”“没有远方,心灵就失去了光明。”
“远方”就在这样的思考中逐渐理清:它不是一个既定或固定概念,而是一个不确定的、相对的概念,历史与未来、故乡与异乡、梦想与现实、空间与时间都可以成为相互的“远方”。这种理性的追思与探寻,使“远方”成为表达作者思想的概念。最终,他找到了答案:“远方在哪里?”在“没有偏见和仇恨的地方。”并在结尾祈求:“请允许我用幻想把色、声、香、味、触等五种妙欲供奉给六道众生及其救世主,愿和谐自在之花开遍世界”。
这样的思考与境界,这样的语言与节奏,让人一下子想到泰戈尔,想到他的诗集《吉檀迦利》里面的诗句:“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罢!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地下到泥土里去罢!”博爱、平等、劳作、追求,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久美多杰在思考与探寻中找到了文学的目的:提倡人间的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给人以理性与良善的启迪。
久美多杰的散文创作内容丰富,绝不止笔者以上所述。但立足家园,走向阔大的家国情怀,关心民族、心系普通民众福祉,是他的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
注释:
①冯骥才: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当代文坛[J].2019,2
②孔占伟:朴拙率真的久美多杰.青海湖文学月刊.2015,12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