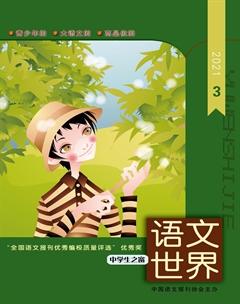是真佛只说家常——邵丽印象
计文君
寒潮骤至的夜晚,北风在天地间放肆地吹着口哨,沉沉入梦之时,被电话叫醒,含混地叫了声“姐”,那端传来姐姐的天语纶音,命写“印象记”一篇,次日交稿,此时离次日不足两小时。她在电话那端焦灼又混乱地解释,且把“印象记”说成了“创作谈”,我竟然毫无障碍地听懂了。
我也曾因为《收获》的缘故这样去难为过别人,理解那份不得已的歉意,于是爬起来,去厨房做了一大杯意式浓缩,啜着咖啡打开电脑,敲打,删除,再敲,再删……屏幕上还只有“邵丽印象”四个字,而“今夜”已经成为了“次日”。
难以下笔,不是因为无事可记,而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涌上来,太多充满矛盾的事情。清晰的印象,往往来自远观,越是了解,越是混沌。你目之所见这是个端丽女子,温暖可人是她,娇嗔活泼是她,七窍玲珑是她,糊里糊涂是她,运筹帷幄精明强干是她,不諳世事丢三落四也是她,她烹茶品香缀珠弄玉,她纵横开阖拢黄河、抟中原于笔端……
这些矛盾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合理性,邵丽既修入世法,亦修出世法。不修入世法,不知人性;不修出世法,难以超拔。她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用她自己的话说,“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毕竟,那梦想之光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是很难发现的”。
慈悲与耐心,不是简单的态度,而是苦修得来的杰出小说家的本领。这条小说家的修行之路,邵丽一直努力地在走,她修来了足够的世故,足够的天真,足够的冷酷,足够的阳光,足够的细腻入微,足够的大气磅礴……
我确定她未必记得和我的初见。那是16年前,在省作协办公室,她似乎也是刚刚去作协,送了本《我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文联主席。我们只有礼貌的寒暄,并没说什么话,我后来就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被她的形象和得体带来的距离感吓到——通常高挑靓丽的女子,越是举止得体,越是会给人骄傲的感觉。也许是读过她小说的缘故,笃定地认为彼此是同类。后来我们有机缘谈话,惊讶地发现她对我毫不陌生。再后来,又熟了些,她“招认”了眼高于顶的骄傲,轻易不肯施人青眼,待人全是因为文字的缘故。锦心绣口的人,骄矜些也是常理,幸好我善于“精神胜利”,没有败给她当初的“拒人千里”。
后来看了邵丽的创作年表才知道,她那时开始写作的时间不过数年而已。接下去她如同“开挂”——用游戏用语形容她,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佳作迭出,频频获奖。从获鲁奖的《明惠的圣诞》到2020年的《黄河故事》,这些年我默默地读着她的作品,仿佛看着那条转过了孟津的大河,越来越宽阔,越来越不动声色的水面下,波谲云诡,暗流涌动。我有时感慨她那支笔,于人情事理描绘得越来越精细微妙,对人心的痛处剖得越来越准、越来越狠,但生命温度不减,情感丰沛依旧,这一点我着实有些羡慕。
文如此,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她,人如此。
2012年,我和邵丽共同参加一次文学活动,返程时接到父亲肾衰进了重症监护室的消息,我就直接把机票从返回北京改签成了郑州。在机场分别时,她默默地朝我手腕上缠了一串上好的朱砂珠串,抱了抱我。
从那个时候起,她成了我故乡的姐姐。我并不惯于和别人姐姐妹妹的肉麻。面对邵丽,我会觉得自然。此前没有细想过原因,此刻想想,却发现这种感觉的来源,大有意味。
最直接的一层原因,当然是她的强大的情感输出能力,这其实是今天非常罕见的一种能力。如果辨析一下,我们日常在人际交往中很多时候唤起的是情绪,而非情感。在被社交媒体刺激得各种情绪膨胀的同时,真实的人类情感反而隐藏甚至蜕化了。情感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能量密度,像我这么敏感又极度缺乏安全感、充满社交压力的笨家伙,面对这样一个稳定的能量输出者,会放松,释然,安心,那声“姐”也就变成了可以跟她各种耍赖的神奇咒语。这一点其实也可以为上文我对她的“羡慕”做一注脚,认知的深刻与情感的强大,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邵丽若无深情,焉有高致?
第二重原因比较复杂,其实“姐”,内蕴着一个颇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文化人格。我身上也有这个“姐”性,带着某种强制力和压迫性。我的自然而然,是一种下意识对共同来源的辨识:我和她都生于河南——更准确地讲,我们都生于豫东周口。我们面对的文化规定性是:人生的所有价值都必须被放置在伦理结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这显然是与现代性有着强烈对冲、值得好好理解、但却无法一笔抹杀的一种规定性。
“对冲”好理解,而不能“一笔抹杀”,意味着无法简单否定——否定是容易的,容易得有些不负责任。这是有着复杂内蕴的文化现实,如果粗暴地处理成地域文化兼性别政治问题,反而会构成对这一现实本身的遮蔽,那是对真实地承受过重重生命苦难的男人和女人,父亲和母亲、一代代儿女的“再度伤害”。
无论邵丽,还是我,在写作的最初都省察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来都是自觉、直面这一问题的。邵丽让我感到钦佩且由衷地愿意以“姐”敬之的一点,是她用一种“正面强攻”的姿态,这么多年来始终、逐步深入地剖析着这一问题。她在用创作,实践着她强调的“慈悲”与“耐心”。
因着慈悲和耐心,才能“入微”。但她“入微”的同时,也在“放大”。邵丽这些年关注点始终都是家庭、婚姻、代际这样的伦理关系,但她通过叙事展现的社会景观却是“全景化”的,从职场到官场,从都市到乡村。她有持续观察的热情和兴趣,而且随着思考的深入,她把这些关系纳入考量的“坐标系”越来越宏阔,因此小说文本生成的内蕴层次也越来越丰富。
她自己说:“一个时期以来,我热衷于写父亲,我的父亲和我父亲以外的父亲。但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也毫无相似之处。他们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在光明之处缄默不言,又在遁入黑暗后喋喋不休,像极了胡安·鲁尔福的小说里那种人鬼之间的窃窃私语……我看到了在历史熹微的光芒之下,他们卑微如草芥的人生逐渐被放大,再放大,直至覆盖了整个宇宙。”
一沙一世界,她的笔下,一个人身上透出了全息的社会历史图景。以作品为镜,邵丽的人生也活得越来越阔大了。我眼中的她,足够知性,深谙在权力结构中的性别关系,抗争是必须的,但对事理人情缺乏足够的理解,也很可能带来“双重悲剧”;但她又始终有着山青水润的女儿心态,譬如我读到过她的爱情诗集,又惊又叹,且又一次满心羡慕了;还有幸见过她作为老母亲的一面,被她可爱的女儿请吃日料,后来我会反复回想那个场景,觉得她的生命何其丰盈!
父母在堂儿女绕膝含饴弄孙,在我看来是尘世幸福的象征,我在情感上会给出很高的价值排序,虽然明知道这话说出来,几乎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了。就像胖子有立场讲胖子的笑话,孑然一身的我似乎也有立场表达这样的羡慕。但是我也知道,人伦关系都附带着压力和牺牲。如同看到她一部接一部出佳作,必然能想到她背后默默做出了何等的付出。
可恨的是,除了小说高产,你还常常读到她的各种文章,赋中原论黄河算是她的本分,可谈《金瓶梅》,论科尔姆·托宾,能量充沛到让人眼睛发红。好吧,看在她总忍不住绕一串祝福的珠子在我手腕上的缘故,就原谅她了。
一路写到此处,还没有找到题目,忽然想起她评论《一减一》的文章标题,又现成,又贴切,就偷来用了。
她在文中说:“‘是真佛只说家常,世间的人情物理莫不如此。”
这话,也正好可拿来说书写常人家事的邵丽,她对人间存有大信。
- 语文世界(初中版)的其它文章
- 冰窗花
- 误入荷花深处
- 穿行一瞬
- 赠人荷花,手有“余”香
- 邵丽:是真佛只说家常
- 在西藏的每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