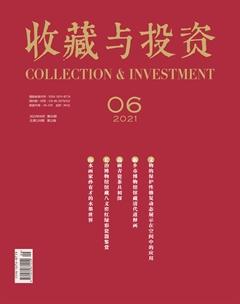中小博物馆的宣教服务发展初探
摘要:博物馆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文化之眼,也是我国在文化事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宣传我国核心价值观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博物馆的功能也逐渐丰富起来,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藏品展览和收藏,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性越来越强,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以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为例,提出一些优化博物馆社会宣教功能的建议,旨在推进中小型博物馆宣教服务的发展。
关键词:博物馆宣教;中小型博物馆;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增多,文化建设是当务之急。人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望从单一的读书写字转变为向多元空间立体化发展。博物馆是文化宣传的重要载体,是社会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也在不断地增强,普及的范围也在变大,由此可见,博物馆在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引导精神层面建设、构建文化服务体系、弘扬我国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博物馆式的教育需要一种新的思路和办法,构建新的发展目标,逐渐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这也是今后博物馆发展的方向。本文以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为例,探析中小博物馆提供宣教服务的途径。
一、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介绍
山东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临朐县博物馆)成立于1981年,1985年正式对外开放,占地面积10 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 000平方米。博物馆藏品总量9.8万余件(套),目前设有民俗文化,山旺动物、植物化石,佛教造像,石刻文物,历史文化六大展览和山旺化石AR数字化互动体验区,是一个集陈列、教育、收藏、研究和利用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2002年7月,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被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评为“山东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0月,被中共临朐县委、临朐县人民政府评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2月,被临朐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临朐县委评为“临朐县青少年教育基地”。
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中的馆藏文物非常丰富,以化石数量多、种类丰富、完好度高而出名。山旺的化石大致是在1 800万年前形成的,目前我国已经在当地发现了十多个门类、七百多个属种。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展出的植物类化石种类非常丰富,有苔藓、被子植物、裸子植物等,其中,植物的枝条叶子脉络非常清晰,花和种子等保存良好。动物类的化石不但种类非常多,保存的价值也非常高,像鱼、昆虫、两栖动物、山东鸟、三角原古鹿等,都属于非常珍贵的化石种类。
1976年,山旺发现了山东鸟的化石踪迹,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我国当时在中新世鸟类化石的空白,甚至引起了国际古生物研究界的热烈讨论,具有非常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山旺古生物化石在博物馆内的展出,十分真实地演绎出了山旺地区在1 800万年以前的生态和地貌,可谓是大自然真正的活教材。如果有机会在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中浏览,必定会感叹,宇宙何其浩瀚。
除了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内地上或地下的文物遗迹也非常多,从大汶口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再到近现代各个朝代的文物基本都有收藏。博物馆中,馆藏的陶器、玉器、青铜器、东汉印章、明清大家的书画楹联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而北魏石佛雕刻壁画更是填补了我国美术史上这一时期墓葬壁画的空白,这些藏品客观地反映了临朐古代文明史的发展。
历史文物上自北辛下至近现代各个时期均有收藏,玉器、陶器、青铜器、瓷器及明清大家的书画楹联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北朝佛教造像繁简得当,线条流畅、工艺精湛,可谓国之瑰宝。北齐崔芬墓壁画填补了我国美术史上这一时期墓葬壁画的空白。
二、博物馆社会宣教服务的特点
我国中小型博物馆是城市进行文化服务的重要“眼睛”,博物馆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明,也反映了其对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是我国建造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基础。作为社会宣教服务的重要载体,博物馆和社会大众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博物馆内的藏品展出和开展的一些文化宣传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博物馆与参观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知识的传递链条。
博物馆开展文化服务,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種是人们主动走进博物馆参观和学习,第二种是博物馆自身“放低姿态”,主动融入大众[1]。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博物馆与人们交流的方式都是博物馆本身对社会宣教功能的具体体现,因此,博物馆的社会宣教功能要以人民大众为第一顺位,再结合每个地区博物馆自身的特点展开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教育。当前,人们对文化层面的需求越来越丰富,这对博物馆提供的文化服务有了更高的质量要求。
三、博物馆在社会宣教方面的不足之处
近几年,我国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很多群众愿意主动进入博物馆,看一看家乡的历史与风采,正因如此,博物馆成为地方文化服务中心,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文化代表。一些中小型博物馆的社会宣教服务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1)一个博物馆的社会服务能力是要建立在自身现有的馆藏资源以及资源所带来的展览之上的,这也是博物馆进行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最重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很多中小型博物馆的展览方式太过简单,形式也非常单一,不管是在展览厅设计、馆藏品陈列还是总体呈现的视觉效果上,吸引力都不足,缺乏动态演示,也缺少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因此,许多人不愿意主动走进博物馆。
(2)博物馆进行藏品展览时最重要的环节其实是讲解,融合藏品讲解与视觉效果,能达到更好的体验效果。进入博物馆的参观者在年龄、学识等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但讲解员在进行讲解时的解说词却往往不变,讲解环节缺少普及性和针对性,观众在这个环境中处于被动的状态,对展品产生的兴趣自然会下降不少。
(3)对社会宣教服务起主导地位的是城市的社教部门,这些社会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将博物馆内的经典展品以展板的形式对外宣传。这样单纯的图片展出不仅没有什么吸引力,还会引起观众反感。由于展览厅的面积受到限制,开展的活动吸引力不足,举办活动时主要的受众群体是青少年和儿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型博物馆的发展。
四、提升中小型博物馆宣教服务品质的建议
(一)优化展览陈列方法,提高服务品质
将藏品进行陈列并展览是博物馆实现社会宣教功能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博物馆与社会大众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更是博物馆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博物馆在进行藏品陈列的时候,在观赏程度上要多下功夫,如此才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博物馆进行陈列与展览不只是对常规文物进行的组合排列,而是一种艺术性的创作,因此,设计师在进行陈列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突出活动中心主题或思想,使观众在参观之后可以了解活动本身的意义。不论是展览的独立性还是群体性,都要对其加以联系和沟通,使整个展览活动流动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线。
文物研究是让文物生动起来的根基,因此需要在对文物进行保护的基础上加强对文物的合理研究,才能够探索更多的历史文化,让文物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在进行文物的展览时,可以适当地运用一些互联网技术,打造数字化博物馆,促进历史文化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用数字化技术填补文物陈列的空白,更加丰富了展览的形式,也加强了整个活动的流动感,如果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就能带给观众更多元化、更丰富的动态性文物展示。
(二)创新讲解方式,增加藏品吸引力
讲解是博物馆展品与大众之间沟通的主要环节,在社会宣教服务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讲解是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是社会宣教服务最重要的环节。基于此,需要注重博物馆在讲解藏品方面艺术性的体现,要在讲解形式之上做出探索和思考,尽可能地丰富讲解的主要内容,找到观众与藏品之间的契合之处。因为博物馆的参观者在年龄、受教育水平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讲解内容要有一定的针对性,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编写不同的讲解内容。就比如,在为青少年儿童进行馆藏品讲解的时候,需要用一些比较通俗易懂、幽默生动的语言,在讲解的时候,要尽可能体现出趣味性,使儿童群体在参观的时候对文物有兴趣。在进行讲解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内容与实际的联系,多运用一些故事丰富藏品的介绍内容,增强藏品讲解内容和方法的感染力,吸引观众主动走进博物馆。这些方面都建立在对文物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只有加大文物研究的力度,探索更多有关文物本身的信息,才能够有效提高博物馆服务的质量水平。
(三)丰富宣教形式,营造特色品牌
博物馆进行社会宣教服务的主要形式总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博物馆展览厅中的宣教活动,另一种是流动性的博物馆宣教活动。不论是哪一种宣教方式,都需要對活动的内容进行探索与创新,根据博物馆自身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活动。实际上,采用互动式的宣教活动,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博物馆内部的文化空间,丰富观众的体验[2]。
外部的流动性宣教活动,可以进一步拓宽宣教服务的受众人群,打造“流动博物馆基层行”的外宣社会教育活动形式。打破固有的文化事业隔阂,可以加深博物馆之间的沟通合作、博物馆与群众之间的合作、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合作等方式。这样可以让博物馆的宣教功能更加贴合现实,接近人群。与此同时,对外宣教的形式也要进行变革和创新,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的形式实现多样化宣教,将藏品内涵赋予参观者,使馆藏文化走出博物馆,走向人群、走向街道、走向生活,以建立具有特色的博物馆服务体系,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五、结语
人们现阶段在物质文化上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博物馆作为精神文明的载体,也逐渐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针对博物馆宣教活动的不足之处,本文进行了分析与讨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即从文物的展览、讲解、研究等方面去提高宣教活动的质量,丰富宣教的形式,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文化服务。
作者简介
张欣,1977年5月生,女,汉族,山东潍坊人,本科,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博。
参考文献
[1]单霁翔.解读博物馆陈列展的思想性与观赏性[J].南方文物,2013(3):1-8.
[2]单霁翔.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质量的思考[J].敦煌研究,2013(6):1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