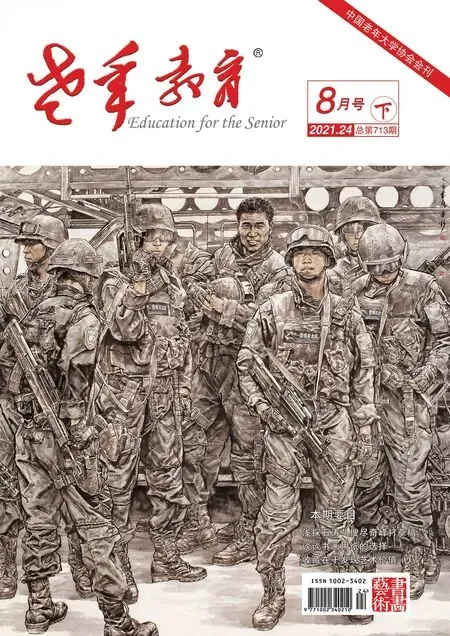印从书出 知行合一
——我的篆刻艺术创作思考
□ 李立山
学术研究,是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发现新角度,找到合适的角度和方式。我的篆刻艺术创作主要从以下三点展开:一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定位;二是关于篆刻研究的路径;三是关于书法研究的路径。这些研究路径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开始。

《吾日三省吾身》李立山

《德不孤 必有邻》李立山
第一,关于研究方法的定位。老子《道德经》中讲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要重视艺术发展规律。一件优秀艺术作品的问世,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如何从“入古”走向“出古”,也即怎样从仿古阶段更进一层,写出自己的感觉。“入古”,主要通过“临摹”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临摹”能力的培养。“准确临摹”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准确的“观察能力”;二是准确的“毛笔调控能力”,对应篆刻研究就是“刀感的寻找”。前者要求眼睛“看”得准,后者要求手中的毛笔(刻刀)能将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准确地呈现出来。在这里,眼睛的“看”起着决定性作用。只要观察判断准确,手上的呈现技术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就能逐渐达到准确。
第二,关于篆刻研究的路径。这主要是在“印宗秦汉”印学思想指引下,对古玺、汉印的实践探索;在“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印学思想的指引下,对明清流派印进行梳理探究,进而完成篆刻艺术创作在刀法、字法、章法上的整体储备。在篆刻艺术创作的研究学习中,找寻自己篆刻、书法以及古文字研究的努力方向。阅读中国印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是篆刻艺术理论生成的大致路线图。选中这些书籍作为研读对象,是因为学术视野的开创性。这些书籍涉及古代印论、书论、文字学等专著,如吾丘衍《学古编》、周亮工《印人传》、包世臣《艺舟双楫》、孙过庭《书谱序》、沙孟海《印学史》、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曹锦炎《古玺通论》、陈振濂《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

《仁者乐山》李立山
通过反复研读这些书籍,我发现了内在全新的观察和描述方式。重读经典,让我感到很多学术研究的整体图景还尚未展开,这些经典书目的深入研究还需时日。这种将印史、印论、印谱、篆刻美学、书论、碑帖经典释读、论文写作指导等类别进行横向和纵向分析的理论构架,共同构成了研究篆刻艺术的理论体系;形成将篆刻临创、篆刻艺术形式构成、篆刻艺术日常应用研讨、五种书体临创、古文字与篆刻等课程进行设置的篆刻艺术实践体系。
第三,关于书法研究的路径。首先,篆隶师法金文、汉隶经典,诸如《毛公鼎》《张迁碑》《石门颂》等;行草书则师法魏晋,诸如《二王手札》《圣教序》《宋四家》等。研究古今经典要成为经典的思维,学习这种思维方法,非简单模仿某个面貌。在书法的临摹过程中,要注意“形”与“神”、“笔到”与“心到”的结合;强调临摹不仅要位置准确、笔法到位,还要知疾涩、知节奏、知轻重。帖学的临摹学习要注意点画两端的表现,如提按顿挫、方圆藏露、起承转折、回环往复等,只有这样才能临出法帖本身精致的韵味。

《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李立山
其次,谈及书法创作。必须从集古字开始找寻自我,不断地置换匹配经典字法的空间造型和章法的区域造型。比如篆、隶书临摹和创作转换,强调空白与线质的重要性。通过对黄宾虹和吴昌硕篆书的比较,我以不同的临摹去感受不同的创作动机,在研究过程中去感受“笔软则奇怪生焉”的用笔状态,丰富和扩展了对书法研究的想象力,同时还注意剖析古今艺术经典作品背后的人文与艺术价值。在书法创作时,关于行草书的造型问题,我对点画、结体、组、块、行、区域、墨色、空白等的造型逐次展开训练;从书法的用笔、点画、结体、墨色、章法等环节中反复运用对比、组合、空间造型等,使其形势合一、情感与形式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既有观念的引导下去认识事物或者从事一项活动,篆刻、书法的研究也不例外。通过对经典佳作、理论文献的品读实践,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篆刻、书法的丰富知识,不断提高感知能力。但在真正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许多具备艺术敏感的人善于捕捉这种细微的瞬间,从这里出发,开始自己新的思考和实践,而这也是艺术研究者最有价值的一点。其中的某些思考实践慢慢发展起来,变成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后来慢慢集合成一条传承有绪、互相关联的艺术形式,这就是艺术风格的基础。再后来,一种艺术流派由此产生。我们对于艺术实践的探索,也由此获得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