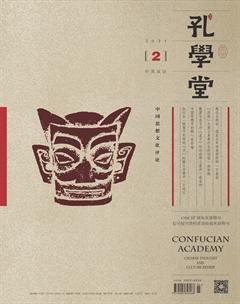戴震与朱子对《孟子》性论诠释之差异
摘要:清朝戴震对南宋朱子之非议,大抵是汉学与宋学争议之延续。朱子反对汉学之流于文字训诂,将与生命疏远,于是依二程而建构了一套理学,虽仍以儒家为宗主,但为了糅合时代学风,业已些微杂有佛、老。后起之戴震,则改以汉学为根据,回头批评宋学特别是以程朱为主之宋学。戴震写了《孟子字义疏证》,内容虽不全谈孟子,但其宗旨认为:欲辨经学之真伪,必从孟子起!本文即以《孟子》之性论为依据,比较宋学之程朱与清朝朴学之代表戴震,借由二人之性论诠释,而以孔、孟为准,看谁较能合于孔、孟?亦由此一窥宋学与汉学各自之思想大义,及其对于时代之关注所在。盖孟子论心性甚多,除了主张性善说之外,亦依此批评告子之性无善无不善说,颇具深意。性论之研究,可谓中国哲学之主轴,不过一直难有定论。本文将探讨性论之历史发展,并试图厘清汉学、宋学二派之争议。
关键词:孟子 朱子 戴震 性即理 血气心知 气质之性
作者蔡家和,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 台中 40704)。
一、前言 [见英文版第31页,下同]
朱子可谓宋学之集大成者,其依二程之理学思想而发扬光大,初始对于汉学亦是不满的!如于《大学章句序》提道:“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这里的“自是以来”,指的是从孟子之后。
朱子的道统观视孟子之后,唯二程能够绍继,而其间(孟子之后至二程之前)的主流学说,大致上特点有二,亦是朱子所批评的:(1)佛、老二家之虚无寂灭教说;(2)专务章句训诂之俗儒,亦指经学之儒,此指汉儒之注经,徒务章句之诵读,而不知更深层且直指生命的学问。
朱子对于汉儒之不满,亦显示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其所收集的注解虽亦包含了汉儒之说,但大致仍以宋代道南派为主,即程子弟子之传承,而朱子编有《论孟精义》,诠释上亦多宗于宋儒,即程子一系。之后,朱学盛行,历宋、元、明、清不衰,或多或少皆占有一席之地,影响所及遍于东北亚、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而在中国,如朱子的《论语集注》既兴,而汉学何晏所编的《论语集解》即废,官学、科举考试等亦以朱子注书为依据。
不过,到了明、清以后,朱学之影响力有了变化。先是明朝中叶,阳明学派兴起,其一主旨便是反对朱子学,欲与朱学一争正统,不过大致上,仍不出宋儒之视角,其采朱学之形式义而不采内容义,争辩于心即理或不即理的问题。到了清代,戴震可谓反朱之巨子,就连朱子之形式义亦不取,不信朱子的“性即理”之说,而改依《礼记》,定义“性”只是血气心知。
清代学风之兴,有回到朴学、古学、实学的趋势,亦被称为汉学,概以汉学为宗,而反对朱学,或以朱学为主的宋学。其视宋学已杂有佛老,虽可谓性命之学,却离先秦古义甚远。方法学上,朱子主张“以义理领导训诂”,不过,戴震则以先秦字义为准则,如其《孟子字义疏证》之作。
《孟子字义疏证》为戴震之重要作品,由此作,亦可看出汉学与宋学两种治学宗旨之大相径庭,汉学可称为相偶论,宋学则为体用论,如此不同观点,亦同时显现于其他“四书”“五经”之诠释上。
由于系统庞大,本文即聚焦于《孟子》之论性一处,借此比较二派对于孟子之性善说有何不同诠释?最后再做一总结,以孔孟为准,检视二派说法有何特点?谁较能接近孔孟之说?
二、戴震与朱子之性论 [32]
(一)戴震:性是血气心知 [32]
关于“性”字之诠释,学界向来分歧,许是因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如《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两派对此诠释即不同。朱子解曰:天之所命令者,在人而为仁、义、礼、智之性,性即理也!而戴震认为:万物分于道而为运命,人道即不同于物道,人性与物性即不相同。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将“性”解为血气心知: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气化曰阴阳、曰五行,而阴阳五行之成化也,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凡分形气于父母,即为分于阴阳五行,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谓性。”以生而限于天,故曰天命。《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然性虽不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故《论语》曰“性相近也”,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言同类之相似,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故诘告子“生之谓性”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天道,阴阳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
这里,戴震举《大戴礼记》语而来证明:性乃血气心知!《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天道之阴阳五行,即为命!借此诠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属《小戴礼记》,而与《大戴礼记》相近。
依于此说,则“天命之谓性”的“命”字,有其分道,则所受者亦有所限,人有德性,而物则无。然反观之,人亦有不及于物者,如人的眼力、嗅觉不及于鹰、犬等,以分于道而有所限之故。故此“命”义乃指命限,有所禀、运气上的不同。至于“形于一,谓之性”一句,意思是,个体成形即有其性,某甲有甲之人性,而牛则有牛之物性。
此说的重点,乃“性”一字,有分类上的不同,如人性这一类,与牛性这一类,两类不同。这里的类概念,不只是生物学上的区别,更是存有论与德性论上的;人之存在属类,不会同于牛一般,而人之食色,亦不同于牛之食色,人是道德之存有,而牛则不是。
孟子亦曾有类概念之说,其曰: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告子上》)
同类则为相似,不同类则不相似,如某甲与某乙同类,则为相似,唯孔子虽属人类,却能成为圣贤,能够出于其类而拔乎其萃!一般来说,如果不知对方的脚有多大(需穿多大的鞋),只要依于同类之概念而来推测或制作,大致也就不会相差太多了。又如人之口味、味觉,彼此之间,便较犬、马等之口味更接近,马食刍草,人却不然。同类之人性较为相近,食色亦相近,道德性也相似。在戴震而言,食色亦是性,属于血气之性。
至于心知之性,戴震认为:
孟子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当于理义,其心气必畅然自得,悖于理义,心气必沮丧自失,以此见心之于理义,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义。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
这里明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非喻言也”(《孟子·告子上》),指理义悦心与刍豢悦口之间,并非比喻的关系,而是指两者都属于人性。部分学者因“犹”字,联想到“性犹湍水”云云,认为此自为比喻无误,然理义悦心与刍豢悦口之间却非比喻,例如“牛之性犹人之性”一句中的“犹”字,即等同的意思。
心知即如君官,心官能思、能知,能依于物之则、人道、义理等而来导正;人道,即是义之道,心官悦于义理、人道,如同依于光之照明,而能中理不谬;心官依其本性,而能悦于仁义之道!
此处所引之文,尚有一个重点,即对于孟子“天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之正解,戴震的说法是:“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参看《孟子》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关于这段话,汉、宋学二派解法不同。汉学家方面,视天下之性乃千古如是,人类、犬类、牛类等各类之性、血气心知等,从古至今,不曾稍改。而宋学家中,朱子所解之“故”,谓依其旧理、故理,此为“性即理”;牛之理千古以来不曾稍改,人之理亦然。
朱子视性即理,而戴震则以性为血气心知,这似乎是孟子性论诠释中的理、气之争。要注意的是,戴震此中的血气心知并非属于形下层次;形上与形下二者,需要两两对立才能成立,若无气化之外或气化之内的区别,又何来形上与形下之切割?戴震的血气心知,并非如朱子所定义的形下之气,而是即于形下形上、无分气化内或外之气。形上与形下在戴氏而言也只是成形前与成形后之说不同,不可以朱子的形上形下之说用在戴震身上。
(二)朱子:性即理 [34]
朱子所主张的“性即理”之说,传承自伊川,而戴震则提出質疑,问如下:
问:《论语》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别之,以为截然各言一性。(朱子于《论语》引程子云,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反取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为合于孔子。
这里质问:依于程朱,则《孟子》之性善论,与《论语》“性相近”说,两者所说之“性”竟不同?不过,程朱的气质之性(张载亦如此发明)与天地之性,其实是同一个性。所谓的气质之性,只是本然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之中,以至于所表现出的本然之性,有多寡程度上的不同,即使在动物上,天理、天性亦同,亦为性善,只是动物气质浊劣,只得表现其偏,如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等,证明动物亦具有性善、道德性之部分。而戴震则不如此认为。
那么,戴震为何要说,若依程朱,则《论语》的“性相近”与《孟子》的性善论,将为二性?这可参看《论语集注》中,朱子对“性相近”的诠释,曰: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程朱诠释孟子之性善论,定义为:性即理,故无有不善。不过,程朱以为,《孟子》一书中所言之“性”,却是要随文看,即有时是指天理之性,有时却是气质之性。若言性善,只能是天性、天理,人、物皆同,又怎可言“相近”?若言“相近”,只能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亦是源自本然之性,但因所秉、客观环境不同,致使气质有美、恶之分,有时甚至相距亦远。
程朱认为,《论语》既言“性相近”,那么也就只能是气质之性;而在其他著作中,也提到告子之说亦是气质之性,这便让戴震怀疑,若依程朱,则反而告子合于孔子,而孟子不合孔子。在戴震“反取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为合于孔子”一语下有小注云:
程子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止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
此戴震抄自伊川之言,用以证明程朱之论,似乎以告子合于孔子,而孟子反远于孔子?那么,朱子对于告子的“生之谓性”,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其曰: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
前面戴震共引伊川的两段话。第一段,“性相近”云云,与“生之谓性”之说,皆指所禀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乃本然之性堕于气质之中而来,遂有善恶、美丑之判,而本然之性亦常为气质之性所掩,致其表现不出本然之性善。
而这里,朱子主张孟子所论之性,乃纯粹之天地之性,性即理也;而告子则不知以性为理,而以气当之,此只是形下之气,不比本然性善的仁义礼智的形上之理;而形下之气所杂的气质之性,主要以知觉运动为主,乃指人之食、色等动物性。
戴震依此朱子义理,而与伊川的气质之性比配,认为若依程朱之说,则反而导致告子能同于孔子,而孟子反不能同于孔子的结果,因为告子与孔子所论之性都是气质之性。
三、程朱对孟子之翻案 [35]
(一)二程论性已不同孟子 [35]
程朱理学揭橥“性即理”说,亦称为理气论,性即天理,而天理无所不善,则关于“恶”的出口,便只能推向另一边的“气质之性”。这应该就是程朱创立“气质之性”的原因,于是形成了二分之性的格局。再者,也正因性之二分,程朱可把历来诸如告子、荀子、扬雄、释氏、胡氏(五峰父子)等人说法,都判定为“误把气质之性认作天地之性”一类,这类人以气当理、认气为性,于是有性善恶混、性可善可不善、性空等说,是则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矣!
程朱学派认为,因着理气之二分,儒家便得以归纳历来关于性论之学派,以便杜荀、扬等辈之口,战国时期的孟子无法做到,如今程朱却办到了,则历史争论至于程朱,或许可以稍歇!不过,戴震却不以为然,评曰:
创立名目曰“气质之性”,而以理当孟子所谓善者为生物之本,(程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耳,故不同,继之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人与禽兽得之也同,(程子所谓“不害为一”,朱子于《中庸》“天命之谓性”释之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而致疑于孟子,(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久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恐孟子见得人性同处,自是分晓直截,却于这些子未甚察。”)是谓性即理,于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于《易》《论语》固宜,孟子闻告子言“生之谓性”,则致诘之,程朱之说,不几助告子而议孟子欤?
这里引了伊川之说。伊川认为,一来,孟子书中的“性”,须要随文看,有时指本然之性,有时指气质之性,二性并存,一是先天本然之性,二是后天落在气质中的性。二来,告子的“生之谓性”,并非全错。告子的“生之谓性”也是性,只不过是指受生之后的性,也就是气质之性,不同于孟子所強调的本然之性。只要区分出《孟子》书中的两种性,则孟、告争议即可平息。而伊川的这些想法,其兄明道早已言及。明道言: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
明道以为,人生而静之上不容说者,乃本然之性;可说者,即是气质之性,这也可比配于告子的“生之谓性”。此气质之性,性即于气,气即于性,原来只是本然之性落于气中者,如此一来,则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本性虽善,但因落于恶的气质之中,也就表现不出其本善。前面伊川的话,便是对其兄明道思想之阐发,而明道此段,大致也可用伊川“气质之性”的理念来做诠释。
伊川又说,犬之性、人之性、牛之性,虽在显现上不同,但不害其本性为一。这样的说法,其实已经翻了孟子的案了。如《孟子》原文:“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意思是,此三性并不同,犬性亦不同于牛性,虽都是动物,但本性不同。
而伊川却说“不害其为一”,此所谓“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天下海、湖之月影稍异,然本源为同一之月、同一之天理,天理即性,万物皆同具本然之性,而性即理也。万物虽同具一个性理,但因人、牛、犬等所禀气质不同,所表现出的本性之程度也就不同。人得其秀而最灵,人的气质中所表现出的本然之性较多;动物则较少,亦有些微道德性之表现,如羔羊跪乳、蜂蚁有君臣之义等。这些论调已与孟子不同,当是一种创造性之诠释,或可用以解决历来各家论性之争议,如荀、扬等人之说。
(二)朱子对二程之承继 [36]
程子尝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而朱子继之而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论性不论气者,指孟子,而论气不论性者,指荀、扬。亦是说,性论之所以历来纷歧,无法定于一尊,乃因各家所言之性不一,孟子所言,乃终极的天地之性,而荀、扬则是以气为性。直到程子,才算真正解决各家之纷争,而得以杜绝荀、扬之口。
然如船山质疑程朱此说,曰:“程子固以孟子言性未及气禀为不备矣,是孟子之终不言气禀可知已。”船山意思是:若以孟子性论有所不备,则知孟子终究未曾言及气禀呀!
不过,朱子于《孟子集注》中,仍是以气禀之说来做诠释。如《孟子·告子上》“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一段,关于“命”者,概有所禀与所值,禀其气清,则行义也易。此所言“命”,亦同于“天命之谓性”一处,天命者,本然之性也,而此性亦在气中。
故朱子注“天命之谓性”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人、物各率其性,人率人性,马率马性,都是天理之生,而表现在气禀之中。朱子又言:“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要人修道、进德修业。这便是程朱的气禀义。
戴震于“人与禽兽得之也同”一句后面,又引朱子《中庸》“天命之谓性”之注,即朱子所注,业已视人、物之间是本根、同性,故不害其为一,即人性、物性源于同一性。
朱子这些说法,亦曾在韩国儒学界引发著名的“湖洛论争”,主要争辩人、物性之同或异?依于朱子,人、物性是为同一性,所谓“不害其为一”者,皆源于同一个天理;不过,朱子亦说人、物性分殊,此因后天所禀气质不同,致使所表现出的“理一”多寡有别。而即便是动物,亦有健顺五常之德,只是气禀较偏,只能微性(道德性)之表现,不若人之周全,然人、物性却是本源同一的!
四、性中有无食色? [37]
(一)戴震:性中有食色 [37]
依朱子“气质之性”说,性善为本然之性,性中没有食色,食色者,气质之性也。朱子注“告子曰:食色性也”处言:“告子以人之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若再加上伊川之语,则可知“食色性也”亦是“生之谓性”之性,亦同于《论语》的“性相近”,皆属气禀之性。总之,在“性即理”中,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没有孝悌,更没有食色。
然戴震有不同看法,他主张“唯有血气心知之一性”,合于血气与心知而为一性,是为“一本说”。性中自有血气、嗜欲、食色……如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又如上文提到,戴震认为“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云云,此非比喻之说,而是指即便是“刍豢之悦我口”,亦是性!
此如韩国儒学古学派之代表人物丁茶山所言“性是嗜欲”,以为所谓的“动心忍性”,其中的性何以要忍?以性即是欲故,当须用忍,不容私欲之任意勃发。孟子也有“可欲之谓善”的说法,这也近于戴震的“性中有食色”。
再来参看戴震以下之诠释:
问: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张子云:“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云:“仁义礼智,天道在人,则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之命。”宋儒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本于《孟子》此章,以气质之性君子不谓之性,故专取义理之性,岂性之名君子得以意取舍欤?
曰:非也,性者,有于己者也,命者,听于限制也,谓性犹云借口于性耳,君子不借口于性之自然以求遂其欲,不借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后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
这里,问者因张子“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之言,视张子亦只说天地之性,而不谈气质,于是将张子等同于程朱,皆以天地之性为本性,而排除了气质。
然而,张子亦言:“性其总,合两也。”合于天地之性与声色之性。又曰:“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而张子对于《孟子·告子上》“口之于味”章的诠释,也颇为地道,其言:“养则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人。”此甚得孟子之旨。
(二)唐君毅:以道德引导食色 [38]
关于戴震上述说法,可以参看唐君毅先生之评论,其言:
清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以《礼记》之血气心知之性释孟子,谓声色臭味之欲,根于血气,仁义礼智为心知,并皆为性,乃以借口释谓字,说孟子立言之旨,非不谓声色臭味之欲为性,而只言人不当借口于性以逞其欲,此亦明反于孟子之“不谓性”之明言,亦与孟子他处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处处即心言性,不即声色臭味之欲言性之旨相违。
看来,唐先生并不苟同戴震之说法,认为其说将有违于孟子之旨。不过,唐先生也不赞成朱子之解法,如言:
朱子承程子之言,于上一命字,以品节限制释之,而于下一命字,则曰谓仁义礼智之性,所禀有厚薄清浊,故曰命,此又以人之天生之气质之性之差别为命,对同一章之命字,先后异训,即自不一致。朱子尝谓气质之说,起于张、程,又何能谓孟子已有此说?
同一“命”字,于同一章内,却有前后不同意思,如此说法,显得牵强。再者,由既有文献来看,可以说“气质之性”一语,起于张子、程子,又怎能牵扯上孟子早有气质之说呢?对此,唐先生亦是颇不以为然的。
唐先生倾向于一种做法——撷取各家之长,或凡合于孔孟之旨者,便来导出他所认为合宜之诠释。从侧重的角度来看,唐先生亦是将血气之性与道德之性合而为一,再以道德之性而来引导食色之性,这种方式最终还是与戴震一致。只不过戴震是先将二性合一而论,先总说一性;唐先生则是先分解为二性,而后再将二性合一。
若回到《孟子》原文,心官则思,应当从其大体,继以大体引领小体,以德性引导食色,孟子本义如此,戴震亦不敢违背。戴震“君子不谓性”之诠说,应是指:君子不会借口食色亦是天性,而随意放纵,在命之不可得时,亦能随遇而安。
五、物性之辨 [39]
(一)人性、物性之辨 [39]
依朱子的“性即理”说,人性、物性本源同一,彼此之不同,只在于禀气之殊异,人得其秀而最为灵气,性理之表现亦多,而动物却因气禀所限较多,仅能部分表现道德性。至于戴震则有不同见解,他认为,人是道德之存有,其心知可以知仁义,而悦于仁义,然动物则缺,以物之类种与人不同之故,并非道德之存有一类,无法表现仁义。
此外,戴震所定义的性,将随种类之不同而不同;人性与牛性不同,牛性与犬性也不同。关于后者的牛性、犬性之异,朱子则不强调,于是戴震批评朱子这点,其曰:
朱子释《孟子》有曰:“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如其说,孟子但举人、物诘之可矣,又何分牛之性、犬之性乎?犬与牛之异,非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不得谓孟子以仁义礼智诘告子明矣。在告子,既以知觉运动为性,使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告子何不可直应之曰“然”?斯以见知觉运动不可概人物,而目为蠢然同也。
这里举了朱子注《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章一段,表示人与物之同者,在于食、色等动物性,统称为知觉运动,人、物皆能知觉,皆能运动。不过,朱子此说,与孟子之说稍异;若依孟子,人、物虽都有动物性,都能知觉运动,但其中之内容毕竟有别,如孟子尝言:“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告子上》)此则显示人、马于性类上之殊途。且口味亦性也。
(二)物性之辨 [40]
上文引言,戴震更强调了物物亦别的概念,以物与物之间应是分属于不同类种,亦如《孟子》原文:“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若只是分辨人与物之不同,则孟子只要举例“牛之性”犹如“人之性”便罢,为何还多了一句“犬之性犹牛之性”?
戴震这里的言下之意,似乎在凸显,朱子之所诠无法契合于孟子原意;孟子所表达的,当是一种类概念,即不只人、牛不同,至于犬、牛亦不同。朱子只是大要地说:知觉运动之蠢然,人与物同,而仁义礼智之粹然,人与物异。孟子此章,只谈人、物之辨,而不提犬、牛之辨。
若回到《孟子》原文,则孟子亦看到牛性与犬性之间的殊异,此由犬能看门而牛能耕作之不同表现上看出,可见牛与犬并不同类,性亦不同。则朱子此章之诠,便显得不够周全。
戴震以为,若孟子只谈人、物之异,则只要说一句“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就好,“犬之性犹牛之性”云云,则为多余,但朱子似未认清物性之间亦有不同这点,其过失归根结底即在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性之分说,以及把“性”定义为天理、仁义礼智等说法有其弊病。
六、结语与反思 [40]
历来汉宋之争,宋儒之于汉学,总认定汉学仅是一种训诂之学,如朱子曰:“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不过,朱子自己对于汉儒文献之抄录与批判,则甚少下过工夫。既然缺乏论据,则朱子的批评也就难以服人。若是清儒,如戴震——做为汉学之一派,对于宋学程朱学派之批评,则用功甚多,他将宋儒作品逐条抄出,而后进行评判及论证,如此做法,说服力较高。
到了近代之“当代新儒家”,其立场则又倾向于宋学,同时也对汉学特别是清代汉学做出批评。个中翘楚,如唐君毅先生认为,戴震视“理”为分理、文理、肌理,只看到先秦于“理”之区分处,而不见其整全,只见于“理”之静态性,而不知其动态性。总之,将“理”视为文理、分理,并非先秦之唯一说法。
唐先生之相关批评,收于其著《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约20页之篇幅,其论述甚是有力。他举出戴震之缺失有三:
其一,孟子乃“即心言性”,如孟子言:“仁义礼智根于心。”不过,依笔者拙见,孟子除了“即心言性”之外,亦有“即生言性”,如告子提出“生之谓性”处,孟子不辩,而只辩其义外。
其二,《孟子》原文“口之于味”等等,“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唐先生认为在性中有命的,如口味,这得之不得有命,故在君子而言,不谓此为性。此处也是唐先生对戴震的反驳,因为他举出,孟子都视口味等,在君子不谓性了。然笔者认为,《孟子》原文也有提到“性也,有命焉”,但仍是性。而唐先生最后以道德之真性可包括口味之次味,则亦是融入戴震之说了。
其三,戴震谓,性乃血气心知,而能达情遂欲。唐先生则问,则由此血气心知,如何达到仁义?若是后者,当需自觉主宰,方能达办,此与达情遂欲,恐怕已是两层问题,而非戴震之一元气论所能解决。唐先生强调,这里要有一股精神之转折,方能由己情之达,而生同理心之自立立人、己达达人,自己若无其情,则不能知晓他人之情。这是发生顺序之义理,而非以性理来领导生理。
唐先生的第三点,可说非常有力。但若站在戴震立场,当須掌握达情遂欲之中相感相通之情,而将此情上看、高看即可。因戴震只是气论之一层、一元,其情将不同凡响、不能低看,总只有这一层,而须即情即理。乃一种依心知而能自觉,从一般之情,而为理想感通之情。
唐先生亦以为,朱子之论性,所谓“性即理”,乃是依于伊川之发明,而朱子之“心统性情”,则是来自张子,并于其性论之建构,区分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一连串的发展,难以溯及孔孟之说。若强以此套建构来诠释孔孟之性,则非孔孟原意。朱子的确需要回答戴震之质问,除了戴震之外,明清之际的许多学者,如阮元、焦循等,以及日本之江户学者伊藤仁斋等,都对程朱有所批评。
唐先生最后以“即心言性”来包括“即生言性”,同理,是否也可把朱子的“性即理”,用以收摄性即气之一面?另一方面,戴震的血气心知、情欲,是否亦能上提而收摄同理心?然无论如何,都不能违反大体摄小体的原则。这些做法,或许更能接近孟子原意。大致上,唐先生似有调和汉宋之意,视两派各有优缺点,而欲平彰汉宋,各美其美。笔者以为,唐先生之论证力道,足以抗衡汉学,而为新宋学之坚强学者,值得吾辈关注。
(责任编辑:陈 真 责任校对:刘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