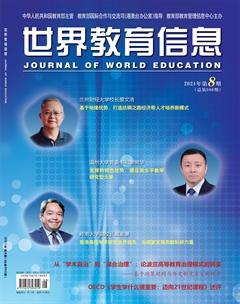从“学术自治”到“混合治理”:论波兰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转变
白鸽 吕云震 冯琨舒
摘 要:作为后共产主义的主要国家之一,波兰的高等教育在近30年经历了从学术自治向混合治理模式转变的发展轨迹。1989年以后,波兰高等教育总体上回归了“学术自治”的历史模式,并顶住了更强的市场化压力,甚至在“博洛尼亚进程”中也是如此。但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后,尤其受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波兰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中处于劣势等因素的影响,波兰的高等教育朝着一个新的混合治理模型发展。新的治理模式旨在重新定义大学的研究使命,促进本土研究和创新。这些新的混合治理模式使波兰能在应对要求变革的全球压力,摆脱对西方经济依赖的同时又不会完全抛弃历史制度。
关键词:波兰 高等教育治理 政策趋同 市场经济 “博洛尼亚进程”
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中欧和东欧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受内外部力量改变:学术专业的复兴、公立部门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引入[1]。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欧洲化和国际化已经渗透到现有治理体系和监管框架中。在改革和适应的整个过程中,后共产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不定。波兰作为后共产主义国家之一,高等教育系统在1989年之后开始朝着“学术自治”的历史模式进行改革,即使在“博洛尼亚进程”中,高等教育也普遍抵制要求更强市场化的压力[2]。本文以波兰过去近30年的公立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线索,分析后共产主义时代波兰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化,并重新对波兰高等教育政策进行评估。
一、后共产主义时代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与教育发展
后共产主义国家在21世纪初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并没有被重视,受重视的是那些直接受共同市场影响的领域(如消费者保护、贸易自由化等)[3]。伴随着后共产主义经济体融入欧洲共同市场,中东欧政治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1989年以后,后共产主义经济经历了重要的去工业化进程,使它们极其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许多在中东欧经营的大中型企业本质上是跨国企业的“东方前哨”(eastern outposts),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身处于跨国企业中各层级的底层位置。相反,中东欧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在于其基于密集低成本劳动力的“半标准化商品组装平台”功能,技术创新往往只从西方进口[4]。它们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迫使中东欧国家维持低税率,这不利于公立教育的发展。因此,一流的研发活动一般在西方进行,而中东欧国家在专利开发方面严重落后于西方国家[5]。可以看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过程强化了欧洲的经济等级,并将中东欧的政治经济转变为他们所定义的“依赖市场经济”[6]。加入欧盟以来,这种现状变得越来越明显,使得中东欧国家的决策者开始尝试利用教育作为杠杆,将自己从经济依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鉴于人们普遍认为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处于劣势,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调整现有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政策模式被视为后共产主义政策制定者进行改革的重要政策借鉴之一。
在过去近30年里,后共产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面临着与西方体系类似的问题,如财政短缺、缺乏透明度和国际竞争力等,还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后共产主义的高等教育机构首先试图将自己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恢复学术自治。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用新的国家监管形式来平衡机构自治,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学术无政府状态”[7]。决策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方面要确保迅速扩大的私营部门的质量和透明度,另一方面公立機构往往在严重的财政短缺中只顾自身生存。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国内需求主导了政策发展的方向,但“博洛尼亚进程”加大了政策制定者的压力,要求他们批判性地评估大学产出的有效性和质量,这对后共产主义国家现有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实际上,“博洛尼亚进程”是一种跨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旨在提高大学的全球竞争力、吸引力和效率。作为一种主要受英美等国家启发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工具”(policy tool),“博洛尼亚进程”得到了推广。此外,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21世纪前10年扮演了更为核心的角色,一直主张大学自治、企业治理的方式以及与商业更紧密的协同作用。与此同时,跨国高等教育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比较”和排名文化,从而使各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本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8]
在这种背景下,政策趋同成为可能。政策趋同一般被理解为“由于经济和体制的相互联系,社会趋向于变得更加相似,在结构、过程和绩效方面表现出相似性”[9]。从理论上讲,社会经济转型、跨国竞争和资金不足导致的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压力,会促使决策者效仿外界认为成功的政策模式。根据“政策同构”理论,组织努力通过模仿来维护其合法性,而不是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自己的解决方案。当组织面临不确定性和模糊目标的困扰时,“同构”便很有可能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后共产主义国家极容易受到同构效应的影响,因为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扩张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新技术的出现、人才流失的现实以及国际竞争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然而,制度同构和政策趋同理论往往忽视了内在的历史制度和预先存在的政策路径。历史制度主义从另一视角出发,有助于解释各国独特的改革轨迹。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面对各自的文化、需求、实践和制度框架,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会新陈代谢、转化和重塑全球趋势[10]。欧洲大学原有的功能逻辑使得它们高度抗拒变革,因为外部模式和做法可能会对国家机构和信仰构成挑战。因此,出于维护现有制度和政策方面的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的目的,欧洲大学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任何政策改变的努力。中东欧的历史制度源自前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期。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会从历史模型中获得灵感和合法性,如洪堡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主义。中东欧国家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典型指导原则是在共产主义失常之后恢复“历史的连续性”。学者们经常将战前基于洪堡自由思想(如波兰、捷克共和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与那些倾向于法国或拿破仑式(如罗马尼亚、俄罗斯)的更强的国家协调高等教育概念的系统区分开[11]。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之后社会的根本变革和重组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学会自动地重新接纳已有结构,或与外部模式保持同构。消除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结构和规范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综上,共产主义制度可能会继续影响高等教育系统,并与现代高等教育政策相融合。
接下来,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和分析并以波兰为分析案例,一方面对波兰高等教育治理的发展路径进行梳理,另一方面探讨波兰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在近30年里发生的变化。
二、波兰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与治理模式
学术界一般将高等教育治理分为三大类: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学术自治模式和“市场化”治理模式。尽管所有的高等教育系统都或多或少地结合了每种理想模式的不同组成部分,但是在分析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路径时,仍需明确该国历史或当前的高等教育系统倾向于哪一种治理模式。接下来,本文将对欧盟最大的新成员国之一——波兰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进行探析。此前的研究显示,波兰在很大程度上希望恢复学术自治的教育传统。而政治、经济的转型和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正将波兰的治理模式推向多个方向。这导致了一种新的混合治理模式的产生,它战略性地结合了上述三种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以提高国家的研究和发展能力。
(一)波兰高等教育发展轨迹
位于克拉科夫的亚吉隆尼亚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是繼布拉格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之后历史第二悠久的中东欧大学,有着悠久的科学研究传统。在波兰—立陶宛联盟时期建立的其他几所大学,如波兰大学,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然而,波兰的分裂从根本上打破了波兰高等教育系统的格局。波兰华沙大学受俄罗斯控制,而大学的法学院被纳入普鲁士。克拉科夫学院是15世纪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堡垒,在1846年并入奥地利帝国之前,它最初是自由城市克拉科夫的一个波兰机构。20世纪初波兰领土重建之后,波兰大学恢复了洪堡学派的学术自由和非功利主义研究制度。然而,在华沙起义后,纳粹侵略者蓄意消除波兰语教育,拆毁了大部分大学建筑,杀害了数十名波兰学者。在苏联的占领下,许多波兰知识分子在大屠杀中遇害。苏联的统治使波兰大学变成了灌输思想和政治镇压的工具。但洪堡模式部分保留下来,因为波兰学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也部分接受了西方的模式。[12]
1989年之后,波兰民众强烈认为高等教育应回归历史逻辑,致使学术自治几乎在一夜之间得到恢复。波兰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于1990年正式颁布,有力地加强了大学的自主权。它还将决策权下放给学院和教授,这削弱了大学管理和国家的监管。波兰还利用战前学术自治的传统,高级学者通过学术参议院管理大学事务,国家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无法进行任何干预[13]。然而,由于波兰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加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严重限制了公立大学实现洪堡主义不受约束的学术研究愿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波兰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还不到GDP的1%,远低于欧洲其他大多数高等教育系统。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人口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中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开始开放市场并允许私有化的介入。
那么波兰公立机构环境的变化是否促进了高等教育治理向“市场化”模式的趋同?有证据表明,波兰的传统学术自治战胜了市场化的压力,因为大多数学术自治模式在公立教育体系中得到了维护。这尤其适用于资金问题,它是根据科学学位学生和教师的加权人数组成的分项公式分配的。国家也立法禁止收取全日制学生学费,但公立机构被授权向非传统学生收取学费,主要是在职学生或通过入学考试但排名相对较低的学生①。在职项目的扩大导致对商业和经济等领域的关注日益增加,削弱了大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一流研究的能力。[14]
尽管波兰学术界内部四分五裂,但他们却一致捍卫集体利益,保护自己不受国家干预。例如,波兰高等教育总理事会是一个新的学术主导的咨询机构,可以使学术界保持对决策的严格控制。为了进一步维护他们的集体利益,波兰校长们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建立了波兰学术学校校长委员会。虽然这两个机构没有正式的否决权,但它们迫使政府对高校的运作非常谨慎。然而,许多教授因不满足于低工资,积极扩大了在私营部门的业务,如在完成公立学校的日间教学任务后,他们还在私立学校开展夜间讲座。上述的这种变化对公立大学的研究能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结构上看,大多数公立大学恢复了战前以洪堡主义为基础的管制模式。然而,沉重的教学负担,加上长期的资金不足,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洪堡式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换句话说,波兰公立大学取消了其洪堡式的“骨架”,即行政结构,却没有恢复其洪堡式的“精神”,即一流基础研究的能力。
到了21世纪,内部管理结构仍然处于权力分散的状态,而大学的整体管理仍然缺乏制定战略目标和引入绩效标准的能力。由于没有采用与成绩有关的标准,波兰的高等教育支出依然由国家平均分配给各个学校,不考虑大学产出。换句话说,公立机构仍然植根于学术自治范式。“博洛尼亚进程”在波兰引发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自治向问责制的转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波兰于2001年成立国家认证委员会(State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起到了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的作用。[15]
(二)波兰高等教育治理的新发展方向
到了2010年,随着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新的经济依赖,再次加大了波兰政策制定者进行改革的压力[16]。尽管不确定性是同构现象的主要驱动力,但波兰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更解放的同构现象,这导致了一种重新调整的治理模式,其目标是通过加大对大学研究的投入,增强经济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在后共产主义阶段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进程。向市场经济过渡和恢复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服务业的扩大和西方工业基础设施的转让带来的。这使波兰看起来像是更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组装工厂[17]。因此,波兰必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克服“技术滞后”(technology lag)的现状。再加上波兰大学在国际大学排名上的糟糕成绩,所有这些长期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促成了更广泛的社会认知,即波兰过度依赖外国创新和资本[18]。这些综合因素促使波兰采取新的措施,使自己与西方的高等教育政策保持一致。
在以竞争和人力资本形成为核心、以提高经济独立性为目的的驱动下,2011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公立高等教育体系朝着上述三种治理模式发展。首先,该法律寻求更好地将波兰公立大学与洪堡大学愿景的初衷——卓越的研究——结合起来。国家重视大学研究职能的努力特别反映在资助计划中。虽然大部分资金仍然来自公共预算和非传统学生的学费,但2011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显著增加了基于成绩的资助。基于对科学产出指标的量化,政府现将额外的资金拨给25个被指定为“国家科学前沿中心”的顶尖学院。此外,2011年波兰建立国家科学中心,在11种资助计划的基础上支持波兰的基础研究。这些资助计划的目标是培养与支持有抱负和有名望的研究人员。加强大学研究任务的另一项努力是钻石奖励制度,它奖励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进行研究,并为更快获得博士学位开辟了道路。[19]
然而,將这种发展仅仅描述为波兰大学的“再洪堡化”是轻率的。事实上,在波兰同时存在着一种实质性的去洪堡化。例如,在与美国科学院、总理事会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协商后,波兰制定了国家研究计划,确定了优先研究领域。国家研究计划所期望达成的目标不仅仅是促进具有高认知价值的研究,还包括促进具有高社会、经济和技术用途的研究。国家科学中心的任务是管理涉及大学研究人员的、与基础研究有关的项目,而国家研究和发展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则负责应用研究。国家研究和发展中心涉及的领域有能源相关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防,以及与波兰在全球化市场中的地位相关的社会科学项目等。[20]
改革还强化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在高校中的地位与影响。例如,在21世纪初,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已经在推动将雇主代表纳入课程设计的现代化大学管理系统。然而,2011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规定,利益相关者必须加入大学管理和咨询机构,如总理事会,同时还要求为大学毕业生建立专业的职业跟踪系统。与法国的类似尝试一样,政府正在创建由国家社会保障办公室提供的关于学生就业历史的信息组成的数据库。
新成立的国家认证委员会(State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也进一步反映出政府在推动大学与劳动力市场相互联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2011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规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最低参与度为10%,从而对学习项目产生影响。此外,认证机制发生转变,这意味着在重新评估与认证过程中,将重点放在具体的机构绩效和产出上。与英国的研究评估工作类似,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地接受基于出版物、专利以及授予学位的评估方式。因此,在波兰高等教育中出现的“评估状态”进一步将洪堡主义下的基础研究制度化,并进一步促进了更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研究[21]。在人事方面,国家也开始削减学术专业的一些特权。2011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允许大学暂时聘用学术教师,并对他们进行绩效评估,一般每两年进行一次。这适用于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或博士后研究员。这些修改为大学根据其自身的发展和规章制度来决定学术人员的去留创造了法律基础。事实上,该法律规定每四年对拥有“教授”头衔的人进行评估。重要的是,2011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赋予大学校长拒绝学术人员与多个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权力。
总的来说,波兰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反映了一种同构转变(主要是趋同于德国和法国的政策),包括建立扩大国家评估机构和个人研究人员的机制,将资源集中到被认为优秀的机构,以及高校的纵向分化。然而,这些改革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是模仿,而是波兰为了提高经济和地缘政治生存能力的路径尝试,是把自己从经济过度依赖中解放出来而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这些转变的指导思想是“波兰应该创新,而不是模仿”,大学必须成为经济创新的堡垒,以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增长。[22]
洪堡式的“大学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专门为学术专业服务”的观念已经逐渐被“大学是服务提供者,服务于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的观念所取代。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和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措施,新采用的以产出为基础的筹资机制加强了机构对国家研究基金的竞争,并促使个别机构对其发展战略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波兰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式的学术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更强调经济效用。
三、结语
波兰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为重新评估全球化、欧洲化和经济快速变化时代的政策趋同现象提供了一个特别的研究案例与视角。尽管波兰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震荡期和自由化阶段。但事实证明,波兰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相对不受市场化加强的压力影响。相反,学术界迅速进行了重组,恢复了共产主义之前洪堡式的“骨架”,即基本符合学术自治的结构框架,却没有强大的科研能力。波兰政府采取了更为克制的立场,将市场机制小心翼翼地注入学术中心。
图1简要概述了第一阶段(1990—2005年)和最近一阶段(2005年至今)波兰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轨迹。在波兰,第一阶段基本上与洪堡模式一致,而现在国家在混合模式中加入更多的“市场”,并对大学的研究任务进行制度化。[23]
在第一阶段,波兰没有明显偏离20世纪90年代在“博洛尼亚进程”中选择的政策框架。然而,该模式无法将学术产出和科学生产转化为基于国内人力和工业资本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因此,其加入欧盟后,新的经济等级制度得到加强,再加上中东欧大学在国际排名上的疲弱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向混合模式的趋同。简单而言,在波兰的教育系统中可以观察到“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洪堡”。2005年后,国家基本上退出了大学的内部运作。波兰政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实施了新的竞争性、市场化机制来提高大学产出,并确保与商界建立更实用的联系。因此,国家越来越成为大学的“市场工程师”,致力于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
注释:
①波兰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通过各类型入学考试(如笔试、面试等)进行选拔,这一选拔机制允许成绩优异的学生注册全日制课程,在一些研究领域全日制课程的名额也提供给特定学校学科的国家竞赛的获胜者和决赛者。其他已通过入学考试但排名较低则被提供其他类型的学位课程,并收取一定费用。
參考文献:
[1]KWIEK M.Universitie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J].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012,11(1): 111-126.
[2]LEJA K. Looking for a model of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M]//The univers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202-223.
[3]SEDELMEIER U. Regulatory alignment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M]//Constructing the path to eastern enlargement: the uneven policy impact of EU identi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131-154.
[4]JASIECKI K. Capitalism the Polish way: a new variety of market economy[EB/OL].(2016-08-14)[2021-05-07]. http://www.aspeninstitute.cz/en/article/1-2014-capitalism-the-polish-way-a-newvariety-of-market-economy/.
[5]Eurostat.Patent applications to the EPO, 2005 and 2012 [EB/OL].(2014-03-05) [2021-05-29].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File:Patent_applications_to_the_EPO,_2005_and_2012 _YB15.png.
[6]N?魻LKE A, VLIEGENTHART A. Enlarging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emergence of dependent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J]. World Politics,2009,61(4): 670-702.
[7]GEORGIEVA P.Higher Education in Bulgaria[M]//Monographs on Higher Education. Bucharest: UNESCO-CEPES,2002:20.
[8]HAZELKORN E.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26.
[9]KERR C.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convergence or continuing diversi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4.
[10]VAIRA M.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Higher education,2004,48(4): 483-510.
[11]SADLAK J. In search of the‘post-communist university-the background and scenario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M]//Higher education reform process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Frankfurt: Peter Lang, 1995: 43-62.
[12]DUCZMAL W.The rise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Poland: policies, markets and strategies[D].Netherlands: University of Twente,2006.
[13]World Bank. Tertiary Education in Poland[R]. Warsaw: World Bank,2004.
[14]OECD.OECD Thematic Review of Tertiary Education: Country Background Report for Poland[R]. Warsaw: OECD,2006.
[15]Polish Press Agency. Polands reindustrialisation to be based on local research[EB/OL].(2016-09-01)[2021-06-11].http://www.pap.pl/en/news-/news,442214,polands-reindustrialisation-to-be-based-on-local-research-minister.html.
[16]Ministry of Science and Higher Education[EB/OL].(2013-05-24)[2021-06-13].http://www.nauka.gov.pl/g2/oryginal/2013_05/de12c442930503e 215e580b8afc2513b.pdf.
[17][18]MILLER M, MROCAKOWSKI T, HEALY A. Polands innovation strategy: how smart is “smart specialis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s and innovation systems,2014,3(3): 225-247.
[19]Science in Poland.Diamond Grants awarded to outstanding students-researchers[EB/OL].(2015-12-05)[2021-06-13].http://scienceinpoland.pap.pl/en/news/news,405682,diamond-grants-awarded-to-outstanding-studentsresearchers.html.
[20]Government of Poland.Attachment to 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M]. Warsaw: Author, 2011:12.
[21]Science in Poland. Gowin for PAP: poland should be innovative, not imitative[EB/OL].(2016-04-08)[2021-06-15].http://scienceinpoland.pappl/en/news/news,408024,gowin-for-pap-poland-should-be-innovative-not-imitative.html.
[22]Board of Strategic Advisers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Poland.Poland 2030-development challenges[EB/OL].(2016-07-12)[2021-06-17].http://agora.mfa.gr/agora/images/docs/radD7BFBPOLAND_ 2030_INT.pdf.
[23]Neave G. The evaluative state reconsidered[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1998,33(3): 265-284.
編辑 吕伊雯 校对 娜迪拉·阿不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