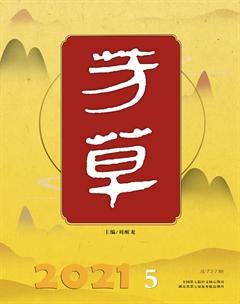从生命如花中寻找一个理由(二十首)

臧棣一九六四年四月生于北京。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诗集有《燕园纪事》《宇宙是扁的》《小挽歌丛书》《骑手和豆浆》《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沸腾协会》《情感教育入门》等。“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二〇一七年十月应邀参加美国普林斯顿诗歌节。
兰花简史
蝴蝶飞走后,它的假鳞茎
很像一个人从未区分过
他的生活和他的人生
究竟有何不同;
并非禁区,被很少谈及,
仅仅是因为,当他的生活
大于他的人生时,
它仿佛躲在铁幕的背后;
据记载,它从未害怕过狮子
或黑熊。也许秘密
就在于它美丽的唇瓣
能令凶猛的动物也想入非非。
而醒目的真实原因很可能
比花姿素雅更深邃;
在领略过芍药或牡丹之后,
它的美之所以仍能胜出,
全赖心灵的暗示最终会平息
我们所有的蠢蠢欲动;
当一个人试图烘托
精神的秩序时,它会及时
从侧生的花葶提供缕缕幽香;
而当他需要从存在的晦暗中
夺回某种无形的归属权,
它就会贡献一个新的基础。
丝棉木简史
能辨认出它的人
基本上都可归入知音的行列;
每一次,走近的脚步
都会让它的卵状叶抖动如小鳟鱼;
一半是仪式,婉转于
诸如此类的私人的秘密
确实没有公开的必要;一半是见证,
纯粹于生命之间的界限
其实还有好多有趣的缝隙呢。
所以非要过浩渺这一关的话,
不妨先参照那可爱的抖动,狠狠剪去
人之树上多余的枝蔓。
季节变幻之际,你的心
能将秋天的颜色浸润到何种程度,
它就能将同样的热忱
分毫不差地反映在醒目的乔木树叶上;
即使你有时会迷惘,它也从未
怀疑过这对应的严肃性。
以貌取人似乎不可取,
但用在它身上,几乎千真万确;
如此好看的椭圆形长叶
必定和发达的根系有关。
秋风萧瑟之际,它并未带来
特别的知识;它带来的是———
远远看去,人的孤独
怎么好意思和它的侧影相提并论。
紫草简史
我们给历史分类时
它显露出的快乐
仿佛构成对人的无知的
一种绿色的嘲讽;
微风吹过,这嘲讽会融入
本地的氣息,生动于
自然的摇曳,但从始至终
也并未太过分;就好像它幻想着
我们最终能进化到
给大地之血重新分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只是偶尔才注意到
混迹在茂密的杂草中,
唯有它的姿态独特于
多年生草本,浑身的粗毛
生硬捍卫着挺立的茎杆;
我们给候鸟分类时,
乌鸦会衔着它的紫色花冠
去挑逗魔鬼会不会
变成好人。而当我们学会了
给春秋的深意分类时,
它会像约好了似的,
在沸水里等着你去更新微苦
在人的精神中的一个含义。
杏仁简史
据说,宇宙中每一样事物
都有固定的总数;
死去的人和未出生的人
尽管面目模糊,但不改变
人作为一个总数;
宿命论者这样说,
无非是想告诫我们———
对付发疯的世界,没有什么
比灰烬更有效;或许
灰烬才是真相。
但我总觉得,这简直
像一次诱骗:既是对结局的出卖,
也是对灵魂的降低。
什么是疯狂,其实和发疯的
次数,是很难分开的。
擦去桌面上的灰尘,
从瓶子里倒出杏仁,
仔细点数,这是保罗·策兰
去黑森林拜访海德格尔
返回巴黎后干过的事。
一开始,和大伙一样,
我以为杏仁是可以数清楚的;
深藏在杏仁里的苦涩
则不容易数清楚。但真相很可能是,
那几粒杏仁从来就没人数对过。
万寿菊协会
为美丽而生,金黄的头状花序
像一次尽情的释放,
将无数可爱的小舌头
倒贴在无名的悬念中。
命运的安排,只能信一半;
春秋的大意里,只有将
长椭圆的针形叶进一步分裂成
劲道十足的羽状,才会助长
姿态蜕变为资格。暂时还没
领悟的话,不妨善意地看待一下
灵魂和芙蓉之间可能的距离:
像是猜对过蝴蝶的脾气,
它们鲜艳的胸脯骄傲得就像
宇宙的黑暗中不乏
命运的例外:在它们身上
美丽的静物始终多于娇娆的植物。
那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任务?
颤动的花蕊深处,蜜蜂忙碌得
像一个豹纹钻头,身份却含混于
既是粗暴的侵入者也是殷勤的小天使。
大丽花协会
美丽到这一步,
它甚至不再需要你的奇迹
来促成这新的认知
只能用在它身上:醒目的妖娆
构成了它的纯洁。
人要做到这一步的话,
保守估计,至少也得十万年。
仅此一列,菊花和牡丹的重瓣
加起来也没有它的重瓣
多得像可手指触摸的
新鲜的岩浆。试图独占
它的花容的女人,最后都变成了
苍白的疯子。围绕它的感激
始终是激烈的,甚至命运女神
有时都想折断一根树枝
做拐杖。就说说你吧。
在它美丽的矛盾中你的真相
是否够用?你的胳膊上
如果没有和魔鬼搏斗时
留下的抓痕,请不要
把它放进送人的篮子里。
巴西风铃木丛书
紫葳科小乔木,树身布满
深刻的纹裂,仿佛是要矫正
你脑海里的一个盲区:
植物不止是生长,它们的生长
同时也是一种劳作;一点也不亚于
人的血泪史中挣扎的形状;
甚至在椭圆形的睡眠中,
它们也热爱着自身的劳作。
如此,粗糙的绿叶不仅记录了
与风雨搏斗的所有结果,
也展示了一种醒目的对称:
它身上的金黄管状花如此美艳,
以至于仅凭肉眼,你根本
就看不出它刚刚诅咒过
一种浅薄:他人即地狱。
初春的堇菜
与早春争艳的花草中,
光瓣堇菜的海拔应该是最低的,
低到一条狗突然冲向
冷嘲的乌鸦时,曾将它们
毫无顾忌地踩踏在脚下;
同样的冲动也常见于野猫的好奇;
几只喜鹊受惊之后,现场的痕迹
虽然轻微,但在那不易察觉的凌乱中
你仍能感觉到一只大猫
踩过的踪影:非常轻捷,
却构成了一种野性的践踏。
还有一些更原始的凹陷,像是出自
很久以前,一头野猪突然调过头,
朝着我们这边突围时,
在它们身上留下的。这虽然是
一个梦,但清醒之后,
你只能保证你自己;你的同类中
有没有人曾将它们的小紫花
不经心地踩在鞋底;谁敢保证?
假如引用人类的法律,
它们显然遭受过很多伤害;
但你的歉疚并不适合它们。如果需要纠正,
朝它们走去时,你应该比过去更轻快,
更懂得如何插足在它们中间,
并将它们的底色放大为内心的喜悦。
莴笋简史
削去粗糙的硬皮,
苏醒的翡翠从植物那里借到
一根意味深长的棍棒;稍微使点劲,
就能握出一把晶莹的露水,
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
你的真面目好到什么程度,
它就可以试出来。当年我读康德读得
有点搁浅时,我就会在金牛座旁边
放上一盘香喷喷的莴笋炒腊肉;
那袅娜的热气仿佛能融化
最缠绕的措辞,思想的火花
又开始发出原始的闪烁,
原本倾斜的天平也渐渐恢复平衡。
这么好吃,我才不心虚呢;
几乎和康德同一天出生的
莎士比亚要是吃过莴笋炒腊肉,
也会讲真话的。如今已很常见,
但它从未辜负过好物;
而你是否辜負过好事,
它只能帮你到你切丝的手艺
确实也曾让腊肉鲜亮欲滴。
当然,将它和鸭块煲成老汤,
也算是对事后有所交代;
但重点依旧是,它是你的
拿手菜,它从未怀疑过你的口味
会偏离它对微辣的腊肉的
怀有一个固执的信仰;
而且将它顺纹理切成片时,
整个世界突然会矮下去一大截,
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紫花地丁协会
见过它们并不意味着
你曾认真地看待过它们;
惊蛰后的北方,春寒尚未完全褪尽,
而它们可爱的身影
已开始随处可见:紧贴着
解冻的泥土,没错,
基生叶里也可爆发出
一个陌生的自信;它们用美丽的幽蓝
将十字花科的集体主义
定格在早春的背景中。
如果花喉可以被温柔地想象,
它们的姿态已接近于自发的
春天大合唱;但有过很长一段时间,
要将倾注在玫瑰或百合上的情感,
再分一些出来,投放在它们身上,
实在太难了:那几乎意味着
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气
将他的爱打回到原形。
黄栌
心灵的距离奇妙
你我的远近。大雁南飞,
比起十年前,更指向浩渺最准时。
深山的深处,浅显一个大道理
偶然也会显得好简单:
万物之中,唯有它和你同姓;
唯有它的树叶变红时,
爱的记忆会像慢慢燃烧的火焰。
因为它,我们既是看客,
也是过客;而这混淆的主体性
并未妨碍到衬托它的背景中
蔚蓝比永恒更悬念;
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印象———
深山像陡峭的基座,
寂静如无形的纪念碑;
而它守在原处,挺立在小乔木的坚韧中,
将原处和远处统一在
宇宙的回声中———
就好像它最深的触须
不是扎根在倾斜的泥土里
而是扎根在我们的青春之歌中。
铁杉
将它从柳杉和冷杉中
明确分辨出来,我差不多
花费了十年时间;
其中有过几次反复,
但最终那些疑惑的瞬间
也被作为乐趣多于教训
收藏在个人的烙印中;
高大的树身像一座正在闭气的塔。
硕大的果球落下时,有人会中奖;
假如在岔路口面对两条路时
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
那么,美丽的铁在哪儿?
伸手之际,我下意识的举动
会不会被命运的小动作所利用?
敲起来硬邦邦的。
坚持下去,那咚咚的声响
虽然一开始确实很像
鼓点的回音,但随着暮色
渐渐加深,它听上去会越来越像
一道从未被触碰过的窄门
颤抖在大地的摇晃中。
玫瑰刺丛书
和人类相处久了,你会不习惯
这些尖锐的刺;小小的突兀感
不起眼,却异常生硬;
而你的温柔,无论怎样出色于
你本质上是个爱劳动的男人,
对它们而言都只是某一类鲁莽;
发作时,它们脾气大得
仿佛我们不是那个神
按神的模样将我们塑造出来的;
据说里尔克就是因为
摘玫瑰花时,太陶醉于
迷人的香气,而被它们刺破手指,
引发了白血病,造成了
不可弥补的诗歌的损失。
所以你心有余悸不是毫无理由的;
轻轻触碰之后,你总想着
用剪刀将它们从坚韧的花枝上
一个个剔除,就好像它们妨碍了
我们安全而亲密地占有
那些娇艳的花朵。所幸
玫瑰和草鱼之间的逻辑关系
还不算太强,否则剪除
这些锐刺,带着嫌恶的表情
或是被罚劳役的感觉,将它们当作异物
丢进垃圾桶,和掏出鱼腹中的
腥味刺鼻的内脏再扔掉
又有何不同?如果这些尖刺
不曾和谐于花朵的美丽,
你身上的刺,又算什么呢?
如果你最终仍没有习惯
美和刺至少在花如玫瑰
这样的肉身上是不可分裂的,
你又怎么能觉察到这首诗中
带刺的小东西已将你刺入
语言的黑暗中究竟有多深呢?
雏菊丛书
重逢之际,装饰性
会很快在这些紫苑族的烂漫中
消退殆尽;可观的纯洁
已反映在它们的容颜中,但暗恋者
却没有一次能正确地把握到
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如果我被允许说出
一个真相,我才不绕圈子呢———
花头即佛头,才不管大小
合不合窸窣的比例呢;
如此,洁白的小花瓣就层叠在
一个紧密的依偎中,向你示范
精灵们是如何巧妙隐身
在我们周围的。多年之后,
我终于想起,我这辈子见过的
最美的雏菊并不是由恋人们精心浇灌的;
它们属于胡同拐角一位收破烂的老太太,
在高高堆起的脏兮兮的回收物中,
她养护的雏菊美丽惹眼,
像一首首无声的圣歌;看上去
与她的身份严重不符,却构成了
卑微的生活中最深奥的秘密。
美人蕉丛书
花姿一贯娇艳,尤其是
清亮的露水浸润花萼时,
它这样纠正你我的目光———
太纯洁了,就不可能太深邃;
太正确了,就不可能太天真;
太极端了,就不可能太诱惑;
如果见过暴雨后依旧挺拔的
小芭蕉,如果你不想纠结于美人
怎么能比得过它的真容,你就恨不得
踢那个没把名字起对的家伙的屁股。
尤其是,从烟波浩渺中收回
远眺的目光时,有它在眼前
安静地轻颤,绝对是一种幸运。
相比之下,另一种幸运则显得偏僻:
你误解过这世界,而它没有眼睛,
仿佛很盲目,可它却从未误解过你。
白玫瑰
一朵白玫瑰就能遮住
你留下的空白。它发挥作用的同时,
我仿佛也把握到了自我的潜力。
比娇艳更美丽,它集中了
静物的力量,在疯狂和治愈之间
投出了纯洁的一票。
心灵的微妙缺乏线索的话,
不妨揉一揉眼圈:它的每一片花瓣
都像舌尖刚刚舔过的嘴唇。
围绕着它的记忆几乎
从不会出错,人的悔恨
不过是它的一种特殊的肥料。
看它身上粗暴的断痕就知道
因為美,它被出售,而命运
并不允诺只有一个真相;
但它选择了爱的原谅:
它的气息比洁白更纯粹,
除非魔鬼对爱神也动过手脚。
冬青
迎着冬天的落日的
慢跑者,它记得你的步伐;
脚尖点地时,它犹如皮革的绿叶
会跟着轻轻颤动。可爱的反光,
任何时候,都像一次未遂的哺育;
除非你默认精灵曾躲在
常绿灌木的后面,像刚刚偷食过
那些鲜红的浆果的山雀一样好奇
我们的顽强似乎得到过
自然的暗示,至少在它身上
体现得更符合性格的神话。
如果用镜头去捕捉,四周的环境
常常显得恶劣,但它像
一道密不透风的树篱,在北风
和虚妄之间做出了选择。
从不知道什么叫凋零,它的祝福
像是从命运的风口处
收集到的弹簧;哪怕只是用手
轻轻一触,记忆的反弹
也会将你的背影反扣在冬天的霞光。
芜菁丛书
你的耳朵被黑格尔
堵住的时候,它叫蔓菁;
名字好听得就好像
上初中的时候,隔壁大院里
最漂亮的女孩差一点
也叫蔓菁。你的眼睛
被惠特曼蒙上的时候,
它叫大头菜;二年生草本植物,
深裂的羽状青叶仿佛知道
你小时候养过至少七只兔子。
细节的力量往往会在
不经意间体现出来;用清水冲去
表面的泥浆时,多肉的块根
会将一个近乎光滑的玉白球形
悄悄塞进你的手心;
虽然无人见证,但仪式感
却一丝不苟,就好像这是专门
为你补办的一次成人礼。
从此以后,你要格外留意
那些只有研成碎末
才能发挥奇效的东西。
没错,它也是母亲偏爱的食材。
将它切成小细块,用温火煮沸;
眼睛再次睁开时,生活的形状
越来越偏向十字花科。
香樟树下
不知不觉,耸立的塔
已经被替换。
挖掘机驶过冒烟的拐角。
在那个位置上,
距离被缩短的意思是,
自然,离你中有我更近。
起伏来自半空,
街道因头顶有鸽群
盘旋而悠长;
流水努力流向
一个背景,向东还是向右,
并不妨碍树荫里的
道德几乎从未输给
人世的恍惚。有没有想过,
被绳子吊起过的
迷途,其实也可以
像过于低垂的树枝一样
在膝盖上被折断。
正好就有两个主题
也需要分成两截
来重新处理:在祈求
得到更多的时间之前,
人的主要问题一直就是
使用好你的渺小,利用好你的孤独。
以紫薇为路标
柿子泛着青黄,它们的弯枝
为时间的粗心挽回了
一点面子。野猫的头顶,
南瓜花正牵手丝瓜花,
煽动金黄的舞蹈。猛然间,
我不觉得我们是不是主人
真有那么重要。荒芜之中
仿佛有一首走调的颂歌。
听不惯,我才觉得有必要
反省一下,我们不一定非得
自认是过客,才能进入
他们为我们裁好的角色。
必经之路,刚拆迁过的大片土地,
尽管砌了围墙,却有很多豁口;
匆忙的一瞥中,电线杆倾斜,
丛生的杂草比邻历史的羞涩;
惟有一只麻雀趴在疲软的电线上
像是在专心减轻这世界的重量。
九月过半,紫薇花依然绽开,
甚至粉红的月季,也没输给
大地的松弛。走到这一步,
事情好像已很明显了:其实,
我们也不一定非要知道,
反方向行走,忘我是如何可能的。
(责任编辑:哨兵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