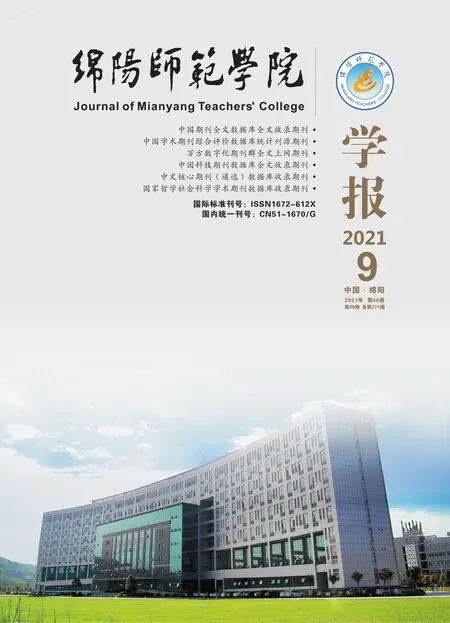吴郡陆氏的侧影:东晋《陆祎碑》研究
刘运杰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00)
《陆祎碑》全称作《吴故征北将军海盐侯陆府君侯之碑》。据《绍熙云间志》载,该碑曾立于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昆山绝顶陆祎墓前,碑文被《云间志》及后世方志所收录[1]54-55(校勘后的碑文附后,本文所引一概从此出)。经考,碑主陆祎为孙吴末期左丞相陆凯之子,吴赤乌六年(243年),起家宿卫郎中,历任黄门侍郎、征北将军,封海盐侯,后遭流放,吴亡入晋。其事迹又散见于《三国志》中,经历与碑文大体相合,但部分信息于碑文仅见,适可补充史阙。目前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吴郡陆氏的碑刻几无实物,文献记载亦是寥寥,拥有700余字的《陆祎碑》可算作目前所见吴郡陆氏最早的碑刻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对此尚无关注,本文对此试作研究,以备参考。
一、《陆祎碑》考释
碑刻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承载着书写者传达的信息,也暗含对族源与身份的认同。本节旨在利用史传对《陆祎碑》进行探究,以阐释陆祎的生平轨迹与家族源流,并窥探其支系在魏晋南北朝之际的发展动态。
(一)陆祎生平
据《三国志·陆凯传》,陆祎“初为黄门侍郎,出领部曲,拜偏将军。凯亡后,入为太子中庶子”,生平仕官大略如是[2]1403。而碑文显示其为宿卫郎官起家,履历较史书尤详。按碑,陆祎于吴赤乌六年(243年)征为宿卫郎中,历任右郎中、左郎中、治书执法、平中校尉、立义都尉、五官郎中、骑都尉,迁黄门侍郎,后封海盐侯、加偏将军,后行左丞相、镇西大将军事。其中宿卫郎中、右郎中、左郎中、骑都尉皆为执兵宿卫之职,孙吴公族子弟起家多充三署郎官、骑都尉之职,如吴郡朱氏、顾氏子弟或“以父任除郎”[2]1315或“拜骑都尉,领羽林兵”[2]1231,外戚会稽全氏子弟“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2]1200。田余庆先生曾作出论断:“三署实际上是吴国官员养成和储备机构,是贵游子弟麋集之所。”[3]303陆祎作为吴地士族子弟,起家郎官也符合孙吴政治惯例。碑文所见治书执法、平中校尉二职。按《晋书》,治书执法系曹魏所新设“掌奏劾”之职[4]738,平中校尉亦不见于史料,二者记载正可补孙吴官职之阙。
值得注意的是,碑文“行左丞相、镇西大将军事”一事,异于史传。陆凯在吴元兴元年(264年)以镇西大将军领荆州牧、督镇巴丘,吴宝鼎元年(266年)任左丞相。据《三国志》,吴宝鼎二年(267年),传闻陆凯欲在孙皓拜太庙时借机废立,裴松之注引《吴录》称:“旧拜庙,选兼大将军领三千兵为卫,凯欲因此兵以图之,令选曹白用丁奉。”[2]829《建康实录》也称:“(宝鼎二年)十一月,将欲还建业,左丞相、大将军陆凯谏曰:……”二史互证足见陆凯系左丞相兼领镇西大将军[5]94。从史料分析,陆凯自宝鼎元年至建衡元年(269年)去世,期间官职并无变更,亡故后也未有继任的记载。碑文称陆祎行左丞相、镇西大将军事,笔者推测应当是陆凯卒后,陆祎暂代陆凯职务。但陆祎官职尚微,是否足以代理左丞相、镇西大将军这一上公级别的官职,由于史料阙失,姑且列此俟考。而其所封“海盐侯”也与其父所封嘉兴侯相异,可见其并未嗣爵或另有封拜。
碑文后叙“皇晋蕃平南境”“抚戎庙算,量敌□□”“北攻”等内容,当指陆祎参与对西晋某场战斗。后提及“君征北”“其委戈执笏,入宾皇储,若珍衽席,讲道论□”等字眼,是指陆祎任职征北将军,转任太子中庶子的史实。《陆凯传》也提及陆祎由地方调还“被召当下,径还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顾”。当即此事[2]828;随后碑文提到“兴遘贝锦”一词,结合后文“受侮以暇迁”,所指正是史书所载的陆祎一族受谗流放一事。据载,天册元年(275年),陆祎与从弟陆式一家流放至建安。天纪二年(278年),陆式等“召还建业,复将军、侯”[2]1410,陆祎应此时一同召还,担任征北将军、封海盐侯,而非流放前的太子中庶子之职。诸多文献都言及《陆祎碑》碑额有征北将军、海盐侯字眼,也可作为旁证,而《三国志》记载并未及此,足可补阙。随后碑文转叙晋灭吴这一节点,据碑文“□□箕之入周,陈洪谟于晋宇”,可知其平吴以后尚存,而“享年不永,春秋知命,□□而□”,未及晋朝任用便逝世,碑末颂辞“将弹南冠,入亮皇室,我翼未挥,□□□折”足可印证;因而墓碑虽立于东晋,但仅称孙吴官爵,正是陆祎在吴亡不久后逝世的缘故。从碑文及史传推测,陆祎少年征为宿卫,晋平吴不久后逝世,生年应在魏黄初元年(220年)前后,卒年在晋太康元年平吴(280年)之后,年龄当在六十岁上下。
陆祎子嗣不见于史书,碑文末记载了陆祎子嗣及仕宦情况:长子陆衠历任西曹①、章安县令,官至奉车都尉;次子由于碑文阙字,仅能推测其历仕大夫、某掾;三子陆喈历任散骑侍郎、前将军、历阳、宣城二郡内史,此人见于《晋书·顾众传》:“时(王)敦又怒宣城内史陆喈,众又辨明之。”[4]2016据《云间志》,陆喈墓与其父冢相临,也有墓碑,但碑亦不存,碑刻情况仅能从《集古录》《隶释》的零星记载中了解一二,《陆喈碑》同样为隶书碑,字体劣弱,又据《集古录》,陆喈字公声,陆祎之子,仕晋至宣威内史②、前将军,东晋建武元年(317年)卒,与《陆祎碑》相互吻合[6]2161。故陆祎子嗣名字可考者为陆衠、陆喈,补充了史载之阙。
(二)再论吴郡陆氏之起源
吴郡陆氏起源最普遍的说法为妫姓之后,该说法于隋唐颇为流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陆氏出自妫姓,田完裔孙,齐宣王少子通,字季达,封于平原般县陆乡,即陆终故地,因以氏焉。”[7]2965《元和姓纂》《史记索隐》引《陆氏谱》及《通志》说法与之大体相近,但也有些许差别,如《新唐书》及《姓纂》等书中,楚人陆贾被纳入吴郡陆氏的谱系,其子孙渡江形成了吴郡陆氏;《史记索隐》引《陈留风俗传》则称陆氏为陆浑之后[8]3267,陆贾则系陆浑奔楚者之后,此说与《新唐书》等产生了矛盾。有学人综合二说,从陆氏祖先所封“陆终故地”入手,考得“陆终故地即为楚人先祖所居之地”,将二说有机联系起来,此处不作过多展开[9]27-29。
尽管存在他说,但妫姓之说于隋唐时期影响甚广,多见于隋唐时的陆氏墓志。可知隋唐以来陆氏族人对该说法普遍认同,但此说是否继承前人,产生于何时,还需利用隋唐以前的文献佐证。按《史记》所引《陈留风俗传》,为东汉末陈留人圈称所撰,其书成于东汉末,可见其说法出现尚早,但从隋唐之前吴郡陆氏成员的文字中几无可见。从自我认同这一角度来审视,《风俗传》之说并未得到陆氏家族的认同,而妫姓之说却更得陆氏之认同。陆云《祖考颂》中称:“在周之衰,有妫之後,将育于姜,……,故能光宇营丘,奄有东海,支庶蕃庑,而胤祚昌大矣。遭世多难,子孙荡析,逐于南土。”[10]2054又《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权舆有妫,爰帝及王……乾鉴南眷,诞降我祖”[10]2057,陆机《遂志赋》中也有“启敬仲乎方震”“系姜叟于海曲”之语[10]2010。《陆祎碑》叙述祖先源流称:“昔龟凤启符,妫□□袭□□之胤,世为诸侯。或家于陆乡,因氏姓焉。”虽碑文残缺,但依然表达了陆氏出自妫氏的含义,“家于陆乡”的说法与《新唐书》遥相对应,可见自魏晋以来吴郡陆氏对于其家族源流一直秉承妫姓之说,沿至隋唐。郭凤娟在《南朝吴郡陆氏研究》一文中认为从六朝时期家族各主要人物的传记中皆未看到关于陆氏家族源流的记载,故认为“‘出自妫姓’以及先秦贵族后裔应为唐宋时期陆氏后人附会之说”[11]14。根据上文所述,其观点或犹有商榷的余地。
至于隋唐以后的谱系将楚人陆贾纳入到吴郡陆氏的祖先当中,此说法反而稀见于隋唐之前文献及碑志。而陆云曾为张昭父子作《张二侯颂》追溯其祖先至汉初张良,陆贾、张良同为汉初功臣,若陆贾为陆氏祖先,足以大书特书,何以为自己祖先、族人作《祖考颂》《陆府君诔》却不及一语?目前就笔者所见,隋唐之前将陆贾纳入吴郡陆氏祖先的文献,仅见《大周柱国谯国夫人故步六孤氏墓志铭》(572年)中“大夫出境,百越来庭”[12]484,及《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道碑》(574年)[10]3945有“南越使者,解汉帝之衣”数语述及,时代已处在南北朝之尾声。至于陆贾为陆氏先祖这一说法何时成为陆氏家族的普遍认同,就目前史料所限,这一探究尚俟日后更多材料的发掘。但魏晋至隋唐以来,吴郡陆氏对于其族姓起源则确实是有着明确认同,《陆祎碑》的记载,为陆氏出于妫姓之说提供了新的佐证。
(三)陆凯支系的复原
魏晋南北朝之际,吴郡陆氏各支系也有不同升降,如丹徒支的陆逊一支在军事失败中遭到打击,幸存者陆机陆云兄弟后遭处死,从而一蹶不振。而陆逊之弟陆瑁一枝则有所发展,其孙陆晔、陆玩在东晋建立后仕途较显,形成后来所谓太尉枝,也是吴郡陆氏在后世发展最为繁盛、最具影响力的一枝。相比以上两支,同属丹徒支的陆凯一系,自吴亡以后,总体呈现出日渐衰微的态势(见图1)。

图1 陆凯支系图(虚线表示世系不详)
陆凯虽官至孙吴左丞相,一门五侯,地位显赫。但自吴亡之后,陆氏门第随着政权倾覆遭到打击。尽管西晋政权随后选取陆喜等南方士人随才受用,以示安抚。但由于陆祎未曾及时参与到西晋政权的仕进当中便去世,失去了一次攀附新朝的机会。而从陆祎三子的仕宦经历看,长子陆衠历任县令,官不过奉车都尉,秩第六品;二子仕官至“□□□□大夫、□□掾”,似乎品秩亦不高;陆喈是陆祎诸子唯一显名者,官至散骑侍郎、前将军、历阳、宣城二郡内史,秩第三品。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在江南称帝建立东晋,次第重用吴地士人,陆氏家族人物如陆晔、陆玩等也在此后次第受到重用,相继登上令仆、三公,而陆喈恰恰于是年逝世,再次与机会失之交臂。
陆祎这一支系并未利用时机及时攀升,陆喈逝世后,陆祎后代便不曾出现在史传之中。同样,陆凯另一子后代仕宦也不显,陆祎从子陆仰仕官至吏部郎,秩第六品,其子陆伊仕至州主簿,品秩亦不高;陆伊之子陆退为丞相谢安主簿、光禄大夫,秩第三品,稍稍显名[13]286。然自陆退以后,陆凯后代在南朝政权中再未出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仕宦也不见史书记载。刘宋时,陆凯之后陆修静入山修道,其父陆琳“九征不起,谥高道处士”,父子皆不热衷于出仕[14]39;梁时,身为“吴丞相敬风六世(陆凯字敬风)”的释道超不乐出仕,出家为僧,其祖父昭任尚书金部郎,为第五班,父遵官至散骑侍郎,为第十二班[15]197。由上观察,陆凯之子孙仕宦东晋,官品大多为二品以下,六品以上,两晋之际以门阀为矜,家族世仕五品以上,即可视之为一流士族,而二品以下六品以上,则可目为次等士族;梁官班制设流内十八班,班内官则为士流之预。可见东晋南朝以来,陆凯一支尽管未曾显名于东晋南朝,但仍可藉家门之望参与仕途,从其后嗣任官品秩来看,大致符合次等士族的仕宦品级,这也与东晋南朝以来吴地士族的地位情况相符。《世说新语》注引《陆氏谱》:“(陆)退,(张)凭婿也。”张凭出身于吴郡张氏,亦为吴姓高门[13]286。可见陆凯一支尽管显赫不在,不能与太尉枝成员相较,但作为吴郡陆氏一员,仍可借家族门第仕官,并贯彻士族之间的通婚制度。
陆凯一枝系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衰弱,一方面是由于家族乏人,另一方面在于未及时把握时机攀升,陆祎、陆喈的逝世,皆与机会失之交臂。东晋南朝一贯重北而偏南,故吴地士族门第与发展远不如侨姓大族显贵,这一政治生态使得吴姓士族整体上都处于“内敛”状态,陆凯这一支系的发展状况,正是吴郡陆氏乃至两晋南朝吴地士族的常态与真实写照。
二、《陆祎碑》的收录与存毁
《陆祎碑》尽管立于东晋,但长期以来不闻于世,其发现与著录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该碑的发现与著录,始于北宋,最早著录于欧阳修《集古录》与曾巩《金石录跋尾》。曾氏何时著录,时间不可考。欧氏曾搜得陆祎、陆喈墓碑碑本,曾为《陆喈碑》作跋尾云“陆氏有二碑,余家《集录》皆有之”,末题“治平元年(1064年)六月二十九日书”,此为《陆祎碑》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6]2161。从《金石录跋尾》所载碑文片段来看,《金石录跋尾》载碑文“转右郎中、左郎中、治书执法,平中校尉”一句,诸方志此处尽阙六字;《金石录跋尾》作“委戈执笏”,而方志此处皆阙“笏”字。可见北宋时《陆祎碑》尚较完好,相较后代诸方志记录的文本,文字多可辨识[16]683。
由于二位金石名家的著录,使《陆祎碑》引起时人注意。朱长文《墨池编》、郑樵《通志》、洪适《隶释》皆有著录。洪氏少时于秀州(今上海、嘉兴一带)生活数十载,或尝亲见《陆祎碑》,对碑文书体还有“体弱格卑,已去黄初远矣”的评价[17]194。尽管该碑多为方家所著录,但迟迟未进入官修方志的视野。直至南宋绍熙元年(1189年),海盐县令李直养作《续题名壁记》,始提及“陆祎为海盐侯”[18]697,又作《武原志》述及石碑下落,方将该碑纳入方志的视野。绍熙四年(1193年),《绍熙云间志》编成,碑文收录其中,而此时距离欧氏作跋尾业已130年。
按北宋修得华亭县方志有二:景德四年(1007年)创辑的《华亭图经》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所修《华亭图经》(《云间志》引称《旧图经》或《祥符图经》)。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知州张元成又修《嘉禾志》。《云间志》在记录遗迹、冢墓时多引用三书,曾提出疑问:“《祥符图经》载诸陆、潘浚、笮融几十二墓……陆祎墓在昆山,碑志尚可考……反不及之,乃未见征北墓碑耶?”[1]38“旧《图经》、《嘉禾志》人物止及冢墓所在兹邑者,而顾野王、陆祎更阙而不著。”[1]14足见淳熙以前《陆祎碑》无闻于官修方志,《云间志》实为首次收录。据《云间志》考证“旧有征北将军陆祎墓碑,今虽断毁不全,而龟趺尚存焉”,《云间志》云“旧有”,可见《云间志》成书时该碑残毁已久,所录碑文当另有所本[1]39。关于此碑下落共有二说:
1.百姓毁碑说。见南宋华亭人许尚《华亭百咏》:“征北将军墓,即陆祎墓,在昆山,有碑,村人疲于官吏征索,遂碎其碑(一作‘半’)。”[19]1427是书编于淳熙间(1174—1189年),许尚为华亭人,活动时间与《云间志》编撰时间相近,考虑到这层因素,对于该说法不得不有所考虑。
2.碎为炮石说。见明天启二年(1622年)修《海盐县图经》引《武原志》:“政和间知秀州毛滂取之置月波楼,建炎三年冬,胡虏南侵,将逼郡城,太守邓根碎为炮石。”[18]917《武原志》即《海盐县图经》,绍熙元年由海盐知县李直养所修,早于《云间志》,所言当有所本;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正月)庚戌,知州程俱率官属弃城保华亭县、(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辛酉,金人陷秀州。通直郎、权知州事邓根留武翼郎、本州岛兵马都监赵士医乘城拒敌。”[20]706-720“(建炎四年六月壬辰)通直郎邓根知秀州”[20]789。可知建炎三年知州为程俱,邓根于次年二月方权知州事,六月才正式任职,如何在建炎三年以知州身份下令将碑破坏充作炮石?许尚诗《征北将军墓》称,“﨑岖寻古隧,衰草隐寒原,欲读将军事,丰碑秪半存”[19]1427。可知南宋时残碑仍在陆祎墓前,而非月波楼;宋末人凌岩也有诗云“九峰西峙比昆仑,晋代将军墓尚存”[21]19b。足见《武原志》“置碑于月波楼”和“碎为炮石”之说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元末人钱惟善有诗云:“年年载酒酹榆枌,征北将军尚有坟。”足见元末时陆祎墓尚可辨识[21]19b。而据明、清方志,明清时期陆祎冢、碑均无处可寻。综上所述,陆祎碑保存至两宋时期,而《云间志》则首次著录《陆祎碑》的官修方志,该碑于北宋时尚较完好,南宋时虽受损较重但元代仍有遗迹。明、清以降,碑、冢已完全不存。
三、碑文之隐:吴郡陆氏的家族浮沉
南齐陆道瞻《吴地记》称“海盐县东北二百里有长谷,昔陆逊、陆凯居此,谷东二十里有昆山,父祖葬焉”[22]1174,《云间志》载陆逊、陆抗、陆凯、陆瑁、陆监诸人冢墓,皆在城外西北三十二里处[1]38。《华亭县志》载昆山东的横云山(旧名横山):“古冢垒垒,世传以为多晋陆氏所藏”,元至正年间更于此一带发掘出东晋太元二年(377年)砖及铜器百余[21]20a。陆祎父子之墓位于城西北二十九里的昆山,与父祖墓葬相近,陆祎父子墓碑的存在也反映了方志所言非虚,昆山一带应是魏晋吴郡陆氏的家族墓地。从碑文“仰堂构之遗荫,蒙析薪之负荷”“蓼莪”字眼推断,碑文撰者或树碑者应当为陆氏族属。魏晋以来,朝廷实行严厉的碑禁政策,东晋渡江之后,碑禁效果日渐式微,私立现象颇多,《陆祎碑》碑文中甚至未避晋讳,这反映出了当时碑禁松弛的状况,也可看出该碑应当并非官立,故而对避晋讳并不严格。结合上述内容分析,《陆祎碑》当是在此背景下由陆氏族人所立所撰的“私碑”。
正如碑额所题,作者的叙事对象是“吴故征北将军”,而并非晋臣。因此碑文在叙述过程中有意模糊正统政权的界定。一方面碑文目“皇晋”为正统,对于其取用东南士人的行为称作“帝鉴海岳,求其隐逸”。另一方面,又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对孙吴法统的认同,在描述陆祎守土有方时作“尔乃抚戎庙算,量敌□□”,毫不掩饰地将晋称之为敌;“及其委戈执笏,入宾皇储”则径直将孙皓太子称作皇储;对于晋灭吴这一行动又称之为“皇晋藩平南境”,有意避开孙吴政权是否为伪朝的问题。陆祎身处吴晋之交,为“亡国之余”,作者身处东晋,基于晋灭吴的历史现实,只有历史回溯中有意避开南北正统的问题,才能在颂扬祖先的叙事中使之不陷入“仕宦伪朝”的尴尬境地。陆云为陆喜所作《晋散骑常侍陆府君诔》中,亦是将吴、晋同视为“皇朝”,淡化政权之对立,碑文之叙事手法,较之类似。碑文末书“夫□□君德,□铭大勋”,最终归结为颂扬陆祎仕吴之功绩,也即树碑者的意图所在。
平吴之后,吴地士族遭到打击,原有地位不再,加之西晋对之态度冷淡,目以为亡国之余。尽管不少吴地士人入洛求仕,但少有建立功名者。而作者身处东晋初年,情况则为之一变,时值北来侨姓寄寓江南,南北士族上层开始联合,吴地士族地位开始普遍上升。在此背景下,吴郡陆氏光大家门的思想应当变得强烈。汉晋之际吴地少有树碑立铭之习,现有实物资料也可证明这一点。从上文推测,陆祎去世的时间在孙吴政权灭亡后不久,而碑文末尾提到树碑时间在“泰宁三年岁次乙酉十二月壬戌朔一日壬戌”,即公元325年。距吴亡近五十年,距陆祎亡故也有相当长的时间。陆喈卒于建武元年,树碑时间在咸和七年六月(332年)[6]2161,也间隔了十五年之久,故而二人墓碑皆为陆氏后人追立无疑。墓碑追立虽然距二人逝世时间已久,但值墓碑树立之际,恰恰是吴郡陆氏在东晋政权中地位上升的时期,陆晔、陆玩正在此间受政权重用,兄弟二人相继登上台阁、三公之位。故而笔者推测,二碑的树立,或与此时吴郡陆氏在东晋政权中地位的上升不无关系,陆氏族人依照北方树碑颂德的习惯为先人树碑立铭,勒石颂德,以达到“封墓轼闾,矜耀门楣”的目的。陆晔“咸和中,求归乡里拜坟墓”[4]2024,或许也有光耀门庭、荣之乡里的目的。
陆机曾在《辩亡论》中表达其强烈的地域观念和家族荣誉感,借对孙吴历史的回顾、陆氏在吴政权中发挥的作用,间接宣扬家族功业。碑文中频繁目吴政权为皇朝,其旨仍是为了“淳曜祖业”,继陆机之余绪而已,加之陆祎碑为家族后代所立私碑,这种昭勋扬名的意图更为强烈。再结合树碑的时代背景,此值东晋拉拢重用吴地士族之际,吴郡陆氏正受倚重,《陆祎碑》的追立,或许正是吴郡陆氏籍此之际通过勒石颂勋以炫耀家门的反映。
四、结语
《陆祎碑》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难得的吴郡陆氏家族碑刻,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本文利用文献校勘,尽可能恢复了碑文原貌;通过碑文与传世文献考证,补充了史书未载的陆祎及其后嗣的史料信息,以及陆凯支系在魏晋南北朝之际的发展情况;藉《陆祎碑》中对族源的表述,也印证了魏晋隋唐以来对陆氏源流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脉相承;最后,墓碑的追立,以及碑文字里行间流露的对家族功业的赞颂,结合其时代背景来审视,这种现象或许正是东晋之初吴郡陆氏家族在东晋政权中地位有所上升的一种反映。
附录:《陆祎碑》碑文
碑文以《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明钞本《云间志》为底本[1]54-55,结合清钞本[23]143、《宛委别藏》本[24]200、清刻本《云间志》[25]3766-3767及《至元嘉禾志》[26]4570、明正德《松江府志》[27]624、天启《海盐县图经》[18]926-927、崇祯《松江府志》[28]1248及《金石录跋尾》校勘而成,清代方志虽业有存录该碑,多系抄录明方志,且时代久远,故不采入校勘。碍于行文篇幅及排版所限,不得不隐去校勘记,全文所引碑文尽出于此,兹点校如下:
吴故征北将军海盐侯陆府君侯之碑
君讳祎,字元容,吴郡吴人也。昔龟凤启符,妫□□袭□□之胤,世为诸侯,或家于陆乡,因氏姓焉。显考吴故左丞相凯,声闻于海内。君系远祖之懿绪,承洪族之清□,嵩岳降其神,渊渎协其气。是以景灵咸赞,奇姿挺杰,合九□□性聪,苞五□□□叡。故能□□大业,□经□徳,指琼雪而□□行,瞰云霄而厉峻节。若夫惇经好古,玄□图□,则思□□□之□,神入幽芒之□,□□□而识其机,苞万品而□其指也。尔乃披褐林□,□迟养真,值□□求士匪□□□□□□薮沈网绕□,□□□□石之□,幽泽无散发之□。君□敛节降志,屈□从时。赤乌六年,征宿卫郎中、□转右郎中、迁左郎中、治书执法、平中校尉、立义都尉、五官郎中、骑都尉,迁黄门侍郎。君克明□宪,允亮纳言,□□□□□封海盐侯、加偏将军,行左丞相、镇西大将军事。于时基辰□御,江河异宗,皇晋蕃平南境。有□□□□□□□□君征北□□□□□□□□□□,□□□则儒色温,□武弁则□气庄。尔乃抚戎庙算,量敌□□□□□北攻前□□□□□□□□□□□□彼场□惮威之□也。及其委戈执笏,入宾皇储,若珍衽席,讲道论□,□□□□□□□而□□□其□□□。世俗方昬,日月不照,鸱枭□□,豺狼竞趋。君耻宁武之详愚,厉祖考之烈□,□□□□□□□□以□□□□□□□□□兴遘贝锦,疾□合采,□受侮以遐迁,永萧□于积祀,到大康之□□□□□□□栖□□水□□□□鳞。君将□□□之蟠,奋朝阳之羽,□□箕之入周,陈洪谟于晋宇。享年不永,春秋知命,□□而□。夫□□君徳,□铭大勲,今之通义,人道之□事也。君元子,西曹、章安二县令、奉车都尉衠;仲子□□□□大夫□□掾□。□子散骑侍郎、前将军、历阳、宣城二郡内史喈。仰堂构之遗荫,蒙析薪之负荷。咏□□□永思,感蓼莪□□□。□□山以代君,命执翰以褒德。庶同辉于日月,垂永照于罔极也。乃作颂焉,其辞曰:
皇纲不□,天裂地□。煌煌南基,敌辉北辰。桓桓□□,□命作□。龙啸江□,威响北振。运否承泰,六合□一。帝鉴海岳,求其隐逸。将弹南冠,入亮皇室。我翼未挥,□□□折。何用不德,命此执翰。镂金作颂,亿载不刊。
泰宁三年岁次乙酉十二月壬戌朔一日壬戌立。
全碑校勘后共计得760字,阙185字,除阙字尚存575字。
注释:
① 西曹,两晋以来并无西曹县,笔者此处怀疑为碑文记载错误,按字形推测此处或为庐陵西昌县。
② 欧阳修《集古录》与《云间志》载《陆祎碑》都写作“宣威内史”,按《晋书》,应当作“宣城”,校勘后的碑文也据此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