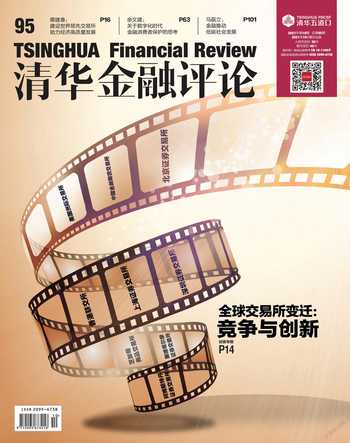以交易为业:为“常青的事业”找到“流动的资本”
回归初心来看,在交易所,无论其交易的是股票、债券、期货、信贷资产还是PPP,本质上都是“使水载舟”的机制集合。铁打的实业唯有找到流动的资本,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流转效率,从而使得,实业常为新,金融行致远。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吕氏春秋·尽数》
二战期间,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以《安妮日记》著名于世。但鲜为人知的是,安妮一家曾购买过一张荷兰“烈克戴克水坝”(Lekdijk Bovendams)债券。这张债券创造了一个信用奇迹。
1648年,这家水务公司发行了面值1000荷兰盾的债券,融资维护克莱运河的堤坝。300多年来,水务公司一直在向债券的持有人支付利息,从未间断。债券不断交易过手,利息支付从未中断。即使是在二战期间,躲在密室里的安妮·弗兰克持有的债券利息,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支付。
2003年,耶鲁大学贝尼克图书馆竞拍获得了这张债券,并且每年继续从该水务公司获得11.34欧元的利息。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在《千年金融史》中说:“自始至终,资金不停地流转,防洪一直得到维护,这一古老的债券也从未食言,带给当时出资修堤者不朽的回报。”如今,在克莱河堤的弯道处,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防洪堤的工事。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这张债券之所以能够始终地不断交易换手,也许正是因为人们相信这项公用事业能够持续,相信水务公司能够做好确权和变更的登记,能够及时、有效进行收益的结算和支付。信用奇迹的背后,是一整套运行良好的交易机制和基础设施,使得长期运营的事业与进出有序的资本达成了一种美妙的平衡。
从室外到室内:先有交易,后有交易所
去阿姆斯特丹旅行的人,不会错过阿斯米尔鲜花市场。那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必讲案例之一:每天全欧洲的鲜花在这里拍卖,随即分装、打包,运往全球各地。这样精致而又宏大的工程,正是靠着“交易”二字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得以高效准确运行无误。
在1602年的阿姆斯特丹,由1143名投资者出资645万荷兰盾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好望角以东、麦哲伦海峡以西的贸易。远洋航行的经验使东印度公司认识到,公司经营需要长期性和稳定性,而股份层面的可流通、可交易是保持公司活力的重要机制。因此,东印度公司的章程规定,禁止投资者撤回资本,但允许股票转让。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转让成为标志性事件,意味着真正的“二级市场”的出现。
最初,东印度公司股票在阿姆斯特河上的新桥买卖,然而阿姆斯特丹秋冬的凄风苦雨让露天交易者吃尽苦头。人们自发涌进附近的圣奥拉夫教堂。不过这里也同时进行木材、食盐和粮食的现货交易,每日教堂里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然而,人们很快发现,金融产品交易并不同于其他商品的交易:投资者需要了解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情况,才能做出对股票价格的准确判断。于是,《每日报摘》等报纸信息也开始持续报道东印度公司船队的新闻(尽管一般是两天前的新闻)。
直到1611年,阿姆斯特丹议会决定,修一座交易所大楼,所有股票交易都在场内固定时间内开展。这是一个有着巨大中庭的大楼,坐落于罗金运河的石拱之上。船只收起桅杆后才可从其下通过。大楼有42根廊柱,每根柱子都有编号,方便买家和卖家约在那里碰头。可以说,那是今天的交易席位的雏形。随后,交易所推动了金融产品的标准化。过去,无论多少面值的股票都可以交易;在做市商拉夫恩兄弟的主导下,交易面额被确定为3000荷兰盾。买家和卖家都以3000荷兰盾为交易单位,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一手。但这也不是强制的,只不过那些持有非标准单位的交易者发现,小于3000荷兰盾面值的股票很难完成交易。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以3000荷兰盾为单位开展股票交易。这一切“交易制度”的积累,正在朝着今天证券交易所的方向稳步演进。
“公共目标+民间资金+行业共识”的“PPP”模式
从这个世界最早的交易所,我们也许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点:
第一,交易是先于交易所存在的。室内的交易大厅、按时开市歇市、份额化交易,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与其说是交易所设计交易品种、引导投融资交易,不如说是交易的诉求和交易诉求(甚至是遮风挡雨的诉求)催生了“交易所”。席位、经纪人与做市商的存在,和交易所大楼的屋顶、中庭和柱子一样,本质是为了促成交易和保障秩序“应运而生”。
第二,交易所是一套服务和机制的集合。形形色色的交易诉求,交易中经过博弈积累下的教训,催生了一整套挂牌、定价、信披、登记、结算、确权、惩戒等机制的合集,被立法、自律、行规和司法所固定下来,于是凝结了交易所。我们几乎可以说:交易所的内核是“市场之手”,而外在是规则和機制,前者是永恒而内生的,而后者应时而变。
第三,交易所提供的服务本质上就是一种“公私合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我们时常以为,交易所是“政府”为民间企业提供融资的公共服务;然而从阿姆斯特丹的经验(美国铁路、威尼斯公债亦是如此)看,似乎恰恰相反:起初,交易所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公共服务、公用事业开展融资而设,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公共目标+民间资金+行业共识”的有机整合机制——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一种“PPP”模式。
风险的定价与分配:交易所何以惠农助商
1848年4月3日的芝加哥,南水街105号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成立了。不过,当时这个“交易所”并无大楼,甚至没有招牌,而是“暂住”于南水街101-105号Gage & Haines面粉仓库楼上的W.L.怀廷(W.L.Whiting)的办公室。这位怀廷先生是一位谷物经纪商,也是交易所83位创始人之一。在交易所建立之前,他和同行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谷物价格大起大落,要么谷贱伤农,要么一麦难求。当时,芝加哥附近的农场主需要长途跋涉100英里,才能到城市卖掉粮食。无论用四轮马车还是水运,都需要好几周。即使到达目的地,他们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寻找买家。因此在收获季,农场主在议价中总处于弱势——高昂的仓储成本和迫在眉睫的新一季播种导致他们只能低价出售,“多收了三五斗”的困境反复上演。然而等到他们卖出粮食踏上返程后,市场上的谷物又严重供不应求,价格飞涨。
尽管商人们筹资修建了巨大的货仓,并使用蒸汽动力驱动的传送带提升了运输速度,从而使芝加哥成为小麦和其他谷物的仓储中心,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仅有仓库是没有用的。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均已经习惯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并且随时讨价还价。因此,一开始芝加哥的粮仓实际上是严重空置的。直到1857年,交易所推出标准化的仓储,所有入库的粮食都经质检后分类,按等级、规格排序储存,形成标准化的“仓单”,情况才有所改善。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可以提前围绕供需进行谈判,在粮食实际运到之前,锁定交割粮食的质量、价格和风险。双方形成了“远期合约”,并用电报形式进行协商和确认。而交易所要做的,就是记录并确认这些交易,然后联手仓储商做好储存、分级、称重和标识工作。每一批运进仓库的粮食,都将形成一份对应的仓单,而仓单可以作为远期合约交易的标的,也可以独立作为金融工具进行支付和融资。当时人们评价:第一批带有等级的粮食仓单于1877年开始签发,而谷物金融化的时代自此开始。
此后,商业模式完全改变,即期交易和远期交割在价格上的差异,开始展现出对冲风险的功能。换言之,活跃的交易得以为风险定价,为预期指路。农场主可以转让、质押仓单,在交割之前获得收益;粮食收购商也可以提前认购仓单,锁定价格并在交割日按之前的价格收货。卖方降低了仓储和营销的成本,实现资金回笼和扩大再生产;买方规避了价格波动的风险,甚至可以在仓单交易中投资获利。期货交易随之发展起来,并吸引更多资金进入芝加哥,建立更多的大宗商品物流枢纽和仓储基地,并形成多种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而最得实惠的,莫过于美国农民,他们得以不断扩大规模,提升产能,并将美国农业迅速打造为工业化大生产的现代产业,直至今日仍令世界各农产国羡慕不已。
提振直接融资,促进信贷资产流动实现“多方减负”
从上述故事来看,助力实业,脱虚向实,既是金融业的使命,又是交易所行稳致远的关键。然而,对比美国、欧洲甚至一些亚洲国家,我国的直接融资比例不高、金融资源长期沉淀,已经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尽管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相继推动股票注册制改革,债券、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简称ABS)市场也在不断壮大,但是体量庞大的信贷资产“趴”在账上难以盘活,仍然是我国金融生态的底色。因此,一边是融资难,许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贷不到款;另一边是融资贵,许多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还赶不上当年的利息。资本何以助力实业,交易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盘活存量的作用呢?
其实,即便是直接融资比重最高的美国,银行也曾经掌握大量的金融资产。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信贷资产交易市场兴起后,情况有所改变。越来越多银行将信贷资产迅速在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LSTA)等市场转让出去,或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担保贷款凭证(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简称CLO)等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实现资金回笼,降低资金成本,化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这一市场当前已相当成熟,形成了做市商机制(进行连续报价,承担成交义务,赚取交易价差)和经纪商模式(如FDIC、DebtX、First Financial以及Mission Capital等)。投资者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各类基金,如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高收益债券基金、保险基金、贷款型共同基金等。该市场还有专业的信用评级、第三方估值定价机制在发挥作用,并由IHS Markit公司的ClearPar平台等登记结算机构提供清算结算服务,确保资金交割和资产过户的顺利完成。
几乎所有的机制设计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美国银行业发展也出现了瓶颈,一方面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大,信用风险高度集中;另一方面贷款利率增长受阻,银行业竞争加剧。信贷资产的交易,既帮助银行盘活了现有贷款资产,提高流动性,实际上降低了利率水平,又为银行提供了主动信用风险管理和投资的工具。这样,能将原本集中于银行的金融资产和风险分散到各类投资机构(均具备较强的分析和对冲能力)手中,将间接融资转为直接融资,缓解了系统性风险在银行体系的集聚累积。这一经验对于中国信贷资产交易所市场的建设,不无参考意义。遗憾的是,虽然包括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在内的交易场所近年来大力参与开展信贷资产交易,但最高的时候成交量仅占全市场资产的1%左右,远未能起到彻底盘活存量、提振活力的效果。
以PPP为例,以“PPP”为业
早在17世纪的荷兰人就明白,东印度公司的运营管理固然应当保持稳定,而各类资金的进出则应该允许流动,应当允许各类资金在项目周期内完成“接力”。另一方面,正是這种资金的进出有序、交易无碍,更能够有效监督运营者的勤勉尽责,否则资金会“以脚代替手投票”或者以股价给予红牌警告。
这个道理对于东印度公司的投资者适用,对于信贷资产交易所市场的建设也适用,对于PPP等公共设施投融资工具的二级市场交易而言,这种流动性更是宝贵。借用航海的例子,实业是船,资本是水。交易所的初心就是为“常青的事业”聚集资本和人心。实业的运营者应当专业和稳定,而资本的流动恰恰是推动实业不断向前的动力。长达数十年的PPP运营周期,必然会面临股权、特许经营权、收益权等多次交易过程;但是,每一次交易不但不应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还应该利用好这种流动性,以交易的流动性,作为公共设施(如PPP项目)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
越是物有所值、透明高效的项目,其可融资性和可交易性越强。反过来,二级市场的交易越活跃,越能对项目形成筛选和评价。在交易过程中,规范的高质量PPP项目自然会被市场机制甄别出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接力”。交易所不但能够而且应该为PPP等公共设施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助力,为资本的进出有序、顺畅流动提供交易机制。这既是交易所的功能,也是作为“公共目标+民间资本+行业共识”的金融基础设施的使命所在。回归初心来看,在交易所,无论其交易的是股票、债券、期货、信贷资产还是PPP,本质上都是“使水载舟”的机制集合。铁打的实业唯有找到流动的资本,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流转效率,从而使得,实业常为新,金融行致远。
(丁化美为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总裁、天津金融资产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本文编辑/王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