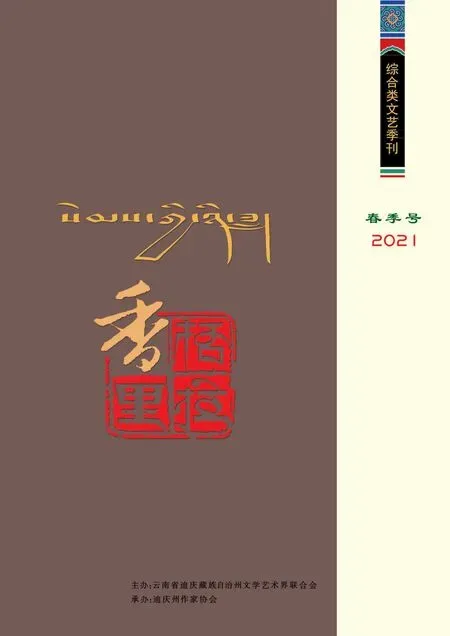龙头江笔记:成长游戏
◎吴治由(苗族)
龙头江笔记:成长游戏
◎吴治由(苗族)
人似乎天生就会游戏,并在各种游戏中得以一点一点地成长。
这听起来多么的不可思议。可只要稍一细想,似乎还真是那么回事。所以每次只要一回想起自己远去的童年,都会情不自禁心生感慨。那情形就仿佛一切过往都是反向的未来,一切忘却只不过是为了一切的记忆。以至有一天我也忽然意识到,如若现实不曾欺骗任何一个人,那么在 1980 年初,以超生、罚款换得一纸人间入场券的我,在四岁左右时就已对这个世界有了自我的认知,并触摸到了游戏与生命之间存在的那层微妙关系。
那时候尚还年幼的我每天早晨只要起了床,就从村东头的家中出发,直奔村南边的家族二哥和大哥家。在那里,我可以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侄女侄子,及村中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孩在一起疯玩,无忧无虑度过每一天。
说来奇怪,每次看到我离开家走出院子即将消失在拐弯处,我的父亲母亲和至死时都未曾挺直过身板的奶奶,他们总会相互效仿,从身后追出来一句“又出去玩了”“记得早点回家”之类的话。不过还好,我当时已懂得了什么叫应付。回头瞟了他们一眼, 什么也不说,转过身又继续朝着既定的方向挪动脚步。
幼小的我喜欢拖着一张轻飘飘的影子, 穿过屋旁被风捋得稀里哗啦喧响个不停的竹林,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后来,在拐过龙头中学的围墙后,原本被树荫遮蔽的天地忽然变得敞亮了起来。几块随时令变化和更迭的庄稼,或满或空的稻田旋即出现于我的眼前。当然,紧跟着出现的还有那些在庄稼丛中无序翻飞的鸟雀、蝴蝶、蜻蜓,以及无数叫不出名字的小飞虫。
再后来,我又经过了一户人家的门口, 两户人家的房背后,从村中唯一的小卖部门前闪了过去。几乎是在抬头望向龙井坎上那棵腰身粗矮的皂角树,和皂角树下家族二哥家灰褐色房顶的一瞬间,捕捉到了高一阵矮一阵的呼喊声与欢叫声。
是他们!我的侄女阿娣、阿池,侄子阿建。他们在我还没有到来前已玩开了,玩嗨了。不由多想,我像突遭电击似的原地蹦起, 踮着脚尖绝尘而去。
那时候我们总不厌其烦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什么老鹰抓小鸡、捉迷藏、摸鱼瞎子、斗鸡、下石子棋、过家家……有时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沙堆,也能将我们留住。然而留在记忆深处的,却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样游戏而已。
斗 鸡
斗鸡,这是用膝盖当武器的一种游戏。我们把男孩和女孩平均,以高矮、胖瘦、血缘, 以及彼此间是否具有好感等为条件将人分成了两拨。如还有单出来的,一个个就都高风亮节,异常慷慨地宣布那人去当替补,兼做裁判。等一切准备就绪,两拨人马就像冷兵器时代对垒的两军士兵,纷纷抓住裤脚勾着鞋帮拎抱起一条腿,昂首挺胸,呈金鸡独立状等待进攻的命令。
在这场混乱的比拼中,最先败下阵来的往往是一帮女生。她们秉承了不善争斗的天性,战斗刚一打响就丢了盔弃了甲,扶着笑弯的小腰,跌跌撞撞走到场边,摇身一变成了隔岸观火的人。我们男生则不能效仿她们, 得咬紧牙关神情紧张意志坚定地继续战斗, 哪怕膝盖在一次次的碰撞中发出声声沉重的闷响,疼得一个个龇牙咧嘴汗水直流,也绝不会有谁轻易示弱和转身败逃,都要坚持战斗到胜负分明的最后一刻。可一般而言,能遵守规则直至平稳收兵的场面向来不多,其间总有一两个缺乏勇武精神的家伙,他们老是喜欢打破常规,刚刚退场又起死回生,偷偷摸摸再次冲入阵地,让原本精彩纷呈的场面一下子炸了窝。
父母因此常指责我不爱惜衣物,尤其是把那两条已经到了无法再下针的裤腿托在手上时,原本还算平和的话里就突然多出了疙疤。而我却毫不在乎,相反在心底里还萌生出了一种类似成就感的东西。他们哪里知道, 我除了喜欢听裤腿“滋”的一声突然撕开了一个大口外,还从未给她们丢过一次脸。哪怕很多时候到最后要与我一争高下的,除了虎头虎脑身体滚圆的侄子阿建,就是村中个别好斗成性且比我高出半个脑袋的对手…… 哪怕在面对他们时我难免会心生怯意,可最终我还是勇敢地战斗到了最后。
值得一提的还在于,整个短兵相接的过程中,小小年纪的我已学会了冷静应对,全然不顾围观看热闹者大声的吆喝和唯恐天下不乱的言语刺激。
哎呦,叔叔快斗不过侄子喽!你看那副要哭要哭的样子……
哪里?你搞错了没有,那是人家在思考着该怎样反击。
倒也是,他一定在想,接下来的这一击是从上面落下来,正中对方的小肚,还是从低处往高处扬,直捣黄龙!一招定输赢。
……
不管怎样,身处斗场,我和阿建都是要全力以赴的。我们要捍卫各自的辈分与尊严, 叔叔不能败给侄子,而侄子又怎能被叔叔给打败?无论是在几千年前的罗马角斗场,还是几十年前龙头江边上的坪洋村,这应该是每一个斗士与生俱来的精神世界,必须为自己的身份和选择战斗到底。
除此之外,我们有时也能快速识破成年人间被遮蔽起来的那些邪恶,不仅心有灵犀地放下“武器”,鸣金收兵,还用指头撩拨一下鼻翼,“哼”的一声潇洒走开。当然, 有时我和侄子阿建也要统一战线,以同一个姓氏和家族的名义,对阵那些同样拥有着相同姓氏和同属一个家族的男孩。这是一场格外庄严而肃穆的战斗。不仅在所有的围观者看来如此,作为当事人的我们自己看来更是这样。所以在发动进攻前,我们往往会心有灵犀相互鼓劲——要勇往直前,力争第一波进攻就能将“敌人”一举干掉。可往往遗憾, 这样使空气凝滞,清晰听到呼吸与心跳的场面注定会招来家长。那情形就像事前有人去通了风报了信,使得他们总能及时出现,并成功地制止了一场由游戏发展起来的姓氏与姓氏、家族与家族、派系与派系间的大混战。于是,我们只有识趣地放弃了这场箭在弦上的战斗,赶在隔空就拉响了警报的父母到达身边之前,抬起胳膊冲对方秀了秀根本尚未长成的弘二头肌,快速地撤离了现场。
可后来直到我们长大,才发现那时候我们小孩间的战争虽被平息掉了,但他们大人间的暗战才刚刚开始。哪怕是直到现在,似乎也从未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消解过一丁半点。
过家家
过家家,这种游戏我们不跟别的小孩一起玩,只发生在我和侄女、侄子之间。用我们父母的话说,别人家的小孩无论男女,总的来说都比较好强,跟他们在一起玩,被欺负和吃亏的难免总是我们。先不说这话在现实里是否客观、公正,也不去管别人的父母会不会在背后也这样议论我们,可我们喜欢说这话时在他们脸上浮现出来的那种既复杂又充满了溺爱的表情。我们呢也就像真的刚被别人家的小孩欺负过,耷拉着耳朵,很听话似地又跑出去玩去了。
我们按照游戏规则组建家庭,父亲母亲、女儿儿子,一家四口。或者,丈夫妻子,一夫一妻,两个家庭。原本我那在游戏中可以忽略不计的长辈身份优势这就凸显出来,不仅能够赢得优先选角、选人的权利,有时甚至还可以乱点鸳鸯和发表指导意见,活脱脱像个忽然被尊崇并拥有无尽权力之人。我只要冲着阿娣或阿池一指:就你吧,两个侄女中就有一个成了我的“妻子”,未被钦选的那一位自然就顺理成章地,要么成了我们的女儿,要么就跟阿建结成了夫妻。
说来奇怪,成人生活中的那些悲伤、沉重的内容,一旦被我们当成游戏来演绎,竟充满了无尽的乐趣。比如阿建和阿池模仿父母吵架,阿建会咬牙切齿,对着眼前的妻子紧绷一张气急败坏的脸,鼓胀着一双随时可以夺眶喷射的眼珠,握着两个嘎嘎响的拳头, 警告加威胁地说:你再顶,你再顶一句嘴试试,老子今天不收拾收拾你,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就不姓 × !说着,把拳头变成巴掌举到了空中。配合默契的阿池这就视死如归, 挺起胸脯,仰着一张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脸, 迈着小碎步迎上去,针尖对麦芒地将自己的鼻尖对着对方的鼻尖,拖着一副哭腔破声控诉:你打你打,有本事你就动手,我决不还手, 你打你打你打死我啊,我、我不活了,呜呜。阿娣演割草归来喂牛马的片段,她用一根细木棍当挑子,在两头插了两匹南瓜叶当草, 走路时故意一高一矮地颠着肩膀和屁股,让前后的“草”随着步伐一悠一晃,之后是一个熟练的侧身摆肩,将草挑子卸放在圈舍边上,接着一边吁气小歇,一边抓着被露水打湿的青草扔给将脑袋探出圈门乞食的牲口,用充满溺爱的咒骂加驱赶的方式跟牛马说话:你这牲口、饕餮鬼,一天到晚就知道伸长脖子吹鼻子瞪眼诓人讨吃,哎呀,还不赶快退回去,闪开闪开!你这样挡着,我怎么扔(草)! 你看看你看看,每天不骂你几句,你就欠皮子, 得脸,看来平时活还是干得太少了!……
有时我们也假扮一家人邀请另一家人帮忙干活。天刚擦黑,隔着屋外的刺篱围栏, 我一面脚步很响地走一面扬起了嗓子:阿建, 阿建,有人在家吗?当得到回应,我立马改变话锋:哦,在家那,见灯亮着,我还以为在外面干活没回来只有小孩在家那。阿建应和着我,用两手比划着假动作,很客气地把我迎进家门,又是递凳子又是递烟点火,忙个不停地问:大伯有事?我就干咳了几下, 慢条斯理地说:其实也没啥,我家在大坡反面的那块地,这几天天气好,日它娘的杂草都快高过包谷秧了,我看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天什么是包谷什么是草都分不清了,这就想着来看看你们两姊妹明天有无时间,去帮我薅一下地里的那些草,不说你也知道, 我家就那几颗颗人,一年四季,只要忙不过来就要请求支援,搬你们这两个大救兵。阿建故作沉吟,眼睛滑向自己的妻子(阿池), 一番眼神交流之后回过头来微笑着说:既然这样,那明天我们就先去帮帮你们,大伯, 你还没有吃晚饭吧?家里前几天新烤了几斤红薯酒,不走了,留下来,我们炒几颗黄豆, 一起尝一尝?等对方言毕,我就一边起身告辞一边不失感谢和继续坚持客气:多谢了多谢了,不吃了不吃了,我还要到寨子里去×× 家去,再找两个帮手,要不然明天一天搞不完,万一老天突然变脸,那就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去了,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到我家里去喝他娘的个痛快,我家那个前段时间也盘了新酒,到时候放开了喝!
一番琐碎的日常完毕,我们演绎起了两小无猜的起居生活。我们在草地上划了两块地当房间,一对夫妻一间。我们以地为床, 草为垫,天空想象成蓝被子,云朵当蚊帐。这多像长大后,在武侠小说里读到那对侠侣“地为床天为盖”的盟誓!开始,我们相安无事地躺着,两手支棱着后脑勺,目视天空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后来,太阳绕过云层掉进了眼里,我们就起身走向不远处的瓜垄,各自摘了一张又大又圆又绿的南瓜叶子回来,盖在脸上,等太阳再次被云层吞没, 便侧过身来默视对方,任由从龙头江涌上来的暖风一遍一遍地拂过我们,钻进村庄里去。再后来,就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我们脱掉衣服睡觉吧。此话一出,我和阿建就吃吃地笑,女生则用手捂住了眼睛,羞红了脸。最终我们还是满足了那个人的提议, 跑进了无人看见的柴棚或草房子。自然,那也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赤裸的身体, 也是第一次从彼此身体的轮廓上对男人和女人有了一个粗浅的、形式上的认识。我们小小的身躯,脑袋和腰身像极了深冬里扑了霜灰的冬瓜,四肢则分别由几个藕节组成,至于有些地方不是与一个掉了花的瓜蒂相似, 就是一支藕尖刺穿水面后被阳光剥开了一张粉嫩的小嘴。
说来奇怪,这样的游戏我们似乎只玩了一次,很快就被无所不知的父母给严厉地制止了。
我的父亲母亲告诉我:十三,你是叔叔, 属老辈,不能跟他们玩这种游戏。家族二哥二嫂和大哥大嫂也告诉我的侄子和侄女:阿池、阿娣和阿建,你们是小辈,这种游戏跟外边的小朋友玩可以,但不能跟我们家十三叔玩。
这些话当时我们还不能理解,但我们却又都很懂事似地,认为既然大人都说我们在一起不能玩这种游戏,就有它不能玩的道理, 就不再玩,转而去玩别的去了。
不过那时候的我们也会感到纳闷,辈分是个什么东西啊?不就一个游戏吗,怎么就不能在一起玩了呢?还真是!
沙 堆
沙堆,普普通通的一堆沙子,只要一块平平常常的砖头加入,就产生了格外的魔力, 总能轻轻松松缠住我们半天或一天的时光。
那时候我们从来不管沙堆的大小,也不管是村里运来修沟渠,还是村中哪一户人家用来砌灶台,亦或是打地坪的,只要听说哪里出现了一堆新的沙子,我们便闻风而动飞奔前往。一旦抵达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或弓身驼背,或不惜双膝跪地冒着磨破裤子被父母用棍棒招待的危险,把手中的砖头想象成任何一种车辆,嗨玩起来。我们那时候能想到的,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上寨大胡子高的那辆气宇轩昂,只要一发动就整个村子都能听到动静的拖拉机;第二种是龙头镇那辆威风八面,从村口的公路上跑过总能带起一条长龙的军绿色小包车(吉普); 第三种是只听大人们在闲聊时说过,从未亲眼见过“跟百足虫一样”的铁皮火车。
我们用口鸣笛:嘀、嘀,呜、呜;用鼻腔代替发动机:嗡、嗡,嗡嗡;同时还像见过火车的大人那样,模仿火车的脚步声:咔嚓、咔嚓。沙堆上的我们就像一群秋天里落在草堆上的鸟雀,一个跟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 从低处到高处、从高处到低处,辗转腾挪, 不停跃动。于是,不到半天工夫,原本好端端新崭崭的一个沙堆就在几个小屁孩的折腾之下坍塌了下来,在平地上摊成了好大一个沙盘。而我们也无一幸免地变成了人形沙雕, 那脸就像戴了面具,上面除了三个鲜活的孔洞格外扎眼外,还有鼻尖之下嘴唇之上的那片小小疆域,由于有两条暗河的不断冲刷依旧闪现着皮肤应有的色泽。
然而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的沙堆总是玩不够的,似乎每次才刚刚玩开就出了意外。大人们总像一个无足的鬼怪,突然就跳了出来。
如果沙堆是属于村集体的,来人就会大喝一声:哦嗬!你们这帮小杂毛,看把沙子都踩成了什么!?还不赶快给老子滚开!如再不滚,老子就让你们的父母来收拾,累死你们的妈。
我们明白对方炮筒里的话,前半句是在赶我们,后半句则是在骂人。至于骂什么, 愣在原地的我们都还来不及想上一想,就把手上的砖头一把扔掉,撒腿抛开了。
如果沙堆是某户人家的,那情况就变得异常的严重了。只要感觉到稍微的风吹草动, 我们就得像一群惊弓之鸟,快速逃离那片是非之地。要知道,这些人往往比前者还狠, 他们得不顾一切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光老远就要指天跺破口大骂,还气急败坏捡起地上的泥巴和石子狠劲地扔过来。如此了都还不解恨,傍晚他们还会登门造访,当着大人的面,吹鼻子瞪眼,不仅指着我们的鼻子尖得理不饶人大声训斥,还含沙射影把我们的父母也数落一通。而我们的父母呢,自知是膝下的孩子理亏在先,只好硬着头皮强颜欢笑应对,往日的威严早已一扫而空,只剩下了一副铩羽的情态。天下人都知道,那是父母在替我们的成长游戏埋单,并以此换取对我们的保护。
吴治由 生于 1982 年 6 月,贵州省都匀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 37 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诗集四部。长篇小说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曾获贵州省第三届乌江文学奖、第三届尹珍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