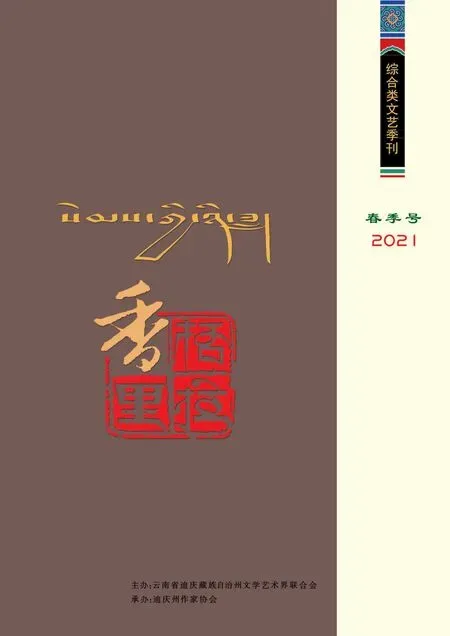我爹我妈
◎李贵明(傈僳族)
我爹我妈
◎李贵明(傈僳族)
一
爹 73 岁那年,大哥病逝
老年丧子,人生不幸,疼痛刻骨铭心
爹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让给了哥
全程看完我们埋了他的儿子
之后躲进房间,每天喝酒,仿佛这世界与他无关仿
佛剩下的六个子女,都不是他的
我们偶尔围着他的房间转
害怕阳光照不到他的房子
爹闭门不出,犹如一个绝尘的隐者
爹的时代,他有自以为豪的“初小”文凭
我不知道“初小”到底是个什么文凭
他会写汉字,但一生都没有当过小队会计
他有一副眼镜,只有在翻阅农历的时候才有用场
73 载中的 10 年
1935 年到 1945 年,爹在兵荒马乱中捡食野果
目睹他的爹和他爹的兄弟与抢夺羊群的土匪血战一夜
他爹的兄弟,在砍死三个土匪后,被土匪的火枪击中
肠子流了一地,传教士用了一个星期
把肠子塞进肚子,把炸开的肚皮缝上,活了下来
活了很多年。他爹和他爹的兄弟,相继死去
他们找了个地方,埋成一排
很多年后,我经过那里,走得飞快
我害怕爹的爹,从坟墓里伸出手来,像他死亡的时刻一般
向我索要一块火烧玉米饼
1955 年,爹 20 岁,昂首挺胸走进新的中国
拥有革命的激情,吃不饱的命运仍然没有改变
20岁的爹,娶了个美女,就是我妈
他们吃洋芋,包谷和苦荞
没什么娱乐,没有电,大地一片漆黑
食不果腹,只有亲吻和拥抱有些许温暖之光
那个年代,儿女的数量是衡量“英雄母亲”的尺度
他们生下了一个姑娘、两个姑娘、三个姑娘、四个姑娘
从大炼钢铁,生到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大革命生到包产到户
他们就像一对旺盛的生育机器
为祖国生下了九个儿女,其中两个夭折
七个成活
1965 年,爹 30 岁
中原大地,饿死不少人,草根树皮全被吃光
滇西的群山里,爹和他的同伴,打点田鼠,挖点地瓜,熬日子
第三个姐姐饿得不行,哭闹着要吃鸡肉,家徒四壁
被她爹扔进粮仓,女儿的哭声在空空的粮仓里回响很久
停了下来,爹担心饿昏了,打开粮仓
看见他的女儿费尽周折
抠出了 21 粒玉米
第三个 10 年,爹和他的祖国一道进入大革命的时代
开会,斗争,批判是生活的主要内容
肚子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初小”文化的爹,没什么政治觉悟
混不着会计,保管员等吃香的差事,混不着集体食堂的司务长
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被生产队长用来调度,集中
灌输,他是思想意识不高的群众,是沉默的一群
看见别人被拉出来游街,批斗
爹暗自庆幸自己是个穷光蛋,避免了改造和批判
我爹我妈,靠工分养活儿女
也当众历数美帝苏修和走资派的罪行
对那些未知的名词,不知道土里刨食的爹
哪来这么多仇恨和愤怒
1978 年,春天,滇西的桃花全部打开
爹和妈生完我这个儿子,祖国传来计划生育的消息
妈也到了更年期,免去了结扎、放环等复杂的程序
我爹我妈的七个孩子,在祖国的怀抱中幸福成长
他们凭借承包来的四亩三分地,养活这七支
祖国的花朵祖国的花朵,饭量惊人,衣服要七份,鞋子要七份
书本要七份,学费要七份,还会生病,逃课,打架
我爹我妈从土里刨食,自力更生,历尽艰辛和屈辱
把七支花朵拉扯成树苗,他们的头上也堆满白雪
2008年,爹73岁,看着他的大儿子在疼痛中死去
看着他儿子的兄弟姐妹们,摆了几十桌,忙活几天,哭了几场
埋了他的儿子。然后各奔东西
2011年,爹76岁,按照他自己的预言,还可以再活七年
躲进他的房间,闭门不出,像是看空一切,在倒数时光
70岁的老伴为他做饭,洗衣,每天看看他
骂骂他。像两个孩子,却是相爱至老的亲人
哥哥姐姐劝我爹,喝酒之余,到村头的山上走动走动
嗅嗅新鲜的空气,土地的气息和温暖的阳光
爹只说了一句,没意思
躲进烈酒之中,爹与这个世界划清界限,独来独往
只有在剩下的六支花朵偶尔来看他们时
才会走出房间,聊一聊,问一问,看一看
穷尽一生的我爹我妈,受尽屈辱和苦难
有着无法抹去的伤痛和记忆,苦尽甘来,他们却日渐苍老
仿佛他们的时代正在转过身去
二
2015 年,爹 80 岁,祖国走进新时代
风起云涌,世界之事苍茫而又亘古轮回
历经 7 年的丧子之痛,爹走出房间,每天在铁皮棚下晒太阳
抽旱烟,不想问题,不做贪图之梦
对偶尔路过的人们点头
从早到晚,看云流变幻,日影穿行
爹思维清晰,视力敏锐,牙齿整齐,身板笔直,言语清楚
却保持着长久的沉默,仿佛这世界已无对话的必要
任繁花路过,秋月升起
我妈依旧每天围着他转,日复一日面对沉默寡言的活木头
走过去说一句,走过来骂几句,而她亲爱的木头
全无往昔生动
保持令人烦躁的全日制安静
肚子问题已经解决,儿孙们年华似锦,母语生哽
在春天里,收起行囊远行
到江浙老板的酒店做服务生,到四川工头手下
搬砖,扎钢筋,浇灌城市文明的屋顶
也和电力技工一道,铺设城市灿烂的霓虹
也有人踏上海南的渔船,扎进陌生的大海
捕捞他们从未见过的海鲜,摆上齐铺白布的餐桌
有人被称为二道贩,收购山茅野菜,从事并不擅长的讨价还价
赚取差价,也赚取落空
他们像五颜六色的候鸟,在春天的寒花里出行
从事一切努力
期待回到秋色渐暖的故乡
他们从事需要体力的任何劳动,从不挑选
也似乎永不沉重
留在村里的儿孙,依旧继承土里刨食的行当
卖炭翁成了护林员,驾犁者有了旋耕机
所剩无几的留守妇女,是村里的广场舞表演队
穿起盛装,在黄昏时分
在群山凝固的波涛里,打开音响翩翩起舞
儿童们把七彩的塑料水桶摆成一排,离开菜园
走进美丽的学校,背诵唐诗
诗里的中国,那么壮阔,那么苍茫
而我们走得太快,来不及欣赏秋水里的月光
月亮中的草木
来不及凝视露水中的星辰,星空里的灵魂
孩子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跟着我们赶路,在即将升起晚霞的天空下
儿童的母亲们,留守大地,躬耕黄土
保持紫铜与阳光的肤色
在周末,也偶尔化妆,变成面孔白皙的少年
骑上摩托,或者搭上乡村面的,往返于集中办学的路途
接送一拨又一拨茁壮成长的花朵
他们依旧是素质不高的群众,是永恒的底层
教育培训的对象
有时被集中起来,培训麻辣火锅厨艺
嫁接果木和阉割牲畜技术
也被组织起来,观摩现代化种植示范基地
有时培训普通话,要求背诵身份证,电话号码和说出自己的名字
他们不善言辞,偶尔出丑,源于与生俱来的木讷与沉默
我妈依旧开垦菜园,种植白菜,豌豆,蒜苗,番茄
菜园的四季,盛开不同的花朵,结出不同的果实
当坚果落地,她扶门遥望,山的尽头云飞霞落
落霞之处,铁塔林立,手机信号塔,高压电线塔
水泥和柏油路面反射匆忙的现代之光
2016 年 3 月,春雨绵绵,山脊上积雪斑驳
仿佛一只豹子静伏高处
成群候鸟正在离开,像一片云遮住另一片云
我爹卧床,七日不起。剩下的六个子女
带领他们各自的花朵从天南海北群起而归
像是香火旺盛,后继有人的家庭宣示
慌张的大会,人声嘈杂,七嘴八舌,准备车辆,讨论医院
像是要掌控和摆布卧床之人的一切命运
我爹转过头来说,没啥毛病,去医院干啥
别忙活了。由于主角的发言,群龙无首的家庭大会安静下来
我爹轻声告诉我,祖父左侧,足下一尺
是他的长眠之地
再来点酒吧,我爹说。两口酒后,我爹闭上了双眼
像一滴露水,像一片云,像一只远飞的大雁
离开了这个难以表述的世界
3 月 8 日,送葬的人们走向山头。走向天空的队伍
把一个儿子埋在了他父亲的身边
与他逝去的兄弟们,排成一排,在村落的对面
父亲无疾而终,魂归先祖之地
像是一滴露水奔向阳光,一颗流星飞向天际,一只大雁永恒归队
又像一朵简单的云
偶尔浮在故乡的上空
三
斯人已永去,幽思长长存
我爹我妈也曾滴翠青竹
华彩出众,鹤立鸡群,也曾嫌车马迟迟,书信遥远
也曾青春同堂,信誓旦旦,非你不娶嫁
凡人之死,如同我爹,习以为常,普天日日都上演
对我妈而言,却是一位皇帝的驾崩,一座江山的坍塌
一场爱情的终结,一次永恒的告别
意味着从此孤芳自赏,形单影只,茕茕孑立
意味着出双入对,相爱相恨成为永恒的往事
在傈僳的民谣里,常常被叙述成一对天鹅的泣血离散
没有惊心动魄,唯有孤傲自守
我妈常常独拭泪水,恐被人见,像故乡屋顶单薄的白露
只有一滴泪,流进自己的心里,是对往日的怀念
是年迈体弱,难以继续关照的日益忧虑
我爹睡了,没有再醒来,从此铁皮棚外,瓜蔓藤延
朝霞夕光,棚下空无一人。那间幽暗的小屋没了往日响动
没了日出日落。没了星辉与月光
他成了古人,祖先和一个微不足道的名字
只有路过的人们,对夕阳下的坟头指点,才被偶尔谈及
他成了一个影子,一张单薄的旧纸
在浩荡向前的尘世中,没有人会在意纸上图形的曲线
他成了一捧黄土,与草木山石一起呼吸,与春花秋叶一起呼吸
与天地山河一起呼吸,与此世无关,与此世有关
在我妈的世界,他成了一场梦,一道光
忽明忽暗,照耀她活着的每一天
除了孤独,我妈的世界必须转动,而且更加
日新月异。祖国开始惩治贪官污吏,消灭人民贫困
滇西北的穷乡僻壤,机器轰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改造房屋,升级4G信号塔,安装网络电视
成群结对的工作人员,在队长的率领下,进村入户
统计户口,务工人员,鸡羊牛马的数量
筛选穷人和富人,建立台账
吃了几袋大米,杀了几只鸡鸭
宰了几头年猪,务工收入几何,都一一记录,在案可查
繁忙的工地和人员,要让穷人们富起来
自然村落开天辟地,建设党支部活动室
国旗升起,党旗飘扬
把更穷的人民,搬到城市,住进高楼,在电梯里进出
热闹的景象,像一场战斗,一次宣泄,一种人类制度的宣言
在宣言中,文盲水平的我妈,被归为脱贫群众
在热闹的乡村建设工地,她门庭冷清
左邻右舍,穷亲富戚,在集体分析千年贫困根源
在举手表决现代产业发展之道
她人户分离,独居一隅,与此无关
我妈性格开朗,像一个孩子,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
常常打探关于精准扶贫的各种名词解释
扶贫工作队任务繁重,行色匆忙
儿孙们各操事业,东奔西走,早出晚归
谋生,或者加入那场宏大史诗的扶贫战役
像光临屋前树上那只歌唱的黑卷尾
我妈常常独自问答
只有村里的保健员前来,她才有摆开家常的机会
轰轰烈烈的革命中,火塘已经过时,旧时代的木房已被拆散
与此而生的民歌、神话、寓言
仿佛昨日帝国,正在分崩离析
而又以不同的面孔恒久延传
旧物已不再
只有在周末,我妈才有机会偶尔看见
她的重孙们离开校园,回到家里,打开电视
然后用各种姿势刷抖音,聊微信,网购,在游戏中战斗
不时抬头,说出几句标准的汉语普通话
儿孙满堂,物质充足,衣食无忧,就医不愁的我妈
是孤独的局外之人
儿孙们向互联网俯首称臣。近在眼前,相隔千里
智能终端的激烈包围中
她的蓝屏手机正在和这个世界失去联系
现代化的节奏,无孔不入
我妈难以掩饰与世隔绝的孤独与悲伤
周末的黄昏,村里的人们集中起来,拿出笤帚
清扫水泥路面,捡垃圾,叠被子,整理家庭内务
投入美丽中国的建设
我妈每日喂鸡,清扫落叶和尘埃
影子投射在院落的水泥地上
一个长长的感叹号,在夕阳的光下移动
我妈依然身体笔直,步伐稳健,追求一尘不染
美人中的美人,与我爹般配绝伦,天下无双
她活在有神的世界,在春天里
为每一朵花浇水,关心每一株白菜的成长
珍惜每一颗粮食,每一滴水
2020 年大雪之前,村庄迎来一场盛大的现代婚礼
年轻的人们觥筹交错,蹦迪狂欢之后
我妈接过话筒,唱了一段深情的民谣
歌声清脆,堪比少年,穿过茫茫的夜色
歌词壮阔如大海起伏,无人可对答,在空空的村落盘旋
曲调悠远像星子之光,独自在空中弥散
又像一只天鹅,在寻找远去的自己
当歌声落尽,我妈放下话筒,村庄归于寂静
仿佛一个民谣的国度关闭门扉
合上了一本族谱
唯有夜色深深,露茫茫
李贵明 1978 年生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约30 万字发表于《诗刊》《民族文学》《作品》《边疆文学》《大家》等刊物。诗歌集《我的滇西》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