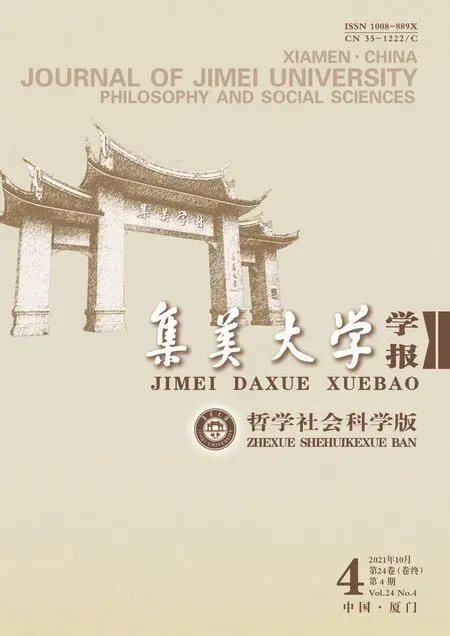中国海洋民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从“彩舟流”到“精灵流”
黄燕青,任江辉
(1.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集美大学 陈嘉庚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 言
经历了被称为“战争的世纪”的20世纪之后,“文明互鉴”成为了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大方法,也是东亚场域下各个不同的文化实体进行“文明对话”的重要手段。何谓“文明互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就此而言,本研究所阐述的是深受流传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送王船”影响的日本版“送王船”,即“精灵流”的祭祀活动,其可谓是最为直接地体现出“文明互鉴”的特性。
所谓“精灵流”,是指在日本九州地区,尤其是以长崎县为中心的地域,在日本盂兰盆节期间为了祭奠逝者送走亡灵而举行的祭祀活动。这一祭祀活动深受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和长崎华人社会中的“彩舟流”之影响,与现今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颇为相似,从祭祀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再到仪式仪轨的表现,乃至精神寄托的寓意都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子,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在空间路径中的渗透是从中国大陆场域传播到海外华侨华人聚集地,进而融入到域外世界的一个过程。
关于“精灵流”的研究,中国学界较少涉及,大多散见于日本学者对于民俗学研究的论文中。围绕这一祭祀活动的研究,日本学者野原康弘撰写了《二度目の葬式——精霊流しに見る長崎人の死生感》[2]一文,将之解析为多元文化背景下长崎人极为复杂的生死观念,突出了“精灵流”作为“冠婚葬祭”(1)冠婚葬祭:该词汇为日语,乃婚丧嫁娶之意,而“精灵流”在日本社会活动中属于丧葬之事宜。之一的风俗礼仪问题。与之不同,在日中国学者王维在其论著《华侨的社会空间与文化符号:日本中华街研究》[3]中则是站在华侨文化的立场上,将“精灵流”看作是华侨华人的文化符号,将其定义为中华传统文化在长崎的“被接受祭祀”(2)被接受祭祀:“精灵流”是被日本长崎地区接受并融合当地的民俗、习惯而形成的祭祀活动。。他认为“精灵流”起源于以前长崎华侨华人社会的“彩舟流”。“彩舟流”有祈祷航海安全、祭奠客死异国他乡的华人灵魂之意。不过,随着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中国海洋文化在日本这一场域下的“文明互鉴”研究日趋获得关注,作为“送王船”文化海外传播的典型——“彩舟流”也逐渐地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而深受“彩舟流”影响的长崎“精灵流”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基于这样的文化考量,笔者拟站在人类学的立场,就深受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长崎华人社会“彩舟流”影响的长崎“精灵流”之话语建构、思想建构、价值建构等系列问题展开研究,从而确立起现今“文明互鉴”视野下“精灵流”的典范意义与重要价值。
二、从“彩舟流”到“精灵流”的话语构建
承前所述,长崎“精灵流”深受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彩舟流”的影响,而“彩舟流”乃发端于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精灵流”就是在这种海洋文明互鉴和交流的宏大叙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因此,“精灵流”的形成与发展,既根植于东亚历史上的文化传承或者文明对话,亦来自于文化活动自身的演绎与变迁,尤其是由外来化到本土化的文化自觉。就此而言,“精灵流”的受容与演绎凸显为一种文化性的、主体间性(3)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拉康提出来的,在阐述中他给现代性的主体性以致命的打击。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这种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的话语建构,展现出了历史语境下东亚文化彼此之间的文明“对话”价值。作为“精灵流”的话语建构,在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彩舟流”以及深受前两者影响的长崎“精灵流”等民俗活动的多样化形态,解析出中国民俗文化在中国大陆场域、华侨华人集聚场域、日本地方场域等空间体系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
1.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以福建为核心的东南沿海“送王船”祭祀活动起源于“送瘟神”的习俗。根据文献记载,借助船只送瘟神的习俗大多存在于长江以南地区,明代《五杂俎》(4)《五杂俎》:该书是由明代谢肇淛论著,主要论述地理、风俗人情、民间宗教信仰等内容,福建民俗也在其中被记载。就专门记载了“闽”即如今的“福建”的相关习俗。这一活动以福州的“出海”仪式、闽南的“送王船”为代表,其目的由最初的驱瘟除灾、保境安民,转向了祈求航海平安、祭奠海上罹难者。整个祭祀活动中,经巫师行法事之后,信众将纸扎或木制彩船放在水边举火烧毁,或推入水中任其漂流,以祈求平安。这一祭祀活动既体现了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激、对于生命的关爱与缅怀,更展现出极为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且根植于走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文化之中。
2.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彩舟流”。提及现今日本“精灵流”民俗活动,则不能不提到长崎华侨华人社会的“彩舟流”。以元龟二年(1571)长崎开港、葡萄牙商船的到来为标志,日本可谓是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一时期往来于中国与长崎之间的贸易商船被称为“唐船”,随船抵达的中国人则被称为“唐人”。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以及到海外逃避战乱等因素的直接影响,不少中国人乘船来到了日本长崎,并依据祖籍地的不同,修建了兴福寺(1623)、福济寺(1628)、崇福寺(1629),此三寺庙俗称“唐三寺”,分属三江帮(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的泉漳帮及福州帮,后来又兴建了广东帮的圣福寺(1677),如此一来便形成了长崎华侨华人社会的雏形。此后至明治维新,由于日本政府的管控,“唐馆”(日文名“唐人屋敷(5)唐人屋敷:唐人屋敷又称唐馆。17世纪中叶至后半叶,日本幕府为了便于管理,将来长崎的华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一定区域,并逐步形成华人的集聚区“唐人屋敷”,即唐馆。”)成为赴日华侨华人的集散之地。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日“唐人”为了祈祷平安、祭奠亡灵,沿袭其故土“送王船”形式,以唐馆为中心举行“彩舟流”的祭祀活动。
依照《长崎名胜图绘》的图示记载,“彩舟流”的基本程式,就是在来自中国大陆的“唐船”平安抵达长崎港之后,“唐人”为了兑现航海途中祈祷保佑而向神佛或者妈祖许下的诺言,故而制造长3.6米左右的“唐船”,摆放供品与偶人,请来唐寺僧人行法事,最后将“唐船”抬到海边烧掉[4]。“彩舟流”的基本仪式按照规模大小,一般分为“小流放”和“大流放”。“小流放”举行次数频繁,分为平安到港即办,每年或隔三、四年一次不等,目的是为了祈愿航海安全,举行之际盛况空前、影响极大(见图1)。与之不同,“大流放”的目的则是祭祀遇难者或者客死长崎的中国人,故而以死者数量超过百人者为衡量是否举行的标准,通常隔几十年才举行一次,规模大、规格高。举行之际,“唐船”施以彩色,各色人偶齐备,唐三寺的僧人念经祈愿,辅助人员维持秩序,华侨华人划小船护送彩舟,到海上沙洲后将之烧毁,象征着送唐人灵魂返回唐土。日本画师川原庆贺(1786—1860)以绘画的方式留下了“彩舟流”的情形,成为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重要文物之一(见图2)。

图1 小流放(出自《长崎名胜图绘》)

图2 彩舟流图(川原庆贺作,现存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
3.日本长崎的“精灵流”。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中的“彩舟流”这一祭祀活动展现了世人对于亡灵的敬畏,对于生命与安全的追求,其祭奠亡灵、祖先崇拜的理念深刻影响着长崎的“精灵流”。历史上,鉴于明治维新之后“唐馆”荒废、华人迁移,日本政府禁止了“彩舟流”的习俗,但是深受“彩舟流”影响的“精灵流”却得以沿袭下来。长崎“精灵流”,亦称“第二次葬礼”,于死者去世之后迎来的第一个盂兰盆节之际举行。“精灵流”的核心在于精灵船的制作,分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船”和以自治会、街区等团体组织共同主办的“合祭船”,以送别本街区、本年度的亡灵为目的,表示对故人的思念,带有祭祀故人的精神寄托。
概而言之,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祭祀活动是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彩舟流”的母型,而“彩舟流”在海洋文化互鉴和交流中深刻影响着长崎“精灵流”的祭祀活动,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形成了长崎当地颇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在这样的话语建构之中,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经由海洋文化交流的路径传至长崎,成就了当地华侨华人的独特信仰——“彩舟流”,并深刻影响着日本“精灵流”的演变和发展,成就了日本人的独特信仰——“精灵流”,其不仅反映出东亚文化实体之间的“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而且折射出中国作为文化母国、文明母体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
三、“精灵流”的思想建构
从人类文化学的视域观之,民俗活动不仅体现出民俗活动场域的人文、风俗、历史,而且凸显了该民俗活动内在的思想建构。由此可见,探究当下祭祀活动的思想建构,其根本与其说是在于追根溯源地找寻这一祭祀活动的思想根源或者文化属性,倒不如说是站在思想的深层去探究这样的祭祀活动究竟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精神寓意、时空观念、道德隐喻、文化记忆。
1.作为“精灵流”的精神意寓。所谓精神寓意,是指“精灵流”这一民俗活动的举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寄托、思想内涵。在此,我们可以借助对长崎“精灵流”影响颇深的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彩舟流”来加以阐述。如果说“送王船”的精神寓意体现在驱瘟除灾、保境安民,而后与妈祖文化结合在一起,转向了祈求航海平安、祭奠海上罹难者的话,那么,“彩舟流”的祭祀活动一方面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寓意,另一方面则是对之加以扩大,即“大流放”呈现出来的祭祀遇难者或者客死长崎的中国人,使之魂归唐土的精神寄托。在这一过程中,“唐船”施以彩色,各色人偶齐备,展现了遇难者或者客死者的“生活情境”;唐三寺僧人念经祈愿,辅助人员维持秩序,突出了“亡灵超度”的佛教信仰;唐人划小船护送彩舟,到海上沙洲后将之烧毁,预示着“千里扶棺、御风而行”的宗教思维。不言而喻,这样的精神寄托亦影响着长崎“精灵流”的发展和演变。长崎“精灵流”的基础活动便是精灵船的制作,精灵船是整个“精灵流”民俗活动的重头戏之一,其制作形制与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彩舟流”颇为相似。从精灵船的制作材料、制作尺寸,再到其制作种类、规格、样式,均蕴含着日本人信仰之中的祖先崇拜、生死如一的精神寄托意寓。
2.作为海洋文化的“精灵流”,亦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阴阳时空互动的观念。所谓“阴阳时空互动”,依照中国民间信仰传统和生死观,便是生者为死者提供物质上的供给,而死者则为生者提供精神上的庇护。从深层次的内涵观之,则反映出“阴”“阳”两个世界的存在和互动。从“精灵流”祭祀活动的形制到其内涵,均蕴含阴阳时空互动的理念。“精灵流”的祭祀活动举行于8月15日,即盂兰盆节的日子。该日傍晚,长崎大街小巷皆响起了鞭炮声、钲的敲击声、人的叫喊声。死者家属拉着或抬着载有故人灵魂的精灵船,装饰以盂兰盆节的灯笼、纸花、水果等,穿街过巷,来到被称为“漂流场”的终点——大波止。不少精灵船悬挂着“西方丸”的船号,长崎港亦面向着西方(“西方”即西方净土,“丸”指船号,即前往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的船),而后皆被放入海中,漂流而逝。以前是将精灵船和供品都放入海中漂流,但现在除长崎县的偏远地区,如岛原、西海、松浦、五岛仍保留着漂流的做法外,长崎市则规定要在指定地点销毁。彼时,大波止的漂流场会有起重机等拆解机器待命,精灵船到位后,故人家属会将遗像、牌位、灯笼等要带回家的物品拿走,在船前双手合十祈祷,看着精灵船被解体,以示送死者亡灵进入西方净土世界。在此祭祀活动期间,鞭炮的“声”、各种装饰的“形”、灯笼蜡烛烟花的“光”既渲染了整个民俗活动的热烈氛围,更装饰起了日本独特的阴阳和合的世界,展现了一种声、形、光彼此辉映、相互交错的“阴阳时空互动”的世界。可见,从其祖先崇拜、亡灵超度等传统民俗活动内容观之,其阴阳时空互动的思想建构贯穿在其整个“精灵流”民俗活动的始终。
3.作为民俗活动的“精灵流”具有深刻的伦理道德隐喻。所谓“伦理道德隐喻”,是指民俗活动中所体现的个人、集体、社会的伦理秩序、道德规制。尤其是民俗活动的仪式仪轨象征着社会秩序,表达着个人和集体的社会道德意识。作为深受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影响的长崎祭祀活动“精灵流”就是如此,其仪式仪轨既是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受容,也是长崎民众生活方式的具体呈现。从精灵船的制作,到“精灵流”的队列游行,不仅反映出日本社会的独特匠心与严密的社会组织,还体现了长崎市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具有一种弘扬孝道文化、遵守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隐喻。在此,深入到“精灵流”的文化仪轨,盂兰盆节灯笼与纸花的装饰,精灵船的制作、形状与装饰,乃至整个船体大小的设计,无不呈现出一种针对故人的追思、关怀、孝敬和崇拜。一言蔽之,围绕精灵船的构思、准备、制作,供品的挑选乃至摆放,皆反映出一种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隐喻。
4.“精灵流”作为集体文化记忆的思想建构。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解,著名的人类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其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5]。“精灵流”中的精灵船便是如此,其既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物质客体,又是长崎民众共同享有的精神象征符号。因此,长崎“精灵流”的祭祀活动,无疑是长崎民众对于历史、民俗加以传承而构筑起来的集体文化记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祭祀活动的传承形式、存在方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近几年来,长崎的“精灵流”获得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已成为招揽游客的靓丽名片,更被冠以长崎夏日的“风物诗”,“精灵流”成为了长崎人共同的民俗信仰,更逐渐走向了世界。不仅如此,“精灵流”更是融入了当下的时代语境之中。根据长崎新闻社2020年8月16日报道,该年5月,天主教徒外崎莉乃身患白血病而不幸离世,外崎家族按照长崎风俗制作了以天主教堂、莉乃照片展示、史努比为主题的大型精灵船,亲人们穿着外崎姐姐设计的体恤衫,一路放着莉乃喜欢的音乐,行进在长崎的街道上。(6)该记载来自2020年8月16日刊载在日本《长崎新闻》的报道,其题为“しめやかに 精霊流し 『18歳の夢 乗せて』 白血病で亡くなった外輪さん”。就这样,“精灵流”不仅融入到长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渗透到不同的宗教信仰人士的精神世界之中。
四、“精灵流”的价值建构
如前所述,作为日本长崎的祭祀活动,“精灵流”深受来自中国的外来文化影响,将之与本土文化相交融,并对之加以受容、演变,从而建立起独特的话语建构与丰富的思想建构。那么,这样的“精灵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在此,笔者尝试站在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旅游价值等多领域的立场来加以阐述。
1.“精灵流”作为中日海丝贸易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现今的长崎“精灵流”的仪式仪轨、精神寓意均与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颇为相似,这与当时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以闽籍华侨华人为主体不无关系。提到“闽籍华侨华人”的正式登场,需要延宕至宋代之后。根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建州出海商人周世昌因遇暴风,漂流到日本。“咸平五年(1002),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6]。这一记载阐述了建州(今福建建瓯)的闽籍商人周世昌旅居日本七载,随同日本人归国之事。在这之后的历史文献之中,闽籍人物的记载不断增加,不少福建商贾客居日本,且频繁地往来于日本与福建之间,不仅从事贸易往来、物资交换的活动,还承担起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信使之职。因此,作为“闽籍华侨华人故土的民俗活动”——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便经由海丝贸易的路径,移植至日本并演变为长崎华侨华人社会的“彩舟流”,从而影响着日本“精灵流”的发展和演变。
而作为日本地域文化之一的“精灵流”,是以九州地区的长崎为中心地域,于每年8月15日为固定时间而举行的一种祭奠死者亡灵的盛大仪式。这一仪式源自江户时代流行于长崎华侨华人社会的“彩舟流”,目的是为了祈祷航海平安、祭奠海上遇难与客死异国他乡的亡灵。而“彩舟流”则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一言蔽之,“精灵流”深受发端于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的长崎“彩舟流”的影响,是华侨华人文化在长崎的“被接受祭祀”。作为这一文化祭祀活动的支撑,则是以闽籍海商为核心的贸易组织往来中国大陆与日本岛国之间的商业行为,或者说“海丝贸易”这样的宏大叙事。如前所述,尽管“送王船”和“彩舟流”有一脉相承的历史影子,但是两者与“精灵流”之间是否存在着历史时代的“断裂”,是否曾有一贯的传承轨迹,目前学术界依然众说纷纭。然而这一历史史实也正折射出“海丝贸易”的一个侧面,其是海洋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2.“精灵流”作为一种民俗性的祭祀活动,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多样化的文化价值。审视日本的民俗性祭祀活动,我们可以提到作为古都的京都,还有独特祭祀活动的札幌、大阪、金泽等。但是,作为一种东亚的文化传承、文明互鉴的代表,我们却不能不提到长崎这一特殊的地域。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长崎历史上汇聚了郑成功这样的华人,开拓了“出岛”这样的专门口岸,树立起了以兰学为核心的江户时代新学问,故而成为了日本文化的“滥觞”之地。这一点可以说亦体现出“精灵流”的文化互鉴和交流之中的文化价值。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灵流”是长崎地区日本民众生产生活的历史文化遗存,并通过每年定期举行盛大活动而让市民理解、认知,从而成为长崎地区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为新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传承的源泉。不仅如此,“精灵流”还蕴含着日本独有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意识,体现出了一种生活审美、文化认同、感情追求的精神价值取向,成为慰藉民众心灵的重要载体,更是长崎市民宣泄内心情感、表述哀思情怀的主要途径。最为关键的是“精灵流”作为地域性的民俗活动,深刻地反映了长崎市民对于祖先、亲人的纪念、崇敬、祭祀的根本情怀,具有了祭祀祖先灵魂、弘扬孝道文化、严守社会规范的现实价值。
3.作为日本地域性的文化活动,“精灵流”具有极为丰富的旅游价值。在此,我们也可以提到“文化软实力”这一范畴,所谓“文化软实力”,就区域而言,是指“区域文化的吸引力、当地居民的素质和道德水平、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等方面,其内涵丰富,表现为综合复杂的大系统,既有思想精神理念层面的内容,也包括文化产业经济方面的考量”[7]。由此观之,“精灵流”不仅具有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质,还具有了区域文化软实力的独特性。
作为地域文化软实力的象征之一,长崎“精灵流”可以说最为直接地体现在其作为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一方面,在“精灵流”的民俗活动中,精灵船的制作推动了原材料的供应与流通,振兴了地方经济产业,推动了日本匠人精神的构筑,促进了地域经济的拓展;另一方面,站在旅游文化的角度而言,“作为传统文化、民间和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原始性、地方性和民族性,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说,也具有奇特性和区域垄断性,能够成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8]。“精灵流”正是具有这种民俗活动的“奇特性和区域垄断性”,成为了长崎地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精灵流”不仅是一场宏大的民俗活动,更是一场独特的旅游观光盛典,不仅吸引着日本的游客,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这样一来,整个“精灵流”活动就能带动长崎的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走向兴盛。
概而言之,作为日本长崎的独特祭祀文化,“精灵流”这一活动不仅具有了重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还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价值,极大地推动了长崎地区的文化振兴、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成为了新时期日本民俗文化的一大亮点。
五、结 语
所谓“文明互鉴”,并不是一味地宣扬文化的主体性和本源性,而是要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7)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990年的12月,在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演讲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这个演讲全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90年第10期上。其指出: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们先是发现自身之美,然后是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的思想境界。作为日本九州地区尤其是长崎地区的祭祀活动,“精灵流”深受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及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彩舟流”的影响,更是融入了日本式的区域特色和地方性格,形成其民俗活动的主体间性。就此而言,这一祭祀活动可谓是中日之间文明互鉴的一大典范,也是当下中日之间展开文明对话的一大桥梁。依循这一目的,笔者探究“精灵流”的话语建构,解析其内在深刻的思想建构,进而凸显其作为海丝文化中“文明互鉴”的价值建构。不言而喻,之所以采取“建构”这一哲学性的术语,即在于围绕“精灵流”的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确证,深入到人类学的根本方法,展开深入的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研究,从而就这一祭祀活动的传统内涵、现实意义、未来价值予以更高层次、更具学术立场的阐发。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践行“文明互鉴”,实现“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