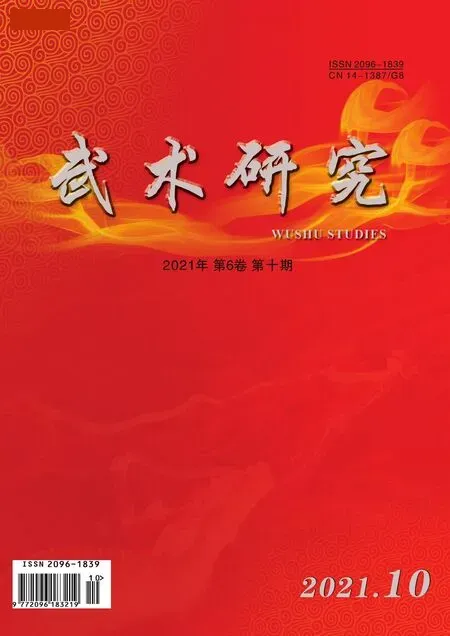自主与同构:场域理论视阈下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特征与发展机制
周丽华 唐 强
1湘潭大学体育部,湖南 湘潭 411105;
2湖南大学体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湘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西北部,作为武陵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此孕育出了独具一格、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苗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是其中一分子。随着社会发展,作为民族文化“田野”的乡村“空心化”现象凸显,文化生态脆弱,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部分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重视与保护,但原生态文化环境的变革导致苗族传统体育正面临着严重的传承危机。
1 湘西苗族传统体育形成的理论逻辑
“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借助于物理学中“磁场”概念向人们阐述社会实践学中人与各种事物之间构成的各种社会性的关系。“场域、资本、惯习”是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在此,从场域交互、资本创造和惯习形成三个方面来探讨苗族传统体育文化场域的构成要素。
1.1 场域交互:民族斗争
苗族是一个多难、不屈的古老民族,其先民在历史上共有五次大迁徙。湘西苗族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为躲战乱的第三次大迁徙而至武陵山区的崇山中隐居,而后历经唐宋时期的第四次大迁徙、元明清时期的第五次大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才结束其迁徙历史。[1]纵观湘西地区苗族历史就是一部本土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的斗争迁徙史。苗族传统体育文化随着湘西民族反抗斗争史的跌宕起伏而不断演进,如在迁徙战争中擂动的战鼓演变为欢乐的苗族鼓舞;在与外来民族战斗中的苗族射箭与射背牌;在军事训练中用于提高体能与技能项目的苗族赛马;在结合地理环境与民族斗争而形成的苗拳、苗族武术等都具有“本土”传统体育文化特色。除此之外汉族传统体育文化也逐步融入到武陵山地区苗族中,开始出现划龙舟、舞狮等汉地风俗体育活动。
1.2 资本创造:特色孕育
根据文献可知,布迪厄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2]是可以物化的成果或者劳动形式。结合长期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实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地理环境影响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影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孕育社会形态,社会形态衍生体育文化的逻辑链条中,[3]其本质是人类创造了以“体育”为核心的文化资本。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与人类生产息息相关的文化元素,其发展离不开人类创造资本的过程。首先,湘西苗族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渔猎等是获得经济资本的基本途径。在获得经济资本的过程中,具有区域特征的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孕育而生,如苗族接龙舞通过模仿神灵与龙王的形态,塑造逼真的人物形象;苗族猴儿鼓舞通过模仿山里的猴子在鼓上蹦蹦跳跳的各种动态及习性而演生而来。其次,湘西地区的苗族人民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和族群意识,各种传统节日,各种传统仪式仪礼,甚至包括日常生活中风俗习惯,都会成为人们调整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在社会资本的积累中,如绺巾舞、八人秋、舞龙、舞狮、鼓舞等传统体育活动成为节庆体育文化的主体;最后,崇山峻岭间溪流密布,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使湘西苗族与外界的交流受到了自然环境的限制,同样独特且神秘的地域文化孕育而生。部分湘西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生活化特征,是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如苗族鼓舞《整地耕田》《收割打谷》等就是专门表现农业生产的一类农耕舞蹈,苗族武术中招术的命名与武器的运用都体现了湘西苗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本的创造。
1.3 惯习形成:民族信仰
“惯习”不是规章制度规定的,是存在于每个人意识之中的,在群体一致的经历和体验中形成的准则系统。湘西苗族经历几千年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虽有民族的独立性,但也有民族的共性,即使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也有差异。[4]在多民族共生的场域中,各种民俗活动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苗族传统民俗活动“赶年场”“赶秋”“百狮会”等节庆活动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民族特色体育活动。2017年至2019年,在调研花垣县“苗族赶秋节”活动获悉,绺巾舞、接龙舞、苗拳、椎牛、鼓舞、舞龙舞狮、八人秋、上刀梯等传统体育活动对增进和强化苗族民族信仰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苗族祭祀仪式中的“巴代”信仰文化也是苗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因素,如巴代法师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的绺巾舞仪式与椎牛仪式活动。这些传统体育活动不仅是因民族信仰而产生,而且成为当地人民意识中与习惯融合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场域分化
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浪潮冲破文化栅格的边界,湘西苗族原有的以宗法、地缘、血缘关系构建的群体结构正逐渐解体,文化核心层面也发生了质变。[5]在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旅游所构建的场域逻辑体系的共同影响下,湘西传统体育的场域架构变化从根本上体现了“资本”需求的底层逻辑。
首先“经济场域”是影响湘西传统体育场域构建的前提,随着湘西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精准扶贫”带动下传统村落的社会空间变革,劳动关系的转变,使湘西传统体育的立足点改变。“政治场域”是影响湘西传统体育发展的风向标,从宏观层面保护与规范其发展。“文化场域”是影响湘西传统体育的“标签”,决定了其归属。“教育场域”是影响湘西传统体育传承的“次源地”,是现代社会影响传统体育发展的传习空间。“旅游场域”是影响湘西苗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驱动力,同时也是其异化的根源。基于五种场域空间共同影响,构建出与传统湘西苗族传统体育迥然不同的场域特征。
在布迪厄场域理论构建中,经济场域与政治场域在社会场域中属于“元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旅游场域属于区隔化的“次场域”。场域的分化导致自主性,场域的关联导致同构性,场域之间既有自主性,又有同构性即元场域对次场域的支配性。[6]湘西苗族的传统体育场域构建中既有文化、教育、旅游的共振效应,又有在经济、政治的支配下发生的波纹效应。[7]
3 现代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场域特征
3.1 自主性:协同发展背景下场域的共振效应
场域的共振效应其本质文化场域、教育场域、旅游场域中的“资本”要素与体育场域的契合,并共同作用于体育场域。在湘西这一特定的场域空间内,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湘西苗族传统体育场域的特质,即自主性。在场域共振效应的作用下,湘西苗族传统体育与“次场域”共振模式体现为转型、重构、互补等形式,首先,文化场域中的传统体育体现了苗族的文化特质,是在各类体育文化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体育文化空间。[8]在现代价值观的影响下,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文化场域与体育场域的共振效应中发生了文化的转型,如传统苗族接龙舞仪式和大龙洞风景区的接龙舞仪式在“龙”的虚实形象、坛台数量、程序繁简、安龙地点、“龙旗”使用、接龙方式和活动主体等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使其从“民间仪式”演变成“国家展演”。[9]同样的体育活动形式通过转型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在整个苗族社会场域中其更多的是作为民族文化标签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其次,旅游场域中传统体育并非真实的民族传统体育,而是重构的“新传统”,即使物质实物的展出,配合导游人员的符号话语也成为了一种可供欣赏的“历史景观”。[10]在乾州古城、凤凰古城、德夯苗寨、山江苗寨等湘西旅游景点,在百狮会、三月三、赶秋节等苗族传统节庆活动中,作为民族旅游资源输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基于游客的需求与民族文化精英的主导,鼓舞、板鞋、舞龙舞狮、上刀梯、接龙舞、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成为可展演的艺术资源。重构的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旅游资源为游客们评论,但这种重构是否被文化主体所接受?满足旅游需求的前提下,展演中的苗族传统体育已经脱离了其原有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再次,教育场域中的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传统传承场域体系的基础上,汲取了现代教育模式优势。教育场域与传统体育的共振效应主要表现为学校教育资源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借用,实现教育与文化互补,从而使苗族文化走进课堂。[11]作为苗族文化代表的鼓舞在湘西各学校得到很好的发展,如吉首大学、吉首职院、吉首实验小学、吉首第三中学、矮寨中学等学校定期邀请传承人到学校开展鼓舞教学。[12]此外,传习所、传承基地等教育空间的设立为苗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多元的空间。无论是文化场域中体育的转型,还是旅游场域中体育的重构,亦或是教育场域中体育的互补,其本质是传统体育符合文化、旅游、教育的“共振”需要,在满足各自场域“资本”需求的同时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多元化的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场域形态。
3.2 同构性:主导机制背景下场域的波纹效应
在布迪厄场域构建理论体系中体育场域与文化场域、旅游场域等同属于“次场域”,在与同级场域的融合中,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元场域的政治场域与经济场域主导下产生波纹效应。当体育场域与文化场域、旅游场域发生某种程度的重叠,重叠部分产生一种波纹团,影响力以此为中心扩散开。[9]在政治场域与经济场域的主导下,“波纹团”的表现形式因主导主体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效应的偏差。当政治场域主导时,体育场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爱国主义及民族精神的表达。在苗族的文化场域中,鼓(鼓舞)是湘西苗族文化认同、加强情感纽带、加强凝聚力的象征。[13]其象征意义延于早期驱邪逐鬼、战争动员、庆祝鼓舞的功能演化。在政治场域的主导下,文化场域中的“鼓”与体育场域中的“鼓”共同形成了代表湘西苗族民族精神的鼓文化。2013年至2018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举办了五届“鼓文化节”,在2018年“世界鼓舞·鼓舞世界”为主题的吉首鼓文化节上,湘西苗族鼓舞作为民族精神的形象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14]当经济场域主导时,体育场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创造更多的商业效应。湘西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的直接经济效益源于体育场域与旅游场域的融合过程中所创造的经济资本。数据显示,吉首市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从2014年的901.14万人次、58.21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725万人次、155亿元。[15]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场域构建以苗族赶秋、吉首鼓文化节、苗族百狮会等传统节庆活动为支点,依托旅游场域所形成的波纹效应,为吉首乃至湘西地区塑造了精品的苗族传统体育旅游品牌,充分体现了旅游展示文化、文化激活旅游的互动效应,发展壮大了文化旅游产业。[16]
4 基于现代场域特征的发展机制
场域是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质素。[17]在以湘西苗族构成的立体场域中,传统体育的传承者或决策者通过资本的多寡来构建场域关系。以场域理论为视角构建多维“场域”空间、重视丰富“资本”模式、变革传统“惯习”思想等机制,为湘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符合时代需求的路径。
4.1 基于多维“场域”空间的构建
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应以文化生态为基础构建具有文化点、文化线、文化面、文化静态空间以及文化动态空间等多维文化生态场域。一是厘清文化点。湘西苗族同一传统体育项目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分布点,如苗族鼓舞分为四面鼓舞、踩鼓舞、猴儿鼓舞等不同种类和表现形式,分布各地的鼓舞名称也不尽相同,可能有些没被发现的鼓舞或已失传。因此,全面厘清并抢救保护文化点是湘西苗族传统体育得以发展的首要前提。二是拉好文化线。在全面厘清并抢救保护文化点的基础上,使同一苗族传统体育文化类型连接成线,如苗族鼓舞许多文化点正面对失传或已失传,据苗族鼓舞传承人YMX老师口述,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苗族鼓舞在整个湘西地区呈现“空城”现象,通过现在传承人的积累与创编,形成了花垣县,凤凰县,古丈县,保靖县等不同的鼓舞风格,才有如今湘西地区苗族鼓舞发展的现状。因此,接好苗族鼓舞文化线,通过各文化点仅存的零星半点历史资料和口述材料,尽最大程度抢救、复原和重构,“深描”各项目的文化本源,使其唤发新生机。三是打造文化面。打造传统体育文化面是打造村落“名片”的最好方式之一。2017年至2019年三年间,多次访谈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SHY老师,在其组织下,苗族鼓舞成为鼓戎湖村(原夯寨村)的精神纽带与文化名片,在重大节日及重大活动中全村200多面苗鼓,男女老幼及回乡的务工人员,共同跳起鼓舞。基于苗族鼓舞文化面的打造,苗族鼓舞成为鼓戎湖村特有的文化“名片”。四是拓展文化静态空间。文化静态空间不只限于文化所在的自然地理场域,还可拓展更多的人文领域。静态空间主要是对苗族传统体育的物质化呈现,在湘西地区有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除了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山江苗族博物馆等特定的静态文化场域外,各特色传统村落也可成为湘西苗族传统体育对外展示的文化窗口。如鼓戎湖村的苗鼓、德夯苗寨的苗鼓、板栗村接龙舞、板栗寨村绺巾舞、坪郞村苗族武术、凉登村苗族武术、阳孟村女子舞狮等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打造以村落为“源地”的传统体育文化静态空间。
最后,创新文化动态空间。文化动态空间不仅包括空间,还包括时间。如2019年、2020年苗族赶秋节活动利用现代传播技术与手段、重构传统节日活动时间与空间,使其打破时空界限,以“赶秋的世界,世界的赶秋”呈现出来,创新了文化动态空间。
4.2 基于丰富“资本”模式的重视
人是场域“资本”的主体。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传统体育面临着环境变迁过程保护力度薄弱、政府层面科学规划缺失的困境,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的主要难题是传承主体即“人”的缺位。传统传承方式的“短板”、现有传承人的高龄结构等因素极大地制约了保护与发展,如大多苗族传统体育存在传亲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等传承方式,导致传承人稀缺而单薄,形成“短板”;湘西地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类的苗族鼓舞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类的苗族武术、湘西苗族接龙舞、苗族绺巾舞等项目传承人绝大多数年龄在70岁以上。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18]只有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重视政治“资本”的宏观调控、丰富文化“资本”的内涵发展是在场域构建下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得以完善的基本保障,以“资本”为基础的创新模式构建能够为保护机制的实现发展新的思路。首先,重视政治“资本”的宏观调控。在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为代表的政治“资本”的宏观调控,湘西苗族就位于其政治“资本”宏观调控下确立的18个国家级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一个(武陵山片区)。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只有赋予苗族传统体育文化全新的时代使命,才能拥有鲜活的持久生命力。其次,丰富文化“资本”的内涵发展。湘西苗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继承原有“本土”属性的基础上,应紧跟跟进时代发展步伐,重视文化“资本”的再创造,多方面丰富其项目内涵,使其吸收时代养分,助力项目再发展。如2019年8月8月在湘西花垣县体育广场举办的苗族赶秋节,其文化“资本”内涵甚是丰富,其一是“世界的赶秋·赶秋的世界”为主题,通过现代化舞台表演和传播手段使苗族赶秋节不再限于苗族人民自娱自乐,而是赋予了其苗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带动世界人民狂欢;其二是借助打造苗族赶秋品牌,启动全域旅游仪式,助力苗乡脱贫攻坚。
4.3 基于传统“惯习”思想的变革
湘西苗族经历几千年的民族反抗斗争,伴随着其悠久厚重的历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信仰,通过各种传统体育项目的形式保留和遗传下来,并成为各种民俗活动中重要的部分,这些在苗族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惯习”难以憾动和改变。“惯习”的思维固化严重制约了苗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龙长卿拳术是苗族武术中的一大流派,其生活的村落凉登村在历史上曾是湘黔边区妇孺皆知的武术之乡,龙长卿曾经湘西王陈渠珍聘为“黑旗大队”的武术教官,创有《苗家拳基本功十二式》,对发明苗拳很有建树。[19]2019年8月在调研凉登村武术发展现状时发现,龙长卿武术现如今的“难以被外人知”状况不仅与凉登村偏僻险俊的自然地理位置有关,更重要的是被其传统保守的思维“惯习”有着莫大的关系。
场域既有持久性,也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转换到另一个场。[20]湘西苗族传统体育文化场域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发生转换,在无意识层面发生变化后又进行重构,继续不断向前发展。近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在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互动中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苗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家-社会影响下,其场域已发生了诸多改变,这已成了不争的事实。时代在进步,思想要跟进。传统“惯习”思想已不能适应当下时代需求、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了,因此,变革传统“惯习”思想最核心的就是唤醒苗族民众的民族自觉。苗族民众应对苗族体统体育文化的来龙去脉有自知之明,对其文化在时代变迁下的变化有自我察觉之感,对其文化变化后出现的问题有自我反省之力,并跟进时代引领下有自我创建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