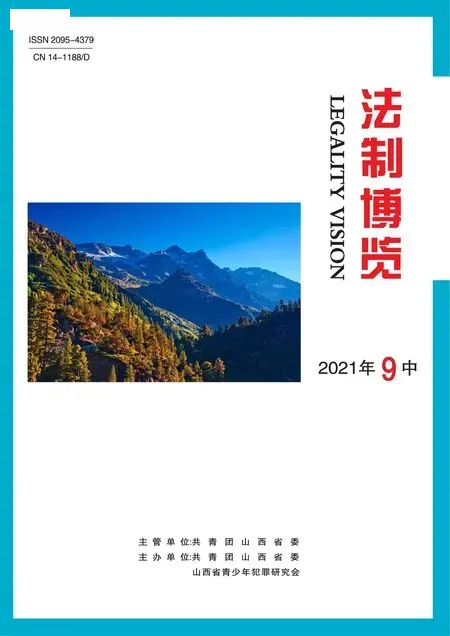涉外专门法院之审判特点与法律监督应对
前海检察院课题组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检察院,广东 深圳 518054)
一、涉外专门法院的制度安排及司法实践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伴随国际贸易额增长而来的是日渐增长的涉外民商事纠纷,对涉外争议解决服务需求和服务质量的要求大幅提升。入世初期,各地城乡发展和法律服务质量存在巨大差异,域外主体对既有的审判体系存在一定的疑惑。加之改革开放的历史不久,国内能掌握国际规则、能从事涉外审判的人才还很短缺。为保障审判质量,提高涉外纠纷解决的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2年和2004年出台了两个司法解释,实现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的集中管辖。
200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部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集中到了国务院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取消了绝大多数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案件的权限。这一制度安排在推出以后旋即面临着实务困境:经济发达地区因涉外案件众多,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负担太重,影响了案件处理的质量和效率,而到远离双方住所地的法院进行诉讼也给当事人带来很多不便。
为解决这些问题,200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调整思路,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由各高级人民法院在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其辖区内可以集中管辖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名单,报请最高法审批。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授权广东省和各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指定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本区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明确基层人民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分工,并将指定管辖的情况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可见,《通知》在《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放权。
按照最高法两个司法解释的精神,对于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的基本审判思路是集中管辖。随着办案量的增大和涉外庭法官办案经验、知识水平的锻炼提升,全国范围内涉外涉港澳台集中管辖案件的法院数量也不断增长。据笔者了解:“截至2014年10月底,全国共有203个中级人民法院、204个基层法院具有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覆盖了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大部分中、基层法院,中西部地区的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也有了适度拓展。”[1]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伴随着法律现代化、司法专门化,法院的设置和管理呈现专门化和精细化的趋势。专门法院是相对于普通法院而言,专门管辖特定案件的法院类型。”[2]笔者认为,随着涉外民商事审判案件的集中管辖,涉外专门法院的建设过程是我国审判机关专门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涉外专门法院管辖案件之基本特点:以对q法院审判实践之观察为例
q法院是我国东南沿海某省份之基层法院。该院经过最高法批复同意,管辖所在S市(地级市)范围内应由基层法院管辖的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以下简称“四涉”案件),以及发生在该市自贸区范围内的民商事以及一般的知识产权案件。课题组选择该基层法院作为观察样本,主要的考虑是:S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交往多,对外贸易额高,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收案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具体到q法院来说,该院受理案件的集约化程度高,受案量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对该法院审判活动进行观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文献阅读。对该法院的年度审判白皮书、官方网站、工作报告等文件进行收集、查阅、比对。二是审查判决文书。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该院近年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了解审判中存在的瑕疵和问题。通过统计分析案由、案件标的、裁判结果等判决关键性要素,该院从事“四涉”案件审判主要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随着对外交往不断扩大,案件数量近年平稳上升。2016年该院受理“四涉”案件1583件,2017年受理1600件,2018年受理1775件,2019年受理2183件,2020年截至7月受理了1711件。数据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增幅并不明显,每年递增不超过10%。
二是案件涉及的法域较多。截至2020年7月,该院共受理涉外商事案件1756件,占全部“四涉”案件总数的18.56%。2015年至2019年的四年之间,受理数为90件、192件、284件、340件、400件,2020年1月—2020年7月的涉外商事受案量为450件,超过了过去五年任何一年的数量。案件当事人涉及的国家或者地区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俄罗斯、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88个。当事人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长,反映了我国对外经贸活动范围不断拓宽,程度不断加深。其中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达34个,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支持响应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双方经贸或商业往来愈加频繁。
三是案由复杂多样,新类型纠纷增多。该院受理的“四涉”商事案件共涉及165个案由,以国际商事交易引发的纠纷为主,涉及跨境交易、离岸交易、跨境运输等领域,包括买卖合同纠纷、运输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委托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股权转让纠纷等,此类型案件占“四涉”商事案件总数的67%。除上述传统的商事纠纷外,新类型纠纷逐年增多,案件类型涉及行业领域广,涵盖了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互联网金融、跨境电商等领域。
四是存在调解结案多、撤诉结案多、缺席审判多、审理期限长“三多一长”的特点。据q法院官方发布的审判白皮书显示,该院2015年至2020年7月,从“四涉”商事案件的结案方式上来看,调解结案有974件,占比13.41%;撤诉结案1824件,占比25.11%;两种方式的结案数加起来占总数的超过三分之一。笔者曾经参与对该院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查,结果显示,2016—2018年审结的2139份“涉外”商事案件中,缺席审判的有1264件,缺席审判率达59.1%。同时,案件审理期限偏长,6个月以内审结的案件仅有436件,占比20.3%。这说明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的跨法域、远距离的基本情况大大制约了法庭上的抗辩行为,对庭审实质性造成了不小的挑战;同时,基于外国法查明、域外送达和办案数量压力等等原因,q院的案件审判周期也明显较长,增加了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时间成本。
三、加强对涉外专门法院审判活动之法律监督
(一)主动作为拓宽涉外审判法律监督的职能和空间
当前,民事诉讼法以及两高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设计是较为保守的,监督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二十三条列明,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的来源可以是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但是该条例的规定较为模糊,可执行性不强。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依职权启动难这一问题,在涉外审判监督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症结在于,大量的调解结案、缺席审判制约了法律监督入口。根据前文选取的q法院作为涉外专门法院的观察样本,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数占总数的超过四分之一,而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数占总数的超过八分之一。即使是判决结案的案件中,又有超过60%的案件是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这意味着该涉外专门法院审理的案件的大多数是缺乏庭审对抗和实质质证的。
究其原因,是涉外审判的案件特点造成的,跨法域的案件诉累成本高,或者是一方当事人出于逃避承担法律责任而一走了之。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程序的启动,往往需要当事人主动申请,证明存在法院应当再审而没有再审的情形;或者证明调解书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存在,才能依法向同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是提请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面对超过60%的缺席审判比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被动的。针对这一问题,建议要通过修改法律拓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案件来源和范畴,例如明确检察机关对某类案件依职权启动监督的权力。针对涉外审判中超过60%是缺席审判、对抗性不强现状,如果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启动类案监督并督促审判机关后续加强执行工作的话,这对于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和实现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增强审判和检察资源配置的协调性
相较于法院系统近年在全国各地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进涉外案件的集中管辖,专门对涉外案件开展监督的检察院则很少见。笔者认为,追诉刑事犯罪毕竟占据了检察机关的主要精力。民事检察依赖当事人主动申诉,且案件受理体现“倒三角”的分布,基层的办案量少,少有基层检察机关能组织专门的监督力量对涉外审判开展监督。这反映出审判、检察机关队伍司法办案专业化的资源投入有差距,需要增强检察资源对于涉外民商事审判案件的监督资源。
笔者建议,要强化检察资源的配置以适应涉外审判的集中化趋势,关键在于完善上下一体化办案相关机制。在基层办案力量较为单薄的情况下,开展上下一体化办案是有必要的。例如某基层法院依照授权对全市范围内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如果检察机关未予及时回应,就会造成该地基层检察院面临着大量该类案件的审判监督需求,人力资源或知识储备方面都难以应付,需要市一级检察机关通过上下一体办案或者是抽调力量方式予以支持,或者是择机开展类案监督。
(三)优化对涉外审判案件的监督思路
涉外民商事诉讼往往有一方当事人在境外,双方的交易习惯、商业模式往往与国内的有较大差异。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双方当事人在涉外争议解决中也可以经协商一致适用域外法律作为争议解决依据的实体法,这对法律查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针对这一监督难点,检察机关需要优化监督思路。
近年来审判机关通过聘请港澳台籍人士出任人民陪审员等途径参与涉外审判的司法实践屡见不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我国港澳台同胞参与庭审,甚至是成为人民陪审员并无法律障碍。在珠海、深圳、厦门、漳州等地,基于毗邻港澳台并有大量的涉港涉澳涉台的案件,这些地方的审判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都探索聘请港澳台同胞出任人民陪审员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以深圳前海法院为例,该院2015年选出了首批13名港籍陪审员。考虑到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新类型案件特点,设置候选人重点考虑了其专业背景,一般需要具有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互联网、现代物流或融资租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或从业经验。基于第一批港籍陪审员参与司法的良好效果,2018年该院又选取了第二批19名港籍陪审员。其中,有12名为普通港籍陪审员,7名专家陪审员。“港籍陪审员分为普通陪审员和专家陪审员两大类,其中专家陪审员20名,按照金融、贸易、财会、股权、知识产权等类别分为5个组。”“建立了专业法官+港籍陪审员+行业专家的专门审判机制,采取分类管理+随机抽取的模式,对疑难复杂的涉外涉港澳台案件,或者是法官认为需要邀请港籍专家陪审员参审的案件,根据案件需要按照专业分类从对应的专家库内随机抽取,确保公开性和专业性。”[3]
反观检察机关,虽然在2016年7月,司法部会同高检院出台了《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高检院单独出台了《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广东等地也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明确港澳台同胞可以担任人民监督员,但实际上该制度的落实效果至今缺乏考核、评价机制。检察机关应当积极探索,在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监督中聘请港澳台籍人民监督员或有专门知识的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