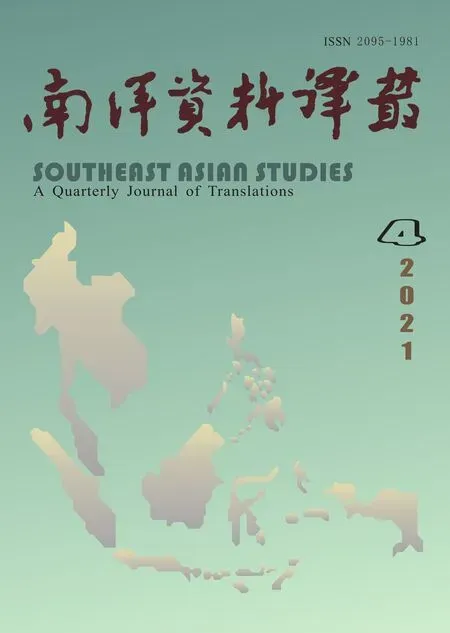印尼亟需制定在叙亲“伊斯兰国”侨民撤回政策
[印尼]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
印尼亟需制定在叙亲“伊斯兰国”侨民撤回政策
[印尼]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
目前,一些印度尼西亚侨民被关押在叙利亚难民营和监狱中。“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在这些难民营和监狱里毫无压力地传播,为了保护这些印尼侨民免受威胁以及避免日后可能出现的跨国恐怖主义活动,印尼政府亟需制定相关撤侨政策。本文摘译自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第59号报告。该报告阐述了印尼侨民在叙利亚难民营和监狱中的境遇,分析了撤侨的急迫性和可行性,并对撤侨后侨民的回归社会给出了方案,旨在提出可能帮助印尼政府解决问题的建议。
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撤侨
一、引言
在叙利亚北部,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控制着的难民营和监狱中,生活着一些印度尼西亚侨民。眼下,印尼政府亟需制定明确的撤侨政策。倘若印尼政府想让其最弱势群体远离恐吓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氛围,那就必须立即在国内先动起来,甚至要在确定撤侨对象以及撤侨数量之前就制定好方案。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多少印尼侨民生活在叙利亚的难民营,也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想要回国。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已于2019年7月组建工作组来解决这一问题。据他们估计,这些侨民共有120人。然而,不同部门统计的人数并不一致,实际人数可能要多得多。
这些侨民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此前生活在“伊斯兰国”控制区,在2018年末、2019年初逃离联军空袭,投靠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有一些女侨民在她们的印尼丈夫被杀害之后就在叙利亚嫁给了其他国家的人(比如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伊拉克人、西非人等),又再次沦为寡妇;另一些女侨民倒是嫁给了印尼人,但他们都被单独扣押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监狱之中。
印尼并不是唯一一个纠结如何处置参与“伊斯兰国”活动的侨民的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政策窘境。他们面临的问题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政府是要撤回所有希望返回家园的人,还是会按风险等级将潜在的归国者分类,仅选择撤回低风险或弱势的群体(例如,无依无靠的孤儿)?
如果政府决定只撤回其中一部分,风险评估该如何进行?毕竟印尼和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任何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往来都会被视为一种不友好的行为。是否可以依靠第三方来进行初步评估,然后再设法让“评估合格”的人员前往伊拉克进行更全面的问询?已经想出了哪些方法来专门评估妇女和青少年的风险等级?
如果一部分人开始转移,会对留在难民营里的人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被选中的在叙侨民到达了伊拉克,印尼政府就不得不将他们全部撤回,因为库尔德人不允许撤出的侨民重返集中营。在这种情况下,又或者政府采取了其他形式分批撤侨,这些侨民回到印尼后又该如何处置?如何在详细了解归国侨民在叙利亚以及难民营的经历之后对其制定有效的劳教方案,以对归国侨民进行教化,让他们重新融入当地社区,并对他们进行长期的管理?针对那些脱离冲突苦海的儿童侨民,有没有制定出或将要制定什么计划?
政府该如何说服那些可能对归国侨民抱持敌意的群众接纳侨民?如果出了差错,比如归国侨民中的某些人日后再次投身恐怖主义活动,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撤侨及其他相关费用会是多少?由谁支付?
需要依照什么样的政策程序?是不是在确定潜在归国侨民之前先要制定什么侨民劳教及回归社会的方案?
对于叙利亚民主力量监狱中关押着的高价值囚犯来说,还有一系列更难解决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没人希望他们回国,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想回国。但据说其中有些人(包括3名印尼人)想要回国,他们表示愿意与政府合作,提供重要的情报来源,并且最可能说清楚“伊斯兰国”中央与其东南亚支持者之间的关系。据报道,库尔德人表示愿意安排与侨民面谈,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就同意该侨民归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这些高价值囚犯全程由88特遣队押送,并对他们采取最高安全级别的监押,但仅仅为了可能获取到的一点情报,是否值得冒险将其撤回印尼?
无论这些选择有多困难,让这些难民营中的囚犯无限期地徘徊在关塔那摩沙漠中的代价也很高。可能发生骚乱、暴动、越狱或袭击,导致营地突然间空空荡荡,难以追捕囚犯。妇女和儿童经常受到嘲讽和威胁,更可能变得更加激进或精神遭受创伤。他们滞留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与外国战斗人员家庭建立长久而牢固的联系,从而导致日后可能出现跨国合作。
本文旨在概述当前面临的问题,提出可能帮助印尼政府解决问题的建议。
二、背景
羁押外国战斗人员的难民营和监狱由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该部队由美国于2015年10月创建,主要由来自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少量来自叙利亚阿拉伯联盟的叙利亚阿拉伯战斗人员组成。在将“伊斯兰国”赶出叙利亚据点的漫长战争中,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包揽了大部分与“伊斯兰国”的地面战斗,并得到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中支援。
从“伊斯兰国”手中夺来的领土、库尔德领土罗贾瓦以及几个阿拉伯地区,共同组成了最初的北叙利亚民主联邦。2019年1月,联邦更名为叙利亚东北部自治区。该自治区占地面积为叙利亚的25%,由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政治分支——叙利亚民主委员会管辖,独立于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之外并站在该政府对立面。
2017年10月,“伊斯兰国”首都拉卡失守,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80%的建筑被毁坏,基本无法居住。①“The war against ISIS nearly leveled Raqqa, Syria. Months later, crews are still digging bodies out”, Washington Post, www.youtu.be/ozN0GDENits, 19 April 2018.
随后,代尔祖尔省的其他据点相继沦陷,最后沦陷的一处据点巴古兹坚持到了2019年3月,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很多人都是“伊斯兰国”的忠实支持者。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住进了叙利亚民主力量的难民营和监狱,有的是主动寻求庇护,有的则是被收容。至少有3个位于哈塞克省的难民营(即阿尔霍尔、艾因伊萨和阿尔罗伊)收容外国侨民,包括印尼人。
许多人道主义组织一直在提供基本援助,包括联合国难民署(UNHC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卫生组织(WHO)、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国际救援委员会一直在帮助难民营里的难民与家人取得联系。一些有胆识的新闻工作者也能够设法进入内部,在里面找到中间人和向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越来越难打入难民营内部。
由于没有中央数据处理中心来记录出入营地的人员的信息或者按国籍收集数据,多国政府了解其侨民人数的途径是要靠这些侨民通过亲属、援助组织或随机接触到的记者表达归国的意愿。
(一)阿尔霍尔
阿尔霍尔是最大的难民营。截至2019年年中,该难民营容纳了约7.3万人,其中94%是妇女儿童。他们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无国界医生组织是这样形容他们的生活环境的——没有足够食物和饮用水,卫生和医疗护理条件差。②“Women and children continue to suffer in northeastern Syria’s Al Hol camp,” www.msf.org, 16 May2019.营地中大约67%的人是不满12周岁的儿童。③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1 April 2019-30 June 2019, p. 24.有些妇女是遗孀,还有些妇女因其丈夫涉嫌与“伊斯兰国”有瓜葛被关押到戒备等级更高的监狱而被迫与其分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控制的最后一块地盘巴古兹失守后,大约240名无依无靠的儿童抵达难民营。④“Syrian camps: vulnerable children of ISIS ignored by the outside world,” www.theguardian.com, 9 March 2019.2019年2月26日库尔德电视频道的一名记者发现了一家8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才15岁,他们的母亲遇害了,而父亲仍在战斗。⑤“WNI Simpatisan ISIS: Nasib Mereka Setelah Baghouz Jatuh,” https://tirto.id/djLT, 19 March 2019;“WNI Simpatisan ISIS di Suriah: ‘Kami Minta Bantuan Bisa Pulang’,” https://tirto.id/dkb1, 25 March 2019.尽管大部分难民是叙利亚人,据2019年5月的统计数字,仍有约11,000名非叙利亚人被关押在阿尔霍尔难民营的附楼里。营地内的活动相对不受限制,但并不安全。据报道,营地内的北非妇女,尤其是表现出回国愿望的妇女被人恐吓。在忠实信徒眼中,这些人就是叛徒。2019年5月的一则报道指出,一些“硬核”女性甚至试图通过强制执行“伊斯兰国”的规则来在营地内重建“哈里发国”。⑥Robin Wright, “A Visit to Post-ISIS Syria: Human Crises Pose Risk,” United State Institute for Peace,7 May 2019.
据悉,一名叫做苏达米尼的印尼妇女于7月下旬在阿尔霍尔被活活打死,当时她已有6个月的身孕。杀人者和杀人动机尚不清楚。
美国国防部2019年8月6日发布了一则警告,称“伊斯兰国”在阿尔霍尔的活动依然活跃,并可能从数量庞大的难民中招募新兵。阿尔霍尔是一个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庞大难民营,居住着数千“伊斯兰国”家属。毫无疑问,缺乏监控使得“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在难民营中的传播毫无阻力。⑦James Hohmann, “The Daily 202: Pentagon Watchdog warns that ISIS is ‘resurging in Syria’ after Trump’s drawdown of U.S. troops,” washingtonpost.com, 8 August 2019.
以上种种表明,印尼侨民在难民营待得越久,就越有可能变得激进或者受到威胁。印尼《时代周刊》(Tempo)的一名记者于2019年6月设法混入了一个印尼难民居住的帐篷。这些印尼难民都是带着孩子的妇女,这些妇女于3月巴古兹失守后抵达难民营,而她们的丈夫则被关押在监狱中。她们都想回国,并且说难民营中大约有200名印尼人,但确切的数字难以证实,而且不清楚这些人中有多少人想要回国。7月,一名印尼官员表示已有约50名阿尔霍尔侨民与亲属取得了联系。
(二)阿尔罗伊
阿尔罗伊是伊拉克边境附近一所较小的难民营。截至2019年5月,约有1700名难民生活于此,其中大部分来自摩苏尔及周边地区,少部分来自国外。印尼官方2018年11月根据人道主义数据编印了一份阿尔罗伊难民名单,包括33名印尼人,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15名在中东出生的儿童。这些妇女有的嫁给了外国人,比如其中一个就嫁给了阿尔及利亚人。⑧名单共有38 个名字,但其中5 个名字重复了。
该名单也包括了乌兹曼·马哈迪一家。乌兹曼是一名重要的印尼籍“伊斯兰国”领导人,目前被单独关押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监狱中。乌兹曼原是印尼梭罗市的一名信息技术
专家,在2015年初到达叙利亚并接受了军事训练,此后成为了一名无线电接线员。⑨“Utsman Mahdamy, Ahli IT dari Solo, Gabung ISIS dan Menyesalinya,” www.tirto.id/dD7P, 15 May 2019.然而,2017年12月拉卡失守后,乌兹曼对“伊斯兰国”大失所望,向库尔德武装缴械投降后被安置在难民营。⑩同上。
2019年2月,他给家人写信说,加入“伊斯兰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如果允许他和家人回国,他愿意与印尼政府合作。11“Polisi Sambut Eks Kombatan ISIS yang Tobat & Mau Kerja Sama, Tapi...,” www.tirto.id/dK4P, 17May 2019.
这种情况让印尼当局陷入两难。当局如何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如何在无法接触他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当局如何证明在众多的案子中非得介入他的案子,尤其是在难以接触到当事人的情况下?同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保护他在阿尔罗伊的家人免遭报复,毕竟其他印尼籍“伊斯兰国”成员都知道乌兹曼“背叛”,而他们显然也想回国。
(三)艾因伊萨
艾因伊萨难民营建于2016年,位于拉卡市和土耳其边境小镇泰勒艾卜耶德之间。截至2019年5月,约有13,200人生活于此,包括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其他国家的人。12“Ein Issa camp directorate prevents Deir Ez-Zour families from accessing the camp,” www.npasyria.com, 29 May 2019.
许多外国家庭在四五月份从人满为患的阿尔霍尔被转移到艾因伊萨,以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撤回本国。但是就像印尼一样,很多国家的政府也迟迟未能做出全面撤侨的决定,因此,被转移到此的大多数难民同样陷入不确定的困境中,与在阿尔霍尔无异。13“Joining IS ‘wasn’t worth it; we failed’, says Lisa Smith,” www.rte.ie, 18 July 2019.
(四)库尔德监狱
叙利亚民主力量下令将大部分成年男性武装分子分散羁押在监狱中,而不是巡逻不严的难民营里,并且对他们使用指纹和面部识别技术来进行登记。14John Dunford and Jennifer Cafarella, “ISI’s Opportunity in Northern Syria’s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Camp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13 May 2019.截至2019年年中,主要的6所监狱总共关押了约1万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但其实这个词包括了许多非战斗角色。这些拘留中心有很多被称为“秒建监狱”,因为它们是废弃的学校或仓库改造而成的。15Robin Wright, “A Visit to Post-ISIS Syria: Human Crises Pose Risk,” United State Institute for Peace,7 May 2019; “As ISIS Fighters Fill Prisons in Syria, Their Home Nations Look Away,” New York Times,www.nytimes.com, 18 July 2018.截至2019年年中,囚犯主要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人,但也包括来自印尼等50个国家的约2000名外国战斗人员。1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1 April 2019-30 June 2019, p. 23. “战斗人员”一词可能会引起问题,因为其中许多人从事非战斗性的工作,例如厨师、驾驶员、会计师等。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非所有成员都推崇“伊斯兰国”的暴力政策。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FTF)被定义为“前往其居住国或国籍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以实施、筹划、筹备或参与恐怖行为,或提供或接受恐怖主义训练,包括因此参与武装冲突的个人。”截至2019年8月,大约400名极度危险分子被关押在马利基耶市(库尔德人称之为德勒)的仓库改建的监狱中。17“Inside the prison holding IS detainees in northeast Syria”, www.al-monitor.com, 15 March 2019.
2019年4月5日,大约半数囚犯试图越狱,但叙利亚民主力量在联合空军的支援下将其制止。此后,安保等级进一步加强。
据称,在这400名试图越狱的囚犯之中有5名印尼人,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乌兹曼·马哈迪;第二个穆纳瓦尔·哈利勒,别名乌斯杜尔·瓦哈,楠榜人,在爪哇岛中部地区为印尼激进组织神权游击队(JAD)工作;第三个哈迪德·纳希鲁尔·哈克是前伊斯兰祈祷团(JI)领导人阿米尔·马哈茂德的次子;此外还有阿布·艾莎和阿布·塔里克二人,18“Munawar Kholil, Teroris JAD, Perekrut 57 WNI Ikut ISIS ke Suriah,” www.tirto.id/dD8t, 15 May 2019.此二人的真实姓名不详,他们参与越狱计划,后来被移出监狱,关到一个秘密地点。
所有人一致认为当前局势难以为继。叙利亚民主力量不想永远看守囚犯,并且越来越迫不及待想要卸下这些责任。他们没有能力审讯外国战斗人员,也没有能力阻止“伊斯兰国”招募新兵。当前政治局势动荡,库尔德人又经常威胁说要释放所有囚犯,这就会让成千上万可能成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人得以重新整编。尽管存在局势难以为继的危险,包括印尼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似乎更倾向于拖延而不愿做出有政治风险的决定。
三、撤侨案例举隅
每个有侨民参与“伊斯兰国”的国家都不得不考虑撤侨的风险,而且风险很高。著名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学者托马斯·黑格汉马于2019年2月在推特上写道:
就安全风险而言,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无法判断“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归国以后是否会成为威胁,这风险可能低,也可能高,我们根本不知道。我来详细说明一下:
一方面,目前的形势没有先例,因此没有数据可供参考。外国战斗人员归国的历史记录帮不上忙,因为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早期的战斗人员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回国的,而现在这些人将在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戴着镣铐”归国。这意味着风险会降低,因为此举能限制归国侨民从事恐怖活动。
尽管早期的战斗人员是自愿回国的,但他们是因外部干涉提前结束军事生涯,这意味着这些人的危险系数更高,因为被迫投降的他们更可能因壮志未酬而初心不改。19印尼人应该回想起乌玛尔·帕特克的案件,他是2002 年巴厘岛炸弹袭击者之一,后来逃到了菲律宾。他在阿布沙耶夫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最终于2009 年悄悄回到印尼。他于2011 年在巴基斯坦的贾拉拉巴德被捕,当时他与哈卡尼网络联系并试图参与阿富汗圣战。当他被驱逐回印尼时,他被视为印度尼西亚有史以来处置过的最危险的囚犯。他被审判,定罪并判处20 年徒刑。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成为了一名模范囚犯。一部分原因是就遣返进行谈判时,印度尼西亚警方同意让他的菲律宾妻子与他一同返回印度尼西亚;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从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人道主义关怀。
另一方面,归国侨民的未来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他们被审判和监禁的经历、他们被社会接纳的程度、政治发展、与其他伊斯兰主义者的交往以及被监视和限制的程度,等等。
这是一个有着太多未知变量和相互作用的方程式,很难做出很有把握的预测。即使是最后悔归国的人,也可能在正确的引导下改变主意,反之亦然。
可以肯定地说,撤侨对安全方面的影响将是负面的。尽管情报部门可以通过归国侨民得到一些情报,但这些好处肯定远不及它带来的风险。20Thomas Hegghammer, https://twitter.com/Hegghammer/status/1096460693526728704, 16 February 2019.
通过多年对极端主义囚犯的研究,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发现,极端主义者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和他们出狱后的表现并无直接联系。有些被认为极度危险的犯人出狱后却和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而有些次要人物反而在狱中变得更为激进,出狱后更积极地投身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叙利亚民主力量营地的人所构成的安全风险既取决于他们在营地的情况,也取决于他们作为“伊斯兰国”战士或追随者的经历。这也是撤侨如此紧迫的另一个原因。
(一)容易处理的撤侨案例
原则上,撤侨案例中最容易处理的应属儿童,但是2019年中拍摄的一些视频中,阿尔霍尔营地年幼儿童严厉声讨“叛教者”,这说明这些儿童从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了“伊斯兰国”价值观,因此也就不那么容易撤侨了。有几个国家倒是已成功地协商了撤回叙利亚民主力量营地儿童的问题,多数是因为这些孩子在国内的亲属频频向政府施压。印尼政府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操作程序一般包括与库尔德当局协商,然后将孩子们跨境转移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都埃尔比勒,然后将他们从那里带回国。21“Belgium strikes deal with KRG to repatriate children of ISIS members: Minister,” www.kurdistan24.net, 13 June 2019.
2019年6月,曾在阿尔霍尔难民营呆过的一个挪威家庭的5个孤儿被移交给挪威外交部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奥斯陆的一份官方声明指出:其目的是将儿童从极端主义氛围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返回祖国得到妥善劳教并重新融入社会。22“Norway to repatriate 5 orphan children of ISIS adherents from Syria,” Defense Post, www.thedefensepost.com, 3 June 2019.
截至2019年6月,比利时已撤回21名儿童侨民,并计划带走所有10岁以下的儿童,但这可能就要他们与母亲分离。23“Belgium to repatriate children of ISIS, but leave mothers in Syria,” www.independent.com, 28 February 2019.司法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不能因为父母的行为而惩罚孩子。”24同上。
澳大利亚在救援机构的帮助下将8个孩子带到伊拉克,随后其政府官员于2019年6月护送他们回国。25“Eight orphan children of ISIS adherents to be returned to Australia from Syria,” Defense Post, www.thedefensepost.com, 24 June 2019.这些孩子包括战斗人员哈立德·沙鲁夫的3个孩子和两个孙子,沙鲁夫曾拍摄并上传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沙鲁夫的1个孩子手提1名叙利亚士兵的首级,该照片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
2019年6月,库尔德政府将12名法国儿童和2名荷兰儿童移交给两国派往艾因伊萨的政府代表团。两名法国儿童的父亲被伊拉克法院判处死刑,母亲就被收容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一个营地中,她已准许孩子返回法国。其他儿童都是孤儿。荷兰政府表示,这些孩子将接受健康检查,然后移交给社工照料,并努力为他们寻找寄宿家庭。26“France, Netherlands receiving 14 children from anti-ISIS forces in Syria,” www.rudaw.net, 10 June 2019.
哈萨克斯坦是为数不多的尝试大规模撤侨的国家之一。截至2019年8月,它从叙利亚撤回侨民548名,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在一个名为“善意劳教中心”的地方接受为期1个月的“放弃激进主义”培训,然后才被允许返回家园。27“Kazakhstan Welcomes Women Back from the Islamic State, Warily,” New York Times, 10 August 2019.(撤回的男性侨民将面临10年有期徒刑。)该中心2019年1月才刚建成,现在还很难说中心这种集心理咨询、宗教咨询和艺术治疗于一体的培训项目是否有效。
事实上,大多数“放弃激进主义”项目,包括印尼的,都被过度吹嘘了。大多数极端主义者都是基于个人原因主动放弃暴力,与政府的干预关系不大。28Julie Chernov Hwang, Why Terrorists Quit: The Disengagement of Indonesian Jihadists, Ithaca, 2018.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这些侨民回国后的经历是愉快的,因为相较于在政府的安置中心待上几个星期而言,他们回国后的第一年能否找到经济上和社交上的安全感更为重要。
印尼政府担心撤侨数量过大,难以应对,其他国家却已经着手开始小规模撤侨。印尼政府何不开展试点项目,从最易受伤害的儿童开始撤侨,就比如2月在阿尔霍尔发现的那8个孤儿?
制定儿童劳教回归社会的方案可能比成年人更容易,特别是汉达雅尼少管所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汉达雅尼少管所是社会事务部专为那些需要保护和引导的儿童设立的一个过渡住所。也可以通过寻找寄养家庭来帮助这些孩子开始新的生活。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后勤跟不上,而是截至2019年8月,撤侨并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
(二)“难处理的”撤侨案例
风险较高的是撤回像穆纳瓦尔·哈利勒那样曾在“伊斯兰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他目前被叙利亚民主力量羁押,有回国愿望。印尼当局对此很是谨慎,这也是有道理的,他们怀疑他的归国愿望是否真实,抑或只是在印尼重组“伊斯兰国”的阴谋的一步棋。毕竟他在2014年就为印尼人前往叙利亚提供便利,29Trial dossier of Rochmat Septriyanto alias Bambang Gentolet, Case No. 1387/Pidsus Teroris/2017,North Jakarta District Court, 2017.2017年,他在资金转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笔资金由他转给印度尼西亚的联系人,让其接着转移到菲律宾,资助马拉维市之前的行动以及为印度尼西亚人前往棉兰老岛提供资金。他还与棉兰老岛马拉维问题战略专家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博士保持联系。
如果他得以回国,他也许能提供“伊斯兰国”东南亚计划的重要信息,包括“伊斯兰国”中央与其区域分支机构之间的财务关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联系,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新兵招募,以及叙利亚民主力量营地和监狱中进行的重组和征募。这些信息对于制定预防策略至关重要。
如果穆纳瓦尔·哈利勒回到印尼,印尼警方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他。警方可以控制让他回国的条件并测试他是否真的对“伊斯兰国”不抱幻想。既然让他回国有诸多明显的好处,风险能有多大呢?至少可以把这当作一个样本,说明本可以直接提出公诉的高价值囚犯只要处理得当,也可能跟政府站在一边。
四、撤侨工作组
2019年7月19日,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部长维兰托表示,政府将会成立工作组更加深入地了解滞留印尼侨民的情况,并可能制定撤侨政策。工作组将由相关部门联合组成,包括国家反恐局、外交部、国防部、警察、军队、社会事务部等,由统筹部领导。
然而,该工作组成立之际恰是众多政府新举措被搁置之时,因为大家都在等待佐科维总统在其正式连任之前(即大约2019年9—10月份)公布其重组后的内阁人员名单。工作组的成立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他们正在着手解决问题但又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从印尼官方的角度来看,主要障碍有:
1. 圈定想要回国的侨民。这一点倒没必要一蹴而就,可以根据人道主义组织的评估结果实行试验性撤侨。
2. 核实国籍,因为许多印尼人销毁或遗失了护照,而在叙利亚出生的孩子就更不会有护照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与移民局相互印证与印尼家属联系等方式进行国籍核实,这可能很耗时,但是可行。
3. 在不损害与叙利亚的关系的前提下进入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区域。其他国家通过美国或其他方式将国民带到伊拉克。这在外交上是比较棘手的,但并非不可能。此举已有先例——有一家人于2017年8月从“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地区出发,经由伊拉克返回印度尼西亚。叙利亚民主力量负责人在2019年年中告诉《时代周刊》记者,那家人返回后还没有与印尼当局联系过。30“Nestapa di Negeri Syam”, Tempo, 23 June 2016, p. 33.在等待工作组决定撤侨方式之前,不妨重新建立沟通渠道。
4. 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现在,监狱和汉达雅尼少管所的工作人员都在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迅速开展初步风险评估。该方法经过调整可用于叙利亚,重点关注妇女和少年儿童,不必等到开发出类似的风险评估方案才去撤回孤儿或弱势家庭。印尼政府可以先派遣一组经验丰富的面试官去盘问他们,抵达印尼之后也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问询和分类。
5. 为试行劳教方案作准备。国家反恐局位于茂物市圣图尔区的去激进主义中心的各种设施可以容纳少量归国侨民。尽管汉达雅尼少管所已人满为患,并且需要追加资金用于基建和员工开支,也还可以再接收5到10人。政府没必要考虑一次性安置成百上千的归国侨民,可以调整计划先安置选定的一小部分侨民,不应该生搬硬套上文提到的2017年为帮助那一大家人归国而在森图制定的粗糙方案,而应该因人制宜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更复杂的情况。
6. 确定寄宿家庭或社区,并与民间团体领袖合作,为侨民的回归做准备,相关准备工作可以立即启动。印尼政府可以研究其他国家在侨民(特别是儿童)重新融入社会方面所做的工作,看看是否可以相应地调整某些内容。不应低估很多社区里的反“伊斯兰国”情绪,应制定应急预案以应对民众的敌对情绪。这样也许能为新的重返社会计划奠定基础,不过必须有人牵头开展这项工作。
7. 长期追踪。政府必须制定一项追踪方案,不能仅仅满足于每半年一次的政府随机访问,但又不能过多干预,以免影响侨民重返社会。
8. 预算。政府需要拨出一大笔资金,哪怕是试验项目也花费不菲,并根据明确的、负责的成本评估加大资金投入。
撤侨工作组成员必须认识到一点,问题远比将前“伊斯兰国”成员从“反对印尼建国五原则”变成“支持统一的印尼共和国”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支持者要复杂得多。仅仅让他们在效忠誓词后签名是不够的,还要提高他们与不同宗教和背景的人交流的意愿。
五、结语
印度尼西亚政府应就如何界定叙利亚难民营中的弱势群体达成一致意见,并立即采取措施将其撤回,可以先将几个家庭或几批儿童作为试点,逐步简化程序。一些棘手的问题可以以后再处理,比如如何处理那些想要回国的高价值囚犯以及曾在“伊斯兰国”担任宣传员、庇护所管理员、教师、军医等重要职位的人,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在回国后面临起诉。
最根本的问题是:加入“伊斯兰国”的印尼人是不是就没有改过自新的希望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就需要加快速度帮助他们回国。如果政府认为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可以改造的,那就需要决定哪种情形更有风险——一种是让他们留在营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越发有可能与更危险的人结为同盟,越发有可能越狱或被库尔德人释放;另一种则是让他们回国,这样至少可以更好地对其进行追踪。
(摘译自印尼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第59号报告,2019年8月27日)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广西民族大学 符成远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