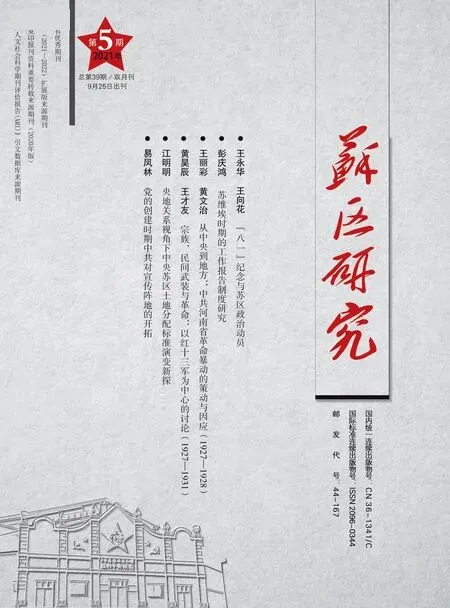宗族、民间武装与革命:以红十三军为中心的讨论(1927—1931)
黄昊辰 王才友
提要:1929—1932年间,红十三军在浙江省永嘉县西楠溪地区形成并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对红十三军结构的研究显示,其主力部队源自以当地宗族为核心的民间武装。地方革命精英通过由亲缘和学缘形成的宗族关系网络将民间武装串联为红十三军,并依托宗族开展游击战争,将浙江革命推向高潮。但宗族在助力革命的同时也制约着革命的发展,“宗族化”的浙南红军与党组织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红十三军的失败,浙南革命也因此陷入顿挫。红十三军从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为理解民间武装与革命的互动提供了极为生动的案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设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是各级党委肩负的重任之一。为此,各地党组织通过组织农民武装、策动旧军队起义或改造“会匪”等民间武装组建了一批革命武装,浙江概莫能外。其中,温州永嘉西楠溪地区被中央和浙江省委认为是浙南武装斗争的策源地之一,各级党委曾多次要求在当地组织、整顿武装力量。1930年2月,王国桢受永嘉中心县委之托前往西楠溪整编革命武装,但不久他即向中央报告整编武装遭遇较大困难,并将之归咎于当地两支“土匪”游击队——胡协和与谢文侯武装对整编的消极态度。(1)《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永嘉、瑞安及温属各县工作决议案》(1928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上,内部资料,1987年,第129页。《中共永嘉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0年2月3日);《王国桢的武装工作报告——在浙南组织红军的经过情形》(1930年3月28日),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内部资料,1989年,第187—188、288页。但此后这些游击队非但通过实际行动支持了革命斗争,甚至最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以下简称“红十三军”)的主要构成部分,王国桢的报告显然未能呈现出这一群体的复杂面貌。
围绕中共对民间武装的动员,学界业已展开一定讨论,如孙江曾分析作为土匪领袖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革命的原因,并提出二人被错杀深层原因是当地的土客矛盾,这无疑有所创见(2)孙江:《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杨会清曾就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土匪动员的策略进行一定梳理(3)杨会清:《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土匪的政策及策略演变——以革命动员的视角》,《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张永着眼于红军和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土匪问题,将中共的土匪政策划分为收编、改造以及清洗三个阶段,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向前发展。(4)张永:《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但已有研究多强调对“策略”与“效果”进行分析,较少考察到“实践”的具体环节。因此,笔者试图理清楠溪民间武装产生的基础,探讨地方革命精英对民间武装参与革命的推动作用,继而把握当地党组织与民间武装关系变迁的深层次原因,以求更全面地理解红十三军革命从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
一、御敌与械斗:宗族与楠溪民间武装群体的形成
楠溪江发源于浙江省永嘉县的溪下和潘坑两乡境内,自北向南汇入瓯江。括苍山余脉和雁荡山支脉在楠溪江流域汇聚,形成了山地、丘陵、盆地以及河谷交错的险要地貌。1920年代,多支民间武装在这种环境的掩护下进行游击斗争,并最终在地方革命精英的推动和串联下组建为红十三军。为全面理解红十三军的革命,首先需要对当地民间武装的情况展开分析。
西楠溪地区的民间武装有着长期的活动史,这首先体现为“绿林武装”的频发。清末民初,即有平阳士绅刘绍宽记载当地“有土匪蠢动”,瑞安乡绅张棡也曾提及此地因“目前土匪又多”而民不聊生。(5)刘绍宽撰、温州市图书馆编:《刘绍宽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99页;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1920年代后该地区绿林武装的活动更加频繁,最具代表性的是谷亨棉武装。1925年,谷亨棉带领同乡200余人参加了乐清李价人组织的浙江游击队,在游击队被蒋介石缴械后,他窃出数十枪支,与周明存、潘熙堂、潘善琴、徐定魁、李启林及李昌年等100余人于云山寺聚义,共盟生死,建立了当地规模最大的民间武装。1928年,谷亨棉率部参加了温州党组织策划的永瑞平三县联合起义,最终在起义失败后向地方政府投降。
团练武装活动的常态化是民间武装活跃的另一种表现。1890年,温州爆发饥荒,土匪横行,“楠溪灾黎亦蠢蠢思动”。鹤阳乡绅谢锡周组织团防,在“永乐交通之要道”分兵驻防,维持了社会稳定。1902年,他又率鹤阳壮丁200余人救援被土匪围困的70多名仙居商贩,使“负贩者皆生还”。1914年袁世凯复辟期间地方局势混乱,台州土匪周永广借“讨袁”之名招兵买马,“四处土匪蜂拥而至”,谢锡周再次率数百壮丁协助官方剿匪,使“匪溃散”。(6)吕渭英:《谢锡周七十寿序》,《鹤阳谢氏宗谱》卷1,1948年重修,永嘉县图书馆藏。在持续的“匪患”压力下,当地团练武装往往能保持较高的战斗力。
西楠溪民间武装的活跃与本地民众抵御外敌的需要紧密相关。长期以来,这一地区面临着倭寇等外来武装集团的威胁,为求自保,地方宗族往往自发或在官府号召下进行抵抗。如洪武二年(1369),枫林徐氏曾攻击掳掠乐清蒲岐的倭寇,使“盗不得入”。嘉靖三十七年(1558),枫林徐氏击退了自乐清登陆的倭寇。(7)徐逸龙:《枫林武术文化文化研究》,《永嘉方志》2014年第5期。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的率领下进攻浙南,并派偏师穿越楠溪攻打温州府城。枫林徐氏和岩头金氏等宗族组织乡勇进行抵御,取得“一日三胜”的战绩,甚至还赴乐清支援当地民团作战,最终击退了太平军。(8)[清]陈瑶:《楠溪战御发贼记》,《永嘉方志》2013年第4期。
宗族械斗亦是民间武装活跃的重要原因。为争夺资源,西楠溪各宗族往往“纠众持械互斗,酿成巨案”(9)[清]戴槃:《议建同知守备衙门移驻枫林镇记》,吴明哲编:《温州历代碑刻二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枫林徐氏与岩头金氏自咸丰十一年(1861)起持续11年的宗族械斗(当地称为“金殿龙控案”)。此事的起因是徐氏和金氏对官山资源的争夺,枫林以南原有公共官山数十亩,向来允许其他宗族入山樵采,但每人每年需向徐氏缴纳一升米作为山租。咸丰十一年春,徐氏族长徐兆庠认为“收米值钱无多”,倡议改为每人出钱一百文。但金氏认为“此山实系官荒”而不肯出钱,并坚持进山樵采。徐金二族随后为此爆发械斗,造成金氏多人死伤。此后,二族针对此事件展开持续多年的诉讼和械斗。最终导致岩头金氏死难101人,12座宗祠和1000余间房屋被焚毁。(10)[清]毛昶旭:《金殿龙控案始末》,郑笑笑、潘猛补编:《浙南谱牒文献汇编》,香港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305页。从“金殿龙控案”不难看出当地宗族械斗规模之大,烈度之高。
正是上述背景催生了1920年代西楠溪的游击队伍。1928年8月,永嘉五鸂人胡公冕奉周恩来之命回到故乡,授意胡协和与胡衍真、胡国金、胡象浪、胡黄金、胡世筻等私交甚笃的族人组建游击队。原隶属于谷亨棉武装的徐定魁、潘善琴以及周明存等人也在此时组建了以宗族成员为骨干的武装。潘善琴武装主要来自岭头地区的潘氏、陈氏和李氏等家族,其中潘氏家族成员超过30名;周明存武装由数十名东皋周氏族人为骨干,此外还包括龚氏等宗族成员;徐定魁武装主要由鹤盛地区的徐氏和谢氏等宗族构成。同期在楠溪地区活动的还有以陡门卓氏为核心的卓平西武装和以马田村、廊下村和花坦村等地朱氏为核心的朱德洪武装,两支武装汇合后人数达100余人。(11)《隘门岭事件死难者英名录》,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永嘉县新四军研究会编:《浙南历史公案:隘门岭事件》,内部资料,1997年,第106—110页;朱文豪编:《两港风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83页。朱茂昌:《革命薪火父子传》,《温州日报》2016年10月12日,第9版。这些武装时常相互配合,影响力日渐扩大。
而同期在西溪地区活动的有谢文侯、董祖光、章华、胡秀及杨岩斌等民间武装。谢文侯是温州党组织创始人谢文锦的胞弟,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受永嘉县委的委派,于家乡潘坑及附近的北溪、碧莲和溪下等地组织起200余人的部队。(12)周天孝:《史林一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9页。董祖光于1928年1月由永嘉县委农运委员李振声发展入党,并与其兄董祖维在家乡上董村及邻近的界坑、杨庄、西岙、黄寮等地组织起300余人的武装。下坑口村章华在1928年时被李振声发展入党,后在家乡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民间武装。茗岙村富户胡秀在1928年被李振声等人发展入党,并组织起以同宗胡继桃、胡继顺及茗岙陈氏族人陈明善为骨干的茗岙农民武装。(13)潘泰勇:《西内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组织的建立》;蒋寿平:《顽强苦斗的红军营章华烈士》;蒋寿平:《红军独立大队长胡秀烈士》,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南红军的摇篮:永嘉县小源地区革命斗争史料》,第18、252、259页。瞿岩龙、徐李送主编:《血染的丰碑:红十三军斗争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富蝉村杨岩斌与董祖光、章华等人同期被发展为党员,将家乡大部分村民组织为武装,并在1928年永瑞平三县联合起义前夕发展为西溪地区最大的一支农民武装。在廿四垅,潘玉如和表哥戚玉波动员了徐岩星、徐岩枢和徐岩印等人组建武装,并很快发展到100余人。(14)潘玉如:《廿四垅区党组织与红十三军》;尤国贤、王昌栋、徐御静:《英勇无畏的红军连长徐岩星烈士》;李长飙、王昌栋:《有胆有识的红军大队长杨岩斌》;蒋寿平:《危难见丹心——戚玉波烈士传略》,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永嘉县新四军研究会编:《风雨钟山:永嘉县西溪地区革命斗争史料》,第129—131、299—301、306—307、332—333页。这些民间武装还利用西楠溪地区“枕戈待旦”的环境获得了武器,如章华和谢文侯在组建武装时从民间收集到枪支、长矛或是腰刀等武器,胡秀在筹备武装之初组织铁匠赶制大刀、长矛、火铳以及匕首,完成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以上述民间武装为核心的5000余人在当地党员的组织下暴动。面对这一有利局面,浙南党组织注意到民间武装与当地宗族的关系,并尝试利用族际关系将他们整编为革命武装。分析理解这一过程首先需要对西楠溪地区宗族关系进行简要的梳理。
二、亲缘与学缘:楠溪革命的宗族网络
西楠溪的宗族多在唐末五代之际自福建迁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诸多地方大族。其中,枫林徐氏、岩头金氏、表山郑氏、五鸂胡氏以及蓬溪谢氏等宗族规模尤其庞大,形成一村一姓的望族聚居格局。由于宗族在西楠溪地区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该区域的历史视为宗族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联系的历史,这些联系使各宗族在亲缘与学缘的作用下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宗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以枫林徐氏为例,望族金氏是其重要的联姻对象。据《凤屿金氏宗谱》载,国学生金德俊有五女,次女与四女先后嫁枫林生员徐存智,其中次女即是后来的监察御史、温州都督徐定超之母。徐定超的母舅金贞元,曾办理团练并参与了抵御太平军的战斗而被授予六品衔候选训导,其子女延续了和徐定超家族的联姻。(15)[清]孙衣言:《羲一公六旬荣寿序》,《浙南谱牒文献汇编》,第110页;卢礼阳:《徐定超年谱》,陈光熙编:《徐定超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28页。如金明汉娶徐定超之妹,其子金省真与中共浙南革命的关系犹深,曾与温州革命主要领导者金贯真共同发起了传播与讨论新文化的“溪山学友会”,并于此后加入青年团温州支部。
徐氏与蓬溪谢氏亦结秦晋之好。徐定超在《鲁庭谢先生七旬寿序》中称蓬溪谢氏乃“吾家旧姻也”,形容的便是双方自徐定超祖母(蓬溪谢氏女)以来连续多代交好并且“迄今勿衰”的关系。(16)[清]徐定超:《鲁庭谢先生七旬寿序》,陈继达编:《监察御史徐定超》,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另外,联姻也扩展了双方的社会交际,如谢文波娶徐定超的表姐后双方往来日益密切,其孙谢雪轩得到了徐定超的提携并进入楠溪高等小学就学,此后又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简称“温独支”)并任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执行委员。
五鸂胡氏是徐氏的另一重要联姻对象。徐定超之妻是五鸂的胡德淑,其内侄胡卜熊与胡惠民则分别娶枫林徐氏的女子为妻。胡卜熊是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在姑丈徐定超的支持下创办广化高等小学,1930年代曾凭借自身影响力暗中协助革命。在徐定超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期间,胡惠民因“内亲而谨厚”被“委充机要”,此后,在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温独支,并在1931年保护了100余名参加红军的胡氏族人。此外,胡德淑的远房侄子、后来的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曾在徐定超帮助下在杭州新军随营学校当兵,后又经徐定超介绍进入浙军吕公望师部工作。(17)胡卜熊:《胡惠民行状》,郑笑笑、潘猛补编:《浙南谱牒文献汇编》第3辑,香港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徐顺平:《胡公冕访谈录》,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资料,2005年,第128页;胡公冕:《我的经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4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作为温州革命的重要参与者,表山郑氏、五鸂胡氏与岩头金氏之间同样互相联姻。表山郑氏与五鸂胡氏较早便开始通婚,据《表山郑氏宗谱》载,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的郑廷坚是首位与胡氏联姻的郑氏子孙。双方的联姻延续至民国时期,浙南革命先驱郑恻尘与胡识因夫妇即是代表。郑氏与岩头金氏的通婚应始于明代早期的第17世孙郑文语,第18世至第20世皆有嫁娶于岩头金氏的记录,而根据笔者对岩头金贯真后裔金爱伦的采访,可知金贯真妻子郑玉钗出自表山郑氏,亦可推测民国时期双方仍相互通婚。(18)《表山郑氏宗谱》卷1,同治五年(1866)重修,永嘉县图书馆藏。
蓬溪谢氏的谢大旭在康熙年间迁居潘坑,形成了不同于本家的婚姻网络,与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枫林徐氏、表山郑氏和北溪杨氏。就枫林徐氏而言,徐定超的舅公谢思义是谢大旭之孙;谢大旭的曾孙谢国广续妻为枫林徐象泽遗孀、珠岸陈道济之女陈氏,他们的儿子是永嘉革命者谢文锦和谢文侯。谢氏与北溪杨氏的通婚不晚于谢大旭之孙谢恭孚,其妻为北溪杨氏女,长女和孙女亦分别嫁给北溪杨茂庆和杨淳晓。潘坑谢氏与表山郑氏的联姻同样广泛,如谢大旭曾孙女嫁给了表山郑朝云,谢国广之女嫁给了表山郑九芳。在日后谢文锦和谢文侯兄弟成长与革命的过程中,枫林徐氏、表山郑氏及北溪杨氏都提供了帮助。(19)《蓬溪谢氏宗谱》卷1、卷5、卷6、卷7,1928年重修,永嘉县图书馆藏。
在婚姻亲缘外,以同学和师生关系为代表的学缘关系是宗族关系网络形成的另一媒介,其中学校成为学缘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同治七年(1868),徐定超讲学于温州东山书院,“门下弟子以数百计,岁科两试,得选者半出于门”,为以枫林徐氏为中心的关系网络的形成奠定基础。(20)徐象藩、徐象标、徐象先:《哀启、行述》,《监察御史徐定超》,第328页。进入20世纪后,新式学堂取代了旧式书院,成为宗族子弟学习与交谊的新渠道,其中楠溪高等小学和广化高等小学最具代表性。光绪二十九年(1903),徐定超委托其侄徐端甫在枫林志仁书院的基础上创办高等小学,并成功游说两任县令秦乐平和程子良各捐100元,之后西楠溪乡人“相继乐输者多至数百家”,共集赀3000余元作为办学经费。(21)[清]徐定超:《楠溪学堂碑记》,《温州历代碑刻二集》上,第232页。一时间,楠溪各宗族学子纷纷汇集于枫林,其中不乏后来永嘉政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广化高等小学由徐定超内侄胡卜熊等人于1908年创立,师生也来自于各大宗族,如出自表山郑氏的郑恻尘曾在广化高等小学堂就职,而蓬溪谢氏的谢文锦和谢雪轩等曾于此就学。(22)胡国洲:《胡卜熊事略》;李仲芳:《我的生平》;周天孝:《李得钊事略》,永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永嘉文史资料》第4辑,第118、169、238页。周天孝:《谢文锦》,张义渔编:《上海英烈传》第3卷,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此外,执教也成为各宗族成员扩展学缘关系的主要渠道。如胡公冕于1912年经姑父徐定超介绍进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任教,结识体专教员、永嘉芙蓉人陈叔平,又在同年秋转任浙江一师体育教员期间结识了谢文锦,为二人日后携手开展革命工作奠定基础。1924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公冕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在郑恻尘等人的协助下征募了30余位西楠溪青年学生到黄埔军校受训,其中有胡秀等未来浙南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双方形成师生之谊。(23)徐顺平:《胡公冕访谈录》,《温州文史资料》第19辑,第128—130页;周天孝:《谢文锦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红旗飘飘》编辑部编:《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而谢文锦从浙江一师毕业后接办岩头高等小学(即原广化高小)并担任校长,期间与金贯真、李立敬及李得钊等青年学生熟识,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宗族间的学缘关系。(24)李立敬:《怀念谢文锦老师和李得钊、金贯真同学》,周天孝编:《师生英烈耀千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总之,西楠溪宗族通过亲缘和学缘缔造并深化了关系网络,在地方教育和文化领域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19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温州传播,一批地方革命精英在宗族关系网络的影响下开展了党团组织的筹备工作。1924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时任上海地委委员的谢文锦回到永嘉建党。在郑恻尘和胡识因夫妇的陪同下,谢文锦考察了西楠溪地区的枫林、珠岸、表山和蓬溪等地,期间创立了由胡识因担任书记的温独支和由戴宝椿担任书记的共青团温州支部。温独支首批党员中,胡识因、胡惠民是五鸂胡氏族人,郑恻尘是谢氏谊族表山郑氏族人,俱与谢文锦私交甚笃。而青年团首批团员中,来自岩头金氏的金守中、金弘谛及金贯真和来自港头李氏的李得钊皆为谢文锦的得意门生,来自溪口戴氏的戴宝椿是谢文锦的同学,谢雪轩则与谢文锦同族。(25)《谢文锦介绍戴宝椿等8人加入S.Y》(1925年);《温州独支早期成员名册》(1925年上半年),解放军档案馆编:《红十三军与浙南革命斗争》,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3、64页。从中不难发现宗族成为温州革命肇兴的巨大助力,这一特征同样体现于日后的革命进程中。
三、串联与革命:从民间武装到红十三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主要革命根据地中存在着强大的宗族力量,而地方革命精英妥当地处理了宗族与红军及革命的关系,使革命顺利发展。早在1925年,赣东北的方志敏和邵式平已在弋阳开展革命活动,依靠亲戚关系创办了农会和党支部,并开展了“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黄道也在横峰组织成立了革命团体“岑阳学社”,并于次年成立了中共横峰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两地的中共组织和农会力量在他们的影响下恢复或发展,如方志敏在1927年9月恢复了弋阳九区的20多个党支部,并在数十个村坊中组织了半军事化的农民武装;而在黄道的堂兄黄端喜带领下,横峰地区的农民组建了农军并攻打了横峰县城。(26)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弋阳县党史大事记》,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中共横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横峰党史大事记》,内部资料,1994年,第2、4页。与之类似,陈毅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东固一带是以附近之知识分子(系吉安南昌读书的学生)为基干,他们在外面加入中国共产党,受豪绅压迫跑回来,利用家族关系,以东固附近一带山林为基础向豪绅游击”。(27)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孙伟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史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其中代表者是赖经邦,他在1927年2月成立了中共东固小组,并动员家人支持和参与革命,其姐夫段月亮是当地“三点会”武装首领段起凤的兄长,因此这支“三点会”武装被成功改编为东固农民武装。(28)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沈庆鸿:《东固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人——赖经邦烈士传略》,政协吉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吉安县民政局编:《庐陵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90年,第37页。
可见,革命精英依靠宗族关系组织革命武装是较为普遍的举措,这也体现在浙南革命武装的形成过程中。以谢文锦的胞弟谢文侯为例,他由于曾赴苏留学而受到了永嘉县委的信赖,同时又具有较为丰富的宗族关系,因而被县委派遣至家乡组织武装。最初,他利用宗族关系动员了潘坑的谢氏族人参加武装,随后又在碧莲徐氏中联系了徐宗挑和徐宗杰等人参加武装,在溪下村通过表兄弟金炳辉、金晶山、金寿康和金寿南的关系组建了溪下农民武装,在有姻亲关系的北溪杨氏中组织了数十人的武装。1929年底,上述部队在溪下村被整编为10个中队,人数达200余人。(29)周天孝:《史林一叶》,第17-19页。
胡协和、戴盛为、徐定魁、周明存、卓平西以及潘善琴等在五鸂及其周边地区活动的民间武装则在另一地方革命精英胡公冕的影响下实现联合。其中,戴盛为来自长期与枫林徐氏及表山郑氏等联姻的溪口戴氏,与胡公冕等熟识并曾任共青团温州支部首任书记的戴宝椿亦出自该族。徐定魁来自枫林徐氏,潘善琴出自岭头潘氏,周明存来自东皋周氏,而卓平西是胡公冕结义兄弟金守辰的妹夫。胡协和利用他们与五鸂胡氏或胡公冕的关系,顺利将上述武装整合起来,到1930年初,胡协和部队已发展至近400人。总的来看,虽然胡协和与谢文侯部队的形成略有区别,但都离不开宗族关系的串联作用。
在西溪地区活动的胡秀、杨岩斌与戚玉波等人或为富裕家庭的子弟,或接受过一定教育,或有一定威望,在各自村落中都具有一定号召力,这成为他们凭借宗族关系组建革命武装的基础。另外,他们由永嘉县委发展入党,其部队与党组织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也成为与上述其余部队的一大区别。1930年初,他们在雷高升指导下完成了对部队的整顿,浙南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已经形成。(30)《浙南农运的杰出领导人——李振声烈士传略》,《风雨钟山:永嘉县西溪地区革命斗争史料》,第325页。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遣胡公冕和金贯真回到永嘉组建红军,作为来自楠溪宗族的革命精英,二人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丰富的党内资历、军事经验以及社会关系使胡公冕迅速被永嘉县委与民间武装接受。金贯真同样具备相应的优势,他来自大族岩头金氏,与表山郑氏、蓬溪谢氏和五鸂胡氏等宗族的联系较为紧密;同时,作为温独支时期入党且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党员,他具有明显的资历优势和威望;更重要的是,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使他在温州党组织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此前,永嘉县委曾尝试整顿相对独立的胡协和与谢文侯武装却未竞其功,而前述优势使胡公冕和金贯真能利用宗族关系理顺红军的内部关系。作为胡协和的“自家人”和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胡公冕迅速完成了胡协和部队的整顿,将其改编为12组96人。金贯真利用同学和亲戚的双重身份,亲自对谢文侯开展工作。(31)李立敬:《怀念谢文锦老师和李得钊、金贯真同学》,《师生英烈耀千秋》,第180—182页;金、谢二人的妻子均来自表山郑氏,参见周新天:《文心涅盘:谢文锦烈士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经批评教育后,谢文侯“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开始配合县委的工作。内部整顿完成后,永嘉中心县委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将温州游击队改编为浙南红军第一独立团,并集中一切力量向温州进攻,胡公冕等人随即利用宗族关系开展武装斗争。红军游击队的首个进攻目标枫林镇是楠溪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处于要冲且地势险峻,防御设施完善,浙江保安第四团的一个连驻防于此,强攻难度较大。恰巧,驻军连长谢次如是受胡公冕招募而赴黄埔军校受训的学生之一,二人存在师生关系,红军遂试图策反驻军巧取枫林。由于这一密切的关系,谢次如“满口赞成”兵变计划,但他随即因“犹豫不决”而去征求豪绅徐端甫的意见。然而此时胡公冕与徐端甫所在的徐氏尚未协商一致,这一行动不出意外遭到了徐的反对,兵运工作未能成功。(32)《王国桢的武装工作报告——在浙南组织红军的经过情形》(1930年3月28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188—193页。
面对不利局面,胡公冕尝试利用亲戚关系说服徐氏同意红军的行动。他致信徐氏,希望允许红军进入枫林,徐氏收信后召集各房代表商议,最终同意红军在枫林集中。5月3日,胡公冕与枫林徐氏所派代表商定了进入枫林的具体方案。5月9日,红军在象征性地攻城后进入枫林。(33)胡国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团战斗在浙南》,《永嘉文史资料》第1辑,第18页。当夜,胡公冕和金贯真在慧日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红十三军军部与第一团,二人分别担任军长和政治委员。(34)周天孝:《“浙江的金龙”——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政委金贯真烈士》,浙江省民政厅编:《英烈千古浙江革命烈士事迹选辑》1,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雷高升担任红一团团长,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由雷高升兼任,第二大队大队长为胡协和,第三大队大队长为谢文侯。
枫林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使胡公冕等人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宗族关系的借助。综合中央要求与实际情况,红军将武装斗争基础良好的平阳作为进攻目标,因此胡公冕计划利用结拜兄弟、时任平阳禁烟专员陈叔平的关系策反当地驻军,并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里应外合攻占县城,政委金贯真遂先期赴平阳联系陈叔平布置攻城方案,红军主力则稍后从永嘉出发。(35)据胡珠生研究,孙九德是金贯真的学生。参见胡珠生:《温州近代史》,第363页。然而,金贯真未完成任务便被捕牺牲,导致红军攻入平阳城内后与闻讯而来的稽查队展开混战,县城驻军亦“闻警遂乘城射袭焉”,城外敌军也开展了反击。多方夹击下,红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36)刘绍宽:《周金标李胜传序论》,《厚庄文稿》(四),手稿本,转引自徐逸龙:《红十三军攻打平阳县城真相》,温州市博物馆编:《温州文物》第13辑,第35页。
平阳之战失利后,胡公冕返回上海向中央述职,红军由陈文杰和雷高升负责。在特委指导下,红军继续在西楠溪开展武装斗争。这一阶段,宗族成为红军肃清地方反对势力的媒介。如西楠溪重要的豪绅据点瓯渠,防御工事完善,地主吴恩侯多次组织民团阻挠红军。(37)瓯渠民众“素工拳棒”,当地豪绅借此组织了强大的保卫团,西楠溪豪绅多于瓯渠躲避红军。参见《永嘉游击队攻下后渠,保卫团丁不肯和游击队作战》,《红旗日报》1930年9月17日,《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然而革命形势持续高涨后,民团首领吴玉林等人有意缓和与红军的关系。来自瓯渠的红军干部吴凤祥得知后,利用亲房好友的关系开展工作,成功推动民团与红军进行和谈。尽管吴凤祥不幸被捕牺牲,但经过策反的民团无意对抗红军,使红军迅速攻克了瓯渠。(38)《碧血丹心的铁夫——吴凤祥烈士传略》,《风雨钟山:永嘉县西溪地区革命斗争史料》,第279页;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永嘉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与此同时,红十三军将五鸂和表山作为主要基地,宗族成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依托。如军部设置在五鸂时,乡长胡卜熊组织妇女和儿童放哨,成功掩护了军部活动。(39)胡国洲:《胡卜熊事略》,《永嘉文史资料》第4辑,第170页。在郑氏的支持下,红军常在表山集结与整训。据当地老人回忆,每当红军回村,家家户户都为部队准备粮食。此外,红军还利用宗族关系发展游击队和赤卫队,协助军事行动。如第二营营长章华和指导员章玉麟组织了石染章氏等宗族的适龄青年参加军事训练,并将其他有家庭和生活牵挂的人编入赤卫队,为出征的红军提供给养。(40)蒋寿平:《顽强苦斗的红军营章华烈士》,《浙南红军的摇篮:永嘉县小源地区革命斗争史料》,第253—254页;胡国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团战斗在浙南》,《永嘉文史资料》第1辑,第18—27页。
在宗族的支持下,红十三军的游击战争顺利开展,沉重打击了地方豪绅和国民党的统治。如李茅村豪绅陈时东、陈乾鸣等人组建民团对抗革命,成为红军首要目标。6月30日,雷高升率第一团攻占李茅,处死陈乾鸣。随后,雷高升率部攻克另一“反革命”乡村下寮,捕获处决对抗红军的豪绅王汉之与王国朗。“反革命”势力偃旗息鼓后,红军依托西楠溪四处出击。8月底,为打通与永康红三团的联系,军部决定攻打缙云。经过一日的激战后红十三军攻克缙云县城,取得建军以来最大胜利。可以说,红十三军如同楔子,成功插入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为进一步支持浙南革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派胡公冕携同留苏回国的老江(临海人)、王麻子(福建人)、杨波(湖北人)、老陆(四川人)与李立敬(永嘉苍坡人)回到永嘉组建教导队,力图解决干部匮乏这一长期制约红十三军发展的问题。(41)李立敬:《军部活动片段》,《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第207页。然而,浙南革命的形势却未持续高涨。
9月上旬,红十三军为打通与台州红二团的联系而向黄岩进攻,然而国军及浙江省保安团此时已经不断增援温州,并从多个方向“清剿”红军。9月下旬,红军一部成功占领黄岩的乌岩,但却在浙保五团的威胁下被迫撤退。10月,雷高升率部向瑞安进攻途中,在浙保四团的袭击下损失惨重。1931年5月后,局势更为恶化,胡协和已在胡公冕的授意下“假招安”,成为了永嘉县政府的“侯差员”;谢文侯因被开除党籍而“刺激很深”并“消极起来”,最终“自首叛党”;仅有雷高升部队300余人尚且坚持斗争。(42)《王国桢给中央的报告——浙南暴动失败后目前党组织的状况》(1931年5月17日),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1931)》,1989年,第90页。谢文侯:《补充反省书》(1949年12月23日),原件藏于温州市公安局,转引自刘定卿:《浙南红十三军传》,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显然,自1930年9月至1931年5月,浙南革命形势发生了逆转,其中缘由值得深入的推敲。
通过比较浙南和赣东北、东固地区革命兴起的过程,不难发现赣东北和东固地区的革命精英虽然同样借助了宗族的力量,但他们首先利用宗族建立党组织和农会,随后通过党和农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最终发动暴动。这一过程中,方志敏和赖经邦等地方革命精英的宗族关系固然无可替代,但他们作为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创建者的威望亦不可或缺。而浙南党组织虽然最初同样在宗族中形成,但大革命失败后,浙南党的缔造者或被捕牺牲(如谢文锦和郑恻尘),或出国暂避(如胡识因)。重新恢复的党组织及后来浙南特委的负责人和宗族的联系不再紧密,革命武装的形成更多的依赖宗族内部和宗族之间的串联而非党组织的主动协调。而党组织和宗族的联系,则更多的取决于革命精英的意志,这使宗族在助力红十三军串联的同时造就了一批“宗族化”的部队,党组织和红军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隔阂”,最终导致浙南革命的命运与赣东北及东固革命产生了较大分异。
一方面,“宗族化”使部队的控制权由革命精英而非党组织直接掌握。如谢文侯部队具备较高的独立性,对党组织的整编和指挥置若罔闻,在武装斗争中“不努力进攻”甚至去当“落壳”(指上山落草),其内部则根据宗族和地域的不同分为“大元班”、“小元班”以及“潘坑班”。(43)《王国桢的武装工作报告——在浙南组织红军的经过情形》(1930年3月28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187—190页。这一情况直到金贯真到来后才有所转变。胡协和部队的“革命性”虽略好于谢文侯部队,但这一部队与胡公冕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在1929年西楠溪暴动后,胡协和等人未经永嘉县委同意便赴上海邀请胡公冕回乡主持大局。为此,浙南特委不得不承认党在红军中“没有很好的基础”,并多次批评红军中的“地方观念”和“不易指挥”的倾向。(44)《中共浙南特委七月份工作报告》(1930年10月8日);《超时关于浙南情况的报告》(1930年11月21日);《中共浙南特委报告第二号——红十三军的现状及其应做的工作》(1930年10月26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258、264、274页。
这种“倾向”对浙南革命的损害颇为严重。如1930年6月,徐定魁、周明存和潘善琴等为补充平阳之战中损失的武器,在未告知浙南特委和红十三军军部的情况下,率领部队前往海门收缴枪支。最终,这些部队在乐清隘门岭遭到大荆民团伏击,徐定魁、周明存及战士400余人牺牲。(45)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等:《关于红十三军隘门岭惨案的调查报告》(1992年6月30日),《浙南历史公案:隘门岭事件》,第14—16页。部队首领叛变革命的现象亦时有发生,如董祖光和周诜袍等人在武装斗争中陆续投敌,他们不仅出卖了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等重要干部,还多次配合浙江省保安团和地方民团攻击红军。(46)潘庆佐:《“赤脚大仙”陈文杰烈士》,《浙南红军的摇篮:永嘉县小源地区革命斗争史料》,第249—250页;《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张小武烈士简介》,中共仙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仙居县民政局编:《仙居英烈》,1991年,第16页;《中共永嘉历史》第1卷,第70页。不得不说,这些情况成为浙南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隐患。
另一方面,“宗族化”使红军的斗争路线逐渐背离中央的要求。对中央和浙南党组织而言,开展政治斗争,尤其是“实行红军应做的整部政纲,实行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必由之路。(47)《金贯真给中央的报告——在浙南组建红十三军的经过情形》(1930年5月13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199页。但在武装斗争中,深受“富农路线”影响的红军却未深入开展土地革命。(48)《王国桢给中央的报告——浙南暴动失败后目前党组织的状况》(1931年5月17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1931)》,第89—98页。所谓“富农路线”指的是红军对宗族力量的借重,如枫林之战时,胡公冕与徐氏议定红军只能“选择一些破房子,拆下木料焚烧,将财产损失减轻到最低限度”,并枪决了有不法行为的红军班长李陀四。(49)谢次如口述,谢庆潮整理:《谢次如回忆》,转引自徐逸龙:《红十三军成立旧址枫林镇慧日寺考述》,温州市博物馆编:《温州文物》第8辑,第83页。这样的局势中,红军显然缺乏开展土地革命的条件。这一策略还使红军对政治工作采取消极态度,胡公冕甚至在游击过程中担心“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而提出“朝做政治夕必消灭”,被王国桢形容为“等待主义”和“军事投机”。(50)《王国桢的武装工作报告——在浙南组织红军的经过情形》(1930年3月28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188—190页。
即使胡公冕因此被调回中央,红十三军的革命策略仍未大幅度调整。在攻占瓯渠和缙云等地后,红军仅仅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和烧毁县署的文契,未能开展“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赤色区域”的工作,因而遭致中央和江南省委巡视员的批评。在五鸂和表山等后方基地,红军因需要当地宗族的支持,也未能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事实上,若在宗族氛围相对和睦的环境下打击地主、焚烧田契,难免使当地的红军指战员产生“当红军这样难,我们不当了”的心态,导致红军的处境更为被动。(51)《潘心元巡视浙南的报告——浙南党和军队的近况》(1930年9月24日);《超时关于浙南情况的报告》(1930年11月21日);《中共浙南特委报告第二号——红十三军的现状及其应做的工作》(1930年10月26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246、264—265、274页。受此影响,红十三军始终未能建立相对稳固的游击根据地,这同样成为制约浙南革命长期发展。
中央和浙南特委对“宗族化”现象的整顿也未能成功。在特委看来,“摧残”民间武装首领,由雷高升部队统一吸收和指挥其余各支部队是最彻底的举措。但在金贯真牺牲后,党组织与宗族的关系渐渐疏远,而在部队中“又没有很好的基础”,很难做好普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故而特委军委到楠溪后,仍然只能召集各部首领举行会议,通过推举谢文侯担任“主席”等“军事投机”的举措维系双方的关系,以致会议“无结果而散”。(52)《中共浙南特委七月份工作报告——浙南的政治形势、党组织状况、军事工作等》(1930年10月8日);《中共浙南特委报告第二号——十三军的现状及其应做的工作》(1930年10月26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258、264页。“宗族化”非但未能解决,反而愈发严重。
最终,这些源自“宗族化”的问题使红十三军的武装斗争逐渐失败。胡公冕于1930年9月初返回永嘉后,抽调了红军的精干组建了教导队,随即自行决定攻打黄岩,与之关系密切的胡协和与谢文侯部队随同行动,雷高升则于10月初率剩余部队向瑞安进攻。而特委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未能获得红军的动向,因此判断红军被胡公冕“带跑了”。(53)胡公冕被调回上海的主要原因便是王国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批评胡公冕“走的旧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参见《中共中央给温州中心县委、金贯真及温台永三属红军的信》(1930年5月23日),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南革命历史文献汇编(一、二战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59页。此次分兵导致红军的战斗力大幅下滑,非但未能完成预定目标,反而分别在黄岩乌岩和青田白岩两次战斗中损失惨重。(54)《中共浙南特委报告第二号——十三军的现状及其应做的工作》(1930年10月26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264页。不仅如此,随着国民党军“清剿”不断加剧,红军面临的威胁日趋严重。为此,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胡公冕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主力部队分散游击。可是,缺乏稳固根据地的红军在经历几次“清剿”后“动摇起来”,部分部队“觉得没有出路,遂投顺了”,剩余部队在坚持1年后最终失败,红十三军革命“从此告一段落”。(55)《王国桢给中央的报告——浙南暴动失败后目前党组织的状况》(1931年5月17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1931)》,第94页;《中共永嘉历史》第1卷,第86—87页。
结语
既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中共改造“会匪”等民间武装的政策,分析其演化与成效。本文以永嘉西楠溪的民间武装为切入点,希望以红十三军借助宗族串联民间武装、推进革命的具体实践,呈现出民间武装参与革命的复杂态势。这一过程中,当地宗族既对浙南革命的发轫和开展产生积极作用,又是革命陷入低潮的根源。
具体而言,宗族间的亲缘和学缘关系了造就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这成为地方革命精英建党、组织武装及开展武装暴动的前提条件。1920年代,谢文锦等人运用这一关系网络将亲戚朋友发展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创建了温州的党团组织。随着西楠溪武装斗争的发展,这一网络亦成为民间武装兴起和汇合的媒介,催生了胡协和与谢文侯等民间武装。随后,胡公冕与金贯真等人继续运用这一关系网络,将上述民间武装动员和改造为红十三军。在宗族的支持下,红十三军先后攻打了枫林、李茅和瓯渠等豪绅据点以及平阳和缙云等县城,对地方反动势力造成沉重打击。然而,部分“宗族化”的红军未能得到彻底的改造,隘门岭事件和乌岩之战都凸显了党组织难以约束红军的困境,这对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不利影响。此外,红军未能贯彻落实上级的革命策略,导致群众基础良好的五鸂和表山未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根据地。这些缺陷在革命顺利时未必有所显现,但在逆境中却使缺乏足够支持和约束的红军最终分崩离析,浙南革命因此陷入顿挫。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客观看待胡公冕、金贯真等地方革命精英和浙南党组织为解决分歧,使多股革命力量形成合力而做出的努力,可以说,双方的协同配合是红十三军革命走向高潮的必要前提。虽然红十三军最终失败,但在三年的斗争中打击了国民党在浙南的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军“围剿”临近苏区的部分兵力,侧面支援了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此外,红十三军传播的革命思潮产生了持续性影响,成为1936年后红军挺进师建设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助力,推动浙南成为“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56)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透过红十三军革命我们还可发现,这类深植于地方社会的民间武装与当地党组织的关系难以概括为单方面的“动员”和“改造”,在革命的动态过程中双方均展现出自身的“主体意识”。对以王国桢为首的浙南党组织来说,解决革命队伍中的隐患,彻底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与要求是其基本目标。但民间武装的首领有其自身的意志和诉求,他们未必能理解和支持党组织的政策方针,其举动便往往有悖于党组织的要求。这种“主体意识”成为影响党组织联络民间武装成败与否的关键,对其分析将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体察民间武装对“动员”和“改造”的反应,从而全面理解革命面临的复杂和困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