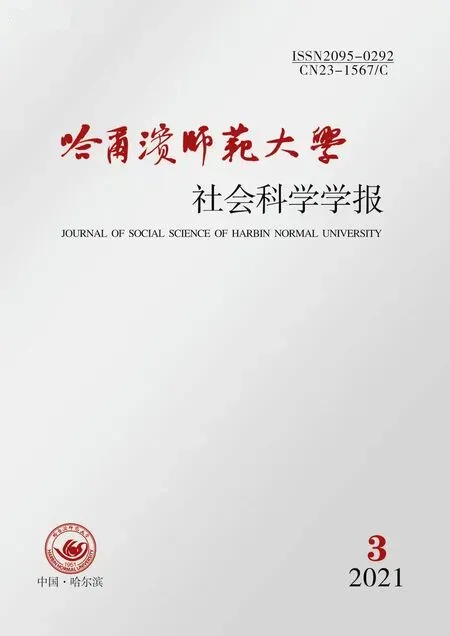大众娱乐与民族复兴
——论民国时期的历史剧
王沛轩,刘 莉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民国时期的历史剧不单为戏剧界所重视,一大批文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等均聚焦于此,成为各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民初历史剧以多元思维和现实诉求出发,极力鼓吹其现实意义,使历史剧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区判。但随着国内危机的日益加重,时人对历史剧的观念逐渐改变,结合爱国浪潮以发挥民族固有精神成为其主流视野。剧作者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使大众娱乐与民族精神二者相融。历史剧在宏观背景变革下所产生的变化,并非单纯的改弦易张,背后是与时代情景的呼应。因此本文意欲通过考察历史剧,探寻大众娱乐与民族精神之间调适的落脚之处。
一、民国时期的历史剧认知
民国时期“剧”之含义网罗了中国传统戏剧与西方话剧等,亦使历史剧承载了新的责任与意涵。正如陈大悲所言“当此旧时代已去新时代到临的时候,一切旧的东西,无论他是中国所固有的或是由外国贩运过来的,都要经过一番重新估价的手续,才能够确定他的地位”[1](P1)此类认知流行于时人之中,故历史剧在民国时期自要革旧图新。
民国时人对历史剧的阐释对应于时事剧,作为表达现代意识的一体两面。时事剧取材于社会热点,明言社会弊端或鼓吹现代观念,体现了剧作者对于现实环境的关注。如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评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一样“历史在这里当然不是指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在专业分工的情况下进行的对过去的学术研究,而是指一个保持着活力或重新激发的集体意识,一个‘被回忆的过去’”[2](P61)。同样,民国剧作者也认为历史剧并非简单的搬运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有论者指出历史剧需要“写成面目一新的现代化的剧本”,以暗讽时弊为责任,并赋予“新思想的表现”[3](P112)。欧阳予倩所言历史陈迹“总是死的”,现代舞台的历史剧应“要现代化而有新生命”,其新意又可分为两层,一是精神,一是形式,“前者就是故事加以新解释,与以新的人生观;后者是演法的变更”[4](P84)。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剧界对历史剧认知框架的更新展露了对其现实价值的追求。简言之,对民国时期的历史剧实则是现代意识的产物。
民初推行之新式话剧及改良戏剧,其内容则尤以时事剧、家庭剧等为最,以历史为题材的新剧寥若晨星,为时人所惋惜。鉴古知今乃中国处事之精髓,1914年有论者认为,编新剧宜扩充范围,见古事演于舞台“则爱国之忱油然而生”,中国历史之长久,可取材者甚多,据实所演寄托金玉之言“为能得信用于人”,一则历史剧考据事实,剧中人物皆有来历,观众已稍具“信仰之心”,既信服于剧情“其感人之力,当有倍于时装演剧者矣”,二则海外新剧皆有历史剧之表演,如若中国独缺“无以表示新剧之价值,亦无以发挥新剧之作用”[5](P11)历史剧之匮乏不单为一家之言,实为民初剧界之共识。
二、民国时期历史剧的发展
自《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后,戏剧地位越发提高,剧本的意义重心随之而变,尝试历史剧创作成为时人反思与批评社会问题另辟蹊径的方式,民国初期稍显端倪的历史剧以现代意识审视传统历史,既表露了中国传统思想“以史为鉴”,又传达了变革时代的观念。
五四运动后的戏剧运动中产生了一批“历史剧”,呈现了时下剧作家的不同尝试。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等历史剧均以倡导女性解放为主题。又如吴我尊感慨道“余研究新派剧八年,所演者非泰西之传记小说,即中国之时事剧,终以未能一演历史上事迹,以表彰中国古英雄侠义为憾”,论者既认识到新剧缺乏历史剧,也产生尝试创作的兴趣,遂以项羽之死为题材编历史剧《乌江》作“以见王之百折不回,允可为我国民武士道之的也”[6](P1)。顾一樵则以荆轲、项羽、苏武等为主角,编写历史剧虽自言“不敢自云负提倡民族精神之巨任也”[7](自序),但其真实用意实在于抛砖引玉,希冀借古人之高情远致与国人共勉。二者以宣扬古人精神为要旨,新编历史剧的尝试,既体现了剧作者对往事的追思,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怀。还有袁昌英改编《孔雀东南飞》对时代氛围进行依附“借旧题创新作”[8](P11),是剧作者试图反映新时期所进行的某种努力。
纵览民国历史剧的发展,五四至全面抗战前夕处于不愠不火的态势,而全面抗战前后则愈发兴盛,原因可归结于客观环境与主观态度的改变。1936年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便决定支持文化事业发展以唤醒国民意识,促进民族精神,追溯中国历史也是其主要手段之一,二者的积极作用恰好为历史剧打开了新的天地。紧接着同年4月国民党在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了《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其《纲领》第三条明确以“阐扬历代民族英雄及忠勇侠义之人物,以发扬吾民族之优点,振作民族之自信心”[9](P29),第五条则要求“电影戏剧与音乐美术之取材,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保存民族美德、提倡积极人生为主要目标”[9](P29)。不难看出,中国的内外形势每况愈下,国民政府希冀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人心,历史与戏剧是其文化事业建设的两大重心,故包含二者的历史剧自然有迈向康庄大道的趋势。但是国民政府支持的文化事业是以拥护其统治为前提,故从侧面看,政策制约之下剧作家大力发展历史剧也蕴含着情非得已的无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审查制度愈发严格,以现实为题材,批评时下情形的戏剧内容被蓄意遏制,故剧作者不得不另寻他法,借助历史题材借古讽今成为政治策略下的一种氛围。1940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中央秘书处请求“转陈提会通过施行”《戏剧剧本审查登记办法》与《战时戏剧审查标准》等文件[10](P2),其部分企图在于以合法化的方式打压戏剧界的进步人士,避免戏剧这一大众娱乐活动对国民政府政权及领导者产生负面作用。刘念渠感喟到“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若于事实应该而且可能做为剧本的题材,却迫着剧作家不得不隐藏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后面了”[11](P56)对现实政策的被迫让步是剧作家躲入“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蓝海认为抗战中的历史剧内容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走这种曲线的缘故,是为了想躲过检查,得以出版及演出”[12](P128)。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面对日趋严峻的局势主张振兴中华文化,追忆光荣历史,借助戏剧等大众娱乐方式宣传民族精神,从正面为历史剧的发展构建了环境,但是国民政府的文化复兴策略在激发国民爱国情怀之上别有用心,目的在于实施“统制运动”,以压制不利自身的文化宣传,剧作家以现实事件为题材的作品难以上演,从背面为历史剧的发展塑造了情势。正如王笛所言“在国家权力及其文化霸权之下?大众娱乐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13](P77),因此,历史剧成为了剧作家最合时宜的创作模式。
全面抗战前后历史剧这一大众娱乐活动与民族复兴价值取向逐渐相一致,故当历史剧精神符合时代潮流,赶上各界对民族复兴的关注强烈,其繁荣也在情理之中。卢燕娟注意到“抗战历史剧首先体现出与启蒙思想不同的文化选择”[14](P68-77)视野由西方现代观念转向中国历史寻求构建民族精神所需的资源。1939年陈伯达在延安《文艺战线》上发表评论“凡是中国民族战斗史绩及其精神,中国人的一切固有美德,中国历史上大人物对于民族和社会的一切立德,立言,立功,为中国人所服膺不忘的,都应以之充实文艺的内容,文艺创作”[15](P24),认为应当注重历史题材的运用,反衬时下以鼓舞人心。1944年赵循伯在《民族正气》的自序中写道张巡许远守睢阳的形势“单独借取来看,和我们今日神圣的抗战,是在寻不出时代的差别”[16](自序),光明的民族意识与黑暗的自私自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在时下环境引发观众共情。
面对“他者”的逼近,民众的爱国心理不断增强,历史剧则通过中国历史的爱国剧情构建民众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认同,两者完成了剧作家与民众的合拍是历史剧兴盛的根本原因。赵景深在《文坛忆旧》回想数年前对历史剧《正气歌》的听闻,1933年后此剧轰动上海“连演了几乎一百次”,原因在于上海沦陷后,观众只能借历史剧“可以发泄胸中的一腔鸟气”[17](P73),自然对其爱不释手。1937年化名香司的论文发表《国势凌夷应多排演攘外历史剧》一文,认为国难“至今已臻斯极”,每有一爱国剧本上演民众“辄闻风群集”,故国人对此危机时刻“都已有相当之认识矣”,倡导剧界“宜多排演涵有攘外事迹之历史剧”[18]。如果说香司的文章略显空泛,那么1946年田进统计的八年抗战戏剧创作,其以1941年为分期“而历史剧在全部剧作中在前期仅占百分之十四,在后期中廿六种则占百分之三十一强,如果将半历史性的剧作合并在一起,则占百分之三十三强,较前期的百分比增加了一倍半”[19](P27),试想,如果历史剧毫无观众市场可言,又怎么可能占据抗战戏剧数量的三成以上呢?因而这则资料可以佐证历史剧对观众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此外,沦陷区内日军采用“国策电影”与“大陆电影政策”企图利用文化曲解,麻痹中国民众的历史认知,清朝龚自珍就有“灭人之国,先必去其史”的认识[20](P67),时下文学界与艺术界人士也明白此道理,不得不对此行为作出回应,历史剧便是相机行事的方式之一。1936年《铁报》认为日本的电影政策是“麻醉奴化,在友邦一贯的政策之下全部发动了,不仅是文学界,现在已经应用到电影这一艺术上来[21]呼唤国人以文化武器回击。1937年上海《电声》记录了伪满洲国成立满州电影会社,摄制影片强迫民众观看,论者对此事件发出了“我们甘愿它们永远存在吗”[22](P438)的质问。故时下反击日本的文化侵略刻不容缓,历史剧的特性自然能够行之有效的吸引国人关注,从而加大创作力度。
由此可见,危难之际国民意识亟待唤醒,故抗战时期限定了历史剧必须是以鼓吹民族精神为主流,这个方向迎合了各方要求,价值取向与实际需求相辅相成为历史剧的兴盛铺平了道路。简言之,历史剧的高产是时代作为推手的表现,也印证了历史剧作主题与观众喜好相一致,其发展才可渐入佳境。
三、民国时期历史剧与爱国主义的结合
民国时期历史剧承载的内涵由其他方面转向“爱国”存在着一个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正如郑大华认识的“中华民族形成虽然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23](P80-91+160),事实也的确如此。1912年12月7日《自由报》记者报道了河南丰乐园观剧时之见闻,观众对《下河南》“叫好之声不绝于耳”、《莲花湖》“四座喝采之声如雷”,然当戏剧终结,“有演说团黄伯廉君邀同凌子黄、胡抱一两君”分别登台演说越南、朝鲜亡国史与俄库协约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欲“以唤醒沉梦,激发热诚”,记者认为二人演说之精彩“闻之而不兴起者,其人必无心肝”,可现场观众的却表现为“不但不为感动,且任意喧哗,一若甚不满意於诸君之喋喋不休,厌人听闻,有阻其观剧之雅兴者”,感慨道“何也?我河南一般社会之心理,其对于亡国破家之悲痛,不如观剧之欢切也”[24]可见,民国肇始一般观众所闻所感多凭一时喜好,还无清醒的危机意识,国家认同与民族精神尚待培植,简言之,传统娱乐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众市场,而民族意识却无,二者可谓天差地别。换个角度看,历史剧充实了民众的生活,但其意象未必连接至社会、民族与国家,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刺激大众的兴趣。
随着民众认知的改变,娱乐开始承载社会责任,与国家意识产生交际,至全面抗战则成为潮流。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就认为“发展的伟大斗争是持续不断的,结果常常不是来自单个信息或单个媒介的影响,而是产生于相关信息或互补渠道的一系列影响”[25](P156)大众传播媒介对国家认同的构建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民国时期的国情之下其影响却未必能够符合预期,需要辅助以戏剧等大众娱乐方式来达成目的。
1937年11月30日《河南民报》记录的山东省立剧院公演爱国历史剧《岳飞》的场景表达了观众之情绪,“自揭幕至终场,观众均为剧情所吸引,情绪随之起伏,激昂处不禁手舞足蹈,悲愤处但闻歌声和血和泪,是悲号,是怒吼,多为之一洒同情之绪”[26],不难看出,在这一刻,观众如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言“共同拥有的文化意义的循环促生了一种‘共识’(Gemeinsinn)”[27](P146),个人倾向逐渐趋向大众的共同意识,如此娱乐承载的不再是一时的欢快,而是长久的意识刻画,观众的情绪波动不再是单纯靠剧情所营造,而是观众本身已能领略剧中之含义。
由此可见,凭借历史剧承载民族精神仅是其发展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并非全部,而剧作家对历史剧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妨可以这样解读,历史剧注定要符合大众预期、相依作家认知与背靠时代任务。
四、结语
可以想象的是,民国时期历史剧这一大众娱乐活动凸显的内涵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欢愉风气-现代意识-民族精神,那么便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大众娱乐的转折在何处?民国时期社会呈现着多元性与复杂性,回顾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接受的价值观念也可能具有多变性,普通大众不一定以单一意识为其准则,王笛以成都戏剧为例,认为“节目和人们的口味根据社会和政治发展而改变?它们的主题和倾向,无论是浪漫史、“淫荡”、“暴力”,还是改良、革命、爱国,都反映了外部社会转型和政治演化”[13](P82),可见,民众虽是决定戏剧市场的关键所在,然而剧作者之间的互动,政府制度的牵掣等也皆是影响戏剧走向的因素。
基于民国时期历史剧的特性,很难直观的将各种因素扮演的角色清晰的划分出来,因为它是时代、社会、剧作家、文本与观众所共同塑造,并非任何一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车人杰根据抗战时期成都戏曲行业的境遇分析认为,“‘救国’与‘娱乐’,应实现某种形式的“平衡””[28](P160-170),既保持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也不影响给观众带来艺术享受。可见,民国时期历史剧的创作并非一开始便欲营造民族复兴氛围,而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共同作用限定了其发展方向,大众娱乐与民族复兴的交叉展示了中国近代鲜明的历史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