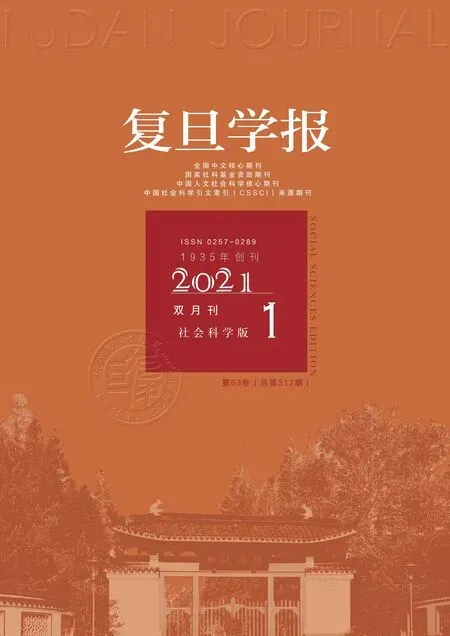“清词中兴”意涵新论
孙克强
(河南大学 文学院,开封 475001)
“清词中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判断,其意义在于确立了清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及价值肯定。“中兴”亦常用“复兴”“复振”“振兴”等词语。所谓“中兴”本是一个历史范畴,指历史阶段繁盛强大的再现,含有由高峰经由低谷走向另一高峰的意思。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描述中经常有“中兴”之说,如传说中的夏朝“少康中兴”、周朝的“宣王中兴”、汉朝的“光武中兴”、宋朝的“建炎中兴”等等。大凡经过衰落阶段之后的复兴,往往可以称为“中兴”。词学史上也是如此,“清词中兴”的意涵是:与唐宋词的高峰遥相呼应,跨越史称“中衰”的明词低谷而攀上清词的高峰。“清词中兴”意谓:清词形成了与唐宋词的双峰并峙。
“清词中兴”作为词史上的重要命题,从清末至今一直是词学研究界的主流认识。词学研究者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叶嘉莹、严迪昌、施议对、张宏生等先生都曾有专门的研究。然而,如果我们对“清词中兴”的命题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关于这一命题还存在一些模糊甚至相互矛盾对立的述论,需要进一步加以辨析。择其要者有以下诸端:第一,如何认识“清词中兴”的外延与内涵。这里所谓外延是指“中兴”的时间界定,具体来说,即“中兴”是否涵盖整个清代;所谓内涵即论者所指出的“中兴”的特征有哪些。第二,“清词中兴”是否清代以后的普遍认识,如有持否定意见者,他们的立论基础是什么,其学术背景与立场观念有何特点。第三,清末民初词学史上的“清词中兴”论与当代学者所讨论的“清词中兴”有何差异,我们应当如何认识。
一、 有关“清词中兴”论的阐述
考察有关“清词中兴”之说,讨论最热烈之时是在清末民初时期。但是“中兴”之说并非仅仅是清末民初词学家的总结,事实上在清代词学史的各个发展时期都有“中兴”的提法。如果将词学史上各种说法加以分析,则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主要着眼于“中兴”的历史时期标志;二是主要着眼于“中兴”的意涵特征。前者将有清一朝作为“中兴”的主体,将清朝立国视为“中兴”的起点;后者主要着眼于清词之“变”,即清词区别于此前词史尤其是明词而所具有的新特质。以新特质为标准,后者将“中兴”的起点标立在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崛起的康熙初年,即清朝开国三十余年之后。两种观点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时间起点的认识上,更是涉及对“清词中兴”特质的认识。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种观点,将清朝立国作为“中兴”起始时间,将有清一朝作为“中兴”的主体。持此种认识的人非常多,考察清代词学史,几乎每个时期都有相似的表述。试举例如下:
明末清初的梁清标云:“南唐北宋以还几数百年,振兴之功,于今为烈。”(1)丁澎:《菊庄词序》引,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顺康年间人张星耀云:“昭代词人之盛,不特凌铄元明,直可并肩唐宋。”(2)张星耀:《词论》,《东白堂词选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康熙十七年刊本。
康熙初期宋荦云:“今天子右文兴治,挥弦解愠,睿藻炳然。公卿大夫精心好古,诗律之高,远迈前代。而以其余业溢为填词,咏歌酬赠,累有篇什,骎骎乎方驾两宋。呜呼,其盛矣!”(3)宋荦:《瑶华集序》,蒋景祁:《瑶华集》卷首,清康熙二十六年天藜阁刻本。
乾隆时期的万之蘅云:“减字偷声,肇自唐贤;移宫换羽,传诸宋代。元明渐降,国朝聿兴。”(4)万之蘅:《小眠斋词序》,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4页。
光绪年间的陈廷焯是阐述“中兴”说最系统的词学家。他亦将有清一代作为“中兴”的主体:“明代绝少作者,直至国朝词,为之中兴。”(5)陈廷焯:《云韶集》卷一二,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2页。陈廷焯对清词“中兴”有全面的表述:“词创于六朝,成于三唐,广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国朝之诗可称中兴,词则轶三唐、两宋等而上之。”“论词以两宋为宗,而断推国朝为极盛也。”(6)陈廷焯:《云韶集》卷一四,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31、332页。陈廷焯称两宋词坛为“盛”,清词为“复盛”“极盛”,即中兴之意。他将清词史分为三个阶段:“再盛”“又盛”“复盛”,举出从清初至清末各个阶段的知名词人作为“中兴”的体现者,这些词人不分流派,不分风格。可以看出,陈廷焯是将“国朝”作为“中兴”的整体来认识的。
民国学者继续对清朝词学整体加以观照,强化了“清词中兴”的概念。龙榆生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7)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陈子龙小传》,《龙榆生全集》第八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将明末清初的陈子龙作为“中兴”之始,十分明确地将清代“三百年”的整体视为“中兴”时代。陈匪石云:“有清一代词学,驾有明之上,且骎骎而入于宋。”(8)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宋词举》(外三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陈乃乾云:“清代三百年间问学之业绝盛,经史辞章,远迈前代,词亦勃然中兴。”(9)陈乃乾:《清名家词序例》,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徐珂云:“词之学,剥于明,至清而复之,直接南北两宋,可谓盛矣。”(10)徐珂:《清代词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第1页。以上诸家皆将有清一朝为“中兴”的主体,其主要特点是着眼于对朝代的关注,以“中兴”的清代对应“中衰”的明代以及“首兴”的宋代。这种认识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当代词学对“清词中兴”的认识基本上是沿袭这种观念。
第二种观点,以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崛起为“中兴”的起点。与第一种观点不同之处在于论者将清词的“中兴”起始点归誉为阳羡词派的陈维崧和浙西词派的朱彝尊。从时间上标示,乃清朝立国之后三十余年的康熙前期。持这种看法的在词学史上亦不乏其人。康熙年间人高佑釲云:
词始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沿于元,而榛芜于明。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文章气运,有剥必复。吾友朱子锡鬯出而振兴斯道。俞子右吉、周子青士、彭子羡门、沈子山子、融欲、抟九、李子武曾、分虎共阐宗风。陈子其年起阳羡,与吾里旗鼓相当,海内始知词之为道,非浅学率意所能操管者也。(11)高佑釲:《湖海楼词序》,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高佑釲为浙江嘉兴人,与朱彝尊同里。这里提到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人与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人“振兴斯道”,改变了明朝以来的词坛风气。这种认识对后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乾隆年间人朱依真说:“燕语新词旧所推,中兴力挽古风颓。”原注:“词至前明音响殆绝,竹垞始复古焉。”(12)朱依真:《论词绝句二十二首》之十五,《九芝草堂诗存》卷一。是以朱彝尊(竹垞)的兴起为“中兴”之始。
道光年间人孙麟趾云:“词学始于隋唐,盛于宋,废于明,至我朝朱竹垞太史,挽回而振兴之。”(13)孙麟趾:《绝妙近词凡例》,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144页。
同光年间的张德瀛说:“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尽袪有明积弊,此一变也。”(14)张德赢:《词征》卷六,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84页。
以上各家的提法不无小异,或将陈维崧、朱彝尊并提,或单标朱彝尊及浙派,然而对“清词中兴”的起始点的认识却是相同的。从词史考察,陈维崧、朱彝尊崛起于词坛以及两人所经历的词风转变是清初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两人早期的词风皆婉丽绮艳,尚有明代以来词风的习染;中年之后在时代的激荡之下,又经历了人生的磨难,词风产生重大的变化,陈维崧的豪放“稼轩”风、朱彝尊的清雅“姜张”韵,共同开辟一个新的时代。陈维崧转变词风、声震词坛在康熙八年之后,朱彝尊及浙西词人树帜立派于康熙十七年。(15)参阅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周绚隆:《陈维崧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陈、朱以及阳羡词派、浙西词派的崛起最为词坛所瞩目。
以陈、朱为起始点说与前述“有清一朝说”分歧的焦点,在于对清朝立国至阳羡、浙西立派之间三十余年词坛风气的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认识和评价。关于清初三四十年词坛走向,词学史上一直有批评之声。如乾隆年间人王昶说:“国初词人辈出,其始犹沿明之旧。”(16)王昶:《姚茝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乾嘉时人凌廷堪云:“我朝斯道复兴……然风气初开,音律不无小乖,词意微带豪艳,不脱《草堂》、前明习染。”(17)张其锦:《梅边吹笛谱目录跋》引,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30页。清末民初的蒋兆兰云:“有明一代,词曲混淆,等乎诗亡。清初诸公,犹不免守《花间》《草堂》之陋。小令竞趋侧艳,慢词多效苏、辛。”(18)蒋兆兰:《词说》,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37页。以上王、凌、蒋三人的说法皆将清初词坛的一段时期视为受明代词风影响的时期,亦即明词余韵时期。他们认为应将这个时期与其后浙派兴起所开创的新时代区分开来,将清初三十余年的特定时期标示为一个独特的时期:“犹沿明之旧”“不脱前明习染”的时期。
考察这一时期,有三人前后领袖词坛:陈子龙、龚鼎孳、王士禛。陈子龙有扭转明词颓风的努力,亦曾产生重大影响,如前引龙榆生对陈子龙“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的评价。但他学南唐北宋,多作小令,词风“风流婉丽”(19)《历代词话》引《兰皋集》:“陈大樽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气,与节义相符。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8页。,很难与明词相区别。龚鼎孳对陈维崧、朱彝尊影响甚大,长调开一代风气,但仍未脱明代以来“芊绵温丽”的旧貌。(20)参阅孙克强、裴喆:《龚鼎孳全集·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至于王士禛的词风,正如唐允甲所称:“作为《花间》隽语,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21)唐允甲:《衍波词序》,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5页。。以上三人有其共性:词作艺术成就颇高,词坛影响巨大,但在体式选择、题材开拓、主题深化等方面缺少新变,基本上还是沿袭明人旧貌。
民国初期词学家叶恭绰更是明确地将浙派兴起之前的清初时期排除在“中兴”之外,他对词史发展历程及清初词风变化有明晰的论述:
清词之超越明代而上接宋元,这是可断言的。词发源于五代,到两宋总算登峰造极了。……及至明代,连词的体质多未辨清,他们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嗣后,浙派首领朱彝尊出,觉得词学日见颓靡,便想设法挽救,标出宗旨,汰去不少恶习,渐将词的品格提高,于是词学渐渐走入正规。(22)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论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5、336页。
叶恭绰所说的“清初”,特指浙派产生之前的三十余年。叶氏认为“中兴”之始是在浙西词派兴起之时,在此之前的清初词风是明人的余绪,仍然存在浮丽、纤巧、粗犷、叫嚣的弊端,不在中兴范围之内。
综以上各家之说,对清初三十余年词坛风气的基本评价是:清初虽然已有复苏气象,但仍然深受明代颓靡之风的影响,未能呈现全新的“中兴”局面。论者对这一时期词坛存在的弊病给予揭示:不脱明词的习染,仍受《草堂诗余》的影响,格调纤靡,或病于粗犷,或病于绮艳。尚不能称为“中兴”。(23)亦应补充说明的是,对待清初这一特定时期,亦有学者予以充分肯定,如严迪昌教授云:“清顺治十年(1653)前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诏试这之间约30年左右,是清初词风胚变,词学振兴的极其重要阶段。按其百派回流、名家辈出的繁荣景观而言,较之后来的经常出现定于一尊的词坛气象,无疑要更充满生气活力,更具有一种不断运动着的勃勃之势。这是一个清词真正堪称‘中兴’的历史时期。”(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在确立了“中兴”起始点之后,民国词学家进一步对“清词中兴”说加以深化,由源及流,将常州词派纳入视野。论者将在清代词坛上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代表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作为“清词中兴”的主体。龙榆生说:“清初词人,未脱晚明旧习,自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24)龙榆生:《选词标准论》,《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夏孙桐云:“清初鸿硕蔚兴,斯文间气,词亦起明代之衰。竹垞、樊榭,以通才为词学专家,上承两宋之遗绪,而词乃有轨辙可循。茗柯、止庵,发表意内言外经旨,实有关于温柔敦厚之教,而词体益尊。”(25)夏孙桐:《广箧中词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陈匪石云:“有清一代词学,驾有明之上,且骎骎而入于宋。……清代之词派,浙西、常州而已。浙西唱自竹垞,实衍玉田之绪;常州起于茗柯,实宗碧山之作。迭相流衍,垂三百年。世之学者,非朱即张。”(26)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宋词举》(外三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俞感音又进了一步,将常州词派的继承者晚清四大家也列入“中兴”之体,还特别强调“晚清四大家”对于“中兴”的意义:“清代号为词学中兴,……直至清季,王半塘(鹏运)、朱彊村(孝臧)两先生,致力宋词之校订,衍常州之余绪,从而恢张之,涉览既多,善识声理,故其所作,类能声情谐会,悱恻动人。”(27)俞感音:《填词与选调》,《同声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甚至认为四大家取得了越常州词派而上的成就。
民国时期的词学家在对清代词史进行系统的总结之后,对“清词中兴”的整体面貌和发展阶段加以描述和概括。蒋兆兰说:
有明一代,词曲混淆,等乎诗亡。清初诸公,犹不免守《花间》《草堂》之陋。小令竞趋侧艳,慢词多效苏、辛。竹垞大雅闳达,辞而辟之,词体为之一正。嘉庆初,茗柯、宛邻,溯流穷源,跻之风雅,独辟门径,而词学以尊。周止庵穷正变,分家数,为学人导先路,而词学始有统系,有归宿。吴门七子,守词律、订词韵,于是偭规错矩者,不敢自肆于法度之外。故以清代词学而论,诚有如外人所谓逐渐改良者。以故清季词人,如前所论列诸家,色色皆精,蔚然称盛,殆亦时会使然。(28)蒋兆兰:《词说》,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37页。
叶恭绰说:
余尝论清代学术有数事超轶明代,而词居其一。盖词学滥觞于唐,滋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朱、陈导其源流,沈、厉振其波,二张、周、谭尊其体,王、文、郑、朱续其余。二百八十年中,高才辈出,异曲同工,并轨扬芬,标新领异。(29)叶恭绰:《清名家词序》,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以上两段文字是清词中兴的完整表述,所表达的观点也大致相同。他们将清词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初的未兴时期,批评这一时期尚沿袭明词之陋;第二阶段是“中兴”之始,其标志是陈维崧阳羡词派、朱彝尊浙西词派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明代以来的词坛面貌。之后阳羡隐而浙派显,浙西词派主盟词坛,厉鹗及吴中词派传承光大,成就引人注目;第三阶段是“中兴”的深化时期,其标志是以张惠言、周济为领袖的常州词派竖旗立帜,尊体的主旨与浙派异曲而同工。晚清四大家作为常州派的衣钵传人,成就了“中兴”的辉煌结尾。
二、 “清词中兴”意涵和特征
考察清代以来的“中兴”之论,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持有将有清一朝作为“中兴”主体的论者,表述关注点主要在朝代的对比上,将清朝与明朝对比,突出清朝词学之时代面貌的“兴”和“盛”,却基本上没有提及“中兴”的内涵和特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研究“清词中兴”的当代学者,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将有清一朝作为“中兴”主体的观点。新时期的学者论析清词中兴的热情更高,专题研究论文不断涌现,在关于“中兴”的内涵和特征的探讨方面也进了一步,综其大要可概括为四点:词人众多,作品浩繁,流派纷呈,风格多样。(30)今人也有类似的认识,如严迪昌《清词史》云:“一代清词以其流派纷呈、风格竞出的空前盛况,终于为这抒情文体的发展史谱就了辉煌丰硕的殿末之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页)参阅杜庆英:《清词“中兴”问题研究综述》,《陕西社会科学论丛》,2016年第6期。可以看出,这些关于清词兴盛的认识,多着眼于清词“盛”的外表,即“量变”的表现;却很少触及清词的“质变”,尚未论及清词“兴”的特质。
其二,反观清代持陈维崧、朱彝尊为“中兴”起始的论者,已将关注点聚焦于明清词风之“变”的特质,注意到“中兴”的意涵特征。最早论及此题的是与陈维崧、朱彝尊同时代的毛奇龄,其云:“迦陵陈君偏欲取南渡以后,元明以前,与竹垞朱君作《乐府补题》诸唱和,而词体遂变。”(31)毛奇龄:《鸡园词序》,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12页。他指出经过陈、朱二人的努力,明代以来的词风产生了变化;同时指出取法南宋,是改变词坛风尚的原因。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文献,毛氏特别标举“词体之变”是很有眼光的。明代及清初三十余年,词风“颓靡”是与当时崇尚北宋、偏好婉丽的观念相联系的,陈、朱提倡取法南宋,在当时颇有“反潮流”精神,词体之变以及“中兴”之始皆与之相关。
乾隆年间的储国钧说:“夫自《花间》、《草堂》之集盛行,而词之弊已极,明三百年直谓之无词可也。我朝诸前辈起而振兴之,真面目始出。”(32)储国钧:《小眠斋词序》,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4页。这里提到“振兴”的意涵是“真面目”。相比以朝代、时代论“中兴”的说法,“真面目”之说无疑又迈进了一大步,更为深刻也更有意义。民国初期的叶恭绰则将“中兴”意涵的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晰:
及至明代,连词的体质多未辨清,他们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嗣后,浙派首领朱彝尊出,觉得词学日见颓靡,便想设法挽救,标出宗旨,汰去不少恶习,渐将词的品格提高,于是词学渐渐走入正规。(33)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论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6页。
叶恭绰指出浙派朱彝尊的意义有三点:其一,挽救明词的颓靡,是理性指导下的行为;其二,汰去恶习,提高品格,实现尊体;其三,走入正规,实现中兴。此论已经深入到“中兴”的意涵和特征了。
从词学史加以考察,浙西词派改变明词颓风的努力和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词风方面,提倡清空醇雅以取代婉丽绮靡;第二,取法时代方面,突出南宋而淡化北宋;第三,词人典范方面,标举南宋姜夔、张炎取代唐五代北宋诸名家;第四,学习范本方面,新编《词综》以取代《草堂诗余》。以上四个方面形成系统性并构成一个核心,就是力图开创与明词面貌不同的新气象。
关于清词“中兴”或“复振”的表现,民国以来词学家提出了一些见解,如张尔田提出清词“厥盛有四”:守律、审音、尊体、校勘。(34)张尔田:《彊村遗书序》,《彊村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洪佳《清代词学》中有“清代词学之特征”一节,列出五项:“(甲)擅音律。(乙)尊词体。(丙)精藻鉴。(丁)明校勘。(戊)尚模仿。”(35)王洪佳:《清代词学》,《女师学院期刊》1936年第4卷,第1、2期。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第二十三章中专论“清词之复盛”,指出“复盛”的表现为:“文人精力所寄,用心益密,托体日尊;向所卑为‘小道’之词,至是俨然上附《风》《骚》之列;而浙、常二派,又各开法门,递主词坛,风靡一世。”(36)龙榆生:《中国韵文史》,《龙榆生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饶宗颐教授从宋词与清词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清词的特点:
宋词与清词,其间异同可归纳如下:宋词重意兴,而复尚思理;此一境界清词无之。宋词多真朴,出于自然;清词多刻露,见其巧思。宋人为词,大半出于余兴娱戏;清人则有以词为专业者。宋词作者,多显宦巨公,藉以达志;清世则名士墨客以至闺秀无不为词,无病呻吟之作遂多。宋词或假以言政治、论国是;清词多体物咏怀,顾不若宋词之有思想内容。宋词中时有微言;清人在词中写经济怀抱者,直如凤毛麟角。至清代作品之多,前古未有;使声家小道,蔚成大国,亦非宋人所可企及,此所以清词在文学史有不祧之地位。(37)饶宗颐:《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第315页。
此文是第一篇比较宋词与清词的文章,视野开阔,颇具启发意义;然而亦有可议之处,如此文将宋词统而论之,不分南北宋。其实南北宋词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文中提到的将宋词与清词进行比较的结论,往往置于北宋则是,置于南宋则非,反之亦然。从词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清词与南宋词有更深刻的联系,这是进行宋词、清词比较不可不措意之处。
“清词中兴”的核心问题是所“兴”的内涵和价值,即与唐宋词相比较,并非一定要达到唐宋词的所有指标高度,比如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名作的经典度、流派的影响力等等,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说:“清词的‘中兴’,按其实质乃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是词重又获得生气活力的一次新繁荣。‘中兴’不是消极的程序的恢复,不是沿原有轨迹或管道的回归。”(38)严迪昌:《清词史·绪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页。应重点探讨清词具有哪些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的价值是否可以与唐宋词媲美甚或有所超越,是否如朱祖谋所说:“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及。”(39)叶恭绰:《全清词钞序》引,叶恭绰:《全清词钞》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这既是判定清词是否有“中兴”成就业绩的标准,也是确定“中兴”起点和终点的参考答案。结合前贤和时彦的论析,笔者就清词的特征亦即“中兴”的意涵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开拓新境界。清词开拓了新的境界,创立了清人特有的品格气质。晚清及民国的词学家皆曾述及清词的新境界。晚清人文廷式说:“词的境界,到清朝方始开拓。”(40)叶恭绰:《全清词钞序》引,叶恭绰:《全清词钞》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民国初的梁启勋亦云:“有明一代,词学最消沉,至清初而复兴,顾贞观、纳兰容若、陈其年、厉鹗等颇能自辟新意境。”(41)梁启勋:《中国韵文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76、177页。清词所开辟的新境界不仅明词所无,甚至唐宋也未必能有。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也。”(4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历史条件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一代之文学”的独特地位。清人陆蓥说:“人有恒言唐诗、宋词、元曲三者,就其极盛言之。风气所开,遂成绝诣。”(43)陆蓥:《问花楼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44页。宋词也像唐诗和元曲一样,以其时代的特色和优势而达到辉煌的顶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以后的词没有能够超越,清词虽称“中兴”也难于和宋词比肩。然而清词仍有自己的特色,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清人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反映方式,开拓了清人的新词境,对词体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词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社会变化及士人心态,尤其是生动真切地表现了清人的独特感受。叶嘉莹教授指出,自清初到清末,一直隐伏而贯穿于这些词人之间的一种忧患意识,令词的意境与地位脱离了早期的艳曲之局限,而得到了真正的提高,也使得有清一代的词与词学成就了众所周知的所谓“中兴”之盛。(44)参阅叶嘉莹:《清词名家论集·序言》,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6年。清人对时代氛围的感受也印证了这一点,朱彝尊说:“(词)有诗所难言者”,“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45)朱彝尊:《红盐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张惠言说:“(词)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46)张惠言:《词选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7页。朱、张这两位先后主盟词坛的词家,虽然词学主张不同,时代相隔百余年,但都认为词可以表达“难言”“不能自言”的内容。这种内容其实就是他们切身感受到,并在其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朱彝尊的词“从来托旨遥深,非假闺阁裙裾不足以写我情怀”(47)李符:《江湖载酒集题词》,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张惠言的词“运心思于幽邃窈窕之路,情寄骚雅,词兼比兴,遂又别开境界”(48)杨希闵:《词轨·总论》,孙克强辑:《词轨辑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3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4页。,皆表现出了新的境界。正如龙榆生所云:“明清易代之际,江山文藻,不无故国之思,虽音节间有未谐,而意境特胜。”(49)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龙榆生全集》第八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3页。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网之密使词人将感情深埋心底,沉溺于山光水色,这时期的词作却染上了一层凄苦迷离的色彩。嘉庆、道光以后,内忧外患,使词风激切而幽愤。总之,有清一代的词人们用独特的方式表现出特定时代的独特感受,此乃谓清人的新境界。
第二,尊体观念。尊体是清词贯穿始终的理念主张和创作实践。叶恭绰曾对“清词中兴”的内涵有过系统的阐述:“清词能上接两宋,实因具有下列两种优点:一,托体尊;二,审律严。”(50)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论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5、335页。其实审律严也是尊体的一种表现。尊体又可分为意格和形式两个方面。
意格上的尊体主要是指创作态度的严肃和端正,叶恭绰曾就此将宋人与清人进行比较:
因为以前的人,往往视词为一种游戏作品,而不认为高尚的,所以宋人作品虽是很多,但是除了诸大家的词饶有寄托外,都不过写些流连光景的话,固然体格不见高尚,而且多伤于率野,无深厚之情绪,及高远的理致,元人也多是如此,而且多流入纤碎一路;及至明代,连词的体质多未辨清,他们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嗣后,浙派首领朱彝尊出,觉得词学日见颓靡,便想设法挽救,标出宗旨,汰去不少恶习,渐将词的品格提高,于是词学渐渐走入正规。(51)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论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5、335页。
清代常州词派词学家周济曾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5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9页。所谓“无谓之词”即指以游戏的态度创作一些流连光景的作品,这种现象在两宋普遍存在,不少名家也难免此态。相比较而言,清人的创作态度则要严肃得多。贯穿有清一代,尊体一直是词坛的主旋律。陈子龙从“用意”“铸调”“设色”“命篇”四个方面为词体创作提出要求;朱彝尊提出“以雅为目”“必出于雅正”;张惠言要求填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53)张惠言:《词选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7页。皆表现出清人填词创作的使命感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清代影响最大的浙、常两派更是典型的代表,正如夏白蕉所云:“清空婉约,深宏柔厚。浙西、常州两派,前后倡导,各标宗尚,而探其源流正变,以氐于大成。”(54)夏白蕉:《清名家词·题辞》,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1617页。浙西派标举清空醇雅,常州词派提倡比兴寄托,虽然审美风格各异,但在尊体的态度上却高度相似,在尊体的道路上前行后继。
重视审律是清代词学的重要特点。讲求词体格律亦为尊体的重要内容。张尔田论清代词学有“四盛”,其中万树订《词律》为一盛,戈载撰《词林正韵》为二盛,朱祖谋校词精审为四盛。(55)张尔田:《彊村遗书序》,《彊村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清代词学的“四盛”皆与音律相关。叶恭绰指出,南宋之后歌词的乐谱失传,元、明以及清初词人填词多不合词律。直到清代康熙之后,万树的《词律》和戈载《词林正韵》出现,词律方为词家所重视。“始兢兢于守律。所以清词词家很少有不合律的,不但讲究平仄,即四声阴阳亦不容混,这也是清词的独优之点。”(56)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论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7、338页。清词与明词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词律的重视。明词被人诟病之处就有词律的内容。明末清初的陈子龙批评明人“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57)陈子龙:《幽兰草词序》,《安雅堂稿》卷三。清代中期的词学家杜文澜云:明人“间或为词,辄率意自度曲,音律因之益棼。”(58)杜文澜:《憩园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52页。皆指出明人在词律方面有不守规矩、率意随便的弊病。清人要开创词坛新局面,词律的要求是重要的条件。朱彝尊提出“倚声中律吕”“审音尤精”(59)朱彝尊:《群雅集序》,《曝书亭集》卷四十。,浙派的后继者将重音律作为传统家法,浙派中期领袖厉鹗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皆极为重视词律,后人称:“至厉太鸿出,而琢句炼字,含宫咀商,净洗铅华,力除俳鄙,清空绝俗,直欲上摩高、史之垒矣。又必以律调为先,词藻次之。”(60)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常州词派的周济对词的音律亦十分注重。周济曾作《词调选集序》(61)按:《词调选集》已佚,《序》见《常州先哲遗书补编·止庵文》。一文讨论音律问题。《词调选集》择词二百多首,“以婉、涩、高、平四品分之”(62)潘祖荫:《宋四家词选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58页。,探讨词调与感情表达的关系问题。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周济用较大篇幅阐述音律与词的艺术风格的关系,涉及韵部、阴阳、四声、双声迭韵、领句单字、换头煞尾等问题。可见周济不仅重视词律,亦精于词律。晚清四大家更是以严于词律而闻名,朱祖谋、郑文焯都是公认的词律专家。蔡嵩云曾指出:四大家“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63)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08页。四大家重词律的思想至民国时期仍薪火相传。从清初至清末,词坛上流派更迭,审美主张各异,但一直强调重视词律,从形式上规范创作,实现尊体。
第三,理性色彩。清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作与批评理论的结合。清代的重要词学流派以及有影响的大词人,往往明确地寻求和确定创作典范,在审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创作;明确地追求特定的风格气韵,这使清词的创作更具理性色彩。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与唐宋词的不同特点,甚至可以说超越唐宋词之上。
清词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就风格的取法对象而论,有崇北宋以前,有学南渡之后,还有专主晚唐五代。清代各个时期有特定的主导风格,各种流派又有独特的流派风格,流派之内各家又各具风格。如清初词坛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以各自独具特色的风格鼎足而立,康熙间人杨芳灿论析他们三人:“陈(维崧)词天才艳发,辞锋横溢,盖出入北宋欧、苏诸大家;朱(彝尊)词高秀超诣,绮密精严,则又与南宋白石诸家为近;而先生(纳兰性德)词,则真《花间》也。”(64)杨芳灿:《纳兰词序》,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陈、朱、纳兰三人具有各自独特的审美追求和风貌,他们分别从唐宋词人或词风中选取了典范和楷模,不仅心摹手追,而且提倡标榜,显示出他们的创作风格特色与词学主张理论相一致的特点。
对于清词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色彩和典范意识,词学史家大多予以肯定和称赞,如江顺诒评论浙西派的朱彝尊和厉鹗:“本朝朱、厉步武姜、张,各有真气,非明七子之貌袭。”(65)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27页。但也有批评者对清人标举典范的做法斥之为“模拟”。如何看待清词的所谓“模拟”,是对“清词中兴”认识的关键。
作品中是否有真实的情感,是判别是否堕入了模拟泥沼的主要标准。试举朱彝尊等浙派词人为例略加分析。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中有一首〔解佩令〕《自题词集》,表达了他身世之感与词学取向的关系:“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词中特意提出要师“玉田”,即学习南宋词人张炎。考察朱彝尊的人生经历,其偏取南宋张炎是因为有身世情感认同的因素,即“涕泪飘尽”“落拓江湖”之后的选择。南宋末年的舒岳祥《赠玉田序》对张炎词风有一则评论:“宋南渡勋王之裔子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饮,……笑语歌哭,骚姿雅骨,不以夷险变迁也。其楚狂与?其阮籍与?其贾生与?其苏门啸者与?”(66)舒岳祥:《赠玉田序》,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页。指出张炎身历家国之痛的情感变化。可以说正是身世经历的落魄坎坷使朱彝尊选择了南宋张炎凄清词风。其实,浙西派的词家推崇南宋词大多有与朱彝尊相似的思想感情因素,如浙西六家之一的李符自称偏好张炎的词,原因是:“余布袍落魄,放浪形骸,自谓颇类玉田子。”(67)李符:《山中白云词序》,《彊村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李符与朱彝尊一样,对南宋末年张炎实有感同身受的身世遭际寓于其中。即使浙派后期的词家推尊南宋,亦是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选择,如浙西词派后期的名家郭麐称自己的词风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少年时期喜好花间词,“中年以往,忧患鲜欢,则益讨沿词家之源流,藉以陶写阨塞,寄托清微,遂有会于南宋诸家之旨”。(68)郭麐:《灵芬馆词自序》,《灵芬馆杂著》卷二。南宋词人遭家国之难,词中表现身世之感,多寓寄托,风格沉郁,这些特点使部分浙派词人产生了共鸣。可以说浙派词人对南宋词人的认识有许多是着眼于深沉、复杂的思想情感。从上例可以看出,清人的标榜典范与所谓“模拟”是有本质区别的。单纯的模拟仅取其形似,而清人标榜典范更多是借鉴其神而又融入自身的情感,这正是清词的一大特色。当然,清代亦不乏拙劣的模拟之作,毋庸讳言。
三、 否认“清词中兴”之论
词学史上,否定“清词中兴”的观点亦有较大影响。民国时期的学界对清词在词史上地位的价值判断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以晚清四大家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旧派(或称体制内派)词学家,力倡“清词中兴”之说;而新派(或称体制外派)(69)本文沿用当代学者的的表述方式,将由晚清延续而来深受常州词派影响的词学家群体称为“旧派”,或称“体制内派”;将民国时期新兴起的更多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的词学家群体称为“新派”或“体制外派”。词学家大多是否定“清词中兴”之说的,对清词的价值是基本否定的。
最早明确否定清词价值的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其词体观和词史观与当时主盟词坛的四大家颇有不同。王国维对清词的看法主要表现在署名樊志厚作的《人间词》两序之中。写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人间词甲稿序》云:
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模拟也。(70)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75、4275、4276页。
王国维还说:“六百年来”词实“不振”。(71)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75、4275、4276页。所谓“六百年来”,是指从南宋灭亡之后到清朝中后期的六百余年,清代词史在王国维看来是属于“不振”之列的。王国维认为清代从“国初”至“嘉道以后”,或“局促”“雕琢”,或“浅薄”“模拟”,总而言之毫无成就可言。在清末词学家的话语习惯中,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和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皆属于“国初”的范围。而“嘉道以后”则指当时主盟词坛的常州词派,也就是说王国维是将浙、常两派一概加以否定的。
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人间词乙稿序》进一步阐发了清词“不振”的观点:
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72)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75、4275、4276页。
此序对纳兰性德多有肯定,但对被视为清初词坛主流的浙西词派的朱彝尊、阳羡词派的陈维崧以及“乾嘉以降”的常州词派皆一概否定,整个清代词坛皆在贬斥之列。
继王国维之后,胡适对清词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胡适将清词视为“词的鬼的历史”,也就是没有生命活力的躯壳。胡适说:清人试图实现“词的中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词的时代早过去,过去了四百年了。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73)胡适:《词选·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页。胡适明确提出了对“词的中兴”说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清词“模仿宋词”,是“词的鬼影”。“模仿”是胡适否定清词的主要理由。胡适对清末以来五十年的词坛基本予以否定,认为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吴文英)派的毒,很少有价值的。(7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他所指的是当时晚清四大家及其弟子提倡学习梦窗词所形成的热潮。胡适不仅否定清词的价值,对继承清词传统的民国初期旧派词也持批判态度。
胡云翼是民国时期撰写词学著作最多的学者,也是影响最大的词学家,他对清词的看法与胡适基本一致。在其《中国词史略》中说:
词至清代,无论小词或长词,无论婉约的词或豪放的词,无论白话的词或典雅的词,都已早有了极好的成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摆在清人的面前,清人既不能在词体里别开新生面,无路可走;同时又看着许多前人留下了很多而且很好的成绩在那里,作为模板,便自然而然的开起倒车来,堕入模拟的圈套里去了。
胡云翼说,大多数的清代词家,只是模拟晚唐五代两宋词,“总不曾跳出古人的圈套,清人的词,因此便堕落了,走上古典主义的死路去了”(75)胡云翼:《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第215页。。胡云翼亦明确否定“清词的复兴”之说,其立论基础也是认定清词是模拟,是“开倒车”,是“堕落”,“走上古典主义的死路去了”。显然,胡云翼之说受胡适的影响甚大。
在民国前期曾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史家郑振铎也持否定清词的态度。郑振铎将千年词史分为四个时期:胚胎期、形成期、创作期和模拟期。其模拟期指元初至清末,郑振铎说:“在这个时期之内的词人,只知墨守旧规,依腔填词,因无别创新调之能力,也少另辟蹊径的野心。词的活动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复为活人所歌唱了,然而他们却还在依腔填词,一点也不问这些词填起来有什么意思”,这个时期“时间最长,恹恹无生气”。(76)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7、18页。基本上否定了清词的价值。与胡适等现代派学者一样,郑氏基本的文学观也是文学进化论以及一切文体出自民间,终于文人的文体演变规律。他认为清代处于词体的衰亡阶段,清词没有生命力,没有生气,也没有了价值。
以上各家皆为民国时期著名的词学家,他们的看法不仅对他们所在的民国时期产生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着后世的词学观念。
四、 南宋词与“清词中兴”
深入考察“清词中兴”意涵以及清词品格的渊源,清词与南宋词的联系尤为值得重视。
嘉庆年间的姚椿评浙西派与南宋词的关系云:“词之义至南宋而正,至国朝而续。国朝之言词者,尤宗浙西,盖皆以南宋为归也。”(77)姚椿:《万竹楼词序》,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153页。明确提出了南宋词对清词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张尔田指出晚清四大家与南宋的关系云:“半塘之大,大鹤之精,彊村之沉,蕙风之穆,骎骎乎拊南宋而上。”(78)张尔田:《词莂序》,《遯堪文集》,民国刻本。指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虽然风格不同,但均受到南宋词的影响。陈匪石先生从词史的全局讨论清词与南宋词的关系:
有清一代词学驾有明之上,且骎骎而入于宋。然究其指归,则“宋末”二字足以尽之。何则?清代之词派,浙西、常州而已。浙西倡自竹垞,实衍玉田之绪;常州起于茗柯,实宗碧山之作。迭相流衍,垂三百年。世之学者,非朱即张,实则玉田、碧山两家而已。……至同、光以降,半塘、沤尹出,始倡导周、吴,而趋其途径,沤尹则直入梦窗之室,吴派遂为清末之新声矣。若学美成而至者,则尚未之有也。(79)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宋词举》(外三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陈匪石指出:清词的特质与南宋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浙西派尊张炎,常州派尚王沂孙,晚清的王鹏运、朱祖谋倡吴文英,皆以南宋末年的词人为典范。虽然晚清四大家也曾标举北宋的周邦彦,而实质是走向南宋的吴梦窗。这段话对清词特质的分析颇为深刻。
南北宋之争是贯穿有清一代的词学论题。云间词派尚北宋而黜南宋,宋征璧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80)宋征璧语,《词苑丛谈》卷四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页。,代表了该派的观念。代之而起的浙西词派朱彝尊在词坛为北宋词一统天下之时提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81)朱彝尊:《词综·发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反云间派之道而行之。经过浙派词人的不懈努力,南宋词成为词人取法的典范,词坛甚至出现了“家祝姜(夔)张(炎),户尸朱(彝尊)厉(鹗)”(82)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一边倒向南宋的局面。常州词派出,试图调和南北宋取法的极端倾向,改南北宋之“争”为南北宋之“辨”,辨析两宋词各自的优劣。如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高者在南宋上”,两宋词相比各有高下之处;“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83)周济:《介存斋论词杂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0页。,各有自身的优缺点。周济此论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清词取法南宋的原因:北宋词自然天成,浑涵高妙,其境界之高乃时代成就之,非后天努力所能企及;而南宋词以人工胜,克服了“拙率”之病,与清人的“尊体”意图相合,又有“寄托”之径可循,给清人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这也正是常州词派特别推重南宋词人王沂孙的原因所在。因而清人自然会选择南宋为典范和楷模。浙西词派以南宋词为号召开辟了词坛新气象,标志着清词与明词划清了界线。清代各个词学流派皆从南宋汲取营养,浙西派取其清雅,吴中词派取其音律谐畅,常州派取其寄托,晚清四大家取其浑厚。可以说,清词与南宋词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清词的“中兴”之峰正是与南宋词的高峰遥相呼应。
与清代各词学流派对南宋词的充分肯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新派词学家对南宋词均表现出完全否定的态度,对南宋词的否定又进一步导致对清词的否定。
王国维词史观的基本认识为:五代北宋是词史的高峰,南宋之后衰敝不振。他推崇五代北宋词,对南宋词除了辛弃疾之外,均持排斥态度:“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84)王国维:《人间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50、4251页。在南宋词人中尤为厌恶吴文英、张炎的词:“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85)王国维:《人间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50、4251页。王国维还将南宋词与清词相联系:“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86)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75页。他认为南宋词的衰敝导致此后直至清代词风的不振。
胡适将唐宋词分为三个时期:唐至北宋中期为“歌者的词”,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为“诗人的词”,南宋中期至元初为“词匠的词”。胡适的分期与传统按照时代划分南北宋时期有所不同,但他说的第三期正是清代和民国词学家所讨论的南宋词时期。胡适对第二期“诗人的词”最为推崇,认为是唐宋词的高峰期。而对第三期“词匠的词”最为鄙视,认为“没有情感”,“没有意境”,“算不得文学”。胡适所说“词匠的词”主要是指南宋姜夔一派,即清人所称的格律词派或清雅词派。胡适指斥姜夔及姜派词人“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他们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迁就音律上的和谐”。(87)胡适:《词选·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可以看到,在胡适的词史观念中,南宋的“词匠之词”与清代“词的鬼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郑振铎对宋词的态度也与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相似,他认为北宋词是真挚的,无意于做作的,是词的黄金时代。南宋词大多在字面上做文章,有刻画过度之病,词的风韵与气魄渐近“日落黄昏”,已经没有生气。南宋之后“词也渐渐成为不可歌了,仅足资纸上之唱和,不复供宴前的清歌,仅足为文人学士的专业,不复为民间俗子所领悟。语益文,辞益丽,离民间日益远,于是遂有‘曲’代之而兴,而词的黄金时代便也一去而不复回。”(88)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3、4页。认为南宋词以及南宋之后的词史是一部衰退史,南宋词的价值已经大大衰减。
综观民国时期新派词学家的否定“清词中兴”之论,可以总结为三个共同观点:其一,认为整个词史的最高峰乃北宋时期,从此之后每况愈下,从南宋,经元明,至清代,愈益不振;其二,清词的主要特点及主要弊病是“模拟”,模拟是没有生气和价值的;其三,认为南宋词是衰颓时期的作品,清词深受南宋词的影响,只能是等而下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代词学家以及民国新派旧派词学家均认为南宋词与“清词中兴”有着高度的正关联关系:“清词中兴”的意涵中蕴含着对南宋词的肯定;反之,对南宋词的否定直接导致对“清词中兴”的否定。两种对立的词史观皆将考察的焦点集中在南宋词与清词的关系上。
对“清词中兴”认识的对立是词学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清末至民国旧派与新派词学观念和主张严重分歧出发,来肯定或否定“清词中兴”是分歧的焦点。我们将旧派与新派分歧或差异之处加以分析,可简要概括为以下诸端:第一,旧派的词学批评理论是用以指导创作,多从入门着眼,能发现南宋的价值;新派则将词史作为经典遗产和鉴赏的对象,发意须高,要标举北宋的高格。第二,旧派学有传承,观念中多有历史积淀,从张惠言到周济、董士锡,再到端木埰、四大家,形成了系统而深植的理念;新派多受西学影响,西方文艺学和美学理念与个人学养、情感和欣赏习惯因素较多。第三,旧派倾向于“以诗为词”,重视词体的社会功能;新派注重诗词之辨,强调词体特色。这些观念的分歧和差异从不同角度聚焦到“清词中兴”论题上,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评《民国时期词学理论批评衍化与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