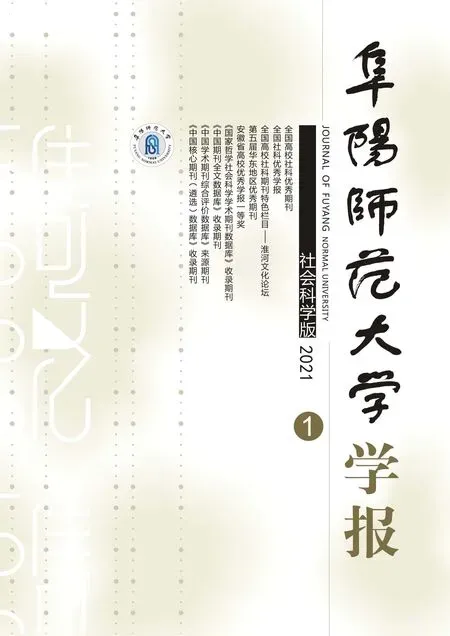“女士”:清代女性诗人独立意识觉醒的标志——以《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为例
尹玲玲
“女士”:清代女性诗人独立意识觉醒的标志——以《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为例
尹玲玲
(山东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女士”,是指“士”这一阶层中的女性。这一概念由来已久,但真正名实相副并作为群体出现却是在清代。《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中记载了众多符合传统“士”之素养与气节的女性,她们或博通经史,或具经济之才,或潇洒凡尘,或驰骋疆场。如若细分,则有女学士、女儒士、女名士等。明末清初以后,女性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成就列入士林并得到社会认可,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除却性别因素,清代女“士”与男“士”并无多少差异,整体看有清一代女性诗人文学成就不亚于男性。“女士”这一文人群体之所以出现在有清一代,既源于女性要求男女平等之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与其日趋强烈的要求参与社会变革之思想观念有关,更与传统士大夫阶层中一些有识之士之评价视角改变相契合。其最根本因素,则在于明末清初之后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
女士;清代;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知识分子
“女士”一词,源自《诗经》。但自“士”这一社会阶层出现后,却并未真正用在女性身上,因为明末清初之前女性是被排除在士林之外的。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对中国古代“士”的起源与发展变迁有精到阐述,却未把女性之“士”考虑在内。其实早在明末清初,伴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越来越多,女性文化修养也逐渐提高,不少女性已经跻身士的行列,且得到社会认可,当时用“女士”一词来品评女性已趋于常见,即为明证。《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以诗话的方式记载了众多女性,展现了多样的女士风采,且闺秀诗话的某些撰写者本身就是女“士”,如《名媛诗话》的作者沈善宝。她们或从性别上自觉泯灭柔性,或博学多才、胸怀天下。虽然她们不能像男“士”一样行走天下、传道授业,却明显展示出士之气质与才华,是士林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女士”一词的含义和用法一直持续至晚清,之后伴随着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加之西学东渐的影响,“女士”一词遂成为对女子的敬称,而其特定内涵以及与“士林”的关系反被忽视。本文所述“女士”,单指女性之“士”。
一、“女士”概念溯源及流变
要明了“女士”,首先要明了“士”。《说文解字》载:“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里“士”就是知识渊博的人;又有《白虎通义·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为士。”据此“士”又指有才干的人。也有论述仅从某一方面指出“士”应具备的品质。如《论语》言“士志于道”,《孟子》言士“尚志”。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一条孔子与弟子讨论士的记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1]245
据此条记载,孔子认为士有高下之分,而这种高下层级恰好符合古代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就是说,“士”最起码要注意自身修养。综上,“士”一般是指有知识、有才能且有修养的人。
至于“女士”的提法,最早见于《诗·大雅·既醉》:“其仆维何,厘尔女士。”[2]514孔颖达疏:“女士谓女而有士行者。”[3]1225意思是有士人操行的女性。这一说法出现后,有关女士的文献记载并不多,目前可见者仅有宋代一条:
此条文献表明,朝廷择有德有识之女子进宫侍御,她们可称为女士,在这个意义上,大致与出仕之“士大夫”相近。此后,元好问《临海弋公阡表》有言:“女一人,适张氏,仁让有‘女士’之目。”[5]659这则是基于女士之道德修养方面给予界定,与传统文化对“士”的自我修养要求也相近。
直至明末清初,“女士”一词始频频出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邹赛真“博学工诗,于时以为女士……俨然道学中宿儒,不当以词章取之也”[6]728。可见邹氏“女士”之称,已为时人共识。邹氏之所以被称为女士,并非仅因词章,而是因其博学多才。又钱谦益《继妻王氏仍前封制》:“割儿女婉娈之私,成丈夫慷慨之节。若尔者,可谓女士矣。”[7]1965以女子比为丈夫,以“慷慨之节”誉之,则与孔颖达的解释前后呼应。钱谦益笔下这两位女性之所以被看作女士,一因其才,一因其德。又俞正燮《癸巳类稿》:“《列女传》云:丹阳罗静者,广德罗勤女,为同县朱旷所聘,婚礼未成,勤遇病丧没,邻比断绝,旷触冒经营,寻复病亡。静感其义,遂誓不嫁。有杨祚者,多将人众,自往纳币,静乃逃窜,祚劫其弟妹,静惧为祚所害,乃出见之,曰:‘实感朱旷为妾父而死,是以托身亡者,自誓不贰,辛苦之人,愿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请守之以死。’乃舍之。后世女子不肎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必若罗静者,可云女士矣,可云贞女矣。”[8]495此条文献指出,只有具备如此高尚节操者才可称为“女士”,而普通女子不可以称为“女士”,同时作者又将女士等同于贞女,显然极为重视妇德。此外袁枚胞妹袁机也是才德并称的女子,著有《素文女子遗稿》,袁机堂弟袁树说她有“不栉进士”之目(《哭素文三姊》(有序)[9],她的外甥陆建评价她:“贤明岂但称闺秀,儒雅难逢此士夫。”(陆建《哭从母》其二)[10]203由此可见清代士林已习惯将有才或有德的女子称作“女士”,意味着传统士大夫阶层对知识女性的认同已由被动转为自觉接纳。
二、《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中的女士群像及诗意生活
相比其他朝代,清代女性更带“士”之气质,也更符合传统文化对“士”之要求。《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由于以诗话方式记录女子生平并加以品评,是考察清代“女士”的最佳渠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众多或有才、或有德、或有识,或三者兼具的女性,而且可以发见男性对“女士”的高度评价和认同。纵观该丛刊,各类闺秀诗话中对“女士”记载最多,但各诗话所载又有重复出现者,归结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博通经史女学士
清代才女并非仅以词章自娱,她们往往喜读史书,并借诗笔传达其不凡史识。又有女学者,勤于著述。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有“泰陵女学士沈琼莲”一条,直接对沈琼莲冠以女学士之名,并且小传中评价:“诗有天庙瑚琏之色,直以女学士呼之亦可。”(1)吴山“吐词温文,出入经史,相对如士大夫”[11]1727。又沈善宝博学工诗,并撰有《名媛诗话》,被称为“不栉进士”[11]2056。
清初王端淑名噪一时,她富有诗才,有诗集传世,且在士夫中有一定影响力,“与四方名流相唱和。对客挥毫,同堂角麈所不吝也”[11]1724。不仅如此,她还穷十余年心力,编选《名媛诗纬初编》,以“诗纬”命名,欲与《诗经》共成经纬,其文学“野心”不可谓不大——试问自《诗经》被冠以“经”之名称以来,有谁敢把自己的作品和《诗经》分庭抗礼?诚如其丈夫丁圣肇叙中言:“《名媛诗纬》何为选也?余内子玉映不忍一代之闺秀佳咏湮没烟草,起而为之霞搜雾辑。其耳目之所及者,藏之不忘;其耳目之所未及者,更悬以有待。盖苦心积玩于字珠句玉者,已一十又余年于兹矣,怜才之心过于自怜。”(1)此外,王端淑经常在评语中发议论,显示自己的卓识,如借金陵宫人宋蕙湘议论如下:“魏武深情,不是一味贪狠,其杀北海,子瞻所谓操不杀融,融杀操也,至于德祖正平,恃才轻躁,殊未善藏其用矣。千金赎琰,使中郎夜台感恸,不愧英心厚道。”(1)又借周宪王宫人夏云英表达某些女子对须眉男子的超越:“弃红颜如尘土,跃身火阱外,蛾眉之勇直过轲政,非餐霞人无此见地。而须眉男子,寝处声华,一双眸子视欲河如涨雾,头白不破,多与火蛾同尽灯烬间,殊堪悲悼。”(1)王端淑读书做学问极为勤苦,她的丈夫丁圣肇曾言:“内子不作唐朝应制举业,何自苦乃尔。”(1)丁圣肇的怜惜正揭示了王端淑的心理:不能身为男子应举业,则必须以其它渠道实现抱负。
汪端,清中期女诗人、学者,著有《自然好学斋诗钞》,编选《明三十家诗选》。在汪端这里,性别似乎被忽略了,抑或她在有意识地避开自己的性别角色。不论作诗还是选诗,她都能站在一定高度,议论恢弘,月旦甲乙。《名媛诗话》评价:“小韫议论古人,具有特识。……议论英伟,可破拘墟之见。”[11]443萧抡《自然好学斋诗钞序》曾言:“小韫好读书,记诵该洽,闻其舅云伯言,尝于十七史中,举隐僻事问之,辄应口对。及观所作《读<晋书>》诗,与诸论古之作,信乎其熟于史也。”[12]323笔者曾有《汪端咏史诗的内涵及其逆传统性》一文,专论汪端咏史诗,其中提到:“《自然好学斋诗钞》咏史诗每每篇帙庞大,诸如《读晋书杂咏》四十首、《张吴纪事诗》二十五首、《读史杂咏》十四首、《元遗臣诗》十三首、《论古偶存》五首、《南都遗事诗》四首、《咏古四首和归佩珊夫人懋仪》《秋夜读史》《夷门歌》《读贾谊传》《咏史》等,借咏古忠臣孝子、节妇烈女故事来表达自己的伦理观念、历史评价,展现汪端学博识精及臧否人物的卓越识见。”[13]71曹贞秀说汪端“所著自然好学斋诗沉雄古厚、緜渺悱恻,扫尽脂粉习气,每一篇出,惊倒耆宿”(2)。据陈文述《孝慧汪宜人传》,汪端曾撰有《元明逸史》八十卷,后毁去。而《明三十家诗选》,则选诗、论史,二而一之:“读是书者不特三百年诗学源流朗若列眉,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瞭如指掌。”(2)不仅如此,汪端还借《明三十家诗选》与当时大家并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清人选明诗云:“清世选本,要以钱牧斋《列朝诗集》、朱竹垞《明诗综》为最博,沈归愚《明诗别裁》、汪端《明诗选》为最正。”[14]239
清代博习经史的女性不在少数,诗话中即有多位。她们见解卓特,显示出不同于男性的睿智。卞梦钰“其父母教之以文史之学,靡不博通,翰墨词章,流传吴越。……而涉韦编略宝钿,而亲班、管、卫夫人之书,管夫人之画,因兼善其长”[11]1728。闵怀英“耽经史,喜文章”[11]1866,赵棻“工诗,能古文,博习经史。性敏达,无巾帼俗态。有客来访谢城,即出与谈。高谈雄辩,辄为折服,较之谢道韫施青纱布障为小郎解围,更高一筹”[11]2009。王照圆是名副其实的女学者,书法、古文俱绝,且著述甚夥,“尤精汉学,握铅怀椠,日与兰皋考订经史疑义,疏《尔雅》,笺《山海经》,名噪都下。所著有《列女传补注》八卷、《叙录》一卷、《列女传校正》一卷、《叙赞》一卷、《梦书》一卷行世。……所著《诗说》二卷、《诗问》七卷、《列女传补注》八卷、《女录》一卷、《女校》一卷,前清光绪八年顺天府尹毕道远等进呈御览,奉上谕,有‘博涉经史,疏解精严’等语”[11]2025。陈尔士“幼习经史,工吟咏。博学通经义,著有《历代后妃表》《清异三录》”[11]2026。严永华“幼有至性,通经史大义”[11]2057。李文慧“工琴,尤好读史。尝手评陈寿《三国志》,具有卓识”[11]844。林以宁“少从母氏受书,取古贤女行事谆谆提命。而尤注意经学,且愿为大儒,不愿为班、左”[11]1797。林以宁不愿为班、左的心愿传达了大部分女士的心声,她们希望人们尤其是男性,忽略她们的女性身份,仅从才能出发加以对待。
集团拥有中国唯一的剑麻农业、工业研究所和剑麻技术开发中心。集团现有土地15000公顷,剑麻种植园6000公顷,年产纤维20000余吨,专业剑麻加工厂18座。生产经营剑麻纤维、白棕绳、剑麻纱、剑麻布、抛光轮、剑麻地毯、水草地毯、絮垫、门口垫、墙纸、剑麻工艺品、剑麻皂素等系列产品和天然地毯泡沫背衬胶、天然标准橡胶、天然浓缩胶乳以及木制品等产品。
(二)胸怀天下女儒士
所谓儒士,不仅以学问著称,且具有儒家“士志于道”的胸怀和理想。清代才女中多具经济之才者,不甘单以柔弱才女面目示人,她们关注时事、忧国忧民,且在特殊时期持操守节。明清鼎革,士人以气节互相期许,女士亦不例外。对此后人多有高度评价,陈寅恪先生之《柳如是别传》就是为柳如是大唱赞歌的巨著,其“著书只为颂红妆”之系列研究实际上就是在为历代杰出“女士”树碑立传,正如有学者所提倡的,是从“女性视阈”所作的“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15]16。对此其好友吴宓有精到分析:“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16]145此外,陈寅恪在其《论再生缘》中,更是对陈端生这位清代大才女兼女士寄予深深的“同情”和最高级别的礼赞:“噫,中国当日知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管家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17]6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在这里已经明确把陈端生列为“当日知识界”之一员,只是尚未使用“女士”一词而已。
而乔玉钰《性别语境下的家国书写——明清之际女遗民创作的精神特质论析》一文则专述明清之际女遗民,文中大致涉及到13位女遗民:王思任女端淑、祁彪佳妻商景兰、孙临妻方子耀、葛徵奇妾李因,方以智妻潘翟、方中通妻陈舜英、方中履妻张莹、张成义女鸿逑;陈之遴妻徐灿、熊文举妻杜漪兰、李元鼎妻朱中楣、刘淑、顾贞立[18]102。这13位女遗民也出现于闺秀诗话中。另外,《清代闺秀诗话》载,吴山以女遗民自诩,其夫刘峻度以“老邓汉仪”题其集,曰:“江湖萍梗乱离身,破砚单衫相对贫。今日一灯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遗民。”[11]1728其诗多玉树铜驼之感。
女遗民外,又有一批女子胸怀天下,以身列巾帼、不能实现功名抱负为恨。顾若璞“文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常与闺友宴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每夜分执卷吟讽,曰:‘使吾得一意读书,即不能补班昭十志,或可咏雪谢庭。’”[11]1731顾若璞的长媳丁玉如“慷慨好大略,常于酒间与灿论天下大事,以屯田法坏为恨”[11]1731。吴巽“好读书,遇慷慨激烈事,辄潸然出涕。尝自言曰:‘使我得为男子,多情负气应更胜也。’”[11]1824张孟缇为沈善宝闺中好友,《名媛诗话》载:“孟缇词笔秀逸,真得碧山《白云》之神。壬寅荷花生日,余过淡菊轩,时孟缇初病起,因论夷务未平,养痈成患,相对扼腕。……孟缇弱不胜衣,而议论今古之事,持义凛然,颇有烈士之风。”[11]487编有《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恽珠,“于经济治体无不通达,尤明心学。慕李二曲先生以孝子为醇儒,重刊其集,制序行世。又刻《逊庵语录》,以述祖德。尝论‘古今世运有治乱,维持不敝者全在纲常。’乃仿《列女传》,博采史志,纂《兰闺实录》六卷。先孝行、贤德、慈范、节烈,而以智略、才华殿焉”。被称为“女中之儒”[11]2002。此类才女众多,如蔡季玉(琬)“才识过人,鱼轩所至,几半天下”[11]358。被评价为“闺阁中具经济才者”[11]359;汪雅安“学力宏深,词旨简远。且能阐发经史微奥,集中多知人论世经济之言,洵为一代女宗”[11]530。丁芝仙“书得《灵飞》之神,胸有经济之学,阅历半天下,洵通才也”[11]605。
总之,女儒士大都以天下为己任,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却又囿于闺阁,无所作为,因此常常有生不为男子、“壮志未酬”的嗟叹,例如沈善宝之“自恨弱草质,不栉非男子”,就是身为女子之悲哀与无奈的生动表述。
(三)林下风致女名士
林下风致,或称林下风气,来源于《世说新语·贤媛》:“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19]142其义主要指女子之娴雅飘逸的名士风度,与前之“女儒士”义有交叉,如柳如是既为女儒士,也是女名士,对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阐释,不赘。
此类女子无脂粉气,不在意物质生活,潇洒出尘。黄媛介“其诗初从选体入,后师杜少陵,潇洒高洁,绝去闺阁畦径”[11]1733。周琼“诗雄宕秀拔,足救刻翠剪红之习……有英杰气”[11]1751。“吴巽诗和雅庄重,如其为人,故有林下风致,不徒无脂粉气已也。”[11]1824她们平时生活亦大多不拘守闺阁之内,山水交游,意致翛然。黄媛介“乙酉鼎革,家被蹂躏,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檇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滞云阳。其所纪述,多流离悲戚之辞,而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既足观于性情,且可以考事变。此闺阁而有林下风者也”[11]1733。在流离转徙之中,黄媛介与吴越诗人多有交往,且这些诗人中不乏男性,主要有:钱谦益、吴梅村、柳如是、商景兰、王端淑、吴山、朱中楣等。黄媛介的游历多有生活所迫的无奈,周琼则适意潇洒,更具名士风度。据载,周琼“诗才清俊,作人萧散,不以世务经怀,傀俄有名士态”。她安于贫穷,善于贫中作乐:“所居陋甚,破窗颓壁,几不避风雨,然羽步意致翛然,略无怨尤意。喜纵观古史书,爱吹弹,时作数弄以遣兴。郡中人士有以诗寄赠者,羽步即依韵和答,诗俱慷慨英俊,无闺帏脂粉态。”[11]1749无论是黄媛介还是周琼,她们与男士的交往中都不同程度忽略了性别身份,以诗词唱和为平台,纯然一种文士的交往。至于绛子则寻求个人的飘然自适,她“质钏镯得千余金,构一小园于亭畔,日摊《楞严》《金刚》诸经,归心禅悦,颇有警悟。尝谒灵岩、支硎等山,布袍竹杖,飘遥闲适”[11]656。而杨素书则乐于躬耕田园,“莳花种竹”[11]1923,寻求陶渊明式的安乐,似可以称为“女隐士”。
上述女名士,其闲适洒脱之风度,不让男性,倘若在魏晋时代,则刘义庆或为其专设一章欤?
(四)奇情倜傥女奇士
奇女在汉代即进入人们视野,《汉书·外戚传》载:“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地有奇女。”[20]1186之后各类“奇女”进入文学书写,如唐传奇中所写之“奇女”,因体裁需要,多具神秘性及传奇性,更近于“超人”。至宋代,性格“豪放不群”、诗有“丈夫气”的楚珍被称为“江南奇女子”(3)。而明代屠隆则编有《奇女子传》,陈继儒《奇女子传序》言:“其间有奇节者、奇识者、奇慧者、奇谋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学者、奇情者、奇侠者、奇癖者,种种诸类。”[21]89奇女子或文或武,文能预卜风雨,武能上马击贼。
此类女子大多身怀绝技,吴规臣“奇情倜傥。工诗词,精医理,通剑术”。其夫远宦,“飞卿尝往来金陵、维扬间,鬻书画自给”[11]799。她以书画养活自己,已经真正做到了自尊自立。尤值得表彰者,诗话中记载了三位带兵击贼的战士。沈云英父守道州城,殁于军,沈云英带兵“甲而驰”“直前击贼”,最终解道州围,且带父尸进城发丧[11]1717。刘淑英自幼习学剑术、孙吴兵法,甲申,“帝后殉社稷。淑英闻变,痛哭曰:‘……吾恨非男子,然独不能歼此渠凶以报国仇耶?’散家财,募士卒,得千人,并其童仆,悉以司马法部署指挥,成一旅”[11]1718。毕著武艺高强,“父与流贼战死,尸为贼所得。著身率精锐劫贼营,手刃其渠,众溃,舆父尸还,葬金陵之龙潭”[11]811。以上三位女子,皆生活于国变之时,义勇与贞节并存。她们也被各种诗话记载、转载,无论是男性诗话作者还是女性作者,都对她们推崇备至。苏轼《论养士》一文将士分为智、辩、力、勇四类,上述奇女子可谓智、勇、力俱全。其他,姚允迪通晓星术,“尤喜读《周易》,晓星数,夜分窥星躔,占风雨,无不应验”[11]840。赵景淑不以诗人自居,更倾向于品评,且气魄直逼须眉。赵景淑先关注名媛,“尝集古今名媛四百余人,各为小传,题曰《壶史》。又著《香奁杂考》一卷,征引详博”。又品评男性诗,“其论有清一代诗,则取王阮亭、李丹壑一派,而不喜明七子,辄效李长吉”[11]647。其品评男性的胆气可与汪端并称。项祖香“倜傥多才,聪明绝世,于书无所不通,口若悬河,胸藏奇气”。被目为“闺中杰士”[11]588。
闺秀诗话中的女士虽类型多样,但她们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有较高的文学才华和艺术修养,她们结社、宴会、出游,尽情享受文士的悠游生活,其中“结社”既是她们具有自觉意识的标志,也是获得男性“士大夫”肯定的结果。据清代闺秀诗话记载,明确以诗社命名并有确切成员的诗社有三:先有“蕉园七子”诗社,林以宁“与同里顾启姬(姒)、柴季娴(静仪)、冯又令(娴)、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媞),提倡‘蕉园七子’之社,艺林传为美谈”[11]1797。后有“清溪吟社”,张允滋“与同里张紫蘩(芬)、陆素窗(瑛)、李婉兮(微)、席兰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岑(珠)、沈蕙(孙纕)、尤寄湘(澹仙)、沈皎如(持玉),结‘清溪吟社’,号‘吴中十子’,媲美西泠,嗣(此处断句笔者有改动)又选定诸作刊《吴中女士诗钞》,附以词赋及骈体文,艺林传诵,与‘蕉园七子’并称”[11]1963。由此可见,诗社并非徒有虚名。后又有“秋红吟社”,沈善宝《名媛诗话》载:“己亥秋日,余与太清、屏山、云林、伯芳结‘秋红吟社’。”[11]493
女文士可以在诗社中联吟倡和,也可以出游赏景,悠游于山水之间。清代中期,女性已不再固守闺门之内,尤其是才女们,结伴出游、享受诗意生活已经成为她们文士生活的一部分。沈善宝《名媛诗话》记述了不少她与好友结伴出游的经历,有时是六七好友同行:“丙申初夏,苹香、芷香姊妹偕渑池席怡珊(慧文)、云林并余,泛舟皋亭,看桃李绿阴,新翠如潮,水天一碧,小舟三叶,容与中流。较之春花烂漫、红紫芳菲时,别饶清趣。将近皋亭,泊舟桥畔,联步芳林,果香袭袂。村中妇女,咸来观看,以为春间或有看花者,至今则城中人罕有过此,盖从未见有赏绿叶者。……推蓬笑语,隔舫联吟。归来已六街灯火上矣。”[11]451又如:“庚子暮秋,同里余季瑛(庭璧),集太清、云林、云姜、张佩吉及余,于寓园绿净山房赏菊。花容掩映,人意欢忻,形迹既忘,觥筹交错。”[11]452有时又与家人相伴:“先慈在时,每年六七月之望,必招姊妹携儿女泛舟游玩,觞咏达旦。家兄等亦邀一二至亲之善音乐者,别驾一舟,相离里许。万籁皆寂,竹肉竞发,歌声笛声,得山水之助,愈觉空灵缥缈。”[11](472)更有一二知己偕游:“吾乡西溪,梅竹最多。平桥约略,流水回环,掩映竹篱茅舍。境之幽邃,景之清逸,虽善图者,亦难描写。春日梅花,秋日芦花,最为大观。犹忆丙申试灯日,云林偕余同往探梅。”[11]489“辛亥试灯后十日,暖姝约苹香及余挈友愉女,同往皋亭山下崇光寺探梅。……纵谈古今,人影花光,相看忘暮。”[11]606她们在美景中徜徉,每一次出游都充满诗情画意。出游之时,她们时或倡和赋诗,时或宴饮叙旧,沈善宝曾言:“余于己酉春暮返杭,重晤苹香、玉士诸闺友,久违暂聚,乐可知也。孙秀玉(静筠)……招余及萍香、玉士饮湖上。”[11]586“庚戌冬日,余返杭扫墓。关秋芙集诸闺友宴余于巢园。”[11]602这些才女有着寻常女子欠缺的才情,又基本摆脱了世俗及家庭的羁绊,其充满诗情画意的日常生活,即使放在今天,亦让人神往不已。
三、明末清初“女士”兴起原因及意义
首先,清代女性受教育机会增多,越来越多女性可以接触到书本,随着女性文化水平的提高,其视野也逐渐开阔,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男耕女织之社会分工,而是期待像男性一样立德、立言,王端淑、汪端、赵景淑、沈善宝等选诗评诗的举动即是其立言愿望的最好注脚。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所录女性著作四千余种,其中清代妇女著作即达到三千六百余种,由此可见清代女性受教育之相对普及程度。
其次,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看法比以前有所进步,“女主内”的观念得到一定改变,女性的才华与智慧逐渐得到认可、受到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清代统治者对女性之禁锢态度较之前代宽松有关。如《女范捷录》曰:“治安大道,固在丈夫,有智妇人,胜于男子。”[22]179明确肯定了女性的智慧。又言:“男子有德便是才,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辩也。夫德以达才,才以成德。”[22]191虽也强调德,但把才提到与德同等的地位,等于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而在家庭教育方面,很多女性诗人家庭宽松的教育氛围也有益于她们的成长,例如沈善宝出身名门,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其父称赞她是“随宦章江擅彩毫,吟成博得双亲喜”(4),母亲也写诗赞叹“尔负奇男志,吾将孝子看”[11]448。显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女性之才华更容易得到表现。有观点认为,就传统意义而言,“中国人侧重人格的群体性,西方人则着眼于人格的个体性”[23]37。其实,清代女性接受教育的相对宽松而自由的环境,恰恰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对人的个体性特别是女性的个体性的逐渐重视。
再次,女性的男性性别向往意识明显提高,构成“女士”这一群体出现的理论基础。自古以来,德才兼备的女性就不少见,但是她们最终的结局也是局限于闺阁之内,如:“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能棋;解文仪,仕至扬州从事。后事发,作妇人服,叹曰:有如此技,还作老妪。”[24]15这样的悲剧让女子时时有男性性别向往。董申林的诗明确表达了这种向往:“闭置深闺每自嗤,可容速变作男儿。鸾靴学试桃花马,快意生平此一时。”[11]641赵棻“天性高朗,有丈夫气骨”[11]823。又如蔡季玉(琬)的《辰龙关》:“一径登微独惘然,重关寂寂锁寒烟。遗民老剩头间雪,战地秋闲郭外田。闻到万人随匹马,曾经六月堕飞鸢。残碑洒尽诸君泪,苔蚀尘封四十年。”[11]359而沈善宝《名媛诗话》对于此类女性的描述也大都带有男性化的痕迹,如言吴佩萱“丰神俊美”[11]610,此类描述,大多用于男性。这种性别向往有时与家庭有关,如前文述及的王端淑,她自幼才华显现,父亲王思任也对她格外器重,只可惜她不是男儿。家人的期待,让年幼的王端淑形成一种心理暗示,她自幼“喜为丈夫装,常剪纸为旗,以母为帅,列婢为兵将,自行队伍中拔帜为戏。父见而笑曰:‘汝何不为女状元乎?’”(1)韩则愈曾言及王端淑的性别感伤:“每叹其有才如此不能置身天禄石渠间,以文章黼黻皇猷而徒徙倚香奁,与春华共开落,良可伤也。”(1)
清代女性的性别向往表现出来的是近于“男女双性”的状态:“明清女诗人纷纷表现出一种‘文人化’的倾向,那就是一种生活艺术化的表现对俗世的超越:例如吟诗填词、琴棋书画、谈禅说道、品茶养花、游山玩水等生活情趣的培养。与男性文人相同,这些女诗人强调写作的自发性(重自然、忌雕琢),写作的消闲性(非功利的选择,怡情悦性),及写作的分享性,这种写作上的价值观本来原是十足的男性化的,现在把它与女性连接在一起,等于创造了一种风格上的‘男女双性’( Androgyny) 。”[25]12她们的这种性别向往来源于对男女平等的渴望以及对“士”这一身份的期许,她们博览群书,有意和男性士大夫交往,并非满足于让世人承认其文学才华,而是有着强烈的立德、立言的愿望。
综上所述,清代才女众多,且已形成比较自觉的“女士”群体,其中有些仅以诗文自娱,有些则于读书作诗之外,目的远非自娱自乐,她们期待着立德立言,跻身“士”之行列,最终意在参与中国社会变革之进程,在事实上成为真正的女“士”。这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当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一直承担着发展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其坎坷命运更是值得大书特书,而清代“女士”被纳入士林显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清代“女士”这一群体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有清一代有记载女诗人多达数千,而真正进入文学研究视野者寥寥无几,更遑论深层次的跨学科比较研究。本文拈出“女士”这一概念,意在引起学术界注意,如能将清代之“女士”纳入全部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历史中给予观照和梳理,并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女性觉醒过程以及外来文化中“女性主义”之研究,必将极大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1)本文所引《名媛诗纬初编》材料,皆出自清代王端淑编撰《名媛诗纬初编》,清康熙间清音堂刻本。
(2)本文所引《明三十家诗选》材料,皆出自清代汪端编撰《明三十家诗选》,清同治十二年蕴兰吟馆重刊本。
(3)本文所引《书录》材料,出自宋代董更撰《书录·外编》,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4)(清)沈善宝著,《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三,民国初年铅印本。
[1]孔子.论语[M].张艳国,注评.武汉:崇文书局,2015.
[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毛亨.毛诗正义[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佚名.大内内侍省尚宫赵氏赠崇德夫人制[M]//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辑校[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俞正燮.癸巳类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9]袁树.红豆村人诗稿[M].长春:博文印书馆,1938.
[10]胡晓明,彭国忠.江南女性别集·四编[C].合肥:黄山书社,2014.
[11]王英志.清代闺秀诗话丛刊[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2]胡晓明,彭国忠.江南女性别集·二编[C].合肥:黄山书社,2010.
[13]尹玲玲.汪端咏史诗的内涵及其逆传统性[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03).
[14]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5]刘艳.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16]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17]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8]乔玉钰.性别语境下的家国书写——明清之际女遗民创作的精神特质论析[J].文学遗产,2015(06).
[19]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0]班固.汉书[M].赵一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1]杜云.明清小说序跋选[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22]沈朱坤.绘图女四书白话解[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23]周波.中国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思路[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
[24]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5]孙康宜.走向“男女双性”的理想——女性诗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C]//叶舒宪.性别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Female Scholar”: The Symbol of th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of Female Poets in the Qing Dynasty
YIN Ling-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250357 Shandong)
“Female Scholar” refers to women in the “scholar” class.This concept ha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real name was deputy and appeared as a group was in the Qing Dynasty.In the, many women who met the traditional “scholar” literacy and integrity were recorded. They may had a history of economics, or had an economic talent, or a world of dust, or a battlefield.If it was subdivided, there were female bachelors, femal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female famous scholar.After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omen were included in Shilin and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ir talents and achievements. This was a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Except for the gender factor, there was no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a female “scholar” and a male “scholar”.On the whole,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female poets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no less than men’s. The “female scholar” literati group appear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awakening of women's self-awareness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ly strong ideological concept of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change, it was more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valuation perspective of some people of insight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class.The most fundamental factor li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civil society after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female scholar; Qing Dynasty;; intellectuals
2020-11-03
山东管理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清代闺秀诗话与女性文化圈建构研究”(XJ2018031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当代诗词史”(AHSK2015D114)。
尹玲玲(1975— ),女,山东日照人,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诗文研究。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1.12
I207
A
2096-9333(2021)01-00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