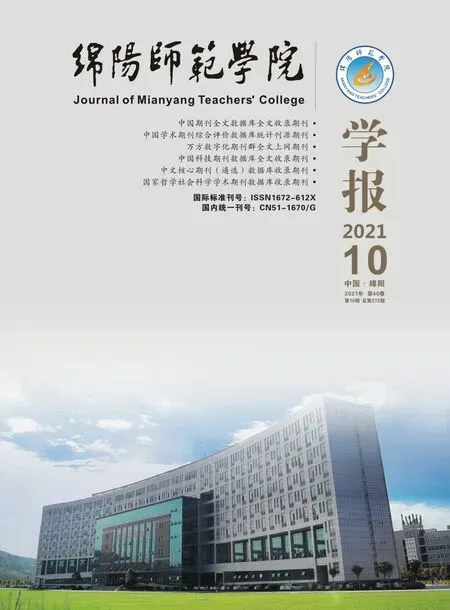如何文学?怎样革命?
——论茅盾的革命文学观
吕周聚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写成于1928年7月16日,于1928年10月在《小说月报》19卷10号刊出。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此文是茅盾对来自太阳社和创造社批判的反击,实际上并非如此,“在 《从牯岭到东京》 发表前,并不存在对 《幻灭》、《动摇》 的责难;相反,正是因为此文的发表,才激起了那些‘来自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家’的‘激烈批评’。”[1]既然此文并非为了反击创造社、太阳社的责难而作,反而是由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了创造社、太阳社批评家的激烈批评,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换言之,茅盾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又是什么?这篇文章为何会引发创造社、太阳社批评家的激烈批评?
1926年4月,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上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开始大力倡导革命文学。1927年,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上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1928年,李初梨在第2期《文化批判》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这两篇文章用阶级理论来阐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正式展开。李初梨否定了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是观念论的幽灵,个人主义的呓语;而“文学的任务在描写社会生活”则是小有产者的把戏,机会主义者的念佛①。他不仅否定了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也否定了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为人生派”主张。在此基础上,他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①将文学与宣传、政治等同起来,文学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当时左翼文坛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明日的新文艺应该是无产阶级文艺,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1)反对小资产阶级的闲暇态度,个人主义;(2)集体主义;(3)反抗的精神;(4)技术上有倾向于新写实主义的模样。”[2]187
作为职业革命家,茅盾当时无暇仔细阅读当时文坛上的新的文艺期刊②,东渡日本之后,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他都远离了当时的革命中心,这使得他能够静下心来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内省,并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进行反思,试图从理论上为当时的革命文学做一些清理工作,为革命文学奠定理论基础,由此写作出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文。我们可将此文与茅盾1928年1月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欢迎〈太阳〉!》和1929年5月发表于《文学周报》的《读〈倪焕之〉》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从中可看出这一时期茅盾对革命文学的思考,其中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革命文学理论问题:应该如何进行文学创作?革命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革命文学应该写什么?革命文学的读者是谁?革命文学应该有什么样的文体形式?
一
早在茅盾写作《从牯岭到东京》之前,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就在大力提倡革命文学。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成员否定了其前期的文艺主张,完成了思想观念的转换。郭沫若声称要当革命的留声机,“当一个留声机——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3]46,如何才能当一个留声机?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你无我”。尽管李初梨不赞同郭沫若“当留声机”的主张,提出了不当一个留声机的观点:“第一,要你发出那种声音(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二,要你无我(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第三,要你能活动(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①,但其观点与郭沫若的观点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强调作家要“无我”,意味着作家没有了主观性,只成了一个政治的传声筒。李初梨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作家的问题,并将其视为无产阶级文学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无论哪一个阶级的人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关键要看其动机如何,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如果是前者,就请他开倒车;如果是后者,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他历来所有的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革命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着重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标语口号化”创作倾向,文学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实际上,茅盾早在1928年1月发表的《欢迎〈太阳〉!》中就谈到了作家主体的重要性。他认同蒋光慈关于新文艺落后于社会的观点,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新文艺落后于社会还有个重大原因,“便是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没有极亲密的关系。文艺的创造者,没有站到十字街头去;他们不自觉地形成了文艺者之群,没有机会插进那掀动天地的活剧,得一些实感。”[4]163新文艺的作者脱离革命实践活动,没有革命工作经验,闭门造车,写作出来的作品没有真情实感,难免空洞无物,充满了标语口号。而且即便有了实感,也不一定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作者所贵乎实感,不在‘实感’本身,而在他能从这里头得了新的发见、新的启示,因而有了新的作品。”[4]164这种新发见、新启示,来自作家的独立思考,如果作家没有自我,就只会人云亦云,不会有这种新的发见。一战时期,从军上战场的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然而只有巴比塞和拉兹古等几个人在战场上看见了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写出了优秀的作品,“所以我以为一个文艺者的题材之有无,倒不一定在实际材料的有无,而在他有否从那些实在材料内得到了新发见、新启示。如果惟实际材料是竞,并不能从那里得到一点新发见,那么,这些实际材料不过成为报章上未披露的新闻而已,不能转化为文艺作品。”[4]164换言之,作家的实感必须经过自己的细细咀嚼,从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才能转变为优秀的文艺作品。
茅盾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标语口号文学”进行了分析,指出:“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狭义的——或虽无此忽略与成见而缺乏了文艺素养的人们,是会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的。然而我们的革命文艺批评家似乎始终不曾预防到这一着。因而也就发生了可痛心的现象:被许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却正是并不反对革命文艺的人们所叹息摇头了。”[2]188茅盾指出了“标语口号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刚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却并不受主张革命文艺的人们所欢迎。茅盾在《读〈倪焕之〉》中对当时许多作者仅仅根据一点耳食的社会科学常识或是辩证法便自负不凡地写他们所谓富有革命情绪的“即兴小说”表示不屑,“作家们应该觉悟到一点点耳食来的社会科学常识是不够的,也应该觉悟到仅仅用群众大会时煽动的热情的口吻来做小说是不行的。准备献身于新文艺的人须先准备好一个有组织力,判断力,能够观察分析的头脑,而不是仅仅准备好一个被动的传声的喇叭;他须先的确能够自己去分析群众的噪音,静聆地下泉的滴响,然后组织成小说中人物的意识;他应该刻苦地磨练他的技术,应该拣自己最熟习的事来描写。”[5]211-212创造社诸君要完成从资产阶级文艺到无产阶级文艺的转变,但他们并没有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经验,便只能进行从观念到观念的转换,郭沫若声称自己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转换,而成仿吾则完成了从把守“艺术的艺术之宫”到把守“革命的艺术之宫”的转变,有人认为他们这是投机,是出风头,但茅盾并不这样认为,而是通过分析指出了其自身的必然性,“并且借此也说明了当时他们因为不曾参加实际运动和地下工作而错误地拾起了‘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以自娱的影响,竟造成了‘引人到迷途’,像他们今日所切齿诅咒别人的。”[5]204茅盾指出作家仅靠无产阶级意识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作家不仅要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而且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判断,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茅盾强调作家主体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尊重作家主体才能克服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标语口号化”文学倾向。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以钱杏邨为代表的太阳社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对鲁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彻底否定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行关注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6]437他认为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和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都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要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7]568这个“革命人”既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经验,又要有自己的革命思想,并不是仅有无产阶级意识就可以成为“革命人”。
茅盾结合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说明创作主体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他是用“追忆”的方式写作《蚀》三部曲,“追忆”的气氛——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合于当时的客观情形,“追忆”是作者回忆自己曾经的生活历程,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茅盾认为《幻灭》《动摇》没有自己的思想,《追求》却有其最近的思想,“虽然书中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2]180-181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强调文学创作要遵循基本的创作规律,即要尊重作家的创作主体,革命文学自然也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无视作家的创作主体,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能是标语口号化的政治宣传品,与文学相差甚远,诚如鲁迅所言,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都是文艺,失去了创作主体的作家不再是作家,失去了文艺性的作品也就失去了艺术生命力。
二
“写什么”是作家创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家能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革命作家也面临着“写什么”这一问题,他们从阶级论出发,否定了有产者和小有产者的文学,提倡写无产阶级文学。何谓无产阶级文学?李初梨做出了明确界定:“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①成仿吾认为:“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③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生活并不熟悉,于是其理论与实践之间便产生了矛盾。正因如此,他们要急于完成从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的转变,要“克服自已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③他们要求文学创作以农工大众为唯一的表现对象。他们认为革命文艺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反对小资产阶级的闲暇态度,个人主义”,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将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文艺的阵营之外。茅盾对此并不认同,并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现在为‘新文艺’一一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该先把题材转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2]191他在后来的《读〈倪焕之〉》中主张应该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的对象,“这句话平常得很,无非就是上文所说一个作者‘应该拣自己最熟习的事来描写’的同样的意义。再详细说,就是要使此后的文艺能够在尚能跟上时代的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间有一些儿作用。”[5]214茅盾并不反对革命文学表现农工大众,他认为革命文学在表现农工大众的同时,也应该表现小资产阶级。茅盾为何会提出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不同的意见?他提出这种观点的依据何在?
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明确地指出,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经指摘当时文坛上“空肚子顶石板”的怪现象,认为那是既顶不起石板,又圧坏了肚子的勾当,“我劝那些有志者还不如拣他们自己最熟习的环境而又合于广大的读者对象之小资产阶级来描写,我简直不赞成那时他们热心的无产文艺——既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只是‘卖膏药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然而结果是招来了许多恶骂。”[5]212空肚子顶石板,是指肚子里没东西(能力)而要做力所不能的事情,用这一比喻来说明作家要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题材,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他认为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重要构成部分,“我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2]190哪些人属于小资产阶级?在茅盾看来,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阵营,“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2]190,这一数据来自何处?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但茅盾的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是相一致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明确把“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归入“小产阶级”(应为“资”,笔者注)阵营,“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单是自耕农,就是一万万至一万二千万。小商人,手工业主,大概自二千万至三千万。合计达一万五千万。”[8]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毛泽东将小资产阶级分为左、中、右三部分,指出其革命态度的差异,同时又发现他们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革命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及小资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毛泽东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8]毛泽东将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真正的朋友,这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将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之外,甚至将其视为革命的对象是有本质区别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表现对象的理解是狭隘的,结果导致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但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所以六七年来不能长成为推动社会的势力。现在的‘革命文艺’则地盘更小,只成为一部分青年学生的读物,离群众更远。”[2]190-191这一方面限制了革命文艺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对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针对当时革命文学批评家把那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不问内容如何便武断地斥之为“落伍”的做法,茅盾也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中间一定很有些“落伍”的人物,但这是书中人物的“落伍”,而不是该著作的“落伍”。他认为那些只描写了些“落伍”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也有它反面的积极性[5]214-215。茅盾认为革命文艺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生活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犹之我们不能说只有农工群众的生活才是现代社会生活。”[41165针对蒋光慈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题材的观点,茅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如果以蒋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的仄狭的路,其非革命文学前途的福利,似乎也不容否认罢?”[4]165茅盾关于革命文学要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主张,纠正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革命文学表现对象的狭隘限定,拓宽了革命文学的题材范围,为推动革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在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之后,革命文艺还存在着“如何写”的问题,这就涉及到革命文艺的语言形式问题。当时的革命文艺批评家们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过于简单。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问题时,李初梨认为文学的内容决定文学的形式,这就导致他重视革命文学的思想内容而轻视其文学形式。他简单地介绍了国外无产阶级文学的四种形式,即讽刺的,曝露的,鼓动的(Agitation),教导的。前两种是美国揭黑幕小说中常用的手法,后两种则是典型的标语口号化手法。这四种形式成为当时新文艺作家经常运用的表现手法,但当时的读者对运用这些手法创作出来的作品并不感兴趣。换言之,此类作品在当时并没有读者群。面对这一困境,有人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目的不会是要人喜欢看的,只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是专门供人欣赏、顽弄的”,茅盾对此并不认同,认为无产阶级文艺也是要给人们看的,由此提出了今后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问题,即革命文艺为谁而写作。文学作品写出来都是要给人看的,不同的读者群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着、决定着作家的创作形式。
在茅盾看来,一种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艺必须要有相对的读者群,许多人认为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是革命文艺的读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是你对劳苦群众呼吁说‘这是为你们而作’的作品,劳苦群众并不能读,不但不能读,即使你朗诵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了解。他们有他们真心欣赏的‘文艺读物’,便是滩簧小调花鼓戏等一类你所视为含有毒质的东西。”[2]189劳苦群众没有接受教育,他们听不懂太欧化或是太文言化的白话,如要他们听得懂,惟有用他们所熟悉的方言来作小说、编戏曲,这又是新文艺作家所不愿做、不能做的,这样新文艺就陷入了一种悖论:“为劳苦群众而作”的新文学只有“不劳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阅读,“你的作品的对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现象!”[2]189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茅盾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扩大新文艺的读者群,二是改变文艺描写的技巧。
湿地生态旅游开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机构,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湿地生态旅游开发是一个综合性工作,需要协调调度多个部门的力量,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湿地生态旅游依托的对象是湿地,必须做好退耕还湿工作,加快湿地生态恢复步伐,保证湿地的规模和质量,做好湿地旅游宣传,彰显湿地魅力。
茅盾从读者的角度来逆向探讨革命文学的文体形式问题,认为革命文艺要先把题材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的生活上,同时在语言形式上也要进行改革,“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2]191因为小商人、中小农等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们对新名词不感兴趣,对欧化的句法难以理解,对说教似的宣传难以接受,只有用他们所熟悉的日常语言来进行创作的作品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才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茅盾强调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要性,认为有了生活实感的人们,也并不一定就能写出代表时代的作品,“要写一篇可看的文艺作品,究竟也须是对于文艺有素养的人们,才能得心应手。因此即使是亲历活剧的人物,也未必一时能有惊人的作品贡献给我们。”[4]163作家只有具备一定的文艺素养,熟练地掌握了文学的语言形式技巧,才能得心应手地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人物呈现出来,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关于文艺描写的技巧问题,茅盾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文坛上流行“新写实主义”,茅盾考察了“新现实主义”的源头——俄国的新现实主义,并分析了其基本特征——电报体(今天来看,这种分析本身并不完备),认为我们将其移植过来,后果会如何,这是个有待试验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第一是文字组织问题。照现在的白话文,求简练是很困难的;求简便入于文言化。这大概是许多人自己经验过来的。第二是社会活用语的性质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所要描写的那个社会阶级口头活用的语言是属于繁复拖沓的呢,或是简洁的。我觉得小商人说话是习惯于繁复拖沓的。几乎可说是小资产阶级全属如此。”[2]192茅盾认为中国旧有的民间文学是最为一般小资产阶级所了解的,“所以为要使我们的新文艺走到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去,我们的描写技术不得不有一度改造,而是否即是‘向新写实主义的路’,则尚待多方的试验。”[2]193茅盾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来思考新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根据中国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日常语言习惯来推断新文艺应该用他们所习惯的旧有的民间语言形式来进行创作,电报体并不适合中国小资产阶级读者的品味。因此,“我们文艺的技术似乎至少须先办到几个消极的条件,——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从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2]193而欧化、新术语、象征、说教正是当时新文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这样的作品只有知识分子喜欢看,小资产阶级是难以感兴趣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从牯岭到东京》并非为了反击创造社、太阳社对自己的批评责难而写,但它却是为了纠偏创造社、太阳社早期错误的革命文学理论主张而作。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发表的相关文章虽然并未点名批评茅盾,但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与茅盾相左的。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通过反思自己在大革命中的经历及《幻灭》《动摇》《追求》的创作历程,通过回顾当时文坛上革命文学的发展,厘清革命文学中所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为革命文学确立一些基本的理论范式,因此而与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观念及创作发生冲突,文章发表后引发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的激烈批判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重要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从牯岭到东京》遵循文学创作规律,针对当时革命文学发展中所存在的种种观念问题,提出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观,对文学的本质是什么、革命文学应该写什么、应该如何写⑤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确立了革命文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批判了当时革命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标语口号化倾向,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是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献。
注释:
①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
② 茅盾既是著名文学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在1925年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文学现象,对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1926年4月,他从广州参加由左派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上海后,便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成了职业革命家。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安排他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192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他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他上任不久即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国共两党分裂;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开始“分共”,茅盾在从武汉向南昌的转移途中因病在牯岭逗留,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到上海后,避居家中开始创作《幻灭》《动摇》《追求》;1928年7月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写下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文。
③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④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12月10日)和潘梓年的《到了东京的茅盾》(《认识》1929年第1期)。
⑤ 茅盾在《读〈倪焕之〉》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阐释:“‘五卅’时代以后,或是‘第四期的前夜’的新文学,而要有灿烂的成绩,必然地须先求内容与外形——即思想与技巧,两方面之均衡的发展与成熟。” (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