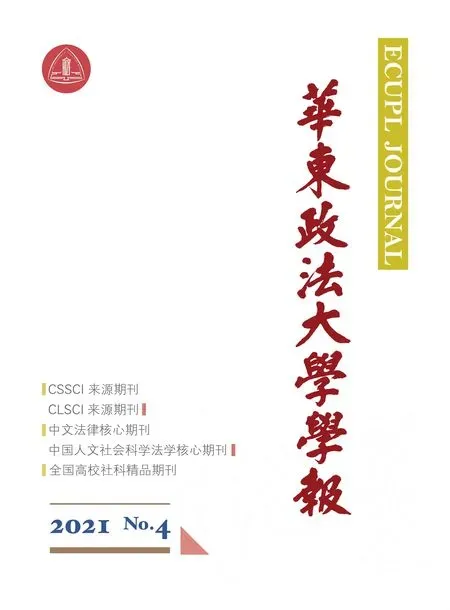名废实存:元代格例法体系与中华法系之真实关系
宋国华
法律史学界一般从两个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一是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角度,如秦有律、令、式、程、课、法律答问等;汉有律、令、科、比等;唐有律、令、格、式等;二是从法律内容角度研究,法律体系是由行政法、民事法、经济法、刑事法、军事法等共同构成的。其实,两个角度是紧密关联的。法律内容是以法律形式为载体的,或者说某一法律形式的功能决定了某一方面的内容。如行政方面的内容,在唐代主要以“令”“格”等法律形式规定,而有关犯罪和刑罚的刑事法则主要由“律”这种法律形式来规定。法律形式和法律内容相比较而言,法律形式及其所表述的立法成果是法律体系的基本要素,〔1〕参见杨一凡:《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 页。故谈到古代法律体系,学界首先从法律形式的角度论述。本文亦同。
学者对用“律令法体系”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法制史是没有异议的。但对律令法体系适用的时期持不同观点。刘广安先生认为,律令法体系这一概括性说法,只适用于秦汉至唐宋时期的法律体系,不适用于先秦时的法律体系,也不适用于元明清时期的法律体系;〔2〕参见刘广安:《令在中国古代的作用》,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2 期。刘笃才先生认为,律令法体系只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前期与中期存在,后期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其结果是被律例法体系所取代。律例法体系的历史时段,至少包括明清两代。〔3〕参见刘笃才:《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载《法学研究》2012 年第6 期。我们知道,宋依然是律令法体系,那么由律令法体系转换为律例法体系,居于宋明之间的元代法律体系应该如何定位?日本学者石冈浩等在《史料所见中国法史》一书中认为,律令法体系完成于唐前半期,此后逐渐演变,至明清时形成律例法体系。演变过程中,元代地位如何,并未明言,仅把辽到元的法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加以介绍。〔4〕参见[日]石冈浩等:《史料からみる中国法史》,法律文化社2012 年版,第23-34 页。杨一凡先生认为,元朝是中国古代从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向律例为主的法律体系过渡的时期。〔5〕参见杨一凡:《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23 页。近来,杨一凡先生对明代“律例法体系”做了修正,认为明代法律体系是按照“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框架构建的,应总称或简称为“典例法律体系”。(参见氏著:《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1 期);陈灵海教授认为,清代的法律体系是“典例”法律体系,“律例”体系只是“典例”体系中的刑法部分,不足以全面概括清代法律体系的特征。(参见氏著:《〈大清会典〉与清代“典例”法律体系》,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2 期。)楼劲先生认为,唐代的《律》《令》《格》《式》体系,形成于唐开元年间,但到中唐,此种法律体系开始瓦解,到宋神宗时确定了敕、令、格、式并行的法律体系,经过元代分部门或事类编纂各种敕例以为条法和条格的过渡,到明清形成了《律》《例》体制。〔6〕参见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658 页。台湾学者李如钧在《评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一文中,期待赵晶未来回应的问题是:令典在元代以后的衰微,以及律例法在明清的兴起,是否实因元代自身所致?而宋代对后世法律形式的影响,是否似学者所言如此之大?〔7〕参见李如钧:《评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 年第2 期。这说明元代法律形式及其法律体系,在律令法体系“嬗变”过程中作用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学者的论述有的在《至正条格》〔8〕2002 年,元代后期编纂的法律文献《至正条格》残本在韩国被意外发现。《至正条格》以条格命名,但其包含“条格”和“断例”两部分。其中,“断例”的篇目、条文及其形态是首次发现。发现之前,有的虽在《至正条格》发现之后,但对于其中的“断例”部分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因此,囿于史料,其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就元代的法律体系及其与律令法体系和格例法体系的关系做初步探讨。
一、格例法体系之提出
元朝法律体系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之处。2007 年,李玉年先生撰文指出,唐代的法律体系是律、令、格、式,宋代的法律体系是敕、律、令、格、式,而元代的法律体系至今不明。李玉年先生在对元代法律组成解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元代的法律体系,即:元代法律是由以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法和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条格组成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体系,即札撒、条格。又因条格具有综合性,在条格内形成了亚系,即条格(狭义) 、断例和制诏。〔9〕参见李玉年:《元代法律体系之构建——元代法律组成解析》,载《安徽史学》2007 年第3 期。
李氏这种法律体系的构建,的确有利于掌握元代法律的全貌及其特征,也有利于掌握各种法律间的关系。但可商榷之处有二。一是与札撒并列的“条格”,李玉年认为是广义的“条格”。“条格的发展路径是由条画到狭义条格再到广义条格,外延不断增大,最后指所有元代立法。”李氏认为,最迟到修纂《至正条格》时狭义条格变成了广义的条格。那么,用元朝后期广义的条格来分析整个元代的法律体系则有不妥。二是札撒是以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法。李氏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主要是其“决定了国家政治面貌,是元代地位最高之法”。这是从法律效力等级而言的。条格在效力上低于札撒,是对札撒的补充。这样,从法律效力等级的角度研究元代法律体系,〔10〕胡兴东亦认为,这可能混淆了法律形式与法律效力位阶两种分类体系。参见胡兴东:《元代法律史研究几个重要问题评析(2000—2011)》,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4 期。与目前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是不一致的。我们可否将元代法律体系的研究置于同一语境中研究。
其实,研究整个元代的法律体系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无法对其准确概括。因为元朝历史通常分为蒙古帝国、元朝与北元等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法律相差甚远,蒙古帝国时主要是其习惯法。即使严格意义的元朝时期,〔11〕元世祖忽必烈定都汉地,将国号改为大元后,直到1368 年元惠宗出亡为止,共九十八年。其法律渊源也是大有不同,开始沿用金《泰和律》,直至英宗至治三年才颁行《大元通制》。〔12〕关于元初的法制状况,参见姚大力:《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载氏著:《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79-321 页。而法律体系是指一定时期内的法律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所以,研究元代的法律体系可研究元朝的主要时期,即严格意义上的元朝时期。
学界在研究元之前朝代的法律时,通常用“律令法”“律令制”等词语。〔13〕如吕志兴《宋令的变化与律令法体系的完备》,载《当代法学》2012 年第2期;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张建国将律令法体系定义为:“以律令为主体、包括众多的法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体系。”〔14〕参见张建国:《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5期。刘笃才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提出了“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的观点,并比照律令法体系的定义方式,将“律例法体系”定义为:“以律、例为主体而包括众多法形式的法律体系。”〔15〕刘笃才:《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载《法学研究》2012 第6 期。作为中国古代从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向律例为主的法律体系过渡时期的元朝,其法律体系是怎样的呢?笔者以为,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研究,可将元代的法律体系称为“格例法体系”。〔16〕需要说明的是,王敬松先生着眼于元代法典的体例,指出了“格例体”。其认为,从法律编制体系上说,《至元新格》《大元通制》《至正条格》三部法律,都属于格例体的法律。(王敬松:《论元代法律中没有“十恶”体系》,载《民族研究》2013 年第5 期。)笔者则是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提出元代的“格例法体系”。
“格例”一词,最初出现于唐、五代时期,延续至宋元。唐、五代时期,格例有三方面的用法:一是一般性的法律规定;〔17〕这方面的例子如:《通典》卷十一《食货一》载:“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唐大诏令集》卷二《中宗即位赦》云:“其应支兵,先取当土及侧近人,仍随地配割,分州定数,年满差替,各出本州,永为格例,不得踰越。”二是指在行政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用于官吏的选举和管理方面,大多数情形下,格例是为了保障“格”的实施而制定的,是政府部门根据格制定出来的一种区分等级次第的细则;〔18〕参见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84 页。三是在某些场合也是格和例的合称。〔19〕参见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84 页。对于第二个方面,李云龙提出质疑,认为“格例是由格发展而来的,其间经过了自发地依照格所确立的规则的过渡阶段,最终发展为有意识地制定以格例为名的,主要适用于官员的举选、迁转、管理和任用方面的规则体系”。〔20〕参见李云龙:《宋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
到了元代,格例大多数情形下是元代法律的总称。如《元史•英宗本纪》云:“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敕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21〕(明)宋濂:《元史》卷二八《英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629 页。此处“格例”是断例、条格、诏敕、令类的总称。〔22〕有学者认为,《元史》称“格例”,是因为《大元通制》虽分为四部分,但主体是条格、断例。参见王敬松《论元代法律中没有“十恶”体系》,载《民族研究》2013 年第5 期。《元史•武宗本纪二》载,尚书省臣言:“国家地广民众,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后不一,执法之吏轻重任意,请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显然,此处“格例”也是法律的总称,主要包括“所行政令”。元代类书《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23〕关于此类书详细介绍,参见仝建平:《〈翰墨全书〉辑录的元史资料价值述论》,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 期。卷二《丧礼门》记载了元代的“丧葬格例”,总名称为“国朝颁降丧葬格例纲目”,下面有11 条内容。这11 条均可在《元典章》中找到相应史料。从在《元典章》的位置来看,1 条出自卷十《吏部•职制一•赴任》,8 条出自卷三十《礼部•礼制三》,2 条出自卷五十《刑部•诸盗二》。出自《吏部》和《礼部》的资料,都是没规定处罚的,只是“禁治”,但出自《刑部》的资料,是规定定罪量刑的。这样看来,《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此处的“格例”也是法律的总称。换言之,将关于丧葬的法律规定汇集,置于此处。元人徐元瑞在《吏学指南》中言“吏员三尚”,即尚廉、尚勤、尚能。“尚能”:“谓练习格例,晓畅行移,是非曲直,先以意决,然后取裁,凡所处画,悉令合宜,文义略通,字无不识,写染端正,算术精明,举止安详,语言辩利,无过可寻,有委可办。”〔24〕(元)徐元瑞:《吏学指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135 页。此处尚能的具体要求之一“练习格例”,也就是“练习法律”之意。诸多史料可证,“格例”是元代法律的总称。
除了“格例”可作为元代法律总称外,“条格”有时也指元代所有法律。学者认为,条格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如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认为:“当时条格一词可能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条格是针对断例而言,是严格的涵义;广义则为条格、断例的统称,虽不确切,但是广为流用的通俗用法。《事林广记》所反映的就是这种通俗日用的世界。《至正条格》虽包括断例,仍称为《至正条格》也当为广义、通俗的用法。”〔25〕参见[韩]金文京:《有关庆州发现元刊本至正条格的若干问题》,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韩国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477 页。黄时鉴、方龄贵以及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宫崎市定等认为狭义条格是以令法规为主,并包含其他若干格、式法规。广义条格则由狭义条格、断例、制诏三部分组成。〔26〕参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2 期;(日)安部健夫:《〈大元通制〉 解说——兼介绍新刊本〈通制条格〉》,载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3 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日)宫崎市定:《宋元时期的法制与审判机构——〈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载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3 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学者对元代“条格”何时有了广义,则意见不一。李玉年认为,条格的发展路径是由条画到狭义条格再到广义条格,最迟到了修纂《至正条格》时,由狭义条格转变为广义条格。〔27〕参见李玉年:《元代法律体系之构建》,载《安徽史学》2007 年第3 期。修纂《至正条格》时,“条格”是元代法律的总称,应无疑。《至正条格序》记载,(后)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书省臣言:《大元通制》为书,缵集于延祐之乙卯,颁行于至治之癸未,距今二十余年。朝廷续降诏条,法司续议格例,岁月就久,简牍滋繁。因革靡常,前后衡决,有司无所质正,往复稽留,奸吏舞文,台臣屡以为言,请择老成耆旧文学法理之臣,重新删定为宜。上乃敕中书专官典治其事,遴选枢府、宪台、大宗正、翰林集贤等官明章程习典故者,遍阅故府所藏新旧条格,杂议而圜听之,参酌比较,增损去存,务当其可。书成,为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里怯不花、平章政事铁穆尔达识、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相搠思监、参知政事朵儿职班等入奏,请赐其名曰《至正条格》。”上曰可。〔28〕(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至正条格序》,《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从中可看出,故府所藏新旧“条格”当包括编《至正条格》之前朝廷降诏条、法司所议格例。或许正是《至正条格》的取名,明人议起元代法律时,以“条格”称之。如《明史》云:“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巳。”〔2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2279 页。“惟元以一时行事为条格。”〔3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三八《周祯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3967 页。但是,根据史料,早些时候,“条格”也有广义。如大德十一年(1307 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尝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事,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制可。〔31〕(明)宋濂:《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492 页。此处“条格”应指世祖即位以来所行的“条格”“格例”等。
笔者以为广义上的“条格”,其“格”已与唐宋所谓的作为法律形式的“格”不同,此处是“法”的意思。〔32〕法律术语的具体含义,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这就决定了同一术语有多重含义。在分析其具体含义时,需要据其语境来考察。元代立国之初,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典。其同一术语往往语义不定,似此似彼,不易识判。其实,用“格”称“法”在汉代就已存在。如汉《律》中有“废格”之罪,“格”便是“法”之意。又如《礼记•缁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郑注:“格,旧法也。”魏晋时期,格和法常常互用并举,如《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减之格,用为世减之法。”就元代来说,广义的“条格”也就是“条法”之意,是元代法律的总称。由此可联系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是把一百二十二卷《庆元敕令格式》和十二卷《申明》,随事分门别类,重新组合而成,其组成部分敕、令、格、式都是“法”,故称“条法”。《至正条格》编纂的技术也是“类集”,即将多条条文按其类别编纂,将“条格”理解为“条法”,是对各类法规的泛称,也未尝不可。
“条格”和“格例”二词均有元代法律总称之意,但前者有广狭二义,用之来概括元代法律体系,区分性不强,故笔者选取“格例”一词。〔33〕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律令法体系”命名的原因,是律和令主要的两种法律形式,“律例法体系”命名的原因是,律和例是明清的两种主要法律形式,元代“条格”和“断例”是两种主要法律形式。
二、格例法体系之构成
在元代“格例法体系”中,其法律形式包括哪些呢?有学者将元初大量存在的“条画”纳入研究的视野,认为“条画”也是元代的法律形式之一。如吴海航认为,条画与断例是元代法律体系内不同的法律形式;〔34〕参见吴海航:《中国传统法制的嬗递——元代条画与断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 页。魏晓欣认为,条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它每一次出现都和“圣旨”“诸王共议”“尚书省奏准”“中书省奏准”等联系在一起,与一般的旨奏条文不同。〔35〕参见魏晓欣:《蒙元〈条画五章〉考论》,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2 期。此处对元代法律形式的不同理解,是由于对“条画”的含义、“条画”与“条格”的关系以及“条画”与“断例”的关系理解不同。
“条画”一词,在唐代已经出现。唐代李翱《兵部侍郎赠工部尚书武公墓志》:“我将死,凡家事细大,皆有条画在文字矣。”〔36〕(唐)李翱:《李文公集》卷十五《墓志六首》,《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此处“条画”含有“规定”“条规”之意。《辞源》 解释“条画”为“分条规划”之意。但如果将“条画”分开来看,“条”可指“条文”或“条制”,“画”则是“画一”之意。
“画一”与法律有关的记载与汉萧何有关,《汉书》载“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此后,“画一”常常用来指法律的作用。如《南齐书》“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之语。
有元一代,“条画”最早出现于成吉思汗颁行的《条画五章》。《元史•郭宝玉传》:“木华黎军忽至,败其兵三十余万。思忠等走。宝玉举军降。木华黎引见太祖,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国之初,宜颁新令。’帝从之。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四顷、人三丁者签一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与军户同。民匠限地一顷。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行禁止之类,皆宝玉所陈也。”
此处的“条画”是名词性的用法,这五章的内容,《元史》仅是举例言之,而且从其文字风格上来说,是概述《条画五章》的内容,故其本来是诏书的形式还是法条的形式不能做出判断。虽然这是“新令”,但此处“令”并非唐宋时期的法律形式角度上所言的“令”,应理解为法律的总称。但颁布条画目的是“画一”,应是没有疑义的。此时元代并未统一,所以不能以律、令形式出现,更不可能制定替代前朝的律、令,只能采用过渡性的、权宜性法律。《条画五章》是朝代更替之间的产物,满足成吉思汗保证攻取中原的制度需要。这是成吉思汗一代颁布有系统的法令条画唯一明文记载。这一次的条画颁布是蒙古势力南下,与汉文化接触后,蒙元法律汉化的起点。〔37〕参见翁独健:《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载彭卫等编:《中国古代史卷(中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548 页。
吴海航高度评价了《条画五章》,其“在元代条画立法史上开启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使得“条画”类特别立法与蒙元时代相始终,“成为元代后世特别立法的仿效标准”。〔38〕吴海航:《中国传统法制的嬗递——元代条画与断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版,第5 页。确实,在《元典章》《通制条格》《至正条格》 等元代文献中,“条画”一词频频出现。如2002 年发现的元代后期编纂的法典《至正条格》(残本)直接出现19 次,其中“条格”篇9 次,“断例”篇10 次。可以推测,完整的《至正条格》中出现的次数肯定更多。另外,含“圣旨”“圣旨内一款”“圣旨节该”“奉圣旨”“诏书内一款”等用语的,也是属于条画。
“条画”既出现在“条格”中,也出现于“断例”中,这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条画”与“条格”“断例”并列。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的角度不同,关系则不一样。我们可从立法的角度和法典编纂的角度理解。
(一)立法的角度
元人如何理解,我们可从元人沈仲纬对“条画”的理解窥其一二。宋太祖建隆四年(963 年)颁行《宋刑统》,宋代律学博士傅霖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便将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刑统赋》。
元人沈仲纬作《刑统赋疏》,“取傅氏赋文而为之疏,引据详析,疏后有直解,概括易晓。解后有通例,则取当时罪案,断例以为佐验。意主戒儆,非泛作刑书也”。〔39〕《刑统赋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载《枕碧楼丛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所整理标点,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9 页。杨维桢作序,言沈氏“以本朝律款会而通之,辩取其要,无不中隙”。〔40〕《刑统赋疏》“沈氏《刑统赋》序”,载《枕碧楼丛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所整理标点,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9 页。沈仲纬在疏解“制不必备也,立例以为总”时,云:“制者,诏旨条画之文;例者,为格为例之事。”〔41〕《刑统赋疏》,载《枕碧楼丛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所整理标点,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8 页。显然,沈氏用元朝的“诏旨条画”“格”“例”来解释宋代的“制”和“例”。“制”,是指天子的命令,在元代则用“诏旨”来称谓。“诏”即“诏书”,“旨”即“圣旨”。
在元代,诏书和圣旨是有区别的。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云:“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42〕(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帝制》,《四部最刊》影印元至正刊本。可以看出,诏书和圣旨的区别在于,圣旨以蒙古文记录皇帝的命令,诏书则由“史臣”用汉文代言。就其内容而言,圣旨多系因特定目的而颁与某一特定机构或人物,诏书内容所涉则多为较具普遍性的国家政策或重要事件。〔43〕关于诏书和圣旨详细论述,参见张帆:《元代诏敕制度研究》,载《国学研究》(第10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条画则是附在诏书或圣旨后的个别条款。可见,“条画”一语,是与皇帝命令紧密相关的。日本学者植松正将元代条画分为四大类,即诏书、诏敕、设立官府的圣旨条画、特定部门的圣旨条画,〔44〕参见[日]植松正:《元代条画考》,《日本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1-46,1979 年。也是以条画是皇帝的命令为基础分类的。
元代“条画”与“格”“例”的关系,同样可借助宋代“制”和“例”的关系理解。沈仲纬言:“制者,诏旨条画之文;例者,为格为例之事。盖律有例条有制,不知例无以见法之所同,不知制无以见法之所异”。“律有条例有制,不备细,止该大节,俱在《名例》卷内,以为总要,自有各断例生于诸条,以总其事。故制不必备,止立例而已。”〔45〕《刑统赋疏》,载《枕碧楼丛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所整理标点,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8 页。在沈仲纬看来,元代诏旨条画,相当于宋的“制”,是“止该大节”,元代的“为例为格之事”则相当于宋代的“立例”,但“为例为格”时,要以“诏旨条画”为总要。“为格”的例子,如《至正条格•条格》卷第二十七《赋役•孝子节妇免役》“至元十年二月”条:〔46〕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韩国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86 页。
至元十年二月,御史台呈:“钦奉圣旨内一款:‘孤老幼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仰本路官司验实,官为养济,应收养而不收养,或不如法者,委监察纠察。’钦此。体察得,大都路左警巡院咸宁坊魏阿张,年一十六岁,适魏明子蔓。其夫荒纵,不事家业,因欠债银,逃窜不知所往。阿张父代还所欠,本妇与姑同居,佣计孝养,甘旨不阙。十余年后,其夫还家,因病身故,并无产业,有子幼弱,其姑九十五岁,眼昏且病,不能行止,依旧孝养。遇有事出,置姑扃户,将子寄于邻居学舍。参详魏阿张孝奉老姑,守节不嫁,钦依圣旨事意,官为养济。仍令免除差役,更加旌表,以〈砺〉[励]风俗。”都省准拟。
根据圣旨,官府养济“孤老幼疾贫穷不能自存者”,御史台履行“纠察”之职,在实践中发现魏阿张孝奉老姑,守节不嫁,便提出立格建议,除了官为养济外,对孝子免除差役,更加旌表,得到中书省批准。
“为例”的例子。如《至正条格•断例》卷第四《职制•亲故营进》“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条:〔47〕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韩国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202 页。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御史台呈:“照得,圣旨条画内一款:‘诸求仕诉讼人,若于应管公事官员私第谒托者,委监察纠察。’又一款:‘诸官府如书呈往来者,委监察纠察。’钦此。近年以来,内外宪台按察司官吏,将亲戚并营求勾当人,于各路总管府及诸衙门,嘱托安插,作酒税务课程等勾当。或转托他人,宛转分付。总管府等处官司,素畏风宪官吏,凡所嘱托,必须安排优便。其人恃赖按察司官吏,恣行非理,实今大弊。江南诸道,此弊尤多,若不惩治,益长贪浊。今后诸宪台提刑按察司官吏,若将亲戚及营求勾当人,于各路总管府诸衙门,嘱托安插,及转托他人,情弊亦〈司〉[同]。如有首告,或体访得知,取问是实,以故违圣旨论,闻奏断罢。”都省准呈。
此断例,是御史台根据两款圣旨条画,对宪台提刑按察司官吏“将亲戚及营求勾当人,于各路总管府诸衙门,嘱托安插,及转托他人”的行为做出具体处罚,然后呈送中书省。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制定法律时,“条画”是“格”“例”的总要。
(二)法典编纂的角度
元朝在其存续期间,制定了法令,编纂了法典。〔48〕详细的论述参见翁独健:《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载彭卫等编:《中国古代史卷(中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546-565 页;刘晓:《〈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法典的编纂》,载《文史哲》2012 年第1 期。但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其受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吸收了中原传统文化,因而其法令的制定及法典的编纂不同于唐宋。元代没有唐宋律令法体系下的律典和令典。一般认为,《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是元代颁布的两部法典。
《大元通制》 颁布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 年)二月。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其编撰的原则为“类集”。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纲有三:曰制诏,曰条格,曰断例。经纬乎格例之间,非外远职守所急,亦汇集之,名曰别类。”〔49〕(元)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载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三十六《序》,《四部最刊》影印元至正刊本。沈仲纬在《刑统赋疏》中疏解《刑统赋》“撮诸条之机要,触类周知”时云:“类,事类也。”并征引元代有关法律:“断例,即唐律十二篇名。名令〔50〕此处“名令”是“名例”之误。提出,狱官入条格,〔51〕学者对此文做了较多的研究,但尚未涉及“名例”提出的原因。笔者以为,这与《大元通制》的结构有关。《大元通制》包括制诏、条格、断例三部分。沈仲纬在疏解《刑统赋》中“制不必备也,立例以为总”时认为,元代的诏书圣旨条画相当于宋的“制”,元代的“格”“例”相当于宋的“例”。此处宋“例”指的是《宋刑统》中“名例”律以下的篇章。沈仲纬在疏解“窃原著而有定者,律之文,变而不穷者,法之意”时,“举律内七杀之事明之”。其云:“杀人者斩,此是一定之律文,若执守其文,但杀人者皆处斩刑,则又不可。盖杀人之情,轻重不同,故例有七色,是名七杀。”接着引用《贼盗律》《斗讼律》《贼盗律》《斗讼律》《斗讼律》《斗讼律》《斗讼律》分别解释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显然“例有七色”中的“例”指的是《名例律》以下的篇章。《名例律》是以下各篇的总要。元人认为,既然制诏是制定条格、断例时之总,那么,在制诏存于法典时,与其相同作用的在古律中称为“名例”的部分,就无存在必要。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大元通制》中“条格”部分,其“类”,根据沈仲纬的征引为: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防、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关市、捕亡、赏令、医药、田令、赋役、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52〕《刑统赋疏》,载《枕碧楼丛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标点,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版,第172 页。
吴澄《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云:“制诏、条格,犹昔之敕令格式也。断例之目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廐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一循古律篇题之次第而类辑,古律之必当从,虽欲违之而莫能违也。”〔53〕(元)吴澄:《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载《吴文正集》卷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吴澄此段话涉及《大元通制》的三个组成部分。断例的篇目容易理解,制诏、条格两部分的性质,吴澄用“昔之敕令格式也”来类比。关于此句的含义,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认为,“犹昔之敕”之语,“其所指虽然颇显含混,但它应理解为《制诏》《条格》具有‘敕’的性质”。〔54〕参见(日)安部健夫:《〈大元通制〉 解说——兼介绍新刊本〈通制条格〉》,载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3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笔者以为,此种理解可以商榷。应理解为,制诏相当于敕,条格相当于令格式,理由有三。其一,按安部健夫的思路,《制诏》《条格》具有“敕”的性质,那么,《制诏》《条格》也具有令、格、式的性质,显然这是讲不通的。其二,现存《通制条格》和《至正条格》中的“条格”,除了与皇帝诏书有关的“钦奉诏书内一款”“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等条文外,还有与皇帝无关的省部拟定的条款,这些条文则不具备“敕”的性质。其三,《大元通制》 和《至正条格》 中“制诏”的作用。《元史•英宗本纪》 云:“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敕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55〕(明)宋濂:《元史》卷二八《英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629 页。此处记载,《大元通制》成书之后,颁行天下,从字面意思来看,应包括其中的“诏敕九十四”。元代后期在《大元通制》基础上编纂了《至正条格》。《元史》对《至正条格》的编纂情况记载较为简单,但欧阳玄《至正条格序》对《至正条格》编纂的记载较为详细。就笔者所见,研究者大多注意了该序的前半部分。但对书名定为《至正条格》后群臣复议的内容尚未关注。群臣议曰:“制诏,国之典常,尊而阁之,礼也……条格、断例,有司奉行之事也……请以制诏三本,一置宣文阁,以备圣览,一留中书,藏国史院,条格、断例,申命锓梓示万方。”结果,“上是其议”。〔56〕(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至正条格序》,《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可以看出,《至正条格》中的“制诏”部分,并未颁行,主要原因,一是制诏是“国之典常”,在国家管理中,“条格”和“断例”就已足够;二是,上文所论述的制诏是制定“条格”“断例”之总;三是,下文所论,制定编纂《至正条格》时,将“制诏”中内容根据其有无罚则分别编入“条格”或“断例”之中。
将“制诏、条格,犹昔之敕令格式也”,理解为“制诏相当于敕,条格相当于令格式”,就与唐代的法律形式有了很好的对应:元代的“制诏”对应于唐代的“敕”;元代的“条格”对应于唐代的“令、格、式”;元代的“断例”对应于唐代的“律”。“令、格、式”在功能上虽不一致,但其在有无惩罚性内容上则是一致的,即无惩罚性的规定。我们知道唐宋律典从性质上而言是刑事法,带有惩罚性的规定。元代编纂《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时,均采取类集的方法,将诏书、圣旨中可以“永为法则”〔57〕此处,笔者借助唐格的编修方法来理解元“条格”的编写。《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其曹之常务,但留本司者,别为留司格一卷,盖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这是把临时性的“制敕”编入“格”中,是指具有永久效力。元代编纂法典时也是如此。的条画以有无惩罚性内容为标准分别归入条格或断例的“类”中。〔58〕有学者认为,《至正条格》中,不管是“条格”还是“断例”的法规都是通过具体判例组成的。(参见胡兴东:《中国古代判例法模式研究——以元清两朝为中心》,载《北方法学》2010 年第1 期。)这种说法似可商榷,除了具体判例之外,还有条画和中书省等直接制定的条文。
第一,将同一诏书、圣旨中的条画按其性质功能归入法典中的不同“条格”篇或“断例”篇。
如至大四年(1311 年)三月十八日《仁宗皇帝登宝位诏》后所附条画,植松正先生搜集整理为27条,这27 条在《至正条格》残卷中有6 条,其中“条格”部分4 条,“断例”部分2 条。〔59〕刘晓:《〈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载《文史哲》2012 年第1 期。归入“条格”部分的4 条如下。
其一,《至正条格•条格》卷第二十六《田令•禁扰农民》“至大四年三月”条:至大四年三月,诏书内一款,节该:“农桑,衣食之本。仰提调官司申明累降条画,谆切劝课,务要田畴开辟,桑果增盛,乃为实效。诸官豪势要经过军马,及昔宝赤、探马赤喂养马驼人等,索取饮食草料,纵放头疋,食践田禾桑果者,所在官司断罪陪偿。仍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常切纠察,考其殿最,以凭黜陟。”
其二,《至正条格•条格》卷第二十七《赋役•均当杂泛差役》“至大四年三月”条:至大四年三月,诏书内一款:“民间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除边远军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备首思站户外,其余各验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诸投下不以是何户计,与民一体均当。应有执把除差圣旨、懿旨、令旨,所在官司,就便拘收。”
其三,《至正条格•条格》卷第二十八《关市•禁中宝货》“至大四年三月”条:至大〔60〕韩国发现《至正条格》本,误“至正”为“至元”,今改之。四年三月,诏书内一款:“诸人中宝,蠹耗国财。比者,宝合丁、乞儿八答私买所盗内府宝带,转入中官,既已伏诛。今后诸人毋得似前中献,其扎蛮等所受管领中宝圣旨,亦仰追收。”
其四,《至正条格•条格》卷第二十八《关市•和雇和买》“至大四年三月”条:至大四年三月,诏书内一款:“诸王、驸马经过州郡,从行人员多有非理需索,官吏夤缘为奸,用一鸠百,重困吾民。自今各体朝廷节用爱民之意,一切惩约,毋蹈前非。其和雇和买,验有物之家,随即给价。克减欺落者,从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
归入“断例”部分的2 条如下。
其一,《至正条格•断例》卷第六《职制•枉法赃满追夺》“至大四年三月”条:至大四年三月,诏书内一款,节该:“内外百司,各有攸职。其清慎公勤,政迹昭著,五事备具者,从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察举,优加迁擢。废公营私,贪污败事,陈告得实,依条断罪。枉法赃满者,应授宣、敕,并行追夺。吏人犯赃,终身不叙。诬告者,抵罪反坐。”
其二,《至正条格•断例》 卷第七《户婚•冒献地土》“至大四年三月”条:至大四年三月,诏书内一款:“国家租赋有常,侥幸献地之人,所当惩戒。其刘亦马罕、小云失不花等冒献河南地土,已令各还元主,刘亦马罕长流海南。今后诸陈献地土并山场、窑冶之人,并行治罪。”
此种方式,首先将同一份诏书中的条画根据其性质拆分为条格和断例,然后分别将归入条格的条画和归入断例的条画再根据其所涉事项拆分,归入已有的“篇目”中,或在不便于归于某一“目”时,另立新目。
第二,将不同诏书、圣旨内条画按其性质功能归入法典中的同一“条格”篇或“断例”篇。如《至正条格•断例》卷第十二《厩库》“茶课”条:〔61〕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韩国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300 页。
中书省钦奉圣旨,节该:恢办茶课公事,省部印造到茶引据。〔62〕韩国发现《至正条格》(校注本),“据”从下。根据上下文,点断时“据”应从上。“引”指“茶引”,“据”指“公据”。客人赴官送纳正课,买到兴贩茶货引,壹道重玖拾斤。年月日料号,并依坐去条画事理施行。
客旅兴贩茶货,纳讫正课,出给公据。前往所指山场,装发茶货出山,将元据赴茶司缴纳,倒给省部茶引,方许赍引随茶,诸处验引发卖毕,限三日以里,将引于所在官司缴纳,实时批抹。违限匿而不批纳者,杖陆拾。因而转用,或改抹字号,或增添夹带斤重,及引不随茶者,并同私茶法科断。仍各处官司,将客旅节次纳到引目,每月一次,解赴合属上司缴纳。
但犯私茶者,决杖柒拾,将所犯茶货,壹半没官,壹半付告人充赏,应捕人亦同。如茶园磨户犯者,及运茶船主知情夹带装载无引私茶,一体科断。本处官司,禁治不严,致有私茶生发去处,仰将本处当该官吏勾断。
应客旅装发茶货车船,各处官司并不得拖拽。若必合和雇,直抵发卖地面下卸讫,方许和雇。如违,陈告得实,决杖陆拾。因而取受故纵者,与同罪。如有邀当客旅、拘买取利者,杖陆拾。茶付本主,买价没官。
伪造茶引者,处死。首告得实者,犯人家产,并付告人充赏。
客贩茶货,若经由关防批验官司去处,私过不批引目者,决杖柒拾。随处官司,常切禁治,不得抑遏客旅,干要牙钱。违者,就便追断。
客旅所贩茶货,江淮迤南依旧免税。江淮迤北发卖去处,依例收税。
此条所载6 款茶引条画,并无颁行的具体时间,但检阅《元典章》〔63〕《元典章》,陈高华等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相关史料,可以确定其颁行的年份,现列表如下:
就可确定的五款来看,这些条画颁行时间不一,但在编纂《至正条格》时都纳入“断例”篇“茶课”条之中。当然,在编入法典中,对以往条画也有所变动,以第6 款为例试做说明:至元三十年(1293 年)与第6 款相关的茶引文字为:“客旅兴贩茶货,随处发卖,依例投税。”〔64〕《元典章》,陈高华等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811 页。依此规定,江南各路府州县商税局,也可收茶货之税。大德四年(1300 年),榷茶提举司认为这“当拦客旅,搅扰涩滞茶法,不能通行”,江西榷茶都转运司提议将“茶货免税”,申覆江西等处行省,移咨都省定夺,结果“都省奏准”。户部便“改铸板面”,“除去至元三十年(1293 年)茶引内客旅兴贩茶货,随处发卖,依例投税一款”,添上“客旅所贩茶货,江淮迤南依旧免税。江淮迤北发卖去处,依例收税一款”。〔65〕《元典章》,陈高华等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811 页。
从以上论述可知,无论是立法的角度还是法典编纂的角度,“条画”不能与“条格”和“断例”并列,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存于格例法体系之中。而“条格”和“断例”则是根据其有无罚则进行的归类,这是元代法典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欧阳玄曰:“条格、 断例,有司奉行之事也。”〔66〕(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至正条格序》,《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所以,“条格”和“断例”是元代“格例法”体系中的主要法律形式。〔67〕胡兴东认为,元代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格和例。例的名目繁多,在元朝达十九种之多。元朝例的基本作用是对法律的解释和补充。(参见胡兴东:《元代“例”考——以〈元典章〉为中心》,载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392-415 页。)胡兴东在其《宋元断例辑考》一书中更加详细地对各种例进行了考辨。(参见氏著:《宋元断例辑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126-143 页)。笔者以为,其一,元代的这十九种例之一的“断例”在《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中,单独列出,作为法典的一部分,是有罚则的条文,相当于唐宋的“律”;其二,《至正条格•断例》篇目有“多支分例”“增起站车分例”“诸奸通例”等直接以“例”为名的条文;《通制条格》中有“户例”“公粮则例”“衣装则例”“大小口例”“鹰食分例”“司农事例”“典卖田产事例”“织造料例”等直接以“例”为名的条文,这说明,元人在编纂法典时,已经按照“例”的性质,把“例”归入“条格”或“断例”之中。
元代的格例法体系,除了条格和断例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法律形式?正如我们研究律令法体系一样,“律”和“令”只是律令法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两种法律形式,汉代除了“律”“令”外,还有“科”“比”等法律形式;唐代除了“律”“令”外,还有“格”“式”等法律形式。吴澄《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中以为,唐代的“敕者,时君所裁处;令者,官府之所流布;格式者,各代之所造设也”。〔68〕(元)吴澄:《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载《吴文正集》卷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前文已经论及元代的条格对应于唐代的“令”“格”和“式”,也就是说元代“条格”这种法律形式将唐的“令”“格”“式”这三种法律形式吸纳,以“条格”为其名称。
在《通制条格》和《至正条格》中的“条格”文本中,大部分是类似于唐的“令”文,〔69〕此“类似”并非从语言角度,而是从功能角度而言的。“条格”中的这些文本,与唐令的功能是一致的。当然,令的功能,学界颇为纷杂,但安部健夫认为,“令”大致上是“为了预防触犯律而作的规定,即对于百姓可能遇到的一般的公事或私事,不论尊卑贵贱,规定其‘为当’或‘听为’‘不当为’或‘不听为’的法规”,这是不会大有出入的。(参见[日]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兼介绍新刊本〈通制条格〉》,载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 3 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还有一部分就是“各代之造设”的法规,也就是吴澄所谓具有“格式”性质的法规。如《通制条格》中有部分内容源于《至元新格》。〔70〕具体来说,《通制条格》中源于《至元新格》的条文为:卷六《选举•选格》方校本141(指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 年版,第141 条。下类推);卷十四《仓库•关防》方校本280;卷十六《田令•理民》方校本318;卷十七《赋役•科差》方校本370;卷十九《捕亡•防盗》方校本420;卷三十《营缮•造作》方校本642。《新唐书•刑法志》 在言唐的“格”“式”时说,“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71〕(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407 页。元代群臣在议定《至正条格》时,认为“条格、断例,有司奉行之事也”。〔72〕(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至正条格序》,《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
比较唐宋对有司所行之事的言论,唐代以《格》或《式》来总之,元代以条格、断例来言之,这也可说明,唐代由《格》《式》所规范的有司常行之事,在元代是在条格或断例之中规范的。如元人王与撰《无冤录》中有“检会通制结案式”之语。〔73〕(元)王与:《无冤录》卷上《检验法物银钗真伪》,朝鲜钞本。这似可说明,元代的条格吸纳了唐的格和式。〔74〕其实,南宋时期,有些“格”编入令典之中,如《庆元条法事类》卷十一《给假》门中载有《假宁格》的内容。所以,与唐宋比较来说,元代的格例法体系主要包括“条格”和“断例”两种法律形式。
然而,《大元通制》编纂之后,皇帝依然因时因事而发布诏令,诏书之后也附有条画,此时的条画当然有法律效力,但这些条画是“临时性”的政令。中书省等上级官府根据对皇帝圣旨的理解或因下级官府请示而制定“条格”或“断例”,这些“条格”和“断例”也有临时的法律效力。所以,元代在编纂《大元通制》之后,其法律体系是有由条格、断例和补充修正其规定的临时性的圣旨条画和法司议定格例所构成的。这些临时性的条画、条格和断例,既补充和修正了《大元通制》而解决新的问题,又为以后《至正条格》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在《至正条格》编纂时,它们被全面清理,或者被纳入,或因与已有条画或格例扞格而被拒,或与原有条画或格例重复而被取舍。被纳入者,编入了法典,具有了“永久”效力,被拒或被舍者,便失去了效力,不能在处理类似事件时被援引。
法律体系所包括的法律形式之间,在各自作用的领域或层次上,总会保持一定的关系。法律体系要求其构成部分互相配合,相互连接,成为一体。律令法体系下,陈顾远先生认为,“令之所在,实以政事法为主”“律之以刑事法为主,礼之以民事法为主”。〔75〕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载《陈顾远法律史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433 页。这是从中国式的部门法角度来解读的。
元代格例法体系中的“条格”和“断例”也应如此。但研读《至正条格》,其配合程度并不高。原因在于三点。其一,元代是“因时立法”“因事立法”。其二,表面上废弃了金泰和律令。我们知道,金代法律深受中原传统法律之影响。中原法律至唐宋时期,律令法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律、令、格、式或敕、令、格、式已经成为一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三,元代没有唐宋时期居于常规法地位的“律”。常法具有基本法的地位,〔76〕参见陈灵海:《国家图书馆周字51 号文书辨疑与唐格复原》,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1 期。不可动摇。唐代突破“常法”的途径是把可以获得君臣普遍认可的“敕”编入唐格,宋代则是“编敕”。元代编于法典之中的“断例”虽然大体相当于“律”,但其地位并不稳定,再次编修法典时,原先的“断例”并非不能修改、删除。
三、格例法体系与中华法系
元朝虽是以蒙古族为主建立的王朝,其法律形式同唐宋也不一致,但元人吴澄在论《大元通制》中“断例”时云:“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可见,元朝法制仍属于中华法系的一部分。杨一凡先生认为,元朝是中国古代从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过渡的时期。〔77〕参见杨一凡:《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23 页。但如何过渡,并未详细论述。笔者以为,其过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律典和令典的分立过渡到律例合编
唐宋时期的律、令分离,形成了各自的律典和令典。北宋天圣七年(1029 年)的《天圣令》已经将具有罚则的“敕”与令合编,只不过是处于附属的地位。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 年)诏曰: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始,命官删定《编敕》,议者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有司又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其罪名轻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78〕《资治通鉴后编》卷三八《宋纪》,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高明士认为有十八卷和一卷两种。〔79〕详细的辨析参见高明士:《“天圣令学”与唐宋变革》,载《汉学研究》第31 卷第1 期。《附令敕》 十八卷,夷简等撰,《官品令》之外,案编敕(敕文),录制度,依《令》分门,附逐卷之末;又案编敕(敕文),录罪名轻简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为《附令敕》一卷(注曰:又有《续附令敕》一卷,庆历中编)。〔80〕参见高明士:《“天圣令学”与唐宋变革》,载《汉学研究》第31 卷第1 期。《附令敕》十八卷其性质,当属于行政法。《附令敕》一卷,则是取自真宗咸平以来到仁宗天圣年间的《编敕》,其中罪名轻简者共有五百余条,具有刑法性质,全部附在《天圣令》最后。
元代法典的编纂将相当于律的“断例”和相当于令的“条格”合编。《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则将相当于“令”的条格和相当于“律”的断例等而视之,并列为两篇。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指出,从法典的本质上看,《大元通制》是“律令的法典”。〔81〕参见(日) 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兼介绍新刊本〈通制条格〉》,载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 3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这为明清律例合编提供了依据。
(二)“断例”这种法律形式进入法典
断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宋代。宋代“从来律令敕式有该说不尽之事,有司无以处决,引例行之”。〔8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八月癸酉》。例是在刑部、大理寺等特定的机构内部使用的,公开性极低。御史中丞汤鹏举认为“例之所传,乃老奸宿赃,秘而藏之,用以附下罔上,欺或世俗,舞文弄法,贪饕货赂而已”。〔8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59 页。这说明了例的非公开性带来的弊端。
宋仁宗庆历年间,由于大理寺审理的疑难案件数量上升,“艰于检讨”,王子融建议“取轻重可为准者,类次为断例”。宋仁宗接受建言,诏“刑部、大理寺,以前后所断狱及定夺公事遍为例”。〔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〇《仁宗庆历三年》。这是宋代断例编纂的开始。熙宁年间,审刑院详议官贾世彦上奏,请求刑部“以熙宁以来得旨改例为断,或自定夺,或因此比附办定结断公案,堪为典刑者编为例”,〔8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刑部编订了断例。另外,大理寺也编订了断例,即《熙宁法寺断例》 十二卷。史料记载宋代的断例还有《元丰断例》六卷、《刑名断例》三卷、《断例》四卷、《刑房断例》、《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淳熙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名断例》等。〔86〕具体编订情形参见[日]川康村:《宋代断例考》,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编:《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45-358 页。川村康指出:“熙宁以前的断例,在刑部、大理寺、审刑院等各机关独立编纂;与此相对,元丰以后的断例,以各机关未编集的例和内部的例册作为资料,由中书刑房和编修敕令所等进行统一的编纂,反映了断例的管理已经统一化、集中化。”〔87〕[日]川康村:《宋代断例考》,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编:《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75 页。
宋代虽然编订了一定数量的断例,但其是作为不完善的法的补充而存在的,即“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但由于经常出现“用例破法”的情况,宋代不同时期对断例的态度不同,如政和七年下诏:“除刑部断例外,今后官司不得引例申请。”〔8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20 页。政和七年(1117 年)下诏:“除无正条引例外,不得引例破条,及不得引用元祐年例。”〔8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21 页。隆兴元年(1163 年)四月,下诏禁止引用例而要求朝廷指挥,诏云;“有司所行事件,并遵依祖宗条法,及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十二月十七日指挥,更不得引例及称疑似,取自朝廷指挥,如敢违戾,官司重作施行。”〔9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0 页。隆兴二年(1164 年),臣僚认为,法都是根据以往的制度而制定,大多符合人情,但例是“朝廷一时之予夺,官吏一时之私意”,“今日之弊,在于舍法用例”,要求“中外悉遵成法,毋得引例,如事理可行而无正条者,须自朝廷裁酌取旨施行”,皇帝“从之”。这说明此时否定了例的使用。〔9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59 页。乾道元年(1165 年),下诏明确禁止断例的使用,刑部大理寺 “见引用例册,令封锁架阁,更不引用”。〔9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0 页。淳熙元年(1174 年),下诏禁止六部引用例,但允许刑部用乾道所修刑名断例。
宋代对断例态度的不一,最终不能彻底否定断例的运用,一是由于断例的公开性较低和断例之间的不一致,导致了用例的不一,甚至“以例破法”,宋代臣僚“屡有建请,皆欲去例而守法”;二是因为法是固定不变的,但人的行为是无限的,“法有所不及,则例亦有不得废者”,法的不完备和欠缺,就产生了由判决例的应用来补充的必要性。
用例的弊端和断例的作用是共存的,解决的方法便是将断例归于“通行之法”。〔93〕刘笃才认为这种方法是“将处于法律体系之外的例吸收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参见氏著:《中国古代判例考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4 期。绍兴二年(1132年),臣僚建言,“凡有陈乞申请,傥于法诚有所不及,于例诚有所不可废者”,让敕令司“详酌审订,参照前后,委无抵牾,则着为定法,然后施行。如有不可,即与尽断,自后更不许引用”,这样一来,所施行的都是法而不是例,由吏用例产生的弊端便自然消灭,“举天下一之于通行之法”。〔9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68 页。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但这一工作是否完成,如何归于法,是以“敕”的形式发布,还是其他方式,从现有史料来看,无法确定。〔95〕梁松涛认为,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法则》卷八中有两则判例,是“以例入法”的表现,可为缺失的宋代“以例入法”的法典形态提供一个直接参照。参见氏著:《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法则〉卷八考释——兼论以例入法的西夏法典价值》,载《宋史研究论丛》(第 14 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但据史料,元代则将“断例”这种法律形式纳入法典之中,换言之,元代的断例归入了“通行之法”。笔者此处所言断例是指断罪事例。因为,元代的断例包括断案通例和断案事例。〔96〕关于元代断例的篇目和性质,在《至正条格》发现之前,日本学者安部健夫、中国学者黄时鉴、殷啸虎、方龄贵、曾代伟、刘晓等各抒己见。具体介绍参见刘晓:《〈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法典的编纂体系》,载《文史哲》2012 年第1 期。从《至正条格》来看,断罪通例,是以圣旨、诏书等形式展现的。如《至正条格•断例》卷第六《职制•枉法赃满追夺》“至大四年三月”条:〔97〕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韩国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219 页。
至大四年三月,诏书内一款,节该:“内外百司,各有攸职。其清慎公勤,政迹昭著,五事备具者,从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察举,优加迁擢。废公营私,贪污败事,陈告得实,依条断罪。枉法脏满者,应受宣、勑并行追夺,吏人犯赃,终身不叙。诬告者,抵罪反坐。”
将临时性的圣旨、诏书等编入法典,使之具有永久效力,这种方法同唐代时将敕令编入唐格和宋时的编敕入律是一样的。但与唐不同的是,唐代的律典和格典是分立的,元代没有独立的律典,其编入法典的圣旨条画就相当于唐宋的律。前文所言,宋代的断例,在元时只是断案事例。
元朝建立之初,法制混乱,在无法可守的情况下,“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各家收置一本,以为准绳”。〔98〕《元朝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明末刻本。这时,虽“断例作为一种法律编纂形式”,〔99〕参见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0 页。但只是民间的编写,直至《大元通制》的编纂,“断例”成为了其中一部分,至此,断例进入了具有稳定性的法典之内。
元代将断案事例纳入法典之中,在体例上,元人吴澄在《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中云:“断例之目,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一循古律篇题之次第而类辑,古律之必当从,虽欲违之而莫能违也。”这是讲《大元通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100〕(元)吴澄:《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载《吴文正集》卷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概而言之,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联系宋代断例的编修来审视,则可认为元代断例的体例直接源于宋代断例编修之体例。宋代的断例编纂始于仁宗庆历年间,将“所断狱及定夺公事”,“轻重可为准者,类次以为断例”。〔10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〇《仁宗庆历三年三月戊辰》。如何“类次”现无从考证。但绍兴三十年(1160 年)的《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其编目与律的编目相同,名例、卫禁(共二卷),职制、户婚、厩库、擅兴(共一卷),贼盗(三卷),斗讼(七卷),诈伪(一卷),杂例(一卷),捕亡(三卷),断狱(二卷),按十二门类编为二十卷,另外还有目录一卷,修书指挥一卷。〔10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59 页。
元代断案事例并不是简单地直接进入法典,而是经过一定的删减、修改,有的成为整齐划一的断案通例,如《元典章》卷四十八《刑部•诸赃三•回钱•知人欲告回钱》“延祐二年二月”条:〔103〕《元典章》,陈高华等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1599-1600 页。
延祐二年二月,江南行台准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札付:
来呈:“备监察御史呈:‘广宁路同知耶律哈剌孙,取受行使伪钞人石抹君宝至元钞六十贯,闾阳县主簿李荣,亦取受讫本人至元钞一十贯。闻知欲告,回付过钱人傅改驴收管。取讫招伏,罪经释免’”。送刑部议得:“诸官吏及有出身人等,因事受财,未发而自首及回付者,当许自新,准首原罪。其知人欲告,回主及有自首,盖因事不获已,即非悔过,合依已拟,减罪二等科断。罪既经断,似难复任。合准御史台所言,解见任,别行求仕。如蒙准呈,照会相应。”都省准拟,依上施行。
这一断案事例,在编入法典《至正条格•断例》卷第六《职制》时,以“知人欲告回主”为目名,其内容为:〔104〕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韩国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228 页。
延祐元年闰三月,刑部议得:“诸官吏及有出身人等,因事受财,未发而自首及回付者,当许自新,准首原罪。如已事发,出首回付,罪合全科。其知人欲告,回主及自首者,依例减罪二等科断,仍解见任。”都省准拟。
此条与《元典章》中的断案事例相比较,有四点不同。其一,名称不同。《元典章》中由于保留了人犯的具体行为是取受“至元钞”,故以“知人欲告回钱”为名;《至正条格》舍去具体人犯具体行为,只保留刑部议拟内容,且“官吏及有出身人”不仅受“钱”,还可受“财”,但所受“钱”或“财”都是原“主”的,故以“知人欲告回主”为名,更有概括性。其二,《元典章》保留此断案事例的公文原貌,《至正条格》取刑部议拟和中书省的批复。其三,《元典章》规定的是,“官吏及有出身人”因事受财,未发于官府,知人欲告,自首或回主的处罚,即“减二等科断”。《至正条格》除规定未发情形下的处罚,还加入了“如已事发,出首回付,罪合全科”的规定。其四,《至正条格》语言简洁。删除了《元典章》中的“盖因事不获已,即非悔过”,“罪既经断,似难复任”等解释性的语言。
“断例”作为例的一种,为明清的“例”进入法典提供了模式。明初“有律有令,而律之未赅者始有条例之名”,〔105〕(清)沈家本著,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221 页。明朝形成了律例并行的体制。明初,例的编纂还存在于法典之外,明代中期万历十三年(1585 年),《问刑条例》开始进入法典之中,具体做法是将《大明律》律文逐列于前,条例附于后,形成了“律为正文、例为辅助”的法典编纂模式。〔106〕参见陈涛、高在敏:《中国法典编纂的历史发展与进步》,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4 年第3 期。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私人刊刻的《大明律集解附例》收入条例405 条,与官方《大明律》不同的是,这些条例逐条附于相关律文之后,律文和例文融为一体。这种形式为清代所继承,顺治四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和后来的《大清律例》都是将条例分门别类附于相关律文之后,律例并称,例在法典中的法律地位进一步确立。
(三)条格和断例的形态决定了其续编的可能性
《大元通制》的编纂,是对以往的圣旨条画和百官有司制定的格例的全面清理,将它们以“类集”的方式分别纳入“条格”或“断例”之中,其结果是构筑了元代的格例法体系。从法律体系的结构来看,唐宋时期律典、令典分立,律正罪名,令定事制,二者相辅相成,皆为“常法”,其地位、权威不可动摇,稳定性极强。元代将相当于律的断例和相当于令的条格,编入同一法典,也是二者并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无论是条格还是断例,其条文的形态都不是律典或令典中的“法条”,圣旨条画和有司制定的格例保留了或部分保留了原有的形态,是随事随时产生的,这也决定了其概括性不强,为以后发布的圣旨条画或有司制定格例纳入法典提供了方便。〔107〕唐宋时,律典制定之后,不能更改。对于随事随时发布的敕令,如果使其有普遍约束力,便采取编敕的方法补充律。元代相当于律的断例,在来源上也是随时随事产生的条画或有司议定的断例,所以对于以后同样性质的条画就可直接编入法典。这可能也是元代除了《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法典外,没有其他形式的法律文本的原因。《大元通制》编纂之后,圣旨条画和法司议定的格例继续产生,它们如何归置,对于法律体系的维护,《大元通制》的作用,以及其中的“条格”和“断例”的权威,都是关键所在。或许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元后期的《至正条格》在《大元通制》基础上“续纂”而成。清代《大清律例》中律条不变,“条例”是“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到同治年间,例同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知:其一,研究元代的法律体系,与“律令法体系”“律例法体系”研究的角度一样,即从法律形式角度研究,有助于把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认识其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其二,元代的法律体系可以名之为“格例法体系”,其是以“条格”和“断例”为主体的,包括其他法律形式的密切联系的整体;其三,元朝法制虽然没有唐宋时期的“律”“令”“格”“式”之名,但其篇目和内容,取自唐宋法典,实际上仍属于中华法系的一部分。中华法系从“律令法体系”到“律例法体系”的转变中,元代“格例法体系”的过渡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律典和令典的分立过渡到律例合编;二是“断例”这种法律形式进入法典;三是断例的形态为其续编提供了可能。
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其法律制度与原来中原法律文化的关系是承袭还是断层,则有不同观点。明初认为,“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大抵多用夷法”。〔108〕《明朝典汇》卷二十《朝端大政》,明天启四年徐与参刻本。但元人吴澄在论及元代刑律时,则认为“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持不同观点的原因在于:明初主要关注元代法律的形式主要是条格、断例,这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而吴澄所关注的是法典的编纂体例和法典的内容。日本学者岛田正郎,注重蒙古族的习惯、判例法,认为元代法律属于“蒙古法系”。〔109〕详细介绍参见徐晓光:《“蒙古法系”质疑——兼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法律制度与中华法系的关系》,载《比较法研究》1989 年第21 辑。
其实,研究法律体系时,形式与内容并重,才能揭示其特点。元人吴澄既考察《大元通制》的形式又注重其内容,揭示了元代法律与中原传统法律的真实关系。然而,由于《大元通制》“断例”之篇已经佚失,从法典编纂体系之角度而言,“断例”的篇目和性质,学界争论不休,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正确认识元代法律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
2002 年,元代后期编纂的法律文献《至正条格》 残本在韩国被意外发现。其存有“断例”全部目录,以往有关断例篇目和断例性质的争论有了公断。残本《至正条格•断例》存有卫禁、职制、户婚、厩库和擅兴等五篇,共12 卷348 目408 条条文。这为我们从法典内容角度研究其与中华传统法律关系提供了新的史料,如《至正条格•断例》第八卷《户婚》中有“同姓为婚”“许婚而悔”“有妻更娶”“居丧嫁娶”等目都承受自《唐律》。所以,元代法律从编纂体例、内容而言,与中原传统法律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其是中华法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属于中华法系。这对了解我国多民族国家法律文化发展的全貌和中华法系形成的整体过程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