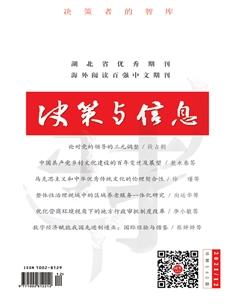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契合性
徐瑾 万宇君
[摘 要]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在四个方面具有契合之处。从道德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决定道德与传统文化“仓廪实而知礼节”有相通之处;从道德基础上看,唯物史观主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传统民本思想有相通之处;从道德原则上看,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集体主义原则与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取向有相通之处;从道德理想上看,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大同社会”理想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伦理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G122;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12-0012-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社会,正如蔡元培所说,“我国伦理学之范围,其广如此,则伦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矣”[1],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伦理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伦理领域的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四个方面的伦理契合点,这些相似相通之处能够成为两者结合的重要抓手。
一、道德本质:经济决定道德与“仓廪实而知礼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本质的认识具有科学的批判意蕴。在批判了资本家鼓吹的凌驾于社会历史发展之上的所谓永恒道德观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道德归根结底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当然,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并非被动消极,而是具有能动的积极意义。马克思这样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 524在马克思看来,精神活动是与现实物质活动密不可分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而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是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 99。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本质的重要论述,即没有任何超越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永恒不变的终极伦理规律或道德原则,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道德思想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特定经济基础的产物。
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似乎传统文化对于道德本质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反的,即传统文化认为道德是超越于社会的,如西汉董仲舒和宋朝二程、朱熹就主张“道德即天理”,强调“三纲五常”的永恒性。但是,当考察先秦时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开端,却发现这种僵化不变的道德观在先秦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强调天道永恒的老子也认为“上善若水”(《道德经·八章》)“反者道之动”(《道德经·四十章》),其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内涵。而且在先秦时代,强调经济基础对道德重要作用的思想甚多,这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本质的认识是有相似相通之处的。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就体现了鲜明的经济决定道德的质朴思想。主張“人性恶”的荀子也有这种看法。“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荀子认为恶的产生是因为人性是“生而好利”的,即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当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相互争夺时,恶就产生了。因为道德的产生前提是经济,所以对于传统社会的民众来说,要“富民”“教民”。《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卫国的人口很多,要想进一步实现社会安定和谐,就要先“富”而后“教”。显然,这“先后”之分体现了孔子的主张,即要先让民众(经济)富足,之后才能实现(道德)教化,这和“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意思是一致的。法家的韩非子也有类似主张,“势足以行法,俸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故民劳苦而轻官”(《韩非子·八经》),“俸足以给事”就蕴含着以经济利益促进公正办事的意思。“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韩非子·显学》)也有这个意思,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民众是难以奉公守法以效死命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的思想,在传统文化中是能够找到共通之处的。当然,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毕竟传统文化产生于专制社会,有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如“富民”“教民”的目的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实现人的解放,而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制的万古长存。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二、道德基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民惟邦本”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因此道德的基础只能在于人民。不同于其他思想家将道德基础付之于理性、情感或某种上帝启示的永恒法则,马克思主义主张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道德基础只能在于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自身,为人民服务是必然的道德要求。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4] 103。马克思甚至这样说:“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工人甚至创造了人。”[4] 72可以说,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经济基础构建)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5] 696。当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人民群众成员的杰出人物也有自己的贡献,因此恩格斯这样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5] 697。在这里,“总的合力”就是由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组成的合力。虽然杰出人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旧只是“合力”中的组成部分,创造历史的主体只能是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者的人民大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7]。
传统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其典型体现。类似叙述还有很多,如《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礼记·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荀子·哀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还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春秋榖梁传》则说“民者,君之本也”,孟子更有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都鲜明体现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和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观点是有相似性的。在传统封建社会中还有朴素的人民至上的观点,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有“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说苑·王者何贵》也有类似记载:“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对于传统社会来说,“天”被视为最高的主宰,所以君王自称“天子”。虽然统治者也重视民众的地位,但终归是将民众视为统治对象,所以君王自称“君父”,民众被称为“子民”“臣民”“顺民”。而“王者以民为天”赋予民众最高的地位,体现了朴素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民惟邦本”的升华,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有暗合之处。
综上所述,在道德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是有契合性的。因为道德基础在于人民,所以一切道德规范都应当以是否服务于人民,是否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物质文化需要)为依据,这也是判断一切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根本標准。当然,传统文化“民惟邦本”“以民为天”等思想还需要与时代结合,因为传统民本思想毕竟产生于君主专制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残余,所以我们应当去除其作为封建统治者“牧民之术”“愚民之策”的糟粕成分,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适应,并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
三、道德原则:集体主义与“家国天下”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正是因为人的社会性本质,所以马克思主张,在工人阶级政党及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集体主义是必需遵循的道德原则。马克思这样说:“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生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2] 18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从孤立的、具有“永恒理性”的个体出发来定义所谓理性的或自然的道德原则,马克思认为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加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获得解放的重要思想武器,“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9]。集体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将个人追求融入到集体追求之中,为了集体利益可以主动放弃个人利益,为了伟大事业可以无私奉献。这正如列宁所说:“工人阶级需要统一。但是,统一只能靠统一的组织来实现,而统一的组织的决议又是靠全体觉悟工人自觉自愿地去贯彻的。探讨问题,发表和倾听各种意见,了解多数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他们缺席时作出的决定中反映这种观点,认真负责地执行这项决定——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切明白人都把这些做法称为统一。而这样的统一对于工人阶级则是无限宝贵无限重要的。一盘散沙的工人一事无成,联合起来的工人无所不能。”[10]
传统文化中有关家国天下的整体主义取向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很相似,两者都强调不计较个人得失,而要把整体利益放在更高的位置上。《礼记·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最高追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开万世太平,只有将个人追求融入到家国天下的理想中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因此,和集体主义相似,传统文化一直强调整体的重要性,并从中生发出大公无私、爱民如子以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如“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左传·昭公四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在传统文化中,如果只注重私利而不顾公义就是小人,就会受到唾弃。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见利忘义,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可见,在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整体主义取向,提倡的是一种超越个人私利、为大众奉献、为国家分忧、为天下担责的大道公义精神。这种精神和集体主义原则是共通的,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主义原则主张集体至上,传统文化则主张整体至上。两者都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如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暴力革命、不怕牺牲,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勇于献身;传统文化强调为了国家大义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要“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取丹心照汗青”。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集体主义原则和传统文化主张家国天下的整体主义取向是相似相通的。当然传统社会强调整体主义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个性的压抑或禁锢,使得传统封建社会中人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而且在强调个性服从整体或君主统治的过程中,愚忠的色彩浓厚。这些缺陷都是我们应当正视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整体主义的历史合理性,那种为了家国天下、百姓苍生而舍生取义的精神时至如今仍旧值得继承发扬。在新时代,我们应当客观看待和科学评价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和思想升华,将家国天下的朴素情怀升华为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自觉追求,以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结合。
四、道德理想: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
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指向。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剥削和压迫彻底消失,决定道德的经济基础有着巨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因此人和人处于平等、团结、互助、互爱的关系中,每个人都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道德理想。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 422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纸面上的理论,而是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趋势,更是革命实践运动的现实指向。“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 538。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途径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剥削政府,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动人民共同享有的公有制社会,“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3] 297。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必须付诸革命实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1] 435。虽然采用的手段是暴力,但目的却是解放,因此革命实践也就具有了解放所有被压迫者的道德内涵。那个能够实现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就成为了一种基于革命实践的必将实现的道德理想。
传统文化有“亲亲而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的道德情怀,每个人都希望“四海一家”“亲仁善邻”乃至于“协和万邦”,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关大同社会的道德理想。《论语·颜渊》中“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较早的四海一家的说法,表达了理想社会的憧憬。“亲仁善邻”则体现了和睦的人际关系要求。《左传·隐公六年》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记载,如果能实现亲仁善邻,那么国家也就太平了。“协和万邦”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说,如果一直坚持弘扬道德,就能够做到家族和睦、百姓拥护、社会安定、天下万邦和谐相处。这种理想社会的具体表述体现在《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个大同社会中,每个人都摈弃了狭隘利己之心,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德,相互关爱、无私奉献,一切行为都出于仁爱公义,整个社会处于高度和谐之中,这种状态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是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只是传统文化所说的大同社会因历史局限性而显得简单而朴素,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么科学完备。大同社会理想產生于封建社会,揭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对于社会现实尚没有深刻的认识,更多体现为一种没有邪恶、只有美善的完美社会的美好向往。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理想,更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还是一种革命实践的现实指向,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科学而深刻。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的相似性在“五四”前后就已经为人所熟知,如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的书信中就曾说过,孔子“立太平世为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2]。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又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大同思想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因而把社会主义理想理解为“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13]。可见,大同社会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的近代中国传播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需要指导思想的明确,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其次,两者的结合要深度发掘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之所在,譬如在伦理道德领域两者就有诸多共通之处。最后,两者的结合具有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之后,还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和升华。因此,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很多优秀的值得继承的内容,但还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切实助力。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务馆,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0] 列宁.列宁全集:第2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13]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