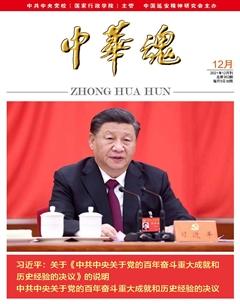华罗庚:一生践行爱党爱国
苏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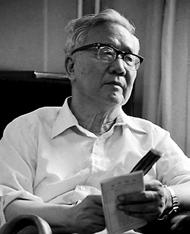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勇攀高峰,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卓越科学家中,享誉国际的数学家华罗庚,开创了中国现代数学学派,培养出陈景润、王元、陆启铿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并深入厂矿农村大力推广“优选法”、“统筹法”,用一生书写了爱党爱国的光辉篇章,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华罗庚的爱国之心不是偶然的,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他,从小耳闻目睹列强的欺凌、国家的孱弱,激发了他为中华之崛起而奋发图强的决心。家贫辍学、在杂货铺打杂的他自学完成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后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赏识。1930年,熊庆来打破常规,让20岁的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工作学习,华罗庚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
1936年,华罗庚被派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租住在一间简陋便宜的房屋。有一天,房东夫妇刚从伦敦看完一场国际田径比赛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华罗庚谈起比赛的盛况。房东不经意问道:“华先生,怎么没看见贵国代表队呢?”这个问题深深刺痛了华罗庚的心。华罗庚心想:“我不能在体育场上为祖国争光,为什么不能在数学赛场上夺取荣誉呢?”于是,他更加忘我学习、刻苦钻研,向科学高峰发起猛烈进攻,用智慧和汗水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数学制高点,在剑桥大学的两年间,他完成了十几篇高水平论文,开始在国际数学界赢得声誉。
回国后,正值全面抗战时期,华罗庚在西南联大任教。当时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他住在昆明郊区一个牛棚上面的阁楼里。每当牛在下面柱子上擦痒痒时,阁楼就开始摇晃摆动。晚上没有电灯,他就往一个小碟子里盛一点桐油,放两根棉线做灯芯。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的环境里,从1939年到1941年,在微弱的桐油灯光之下,华罗庚写出了数学经典著作《堆垒素数论》,在数学界引起轰动,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以华罗庚为首的中国数学学派已举世公认,实现了他在数学赛场上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决心和愿望。
华罗庚不仅自己奋发治学,还思考中国科学发展的前途。他认为,抗战期间应先打好纯粹科学这个基础,这是治本所在,将有利于20年后纯粹科学与应有科学兼顾的科技发展思路。这一真知灼见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科学发展路线可以说是遥相呼應。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切实的爱国行动,为此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调。
1946年9月,在数学界声名鹊起的华罗庚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后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为正教授。此时的华罗庚,虽然身在美国,心却始终牵挂着祖国,思考着中国数学与科学发展的大问题。他对美国朋友说: “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我想我们能够赶上去。”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引起强烈反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高教部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1950年2月,华罗庚舍弃美国的汽车、别墅和丰厚薪水,带着妻儿踏上了归途。他和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在香港逗留期间,他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于3月10日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写道:“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才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最后发出号召:“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公开信中,华罗庚引用“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他发出的号召“我们应当回去”,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国,引发了留美学生的归国热潮,成为华罗庚人生中的一大壮举。
1979年,华罗庚赴英国讲学,回国后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朋友悄悄问我: 你从美国回中国是不是后悔呀! 因为他觉得去美安家落户当教授的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他现在所求的却正是我当年所弃的。论生活差距,中美比英美更大,所以他不能理解 1950年初我的行动。但当我说出为人民服务是第一位的,个人生活享受是第二位的时候,他不禁脱口而出: ‘这真伟大! ’”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道路,往往都从朴素的爱国情感出发,上下求索、诸路皆走不通之后,最终都会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作为一名富有爱国精神的科学家,华罗庚走的也是这条道路。
早在中学时期,华罗庚就与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王时风和钱闻关系亲近,三人亦师亦友,友谊保持了终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25岁的华罗庚已是清华大学教师,尽管小时候因为伤寒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导致左腿残疾,他仍然拄着拐杖,拖着一条残腿,走在队伍前列。国民党后来大搜捕,华罗庚还在自己家中掩护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躲过当局搜查。
抗战期间,华罗庚一直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1940年前后,他还曾想去延安。1946年春,华罗庚访问苏联三个月,很受触动,回国后他积极在《新华日报》和一些公开场合介绍苏联先进兴旺的科学、教育、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1947年《时与文》杂志连续刊登他长达3万字的《访苏三月记》,其中写道:“参观莫斯科大学,当我一进巍峨的大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座列宁像,他手里捧着的却是一本书! 先到图书馆参观,四壁挂的是相片”,“走近一看,原来都是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科学家有苏联大数学家维诺格拉朵夫和卡皮察等苏联的大物理学家……文学家托尔斯泰等。”
1950年3月,从美国归来的华罗庚回到北京,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2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首任所长,9月加入民盟。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夏,华罗庚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这年,华罗庚调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并走上了为生产实践服务的应用数学道路。他创造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即“双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在管理运用和科学实验上,大大优化了各方面建设事业,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广泛提高了国人的科学素养。为此,他与毛泽东还曾书信往来,毛泽东两次亲笔写信给他,予以支持和鼓励。1964年3月,华罗庚收到毛泽东亲笔回信:“华罗庚先生: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第二次是1965年7月,“华罗庚同志: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这封信上,毛泽东把对华罗庚的称呼从“先生”改为了“同志”。
1979年3月,华罗庚应邀赴欧洲讲学前,再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写道:“虽然现在蒲柳先衰,心颤、眼花、手抖、头发白,但决心下定,活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活一小时就为党工作一小时。”6月13日,在英国讲学的华罗庚收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知。这位69岁的“新党员”兴奋得一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到英、荷、法、德四国讲学,尽管关节经常疼痛,但一想起这是为党争光,就讲得起劲多了。”
1980年元旦,邓颖超见到华罗庚,祝贺他实现入党夙愿,夸他是“老同志,新党员”。华罗庚很感动,对周围的人讲:“这六个字是对我一生最好的总结。”并写下“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的诗以奉答邓颖超,还写道:“实干、苦干、拼命干,党员本色;空话、大话、奉迎话,科学罪人。”
1959 年,华罗庚开始转到研究应用数学和推广应用。他一直就倡导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兼顾的科学发展理念,他明白应用数学的巨大价值,并别具慧眼地提出数学工程、数学技术等重要观点,认为“应用数学是一种技术,现在人们没有认识到,将来会认识到的,等将来国际上一旦有人提出数学技术的观点时,你就说我华某人早就看到了”。1958年后,全国兴起到工农中去、到生产实践中去的社会运动,华罗庚也想为此作出贡献。他在访问一些工厂和农村后,发现这些地方管理工作极其落后,决定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把“双法”作为应用数学的突破点。
他曾对工作人员说:“在回国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和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科学工作者一样,仍习惯于灌注式的教学和经院式的科研,在课堂上讲的是‘厚本本’、‘大套套’,在书斋里钻研的是别人越不懂越玄妙越好,这种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的道路,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度越来越不相适应。”這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科学要为生产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他也是这样做的。
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罗庚选择优选法、统筹法作为运筹学的推广应用重点,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进行生产工艺上搞优选、生产管理上搞统筹的普及活动,他下农村、去厂矿,不辞劳苦、不遗余力,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一次次病倒又一次次爬起来,人们劝他注意休息,他却回答:“生产若能长一寸,何惜老病对黄昏!”
1975年,65岁的华罗庚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积劳成疾,第一次发作心肌梗塞,昏迷了6个星期,一度病危。出院后,他仍然坚持工作,仅在1976年到1977年初就两次到山西。每次出门,必备氧气袋,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华罗庚仍坚持奔波在各地推广应用数学,他透支着自己的生命,燃烧着自己的才华与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华罗庚在不同场合数次提到,选择科学方法进行普及推广要注意四点:要适应我国经济和工业的实际情况;应该尽量采用现代方法;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
关于采用现代方法,华罗庚可谓富有远见。1969年,他出版的《优选学》提出,将人类生产、设计、制造等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当时正值第三次科技革命刚刚兴起计算机电子技术,华罗庚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尖端科技的前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计算机电子技术在国外已经开始微型化,华罗庚意识到这是应用数学新的发展契机,积极推动成立应用数学研究所,支持组建中国运筹学会、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这些前瞻性重大决策为我国应用数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华罗庚不仅是一位蜚声国际、为国争光的数学大师,还在人才培养、数学科普等方面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潜心研究、推广应用,他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可以说是科学报国的典型代表,是科学家精神的突出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把原有数学研究方面的物资都搬去了台湾,再加上帝国主义封锁,研究工作面临困难。在异常艰苦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下,肩负着新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重任的华罗庚发挥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数学所上下团结一心、艰苦创业,不到五年就初具规模,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科研成果与专业人才。
华罗庚对培养人才很有一套,最突出有效的便是组织讨论班,这源于总结自身学习经历和国内外教学经验。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就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在其中受到教益成为著名数学家的有段学复、闵嗣鹤、樊畿、徐贤修等人。20世纪50年代初,他又在新建的中科院数学所组织了两个数论讨论班,一个是基础性的,由他每周讲一次,讲义交给学生分别负责,反复讨论后再定稿;另一个是哥德巴赫问题讨论班,由学生轮流报告,凡有疑难之处,他都要当场追问清楚,激发学生不断思考和解决问题。节假日,他还常到宿舍找学生谈数学问题,常常用“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的话鼓舞大家。受他直接领导成长起来的学生有越民义、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王元、许孔时、陈景润、吴方、魏道政、严士健与潘承洞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院士或教授,有些是国际著名数学家,受过他影响的数学家更是不计其数。
华罗庚不仅培养数学专业人才,还特别重视推广数学竞赛活动、出版通俗读物,激发广大青少年对数学的热情。1956年,在华罗庚倡导下,我国首次开展数学竞赛,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四大城市举办了高中数学竞赛。50年代北京的历次数学竞赛活动,华罗庚都热心参与组织,曾亲自担任北京市竞赛委员会主席,从出试题,到监考、改试卷都亲自参加,还多次到外地去推动这一工作。比赛前后,他都亲自给中学生作报告进行动员,当时称为“数学通俗讲演会”。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华罗庚出版了一批通俗读物,如《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等,不仅普及数学知识,更富有启发性,也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这些书一版再版,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并影响至今,成为他们最喜欢的课外读物之一。
华罗庚一生拼搏不断奋进,曾以“老骥耻伏枥”自勉。197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他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即使卧病在床,仍然坚持工作,“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工作尽量多做”,“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0年春,华罗庚开始酝酿遗嘱稿。主要内容有:死后丧事从简,骨灰撒到家乡金坛县的洮湖中;我国底子薄、基础差,要提倡多干实事、有益的事,少说空话大话;发展数学,花钱不多,收益很大,应该多加扶持;死后,所收藏的图书及期刊赠送给数学所图书馆。
这一时期,华罗庚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不仅继续到各地推广应用数学,更是发挥自身影响力,活跃在国际数学界,带领中青年骨干到国外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为中国科学界走出国门追赶世界贡献力量。1983年在美访问期间,有人建议他利用这次出国机会治疗心脏病,他则认为,“先把工作搞好”,“为党为国为人民更努力,献出仅有的余力”。1984年8月,华罗庚在病榻上写下《述怀》:“即使能活一百年,36524日而已。而今已过四分之三,怎能胡乱轻抛?……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
1985年6月12日,75岁的华罗庚在东京大学向日本数学界作题为《理论数学及其应用》的演讲,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于当晚与世长辞,一颗数学巨星就此隕落。毕生驰骋在“数学王国”的华罗庚,是在数学讲坛上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践行了他生前的志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华罗庚的一生,矢志践行爱党爱国。人生的序幕、开篇是个人的数学理论水平达到世界高峰,而发展、高潮却无一不与国家命运、应用数学、社会价值息息相关,在人生结尾处,又以“理论数学与应用”落下帷幕,这也正是“老同志,新党员”、“人民科学家”华罗庚75年光辉人生的最恰当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