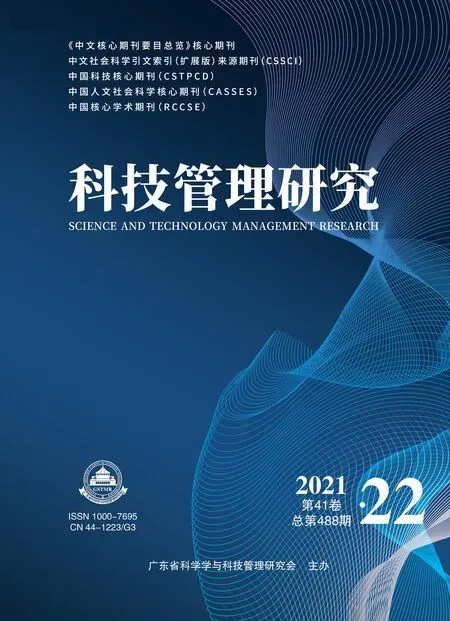环境知识与农户亲环境行为
——基于环境能力中介作用与社会规范调节效应的分析
薛彩霞,李 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1 研究背景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绿色农业是多种亲环境技术的集成。目前我国的亲环境技术已经比较先进[1],但农户难以突破传统种植方式的习惯,实施亲环境行为的程度依然不高[2];尽管政府通过激励政策或管制政策在短期内促使农户实施了亲环境行为,但效果缺乏可持续性[3]。因此,建立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长效机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有文献关于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主要从政策支持、土地特征和农户效益认知等方面分析其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促进了农户对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用[3],经营规模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有促进作用[4],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5]。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如研究发现了解过量施肥对环境危害的农户更倾向于施用有机肥[6],过量施肥危害认知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有促进作用[7],对生物农药防虫原理的了解有助于农户施用生物农药[8];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不显著,如有研究发现农户对氮磷钾不同配方的了解对其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影响不显著[9],农户关于农药对环境影响的认知对其采纳IPM 技术影响不显著[10],农业污染知识对农户环境友好技术的采用影响不显著等[11]。农户无法实现知行合一,往往是受到了环境能力的制约,即缺乏相应的环境能力[12]。
已有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需完善之处:第一,关于环境知识的测度较为单一,而环境知识具有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知识在引导农户亲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同[13]。第二,没有将环境能力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进行研究,忽视了环境能力在农户亲环境行为中的作用。第三,没有将社会规范纳入到环境知识与环境能力的分析框架中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路径,而社会规范作为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重要情景因素,与环境知识、环境能力共同对农户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秦巴山区茶农的调研数据,在将环境知识分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的基础上,探讨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环境知识通过改变环境能力对亲环境行为的间接影响,并对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环境能力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以期为提高秦巴山区茶农的亲环境行为及政策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2.1 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
环境知识具有多样性。Frick 等[13]把环境知识分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3 类。其中,系统知识是指生态系统如何运行或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知识,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行动知识是指导个体实施具体行动或行为选择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效用知识是与行为结果相关的知识,是关于“哪种方法更有效”的知识。首先,系统知识丰富的农户往往持生态价值观,更能意识到环境污染行为的不利后果,且能将不利后果的避免归因到亲环境行为上,而对不利后果的认知和归因会激活个人规范,促使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14]。其次,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通过提高农户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降低了农户对亲环境行为的接受度。通常来说,农户亲环境行为主要体现在对亲环境技术的采用上,农户是否采用亲环境技术,是由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决定的。农户对亲环境技术感知易用性的判断依赖于其掌握的行动知识,行动知识越丰富的农户,其自我效能感越强,越能感知到技术的易用性。农户对技术感知有用性的判断主要依靠效用知识,根据保护动机理论,效用知识多的农户,其应对评估中的反应效能更高,采取亲环境的可能性更高[1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1:环境知识直接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
2.2 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与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社会规范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有的行为准则[16],属于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外部情景因素。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规范通过以下3 种途径影响环境知识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联结关系:第一,信息流动机制。社会网络为农户采用农业技术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当农户将要采用亲环境型技术时,通常会与其所处社会网络中的亲朋好友交流该技术的优缺点,当农户所处的社会网络中已形成亲环境的社会规范时,不仅可以缩短农户获取环境知识的搜寻过程,而且可以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有利于其实施亲环境行为。第二,参照点作用。与群体保持一致是中国人特有的社会规范之一,农户决策时会将所属群体的规范视为参照点[17],当农户所在村庄的其他大部分农户都实施了亲环境行为时,其也倾向于实施亲环境行为,因为参考大多数人都遵循的行为规范行动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更为安全合理;当农户感到参照群体未实施亲环境行为时,即使农户所掌握的环境知识告诉他应该实施亲环境行为,但为了避免与他人行为不一致而受到“惩罚”,就可能发生知识与行为的背离。第三,互动学习机制。亲环境技术的学习具有长期性和过程性特征,且效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在亲环境氛围下,农户间的技术交流不仅有助于农户在技术采用过程中获得及时、有效的指导,还有助于积累相应的环境知识,因此社会成员间的互动学习可以促进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18]。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2: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与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2.3 环境知识通过环境能力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环境知识在直接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同时,还通过改变农户提高环境能力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行动力间接影响其亲环境行为。首先,系统知识丰富的农户更能意识到传统种植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安全所带来的危害,使其产生“想做好”的动机,激发其提高环境能力的积极性,效用知识则可以为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提供动力,引发其提高环境能力的主动性。其次,行动知识可以帮助农户获取精准的技术采用信息、风险应对信息和资源利用信息,切实增强农户提高环境能力的行动力,从而使其具备“能做好”的能力。
个人能力作为一种内源性特质,对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有直接影响[19]。技术不会用和收益不确定是制约农户采用亲环境的关键因素,环境能力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后顾之忧,促使其实施亲环境行为。首先,高环境能力有助于降低农户的技术运用不当风险。环境能力强的农户,对亲环境技术的操作规程更为规范,并能及时处理技术采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且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和借鉴成功的经验,从而降低了技术运用不当的风险。其次,高环境能力有助于降低农户的收益不确定风险。环境能力强的农户,不仅能获得更多的产品价格信息[20],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品价格的信息不对称性,使采用亲环境技术所生产的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而且在遇到自然灾害时会尽可能采取多样化措施以减少作物产量损失[21],从而降低收益不确定的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3:环境知识通过改变农户环境能力,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
2.4 社会规范在环境能力与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根据动机-机会-能力模型,个体行为的发生是动机、机会和能力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能力是行为所必须的技能,机会是外部情景因素[22]。当情景因素极为不利或有利时,可能会阻碍或者促进行为的发生,能力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几乎为零;当情景因素为中性时,能力与行为的关系最强。这说明,能力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情景因素的调节。社会规范作为无需法律的社会秩序[23],对某一行为越支持,个体感到自己可以掌握的资源越多,预期的阻碍越少,行为能力越强,执行某一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方面,观察学习是农户最主要的社会学习方式[24],亲环境的社会规范可以为欲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农户提供观察学习的机会,帮助其积累实践经验和替代性经验;另一方面,社会规范水平高的区域易形成亲环境物质投入品供给的规模效应和亲环境技术的溢出效应,这有助于降低农户的行为成本和技术障碍,增强自我效能感。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4:社会规范在环境能力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实施过程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环境知识、环境能力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理论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3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笔者所在课题组成员于2018 年7 月至8 月在秦巴山区对茶叶种植户一对一入户调查所得。秦巴山区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上游的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地跨甘肃、四川、陕西、重庆、河南、湖北6 省市,主体位于陕西省,承担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生态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三峡库区生态建设等重大任务,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秦巴山区曾是我国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茶叶因是“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而成为秦巴山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截止到2018 年年末,秦巴山区的76 个县(区)中超过65%的县(区)种植茶叶,茶园面积已达45.02 万hm2,占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15.36%[25]。
样本农户的选取采用四阶段抽样方法。首先在秦巴山区抽取种植茶叶较为有名的紫阳县、西乡县、南郑县、万源市和青川县5 个县(市);其次在所抽取的每个县(市)中选取茶叶种植面积较大的3个镇;再次,在所抽取的每个镇中选取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的2 个村庄;最后,在每个村庄中随机抽取了15~18 户农户进行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498 份,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户茶叶种植的亲环境行为、环境知识、环境能力、户主特征及影响农户茶叶种植的外部环境等。
3.2 变量选择
3.2.1 因变量
亲环境行为是指为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采用的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尽量降低的行为或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26],因此,亲环境行为应该包括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两个维度。根据我国标准GB/Z 26576—2011《茶叶生产技术规范》和NY/T 5018—2015《茶叶生产技术规程》中对茶叶种植日常管理的要求以及调研区域的实际情况,农户在茶叶种植过程中的亲环境行为包括地表覆盖、施用有机肥、间种绿肥的土壤管理措施,测土平衡施肥、化肥与有机肥配合使用的施肥措施,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技术、施用无公害农药、物理除草的病虫草害防治措施,修剪枝叶还田、农药包装物回收的废弃物处理措施。采用李克特五点法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测度,即从不=1,偶尔=2,半数=3,多数=4,总是=5。表1给出了样本农户亲环境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样本农户亲环境行为描述性统计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亲环境行为进行分类。运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选取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特征根大于1 的两个公因子。公因子1 的方差贡献率为37.498%,包含物理除草、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无公害农药、IPM 技术、农药包装物回收,这5 种行为都会导致农药化肥污染的减少或减轻,属于减少污染行为。公因子2 的方差贡献率为25.509%,包含地表覆盖、种植绿肥、修剪枝叶还田和施用有机肥,这4 种行为通过蓄水保墒、防治水土流失、培肥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来改善茶叶生长的生态环境,属于改善环境行为。
3.2.2 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是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系统知识的测量题项来自于洪大用等[27]的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中与生态系统较为密切的题项;行动知识的测量题项是依据GB/Z 26576—2011《茶叶生产技术规范》和NY/T 5018—2015《茶叶生产技术规程》的要求设置;效用知识的测量题项是根据茶园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效用设置。每个问题均设置3 个选项:a.正确;b.错误;c.不确定/不知道。若农户回答正确,则赋值为1;若农户回答错误或选择“不确定/不知道”,则赋值为0。样本农户环境知识的具体测度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 所示。

表2 样本农户环境知识描述性统计
3.2.3 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
中介变量为环境能力。环境能力是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所体现出来的素质,属于主观条件,从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应对风险能力、资金投资能力和劳动投入能力6 个方面对农户的环境能力进行度量。具体测量题项如下:(1)“我很容易就能获得亲环境型茶叶种植的信息和技术”;(2)“我具有辨别农资和技术是否亲环境的能力”;(3)“我很容易就学会一种新型的茶叶种植技术”;(4)“我具有解决采用亲环境技术种植茶叶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能力”;(5)“我有采用亲环境方式种植茶叶的资金保障”;(6)“我有采用亲环境方式种植茶叶的时间保障”。以上各问题,均采用李克特五点法进行测度,即完全不同意=1,有点不同意=2,不确定/一般=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调节变量是社会规范。通过咨询农户“您感觉您所在村中茶叶种植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情况如何?”这一问题来测度,选项为:a.几乎没有;b.较少;c.一般;d.较多;e.很多。
3.2.4 其他控制变量
选取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种植年限、政府补贴、市场收益和地理区位作为控制变量。
表3 给出了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3 研究方法
3.3.1 环境知识的测度方法
环境知识包含多个测量题项,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农户的环境知识进行综合测度。首先,进行因子分析法适用性检验。结果显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的KMO 值分别为0.758、0.742和0.728,Bartlett 球形检验卡方值分别为417.154(sig.=0.000)、1047.036(sig.=0.000)和1048.549(sig.=0.000),表明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皆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选取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子。结果显示,系统知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6.567%,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子为1 个。行动知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213%,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子为2 个,其中公因子1 的方差贡献为率41.219 %,包含K21、K22、K26和K27的4 个测量题项,因该类测量题项与农户减量施肥施药有关,故将其命名为“减量施肥施药知识”;公因子2 的方差贡献率为22.994%,包含K23、K24和K25的3 个测量题项,该类测量题项与土地资源利用、废弃物回收利用与有关,故将其命名为“资源利用与回收知识”。效用知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986 %,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子有2 个,其中,公因子1 的方差贡献率为41.328%,包含K31和K32两个测量题项,这两个测量题项与提高茶园的经济效益有关,故将其命名为“经济效用知识”;公因子2 的方差贡献率为22.658%,包含K33、K34、K35、K36和K37的5 个测量题项,该类测量题项与减少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有关,故将其命名为“生态效用知识”。
最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农户的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得分。具体公式如下:

3.3.2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
检验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的方法主要有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 法两种。与逐步回归法相比,Bootstrap 法具有以下两点优势:一是在同一个模型分析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下的中介作用,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数据遗漏;二是通过直接检验中介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来检验中介效应,而不以自变量对因变量直接影响是否显著作为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可以有效避免“遮蔽效应”对检验结果的影响[28]。因此采用Bootstrap 法对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过程中环境能力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规范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具体的概念模型如下:

式(4)~(6)式中:X为农户的环境知识,包括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Y为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包括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M为农户的环境能力;V为社会规范;a、b、c为待估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 。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检验
采用Preacher 等[28]提出的基于Bootstrap 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对图1 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对检验结果是根据95%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置信区间共有3 种情况:一是置信区间下限取值为负、上限取值为正,影响不显著;二是置信区间下限和上限取值均为正,影响显著且为正向;三是置信区间下限和上限取值均为负,影响显著且为负向。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也就是说,不论是系统知识还是行动知识与效用知识,农户的环境知识越丰富,农户实施减少污染环境行为的程度越高。因此,H1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上得到证实。其中,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系统知识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农户意识到了过量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板结,知道应该采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但不清楚间种绿肥和地表覆盖对于改良土壤的作用。因此,H2在农户改善环境行为上得到部分证实。

表4 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直接作用检验
4.2 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提供调节效应直接检验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调节变量按照(均值+标准差)、均值和(均值+标准差)分为低、中和高3 组,提供不同组别下核心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如表5 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表5 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5 (续)
(1)社会规范在系统知识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也就是说,在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系统知识丰富的农,实施减少污染行为的程度较高。减少污染行为具有利他主义特点,农户直接从这一行为中获利较少,但农业污染引起的生态环境改善需要农户集体行动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在行为存在成本压力时,农户只有在相信其他人已经做了各自应当公平分摊的那一份时,自己才会行动[29],因此在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农户接收到了其他人行动的信号,责任感会促使其也采取相应的行动。系统知识对农户环境改善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故不需要检验调节效应。
(2)社会规范在行动知识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行动知识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都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行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都较高。原因是,农户普遍具有按照大多数人行为行事的从众心”,环境友好的社会规范为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奠定了心理基础;另外,农户处于社会规范水平较高的环境时,社会规范的信息流行机制和互助学习机制使得农户的行动知识水平得以提升,自动清除了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技术障碍。
(3)社会规范在效用知识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效用知识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调节效应均不显著。也就是说,不管农户周围其他村民实施环境友好水平的高与低,效用知识都会有助于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原因是,效用知识包括经济效用知识和生态效用知识,经济效用知识对农户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比较直接,生态效用知识是帮助农户改善茶叶的生长环境来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经济效益的显现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最终也会提高经济效益,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因而效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程度越高。
综上所述,H2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上都得到部分验证。
4.3 环境能力在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
由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见表6)可知,在系统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环境改善行为的过程中,环境能力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系统知识过于笼统,无法有效指导农户去提高哪一方面的环境能力。

表6 中介作用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表6 (续)
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行动知识水平会促使农户提高实施行为须具备的环境能力,伴随着环境能力的提高,行为实施的障碍随之减小,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环境改善行为得以实施;反之,农户行动知识缺乏,环境能力差,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均无法实施。结果表明,“如何做”的知识会驱动农户提高“能做成”的能力,进而使其预期目标得以实现。
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过程中,环境能力的中介作用因农户所处的社会规范的环境而有所差异。环境能力的中介作用在社会规范水平低值组显著,而在中值组和高值组不显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环境能力有助于农户实现茶叶的优质优价,在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物以稀为贵”,环境能力的优质结果在产品优价上能到回馈;相反,在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环境能力的优势可能无法在价格上得到回馈。
环境能力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过程中介作用不显著。原因是,农户具有兼业性,兼业程度低的农户在经济上对茶叶种植的依赖度高,兼业程度高的农户对茶叶种植期望收益低,而环境改善行为属于生态性投入行为,具有劳动投入多、风险低、见效慢的特征[30],兼业程度高的农户即使效用知识水平高,出于务工经济利益的比较优势也不愿意投入精力实施环境改善行为,因此,农户的分化特征导致环境能力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综上所述,H3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上都得到部分验证。
4.4 社会规范在环境能力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中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6 可知,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的中介系数随着社会规范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加,且系数差异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规范对农户的环境能力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当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农户对减少污染的相关技术和物质需求(比如无公害农药、测土配方施肥、物理防治病虫害的物质)已形成规模效应,供给主体提供的服务更加专业化,这不仅降低了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技术障碍、资金成本和搜寻成本,而且增加了行为的便利性,农户的环境能力得以提升,亲环境行为得以实施。
环境能力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社会规范的低值组显著,在中值组和高值组不显著,说明社会规范对环境能力的调节效应显著。在调研中发现,农户所处村庄的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往往是当地政府致力于打造当地茶叶的绿色品质,不仅采取多种方式向农户宣传效用知识,促使农户从主观上产生想要提高环境能力的动机,而且客观上从补贴政策、信息支持等帮助农户提高环境能力,使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农户不仅无法获得替代性经验,行为心理障碍较高,而且由于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导致亲环境型的物质投入成本较高,较低的社会规范提高了农户环境能力的门槛,制约其无法实施减少污染行为。
随着社会规范水平的提高,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环境改善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断增加,且系数差异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规范对农户环境能力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在调研中发现,农户种植的茶叶主要是卖给当地的茶厂,辐射范围较大的茶厂通常与农户提前签订销售合同,合同中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茶叶收购标准和时间,为履行合同,农户需采用可以促使茶树新梢生长高峰提前的地表覆盖技术和施用有机肥,甚至有茶厂以优惠价格向签订合同农户提供已修剪的大枝条粉碎服务,以有利于农户进行枝叶还田。茶厂的行为带动了社会规范水平的提高,农户即使没有与收购商签订销售合同,身处社会规范水平高的氛围里耳濡目染,环境能力也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改善环境行为得以实施。
环境能力在系统知识与减少污染行为、系统知识与环境改善行为、效用知识与环境改善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故不需要检验社会规范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H4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上都得到部分验证。
4.5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7)可知,种植年限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种植茶叶年限越长的农户,其实施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更高。种植规模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茶叶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采取减少污染行为的措施更多。政府补贴和市场收益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补贴政策和市场激励都是促使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重要推动力。

表7 控制变量回归系数

表7 (续)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秦巴山区茶农的调查数据,利用Bootstrap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在考虑环境能力中介作用和社会规范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对异质性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路径进行了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行动知识、效用知识正向直接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而系统知识仅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
第二,社会规范在系统知识直接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在行动知识直接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都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在效用知识直接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环境改善行为过程中调节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在环境友好水平较高的社会规范氛围下,不论是系统知识丰富的农户还是行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的程度都较高,但只有行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较高;无论社会规范的环境友好水平的高与低,效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均较高。
第三,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过程中仅在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中介作用显著。即行动知识会驱动农户提高环境能力来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而效用知识仅在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驱动农户提高环境能力以实施污染减少行为。
第四,社会规范在行动知识通过环境能力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正,但在效用知识通过环境能力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负。即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行动知识丰富的农户通常环境能力较高,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较高;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效用知识丰富的农户更有动力提高自己的环境能力以实施污染减少行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要促使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系统提高农户的环境知识水平。在对农户进行环境教育时,不仅需要告诉农户传统种植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系统知识,更需要告诉农户怎么做的行动知识和哪种方式更有效的效用知识。二是全面提高农户的环境能力。不仅要搭建一个茶叶种植专家与农户的信息交流平台,为农户提供精准的环境友好种植技术,而且需要建立一个随时为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排忧解难的组织,以确保农户在技术采用过程中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另外,还需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物质给予补贴,以降低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资金成本。三是努力塑造亲环境的社会规范。通过对茶叶种植示范户进行适当的奖励和表彰,树立起亲环境的方向标,同时可以组建若干茶叶种植技术学习小组,让示范户担任小组领导,推动小组内与小组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与竞争,逐步塑造绿色生产、生态文明的亲环境型社会规范。